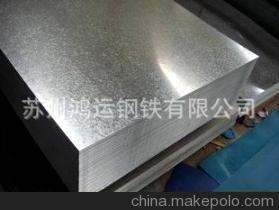东方和西方:薛西斯与塞万提斯的海洋
刘仲敬
东方和西方对抗的主题首先在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伟大戏剧中出现。谁能忘记温泉关的舞台呢?斯巴达的三百勇士面对薛西斯的百万大军,向世界展示自由人如何遵守自己的律法。萨拉米斯的希腊联合舰队勾心斗角,猜忌邻邦多于猜忌敌人。波斯的附庸海军更关心万王之王的喜怒,不太关心战争本身的得失。亚细亚依靠廉价的生命和诡诈的权术。欧罗巴依靠自由民的勇敢和优越的技术。西方本来能够以少胜多,但内部的分裂和技术的流失破坏了他们的优势。东方本来能够以多胜少,但宫廷的混乱和将领的奴性虚掷了人力物力的巨大牺牲。这种戏剧结构似乎非常切合人类共有的思维模式,从“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开始,一次又一次重复。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历史和戏剧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九缪斯团队的成员。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历史的地位变得暧昧而复杂,在文学和科学之间摇摆不定。十九世纪末叶,兰克的某些追随者开创了自命科学的史学传统。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完全兑现自己的承诺,仍然在二十世纪以降的史学传统中稳居一席之地。与此同时,怀疑“社会科学”概念本身的史学传统继续走自己的路。罗杰·克劳利的《地中海三部曲》属于后者,堪称《波斯人》和《统治者》的继承者。他的特长不在思想的敏锐,而在布局的戏剧性。他的目标不是让读者思考,而是让读者感动。
流水的演员,铁打的主角。十字架与新月旗取代了希腊人和波斯人,但剧本的结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第一幕:拜占庭的黄昏。罗马的荣耀在君士坦丁堡的没落帝国手中黯淡下来,但帝国的断壁残垣仍然保护了欧洲的摇篮。阿拉伯人如火如荼的弯刀在金角湾的铁索前折断,将舞台让给了迟缓而坚韧的土耳其人。拜占庭的柔道能够消解哈里发的轻锐之师,却在苏丹的耐性消耗战中败北。
第二幕:土耳其继承了哈里发和凯撒的双重遗产,君临四分五裂的欧洲。西班牙人和法兰西人勾心斗角,尤甚于当年的雅典和斯巴达。苏丹的大军似乎所向披靡,却在勒班多重演了萨拉米斯的败绩。地中海保护了大西洋,正如当年拜占庭保护了欧洲。杰尔巴的金鼓烟消云散,因为历史的中心已经随着无敌舰队一起西移。
第一幕从君士坦丁堡的营造开始,仿佛出自某一位天真的马可·波罗之手。露台。柱廊。花园。凯旋门。赛马场。宏伟宽阔的大路。无数精美的雕塑。教堂“比一年的日子还要多”。见著知微不是作者的特长或目标,《地中海》更不是《罗马盛衰原因论》的姊妹篇。他没有从帝都的掠夺性建设看出罗马宪制的衰败。虽然故事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但他对晚期罗马军队的描述仅限于技术层面。我们愉快地浏览“希腊火”的秘密、杰出工程师和技术员的生平、舰队的指挥,却不知道军费如何筹集、兵员和各省的关系。他只关心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却不大关心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阿拉伯舰队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支大军的存在仿佛像达达尼尔海峡一样理所当然。作者一直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就足以解释整个战争了。问题在于,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宫廷处境不同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元老,自身的党派性质非常明显。他们派出了包含大批基督徒的叙利亚军队,讨伐阿拉伯半岛的敌人。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麦加的天房付之一炬。大马士革宫廷与其主要根据地的关系极其微妙,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战争依靠水师。不久之前,麦加的元老甚至不允许他们出兵塞浦路斯。这些隐秘和复杂的关系其实比战场上的英勇和失误重要得多,在书中基本没有体现。
第一幕的时间跨度比第二幕长得多,但历史线索的连贯性不强。希拉克略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帝国除了名字以外,相同之处不多。大马士革哈里发政权、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和亚德里亚堡苏丹政权的跨度更大,脉络更难厘清。作者完全放弃了这方面的任务,将所有序幕当做舞台布景一类的道具,跟后来登场的演员缺乏有机联系,以跳跃的方式直扑1453年的大决战。尽管尼西亚陷落以后,故事的悬念已经不大,但杰出的文学家娴于雄词丽句,仍然可以演得有声有色。
“奥斯曼帝国军事行动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们动员人力和资源的规模远远超过敌人的计算能力。”土耳其人是东方主义刻板印象的最佳体现者:庞大、专制、重量不重质,关键的技术部门依靠西方的客卿或叛教徒。帝国为他们提供的优厚待遇和荣升机会,是他们的母国望尘莫及的。相反,西方在这次战役中充分暴露了涣散和分裂的本性。君士坦丁堡在其最后的人口统计中,发现“真正的罗马人”只剩下几千。帝国的精英丧失结婚和生育的习惯,为时已久。他们更擅长在修道院里著书立说,驳斥节节胜利的穆斯林。皇帝依靠突厥雇佣兵打击竞争对手,依靠西方干涉的威胁恐吓苏丹,勉强拖延苟且偷生的岁月。这样的国家和民族似乎不可能产生英雄人物,但英雄人物居然出现了。君士坦丁十一世搭乘的快船离开暂时可保无虞的爱琴海隅,偷渡不再属于帝国的色雷斯海岸,越过金角湾的横海铁索,迎接不再属于自己的命运。
即使如此,帝都的主要卫士仍然是热那亚人和西方雇佣兵。这些人组成数十人、至多数百人的小分队,彼此没有合作的习惯。他们参加远方的战争,主要是出于冒险的癖好和丰厚的酬金。真正的罗马人和正教徒直到最后关头,仍然将罗马教皇视为最大的敌人,多次扬言宁愿要土耳其人,现在土耳其人果然来了。他们依照惯例,带来了二十倍于守方的部队。匈牙利人为他们造炮,意大利人为他们造船。巴尔干基督教家庭为他们提供了近卫军的兵员,真正的穆斯林反而无望高升。然而,苏丹的宠臣永远不能跟欧洲贵族相比。他们都是苏丹的奴隶,随时可以刑讯或处决。在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战败的将领是没有多少生存机会的。晚期的苏丹开始对臣子心慈手软,军队的战斗力也就每况愈下了。
穆罕默德二世当然不是这种弱者,他的赏赐和惩罚同样慷慨。他精通拉丁文,懂得运用特洛伊战争的典故,却仍然无愧于薛西斯的传人,不介意临阵拷打大将,似乎并不在乎军心士气。苏丹希望部下害怕自己的惩罚,超过害怕敌人的火力。西方骑士那种无法无天的个人英雄主义,对君主的危险性经常大于对敌人,绝不是他愿意鼓励的。土耳其近卫军的美德是集体主义,不以人力物力的不成比例的消耗为耻。欧洲人发明了三角堡和棱堡,使数百人的交叉火力足以长期抵抗数万大军。土耳其人发明了义务劳役制度,让数百万东正教和穆斯林顺民免费修缮道路、运输辎重。君士坦丁堡战役的胜利是由无数民工的滚子和推车造就的。没有这些无名英雄,土耳其人的消耗战就会首先将自己消耗殆尽。
欧洲人鄙视东方顺民,包括自己的东正教表兄弟,为此付出了代价。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都将这些软弱的土著视为纯粹的贸易和财政来源,一面从他们身上赚取巨额利润和酬金,一面将他们排斥在自己的小团体外。骑士团根本不把没有战斗力的东方人放在眼里,更怀疑他们反覆无常的效忠。土耳其人不善于经营货币经济,却更擅长组织古老的劳役制度。在劳动力充足、经济贫困、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东方村社中,看似原始的劳役动员制度往往更有实效。土耳其的专制主义也比欧洲的法团自治政体更开放。帕夏和军官都是苏丹的奴隶,除了才能没有别的门槛。热那亚共和国的公民权或圣约翰骑士团的资格却不是利凡特殖民地臣民有望染指的。
第二幕开始时,西方更换了自己的演员。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证明了东方组织模式的成功,土耳其人的兵锋随即指向罗德岛。“保卫罗得城的守军很可能只有五百名骑兵、一千五百名雇佣兵各当地希腊人。”苏丹苏莱曼的工兵就有六万人,总兵力很可能三倍于此。骑士团进行了短暂而英勇的抵抗,最后还是决定签署和约,把岛屿交给土耳其人,换取少量精锐部队全师而退。苏丹得到小岛的喜悦,还赶不上得到意大利著名军事工程师塔蒂尼的喜悦。英明的苏莱曼非常清楚土耳其的优势和缺陷。这种体制的动员能力比一盘散沙的欧洲大得多,却很难产生为世界提供创造力的关键少数。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帝国像土耳其人一样,文武精英和技术人员主要依靠敌对势力供应,将国家变成了汲取穆斯林和东正教顺民、奉养叛教徒帕夏和士兵的机器。即使以前的阿拉伯帝国也有自己的贵族骑士,只是在专业技术方面依靠犹太人和希腊人。

奥斯曼其实没有自己的海军传统,直到他们招安阿尔及尔的海盗王国。他们用陆战的方式打海战,沿着海岸线步步为营地推进,逐一拔除威尼斯人的港口据点。最后,城邦和帝国的角逐形成了奇特的布局。地中海四分之三的海岸线已经落入苏丹手中,大部分岛屿仍然在基督教欧洲各国掌握之下。由于航海习惯的差异,大多数有经验的水手都是意大利人或其他西欧人。苏丹依靠海盗和叛教徒建立海军,表面上比西班牙人或威尼斯人强大得多,但表象总是欺人的,土耳其舰队只有经费和原材料属于苏丹。航海和贸易不是土耳其人的正常生活方式,像铸炮和棱堡一样依赖高薪引进的客卿。苏丹比国王和大公强大得多,但苏丹的臣民几乎没有在地中海洗脚的自由。如果苏丹不再有钱雇佣西方的叛徒,土耳其就不再是一个海上国家。相反,意大利民间的船队比政府的舰队多得多。英格兰和荷兰更不用说,击败无敌舰队的战役大部分由伦敦市和士绅自己筹款建立的武装民船完成。
东方依靠中央集权的统一规划和动员效率,弥补民间社会缺少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弱点。西方本来处于绝对优势,却因为政治的分裂和混乱,无法发挥应有的优势。威尼斯人其实更关心将敌对的城邦赶出利凡特贸易的禁脔,跟土耳其人友好相处。即使在苏丹一再侵夺他们的殖民地以后,他们仍然擅长利用基督教盟国的胜利,作为跟土耳其单独议和的资本。西班牙国王更关心保存舰队,而非争取胜利。如果他能挪用意大利和德意志各邦筹集的反土耳其经费,讨伐荷兰和英格兰的另类异教徒,他也不会觉得问心有愧。海军司令多利亚不愿让自己出资的几条船冒险,积极执行菲利普国王不得浪战的旨意。只有年轻的堂·胡安急于追求荣誉,才打响了意外的勒班多战役。
战役当天早上,未来的《堂吉诃德》作者正在发烧。但他听到炮声,立刻跳下帆布床,迎接荣誉和牺牲。多年以后,他跟人打笔战时,仍然自豪地宣称:我的手臂是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役中残废的。如果我能重新选择,也一定不会珍惜手臂,错过这次战役。的确,勒班多战役打破了多年的海战常规。失败的土耳其人几乎全军覆没,折兵两万余人。过去几十年来,双方将领忌惮大海的不测风云,很少恋战,更擅长掳掠倒霉的沿海居民。考虑到他们大多数都是意大利同行,只是一部分叛教、另一部分没有叛教而已,这种表现不太令人惊讶。上个世纪的职业雇佣兵轮流为意大利的敌对城邦作战,表现也是这样。堂·胡安这样不按牌理出牌的外行异军突起,才会造成这样出乎意料的大战。
基督教联盟出于一贯的勾心斗角,没能利用勒班多战役的胜利。其他各国参战,原本是为了援助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却抢先议和,使他们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动力。菲利普国王不是苏丹在西方的镜像,只是列强的一员。他在基督教世界有太多的敌人,不能在地中海全力以赴。法兰西为了打击夙敌,很乐意将土伦港借给共同信仰的敌人。北欧各国正在开发新式快船,很快就要将圆胖迟缓的地中海大帆船变成任人宰割的猎物。德雷克舰队一旦驶入大西洋-美洲航线,就会给西班牙造成比土耳其人更大的威胁。无敌舰队出海以后,地中海不再是菲利普二世政府的战略重心。
几乎与此同时,土耳其人放弃了海上霸业。他们公开宣称并不介意勒班多的损失,确实也神速地重建了更大的舰队,“比胡须生长的速度更快”。他们的压力不在战争,而在财政。只要苏丹宫廷的慷慨依然如故,不愁没有技术能手叛教投靠,改名易卜拉欣或阿里,踏上帕夏的荣华或死亡之路。然而,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在帝国事务的优先级顺序中,买来的海军近代化是排不上前几名的。一旦没有海军,阿尔及尔的海盗和开罗的就会恢复桀骜不驯的本性,恣意欺凌可怜的土耳其总督。通货膨胀一旦引起禁卫军的愤怒,苏丹就会自身难保。土耳其帝国沿着这条下降的螺旋线,在两百年内沦为西亚病夫。作者对帝国衰落的分析是非常粗略的,因为他的倾向就是不要用没有人物和情节的内容烦扰读者。《地中海》应该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戏剧,这就足够了。他能给读者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现在的历史著作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