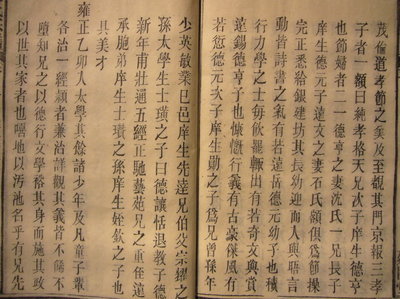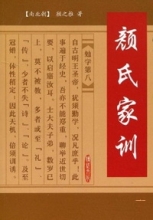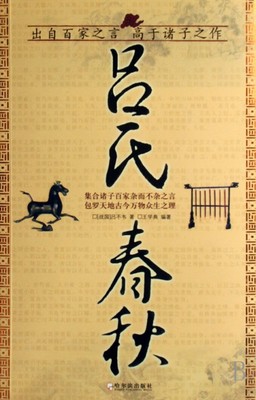包氏父子
一
天气还那么冷。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可是听说那些洋学堂就要开学了。这就是说,包国维在家里年也不过地就得去上学!
公馆里许多人都不相信这回事。可是胡大把油腻腻的菜刀往砧板上一丢,拿围身布揩了揩手——伸个中指,其余四个指头凌空地扒了几扒:
“哄你们的是这个。你们不信问老包:是他告诉我的。他还说恐怕钱不够用,要问我借钱哩。”大家把它当做一回事似地去到老包房里。
“怎么,你们包国维就要上学了么?”
“唔,”老包摸摸下巴上几根两分长的灰白胡子。
“怎么年也不过就去上书房?”
“不作兴过年嘛,这是新派,这是……。”
“洋学堂是不过年的,我晓得。洋学堂里出来就是洋老爷,要做大官哩。”
许多眼睛就盯到了那张方桌子上面:包国维是在这张桌上用功的。一排五颜六色的书。一些洋纸簿子。墨盒。洋笔。一个小瓶:李妈亲眼瞧见包国维蘸着这瓶酒写字过。一张包国维的照片:光亮亮的头发,溜着一双眼——爱笑不笑的。要不告诉你这是老包的儿子,你准得当他是谁家的大少爷哩。
别瞧老包那么个尖下巴,那张皱得打结的脸,他可偏偏有福气——那么个好儿子。
可是老包自己也就比别人强:他在这公馆伺候了三十年,谁都相信他。太太老爷他们一年到头不大在家里,钥匙都交在老包手里。现在公馆里这些做客的姑太太,舅老爷,表少爷,也待老包客气,过年过节什么的——赏就是三块五块。
“老包将来还要做这个哩,”胡大翘起个大拇指。
老包笑了笑。可是马上又拼命忍住肚子里的快活,摇摇脑袋,轻轻地嘘了口气:
“哪里谈得到这个。我只要包国维争口气,象个人儿。不过——嗳,学费真不容易,学费。”
说了就瞧着胡大:看他懂不懂“学费”是什么东西。
“学费”倒不管它。可是为什么过年也得上学呢?
这天下午,寄到了包国维的成绩报告书。
老包小心地抽开抽屉,把老花眼镜拿出来带上,慢慢念着。象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对信封瞧了老半天。两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开一合的,他从上面的地名读起,一直读到“省立××中学高中部缄”。
“露,封,挂,号,”他摸摸下巴。“露,封,……”
他仿佛还嫌信封上的字太少太不够念似的,抬起脸来对天花板愣了会儿,才抽出信封里的东西。
天上糊满着云,白天里也象傍晚那么黑。老包走到窗子眼前,取下了眼镜瞧瞧天,才又架上去念成绩单。手微微颤着,手里那几张纸就象被风吹着的水面似的。
成绩单上有五个“丁”。只一个“乙”一那是什么“体育”。
一张信纸上油印着密密的字:告诉他包国维本学期得留级。
老包把这两张纸读了二十多分钟。
“这是什么?”胡大一走进来就把脑袋凑到纸边。
“学堂里的。……不要吵,不要吵。还有一张,缴费单。”
这老头把眼睛睁大了许多。他想马上就看完这张纸,可是怎么也念不快。那纸上印着一条条格子,挤着些小字,他老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了第二行的下半格。
“学费:四元。讲义费:十六元。……损失准备金:……图书馆费:……医……医……”
他用指甲一行行划着又念第二遍。他在嗓子里咕噜着,跟痰响混在了一块。读完一行,就瞧一瞧天。
“制服费!……制服费:二——二——二十元。……通学生除——除——除宿费膳费外,皆须……”瞧瞧天。瞧瞧胡大。他不服气似地又把这些句子念一遍,可是一点也不含糊,还是这些字——一个个仿佛刻在石头上似的,陷到了纸里面。他对着胡大的脸子发愣:全身象有——不知道是一阵热,还是一阵冷,总而言之是似乎跳进了一桶水里。
“制服费!”
“什么?”胡大吃了一惊。
“唔,唔。唵。”制服就是操衣,他知道。上半年不是做过了么?他本来算着这回一共得缴三十一块。可是这二十块钱的制服费一加,可就……突然——磅!房门给谁踢开,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
房里两个人吓了一大跳。一回头——一个小伙子跨到了房里。他的脸子我们认识的:就是桌上那张照片里的脸子,不过头发没那么光。
胡大拍拍胸脯,脸上陪着笑:
“哦唷,吓我一跳,学堂里来么?”
那个没言语,只膘了胡大一眼。接着把眉毛那么一扬,额上就显了几条横皱,眼睛扫到了他老子手里的东西。
“什么?”他问。胡大悄悄地走了出去。
老头把眼镜取下来瞧着包国维,手里拿着的三张纸给他看。
包国维还是原来那姿势:两手插在裤袋里,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
象是因为衣领太高,那脖子就有点不能够随意转动,他只掉过小半张脸来瞅了一下。
“哼。”他两个嘴角往下弯着,没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张方桌跟前。他走起路来象个运动员,踏一步,他胸脯连着脑袋都得往前面摆一下,仿佛老是在跟别人打招呼似的。
老包瞧着他儿子的背:
“怎么又要留级?”
“郭纯也留级哩。”
那小伙子脸也没回过来,只把肚子贴着桌沿。他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那张方桌就咕咕咕地叫。
老包轻轻地问:
“你不是留过两次级了么?”
没答腔,那个只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接着倒在桌边那张藤椅上,把膝头顶着桌沿,小腿一荡一荡的。他用右手抹了一下头发,就随便抽下一本花花绿绿的书来:《我见犹怜》。
沉默。
房里比先前又黑了点儿。地下砖头缝里在冒着冷气,老包两只脚仿佛踏在冷水里。
老包把眼镜放到那张条桌的抽屉里,嘴里小心地试探着说:
“你已经留过两次留级,怎么又……”
“他喜欢这样!”
包国维叫了起来。
“什么‘留过两次留级’!他要留!他高兴留就留,我怎么知道!”
外面一阵皮鞋响:一听就知道这是那位表少爷。
包国维把眉毛扬着瞧着房门,表少爷象故意要表示他有双硬底皮鞋,把步子很重地踏着,敲梆似地响着,一下下远去。包国维的小腿荡得利害起来,那双脚仿佛挺不服气——它只穿着一双胶底鞋。
老头有许多话要跟包国维说,可是别人眼睛盯到了书上:别打断他的用功。
包国维把顶着桌沿的膝头放下去,接着又抬起来。他肚子里慢慢念着《我见犹怜》,就是看到一个标点也得停顿一两秒钟。有时候他偷偷地瞟镜子一眼,用手抹抹头发。自己的脸子可不坏,不过嘴扁了点儿。只要他当上了篮球员,再象郭纯那么——把西装一穿,安淑真不怕不上手。安淑真准得对那些女生说:
“谁说包国维象瘪三!很漂亮哩。”
于是他和她去逛公园,去看电影。他自己就得把西装穿得笔挺的,头发涂着油,涂着蜡,一只手抓着安淑真的手,一只手抹抹头。
……
他把《我见犹怜》一摔,抹了抹头发。
老包好容易等到包国维摔了书。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制服费,……”
没人睬他,他就停了一会。他摸了三分钟下巴。于是他咳一声扫清嗓子里的痰,一板一眼他说着缴学费的事,生怕一个不留神就会说错似的。他的意思认为去年做的制服还是崭新的,把这理由对先生说一说,这回可以少缴这意外的二十块钱。不然——
“不然就要缴五十一块半。这五十一块半——现在只有——只有——戴老七的钱还没还,这回再加二十……你总还得买点书,你总得……。”
停停。他摸摸下巴:又独言独语地往下说:
“操衣是去年做的,穿起来还是象新的一样,穿起来。缴费的时候跟先生说说情,总好少缴……少缴……”
包国维跳了起来。
“你去缴,你去缴!我不高兴去说情!——人家看起来多寒伧!”
老包对于这个答复倒是满意的,他点点脑袋:
“唔,我去缴。缴到——缴到——唔,市民银行。”
儿子横了他一眼。他只顾自己往下说。
市民银行在西大街吧?
二
老包打市民银行走到学校里去。他手放在口袋里,紧紧地抓住那卷钞票。
银行里的人可跟他说不上情。把钞票一数:
“还少二十!”
“先生,包国维的操衣还是新的,这二十……”
“我们是替学校代收的,同我说没有用。”
钞票还了他,去接别人缴的费。
缴费的拥满了一屋子,都是象包国维那么二十来岁一个的。他们听着老包说到“操衣”,就哄出了笑声。
“操衣!”
“这老头是替谁缴费的?”
“包国维,”一个带压发帽的瞅了一眼缴费单。
“包国维?”
老头对他们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接着他告诉别人——包国维上半年做了操衣的:那套操衣穿起来还是挺漂亮。
“可是现在又要缴,现在。你们都缴的么?”
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没答。
老包四面瞧了会儿就走了出来:五六十双眼睛送着他。
“为什么要缴到银行里呢?”他埋怨似地想。
天上还是堆着云,也许得下雪。云薄的地方就隐隐瞧得见青色。有时候马路上也显着模糊的太阳影子。
老包走不快,可是踏得很吃力:他觉得身上那件油腻腻的破棉袍有几十斤重。
棉鞋里也湿禄禄的叫他那双脚不大好受。鞋帮上虽然破了一个洞,可也不能透出点儿脚汗:这双棉鞋在他脚汗里泡过了三个冬天。
他想着对学堂里的先生该怎么说,怎么开口。他得跟他们谈谈道理,再说几句好话。先生总不比银行里的人那么不讲情面。
老包走得快了些,袖子上的补钉在袍子上也摩擦得起劲了点儿。
可是一走到学校里的注册处,他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
这所办公室寂寞得象座破庙。一排木栏杆横在屋子中间,里面那些桌旁的位子都是空的。只有一位先生在打盹,肥肥的一大坯伏在桌子上,还打着鼾。
“先生,先生。”
叫了这么七八声,可没点儿动静。他用指节敲敲栏杆,脚在地板上轻轻地踏着。
这位先生要在哪一年才会醒呢?
他又喊了几声,指节在栏杆上也敲得更响了些。
桌子上那团肉动了几动,过会儿抬起个滚圆的脑袋来。
“你找谁?”皱着眉擦擦眼睛。
老包摸着下巴:
“我要找一位先生。我是——我是——我是包国维的家长。”
那位先生没命的张大了嘴,趁势“噢”了一声:又象是答应他,又象是打呵欠。
“我是包国维的家长,我说那个制服费……”
“缴费么?——市民银行,市民银行!”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们包国维——包国维……”
老包结里结巴说上老半天,才说出了他的道理,一面还笑得满面的皱纹都堆起来——腮巴子挺吃力。
胖子伸了懒腰,咂咂嘴。
“我们是不管的。无论新学生老学生,制服一律要做。”
“包国维去年做了制服,只穿过一两天……”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他懒懒地拖过一张纸来,拿一支铅笔在上面写些什么。
“今年制服改了样子,晓得吧。所以——所以——啊——噢——哦!”
打了个呵欠,那位先生又全神贯注在那张纸上。
他在写着什么呢?也许是在开个条子,说明白包国维的制服只穿过两次,这回不用再做,缴费让他少缴二十。
老包耐心儿等着。墙上的挂钟不快不慢的——的,嗒,的,嗒,的,嗒。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
那位先生大概写完了。他拿起那张纸来看:嘴角勾起一丝微笑,象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纸上写着些什么:画着一满纸的乌龟!
老实说,老包对这些艺术是欣赏不上的。他嘘了口气,脸上还是那么费劲地笑着,嘴里喊着“先生先生”。他不管对方听不听,话总得往下说。他象募捐人似的把先生说成一个大好老,菩萨心肠:不论怎样总得行行好,想想他老包的困难。话可说得不怎么顺嘴,舌子似乎给打了个结。笑得嘴角上的肌肉在一抽一抽的,眉毛也痉挛似地动着。
“先生你想想:我是——我是——我怎么有这许多钱呢:五十——五十——五十多块。……我这件棉袍还是——还是——我这件棉袍穿过七年了。我只拿十块钱一个月,十块钱。我省吃省用,给我们包国维做——做……我还欠了债,我欠了……有几笔……有几笔是三分息。我……”
那位先生打定主意要发脾气。他把手里的纸一摔,猛地掉过脸来,皱着眉毛瞪着眼:
“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学校又不是慈善机关,你难道想叫我布施你么!——笑话!”
老包可愣住了。他腮巴子酸疼起来:他不知道还是让这笑容留着好,还是收了的好。他膝踝子抖索着。手扶着的这木栏杆,象铁打的似的那么冰。他看那先生又在纸上画着,他才掉转身来——慢慢往房门那儿走去。
儿子——怎么也得让他上学。可是过了明天再不缴费的话,包国维就得被除名。
“除名……除名……”老包的心脏上象长了一颗鸡眼。
除名之后往哪里上学呢?这孩子被两个学校退了学,好容易请大少爷关说,才考进了这省立中学的。
还是跟先生说说情。“先生,先生,”老包又折了回来。“还有一句话请先生听听,一句话。…… 先生,先生!”
他等着,总有一个时候那先生会掉过脸来。
“先生,那么——那么——先生,制服费慢一点缴。先缴三十——三十——先缴三十一块半行不行呢?等做制服的时候再——再……现在——现在实在是——实在是一一现在——现在钱不够嘛。我实在是……”
“又来了,喷!”
先生表示“这真说不清”似地掉过脸去,过会又转过来:
“制服费是要先缴的:这是学校里的规矩,规矩,懂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各种费用都要一次缴齐,缴到市民银行里。通学生一共是五十一块五。过了明天上午不缴就除名。懂不懂,懂不懂,听懂了没有!”
“先生,不过——不过……”
“嗨,要命!我的话你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尽说尽说有什么好处!真缠不明白!……让你一个人去说罢!”
先生一站起来就走,出了那边的房门,接着那扇门很响地一关——匐!墙也给震动了一下。那只挂钟就轻轻地“锵郎”一声。
给丢在屋子里的这个还想等人出来:一个人在栏杆边呆了十几分钟才走。
“呃,呃,唔。”
老包嗓子里响着,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他仿佛觉得有一桩大祸要到来似的,可是没想到可怕。无论什么天大的事,那个困难时辰总会度过去的。他只一步步踏在人行路上,他几乎忘了他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事,也忘了会有一件什么祸事。他感觉到自己的脚呀手的都在打颤。可是走得并不吃力:那双穿着湿渌渌的破棉鞋的脚已经不是他的了。他瞧不见路上的人,要是有人撞着他,他就斜退两步。
街上有些汽车的喇叭叫,小贩子的大声嚷,都逗得他非常烦躁。太阳打云的隙缝里露出了脸,横在他脚右边的影子折了一半在墙上。走呀走的那影子忽然缩短起来移到了他后面:他转了弯。
对面有三个小伙子走过来,一面嘻嘻哈哈谈着。老包喊了起来: “包国维!”他喊起他儿子来也是照着学堂里的规矩——连名带姓喊的。
包国维跟两个同学一块走着,手里还拿着一个纸袋子,打这里掏出什么红红绿绿的东西往嘴里送。那几个走起路来都是一样的姿势——齐脑袋到胸脯都是向前一摆一摆的。
“包国维!”
几个小伙子吃一惊似地站住了。包国维马上把刚才的笑脸收回,换上一副皱眉毛。他只回过半张脸来,把黑眼珠溜到了眼角上瞧着他的老子。
老包想把先前遇到的事告诉儿子,可是那些话凝成了冰,重重地堆在肚子里吐不出。他只不顺嘴地问:
“你今天——你今天——你什么时候回家?”
儿子把两个嘴角往下弯着,鼻孔里响了一声。“高兴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家里摆酒席等着我么!……我当是什么往下说。
市民银行在西大街吧?
二
老包打市民银行走到学校里去。他手放在口袋里,紧紧地抓住那卷钞票。银行里的人可跟他说不上情。把钞票一数: “还少二十!”“先生,包国维的操衣还是新的,这二十……”“我们是替学校代收的,同我说没有用。”钞票还了他,去接别人缴的费。缴费的拥满了一屋子,都是象包国维那么二十来岁一个的。他们听着老包说到“操衣”,就哄出了笑声。“操衣!” “这老头是替谁缴费的?”“包国维,”一个带压发帽的瞅了一眼缴费单。“包国维?”老头对他们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接着他告诉别人——包国维上半年做了操衣的:那套操衣穿起来还是挺漂亮。“可是现在又要缴,现在。你们都缴的么?”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没答。老包四面瞧了会儿就走了出来:五六十双眼睛送着他。“为什么要缴到银行里呢?”他埋怨似地想。天上还是堆着云,也许得下雪。云薄的地方就隐隐瞧得见青色。有时候马路上也显着模糊的太阳影子。老包走不快,可是踏得很吃力:他觉得身上那件油腻腻的破棉袍有几十斤重。棉鞋里也湿禄禄的叫他那双脚不大好受。鞋帮上虽然破了一个洞,可也不能透出点儿脚汗:这双棉鞋在他脚汗里泡过了三个冬天。他想着对学堂里的先生该怎么说,怎么开口。他得跟他们谈谈道理,再说几句好话。先生总不比银行里的人那么不讲情面。老包走得快了些,袖子上的补钉在袍子上也摩擦得起劲了点儿。可是一走到学校里的注册处,他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这所办公室寂寞得象座破庙。一排木栏杆横在屋子中间,里面那些桌旁的位子都是空的。只有一位先生在打盹,肥肥的一大坯伏在桌子上,还打着鼾。“先生,先生。”叫了这么七八声,可没点儿动静。他用指节敲敲栏杆,脚在地板上轻轻地踏着。这位先生要在哪一年才会醒呢?他又喊了几声,指节在栏杆上也敲得更响了些。桌子上那团肉动了几动,过会儿抬起个滚圆的脑袋来。“你找谁?”皱着眉擦擦眼睛。 老包摸着下巴:“我要找一位先生。我是——我是——我是包国维的家长。”那位先生没命的张大了嘴,趁势“噢”了一声:又象是答应他,又象是打呵欠。“我是包国维的家长,我说那个制服费……”“缴费么?——市民银行,市民银行!”“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们包国维——包国维……”老包结里结巴说上老半天,才
说出了他的道理,一面还笑得满面的皱纹都堆起来——腮巴子挺吃力。 胖子伸了懒腰,咂咂嘴。“我们是不管的。无论新学生老学生,制服一律要做。”“包国维去年做了制服,只穿过一两天……”“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他懒懒地拖过一张纸来,拿一支铅笔在上面写些什么。“今年制服改了样子,晓得吧。所以——所以——啊——噢——哦!”打了个呵欠,那位先生又全神贯注在那张纸上。他在写着什么呢?也许是在开个条子,说明白包国维的制服只穿过两次,这回不用再做,缴费让他少缴二十。老包耐心儿等着。墙上的挂钟不快不慢的——的,嗒,的,嗒,的,嗒。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那位先生大概写完了。他拿起那张纸来看:嘴角勾起一丝微笑,象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纸上写着些什么:画着一满纸的乌龟!老实说,老包对这些艺术是欣赏不上的。他嘘了口气,脸上还是那么费劲地笑着,嘴里喊着“先生先生”。他不管对方听不听,话总得往下说。他象募捐人似的把先生说成一个大好老,菩萨心肠:不论怎样总得行行好,想想他老包的困难。话可说得不怎么顺嘴,舌子似乎给打了个结。笑得嘴角上的肌肉在一抽一抽的,眉毛也痉挛似地动着。“先生你想想:我是——我是——我怎么有这许多钱呢:五十——五十——五十多块。……我这件棉袍还是——还是——我这件棉袍穿过七年了。我只拿十块钱一个月,十块钱。我省吃省用,给我们包国维做——做……我还欠了债,我欠了……有几笔……有几笔是三分息。我……”那位先生打定主意要发脾气。他把手里的纸一摔,猛地掉过脸来,皱着眉毛瞪着眼:“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学校又不是慈善机关,你难道想叫我布施你么!—— 笑话!”老包可愣住了。他腮巴子酸疼起来:他不知道还是让这笑容留着好,还是收了的好。他膝踝子抖索着。手扶着的这木栏杆,象铁打的似的那么冰。他看那先生又在纸上画着,他才掉转身来——慢慢往房门那儿走去。儿子——怎么也得让他上学。可是过了明天再不缴费的话,包国维就得被除名。“除名……除名……”老包的心脏上象长了一颗鸡眼。除名之后往哪里上学呢?这孩子被两个学校退了学,好容易请大少爷关说,才考进了这省立中学的。还是跟先生说说情。“先生,先生,”老包又折了回来。“还有一句话请先生听听,一句话。…… 先生,先生!”他等着,总有一个时候那先生会掉过脸来。“先生,那么——那么——先生,制服费慢一点缴。先缴三十——三十——先缴三十一块半行不行呢?等做制服的时候再——再……现在——现在实在是——实在是一一现在——现在钱不够嘛。我实在是……”“又来了,喷!”先生表示“这真说不清”似地掉过脸去,过会又转过来:“制服费是要先缴的:这是学校里的规矩,规矩,懂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各种费用都要一次缴齐,缴到市民银行里。通学生一共是五十一块五。过了明天上午不缴就除名。懂不懂,懂不懂,听懂了没有!”“先生,不过——不过……”“嗨,要命!我的话你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尽说尽说有什么好处!真缠不明白!……让你一个人去说罢!”先生一站起来就走,出了那边的房门,接着那扇门很响地一关——匐!墙也给震动了一下。那只挂钟就轻轻地“锵郎”一声。给丢在屋子里的这个还想等人出来:一个人在栏杆边呆了十几分钟才走。“呃,呃,唔。”老包嗓子里响着,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他仿佛觉得有一桩大祸要到来似的,可是没想到可怕。无论什么天大的事,那个困难时辰总会度过去的。他只一步步踏在人行路上,他几乎忘了他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事,也忘了会有一件什么祸事。他感觉到自己的脚呀手的都在打颤。可是走得并不吃力:那双穿着湿渌渌的破棉鞋的脚已经不是他的了。他瞧不见路上的人,要是有人撞着他,他就斜退两步。街上有些汽车的喇叭叫,小贩子的大声嚷,都逗得他非常烦躁。太阳打云的隙缝里露出了脸,横在他脚右边的影子折了一半在墙上。走呀走的那影子忽然缩短起来移到了他后面:他转了弯。对面有三个小伙子走过来,一面嘻嘻哈哈谈着。 老包喊了起来:“包国维!”他喊起他儿子来也是照着学堂里的规矩——连名带姓喊的。包国维跟两个同学一块走着,手里还拿着一个纸袋子,打这里掏出什么红红绿绿的东西往嘴里送。那几个走起路来都是一样的姿势——齐脑袋到胸脯都是向前一摆一摆的。“包国维!”几个小伙子吃一惊似地站住了。包国维马上把刚才的笑脸收回,换上一副皱眉毛。他只回过半张脸来,把黑眼珠溜到了眼角上瞧着他的老子。老包想把先前遇到的事告诉儿子,可是那些话凝成了冰,重重地堆在肚子里吐不出。他只不顺嘴地问:“你今天——你今天——你什么时候回家?”儿子把两个嘴角往下弯着,鼻孔里响了一声。“高兴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家里摆酒席等着我么!……我当是什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