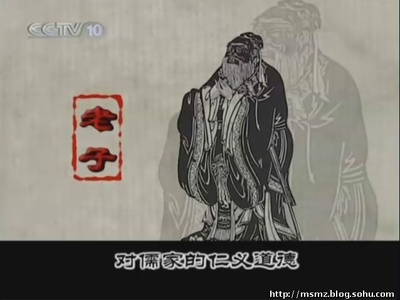苗学研究新成果
“苗图”研究概述
史晖
中国明清时期滥觞的“苗蛮图”又称“百苗图”,是南方各种有关少数民族图册的泛称,考虑到图册反映的地域多样性以及民族及其支系的多样性,笔者分别采用“黔苗图”、“滇夷图”、“楚苗图”、“琼黎图”、“台番图”等来分类进行指称。在国外著述中,习称“苗图”(Miaoalbums,Miau albums ,Miao-tze Albums),“苗图”以绘图形式保留明清时期大量珍贵的少数民族形象资料,是研究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一份宝贵遗产。本文尝试梳理国外“苗图”的收藏与研究状况,介绍海外收藏珍贵版本资料,以资国内参考;勾勒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进展,介绍西方史学、人类学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比较、探讨其理论成果,为以“苗图”为媒介,实现中西的一种交流与对话作引玉之砖。
一、国外“苗图”收藏概述
早在19世纪中期,适应西方势力渴望了解中国的需要,“苗图”作为民族学文献引起兴趣,一些西方政府官员、传教士、探险家、学者开始关注并搜集、研究“苗图”,使大量版本包括珍本流传海外。我国人类学家刘咸最早于1936年在《方志》上发表《苗图考略》一文,汇录了国外图书馆、博物馆及私人收藏情况;1995年,美国学者劳拉•霍斯特勒(LauraHostetler)通过调查、访学、实地查证等多种方式,详细搜集中、英、法等六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等的苗蛮图收藏版本信息,整理成82册“苗图”信息附录(LauraHostetler,1995:283-364).这对今后的苗蛮图版本研究,考证真伪、源流具有极其重要的帮助。稍后捷克学者VladimirLiscak也发表文章,简介中、英、法等九国共80种“苗图”版本收藏(VladimirLiscak,1992:73)。除此之外,一些散见于学术期刊、书籍等文献的相关记录,也可作为线索。笔者以上述资料为主要依据,结合自身调查,参考其他信息,按国别分类,综合整理海外收藏:已知英国收藏版本十九种;意大利收藏版本十六种;美国收藏版本十四种;日本收藏版本十二种;德国收藏版本七种;法国收藏版本六种;俄罗斯收藏版本十种;捷克斯洛伐克收藏版本二种(祁庆富,2003)。
检视海外“苗图”的收藏我们发现:较优的抄本可能已流出海外,虽然一些西方学者将一些版本中部分图像和文字内进行翻译和介绍,但他们尚无法为我们揭示这些珍本的庐山真面目,能看到这些珍贵资料,与国内资料进行互校,是实现研究突破的必需和关键
二、国外“苗图”研究综述
“苗图”,作为被带到国外的中华文明渊博文化资料的一部分,也融汇入西方的史学、汉学、中国学的发展脉络之中。通过收集主要研究著述、分析其理论方法、探寻学术流派渊源,比较研究成果,笔者将海外的“苗图”研究归纳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苗图”研究
1.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苗图”研究:介绍、翻译与传播
1845年,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中国丛报》发文,对一部“苗图”的文字和序言进行了部分的翻译和介绍(Laura Hostetler,2001:195),他重视翻译“苗图”中的族名,认为有重要意义。
1859年,美国来华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裨治文(Rev. E. C.Bridgman)也翻译并注释了二册、有82人物的“苗图”,刊登在亚洲文会会刊上(Rev. E. C. Bridgman,1859:257-287)。裨治文在文中介绍该图册的版本特征,说明这是一个稀有版本以及其对了解苗族的意义。他翻译的这册苗图和卫三畏前述苗图是同一图册,只是卫三畏是部分翻译,他则是全文翻译。他提到,该苗图的完整复制本在传教士洛克哈特(DrWilliam Lockhart)手上。
裨治文提到的洛克哈特,于1861年也写了一篇文章,提及自己拥有苗图。他主要关注的是“苗图”中的民族学内容而非其形式的变化。伦敦中国内地教会图书馆中文部藏苗图一部,据书目第二册载,系当年洛克哈特旧物,或即裨治文所谓“最完善之苗图”。
不列颠驻华领事勃勒法(T.M.H.Playfair)于1877年,在《中国评论》著文介绍、翻译他购于北京的三册苗图:两册贵州苗图,无题佚名;一册云南苗图,题名为《丽江府十种彝人图》(T.M.H.Playfair,1877:92-108)。我们尚无法确证勃勒法所译两册贵州苗图与前述裨治文等所译苗图是否确定为同一版本,但我们已可判断伦敦中国内地教会图书馆中文部所藏的苗图——卫三畏、裨治文、洛克哈特先后对其翻译论说,勃勒法也对其进行资料比较——应当是当时所见珍本,在未来研究中的价值意义不容忽视。
2.探险家、游历家的“苗图”探求
(1)克拉克与《贵州与云南》:《伯麟图说》传世的西方见证
清嘉庆年间官云贵总督伯麟在滇任职期间,奉上谕绘制滇省夷人图册,附说,被后人习称为《伯麟图说》。据刘咸记述:“1894年,有居中国西部之教士兼游历家克拉克(GeorgeW. Clark)者,著一小书,名《贵州与云南》(Kweichow And YunnanProvince),其中叙述(贵州)苗人八十二种,......一望可知是以“苗图”作蓝本者。”然而笔者再细察全书,还有更有意义的发现:在第一章“云南省:过去、现在和将来”中,还“隐藏”有一部“滇夷图”!这部夷图的文字,按粮道所辖、迤东道所辖、迤西道所辖、迤南道所辖地域排列。通过将这部分文字进行翻译,与《伯麟图说》的完整无缺的文字刻本(清)佚名《夷人图说》(石光明,2003)相比较,基本一致,可判断这至少是《伯麟图说》依然存世的一种英文记录与历史见证,在今后的版本研究中,《贵州与云南》中的文字可以作为重要的“异本”,为继续搜寻考证《伯麟图说》的源流提供比较与参考。
(2)柯勒洪与《通过华南边疆》:寻找“苗图”,也绘制“苗图”
柯乐洪( A. R.Colquhoun)是19世纪的英国殖民官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通过华南边疆:经历华南的勘探旅程》一书,记述了柯于1881至1882年间,深入中国腹地,对广西、云南、贵州以及中越边界、滇缅边境地区进行社会、文化、地理考察的收获。书中柯勒洪还记述了当时他在云南开化府复制苗蛮图的经过(Colquhoun,ArchibaldRoss,1883);发表了一批云南民族照片,还有许多手绘的云南民族图稿。这些图稿记录了清同治年间一些云南民族支系真实可信的形象。这种对西南民族的图像描绘,结合书中的文字记述,本身就具有历史学、民族学价值,甚至可以定义为西人所画的“苗图”,如果将其与我国西南民族史和“苗图”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中西史料的互相印证,将有助于呈现历史文化变迁的脉络。
3.早期来华学者的研究:收集材料,开拓汉学
国外最早关于“苗图”的研究文章出现于1837年,德国历史学家诺孟(Carl Friedrich Neumann)的文章详细描述和完整翻译一册佚名苗图的图说,有79人物(LauraHostetler,2000:195)。20世纪欧洲汉学大师,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目录学家、珍本收藏家亨利•科尓迪埃(Cordier,Henri)于1907年出版著作《倮倮:现状和问题》一书,将“苗图”作为研究彝族的历史文献之一,引用前述裨治文、克拉克、勃勒法的“苗图”译文,翻译为法文,介绍给法国各界(Cordier,Henri,1907:598-600)。德国学者耶格尔(F.Jaeger)于1916、1917年发表文章,将“苗图”和皇清职供图比较研究,认为最早出现“苗图”应是在雍正时期。这是西方学者较早从版本渊源上进行的考证。以科尓迪埃和诺孟为代表的汉学家以及汉学前驱的研究,和他们带回国的丰富文献资料一道,为本国后继汉学的发展,打下基础,对本国的中国观、中国学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二)20世纪中后期的“苗图”研究
西方对苗图的研究随着收藏的丰富和各国汉学、中国学的学术积累而发展,学者们从以前着重于基础性研究,即直接翻译和介绍收藏于欧洲的苗图,到开始研究苗图的形成、关注其版本、风格,阐释“苗图”反映的族群历史文化特征。
1.德国苗蛮图研究
德国在翻译究资料积累、形成承前启后的学术脉络,产生丰富成果,融汇入本国的汉学研究之中这几个方面来看,都很突出:
1937年,Chiu Chang kong ,汉堡民族学博物馆主管,将Friedrich Hirth于1890
年捐献给Gotha图书馆的所有苗图全文译为德文,并作注释,由德国Friederichsen 出版社出版发行。他还写了苗图的历史、渊源的介绍文章(ChiuChang kong,1937)。
德国汉学家爱伯华(WolframEberhard)继承发展了20世纪初德国汉学重视中国邻邦与临近民族的趋势(魏思齐,2006:38),在他的专著《中国及其西南邻邦》中,将藏于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柏林、汉堡博物馆、哥打图书馆,以及其他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德国收藏“苗图”共13册中的族群按文化特征进行规类对照列表,使人一看就知何族有何文化和习俗特征(WolframEberhard,1978:314-328)。其研究优势是多种版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角度是立足于“苗图”本身,将其界定为历史民族志资料以研究其反映的历史文化特征,这种研究路径与我国国内早期“苗图”研究趋势是相似的。
(三)跨越20世纪的苗蛮图研究:文本的“重读”——人类学视角和世界民族志视野
前述德国苗图研究反应了西方学者在无法到达中国实地考察的背景下依赖文献资料开展历史研究的情形。到了20世纪中后期,研究西南民族的西方人类学者有机会来到中国,他们的研究建立在田野和文献的结合上,引入人类学视野、理论与“他者”的眼光,因此他们观察和解读作为民族志文本的苗蛮图,别有一番新意。
1.劳拉•霍斯特勒(LauraHostetler):历史的“透镜”
劳拉•霍斯特勒是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在霍氏的研究历程中,为搜集《苗蛮图》,掌握世界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等中的收藏情况,她做了许多调查和实地查证工作:她曾到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查证苗图;她曾通过德国学者交流机构的资助,前往德国研究苗图;她也曾到访中国,在贵州师范大学,与当地历史、民族学者交流研讨。
霍斯特勒的博士论文《18世纪的中国人种志:贵州苗图》,将“苗图”界定为中国西南人种志图绘文本,原用于帮助官员了解不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便更好地治理一方。霍斯特勒主要从西方人种志图象发展的学术视角比照中国的“苗图”,指出其与早期的中国文献描述在重点和观察方向上都有质和量的不同,以直接的实地观察和写实的描绘等为重要特征,从而将其纳入民族学的范畴。霍斯特勒将“苗图”视为清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想像”和掌控的见证,认为从其收集、组织和传递信息的方式中,苗图显示出某种程度上和政治技术的密切相关,而这种技术加强了为清帝国服务的“科学”知识的获得(LauraHostetler ,1995)。
2001年,霍斯特勒出版专著《清代殖民扩张:近代早期中国的人种志与地图》在沿袭其博士论文丰富的材料基础之上,她试图论证中国清代怎样利用人种志和地图来实现帝国殖民扩张的和统治目的。她将清帝国放置在世界史范畴的视角中,以近代欧洲与清帝国作比较,认为清王朝运用民族学、地图学以助帝国建设,这近似于同时代许多欧洲国家(17--18世纪国家)利用地域和人种的描述,由此提出清和欧洲同处于“近代早期”的一般论断。
霍斯特勒与同是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历史系的戴维•迪尔(DavidDeal)教授合作出版的最新著作《人种志的艺术;一册中国“苗图”》于2006年问世。该书复制了一册年代判断在1797年以后的佚名贵州苗图,并对其中文内容进行了全部的英文翻译。书中霍斯特勒介绍性地论述苗蛮图的起源和版本衍变,以所复制的苗图为例,阐释苗图反映的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内容,还引入日本德川时代和相近时期土耳其的人种志图册资料与中国苗图进行比较研究,凸显苗图在世界民族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霍斯特勒的研究,特别是《清代殖民扩张:近代早期中国的人种志与地图》,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肯定其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在世界史大背景下研究中国清代的特点,有助于对清史研究、中国史研究、非欧洲民族志有兴趣者(MonikaK.Rieger,2000:85) ;争议集中在霍斯特勒对清代“殖民扩张”和“处于近代早期”的界定。James A.Millward指出,“尽管期间有大规模起义,但是由十九世纪中期,清廷和官僚已不再关心了解这些民族的准确信息的事实使认为清和欧洲同处于“近代早期”的一般论断遇到难题”;MonikaK.Rieger指出,其“引用15、16世纪欧洲绘图学的例子,但没用中国方面的图例拿出来比较;其假设的有效性正确性难以评估,材料和分析还不足以说明这一宏大观点”;Shana J. Brown和Richard. J.Smith的评论都在质疑将人种志研究与殖民政治联系起来,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有解释性 (James A.Millward,2002:248;MonikaK.Rieger,2000:85;Richard.J.Smith,2003:163-164;243-247;Shana J.Brown,2007:243-247)。
笔者认为,在采用中西比较进行宏大的理论构建时(特别是这种理论构建尝试要跨越东西),必然要遇到学贯中西的难题。在研究中,霍斯特勒要处理的最大问题,是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的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多元一体的民族历史、民族关系。霍斯特勒虽然尽可能的运用了广泛的研究资料,领域包括中国地图、族群、地域政治、对外关系等,但除了有限的几种中文文献,几乎全然依靠西方其他学者著述来帮助她的观看,有些材料停留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认识阶段,完全没有了解到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她的立足点相对于她的宏大视野来说并不充分:虽然从地图和人种志的使用上也许可以自圆其说——我国地图绘制在清代确有较大突破,传统地理志的特点是对民族和地方的浪漫描述,而清代民族志不再依赖于想象或旧的描述的循环再用,而基于直接观察的人民本身;(JamesA.Millward,2002:348)。但据此就直接认为是一个认识论的转变和殖民扩张的结果,这是一种简单的比较,毕竟在“苗图”和地图之外,存在着更为广阔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需要钩沉。这反过来启示我们的研究:不但要尊重与兼顾中西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更应注重苗图这一“文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语境,至少需要考虑如社会史这样的大维度,才能做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推测。

2.王富文(Tapp.Nicholas):“他者”的眼光
王富文(Tapp.Nicholas)是澳州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人类学系教授,他通过英国的FrancesWood提供资料帮助,选择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的两册“苗图”为材料,与Don Chon合写著作《中国西南种族:中国人对国内“他者”的观点》一书。该书对两册苗图的图文进行重新编排和翻译,并做“当代民族学注释”,在注释中,作者援引中外文献介绍苗图所绘民族的历史,阐释图像呈现的生活习俗与文化内涵,与劳拉•霍斯特勒的研究不同之处是:虽然都注意比较苗图和中国早期其他描绘种人和异邦的历史文献,但霍斯特勒强调在“苗图”中开始出现以实地调查和写实描绘,反映认识论的转向,而王富文则从艺术视角出发,认为“苗图中的背景绘制,在我们看来是为了使人物更具有人性,而不是自然主义地描绘环境。”他还认为“以前的文献如《山海经》常把少数民族异化、神秘化,而苗图不同,绘图充满同情和理解。”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利用的资料有限,采用两册文人画色彩浓厚、精致的“苗图”,可以说没有对中国“苗图”的多样性给予充分的注意。(NicholasTapp and Don Chon,2003:4;67-87)
三、试探中外“苗图”研究的发展:期待溯本清源,交流对话
21世纪的“苗图”研究,随着西方学者纷纷编辑、翻译、出版各种“苗图”版本拉开序幕:2003年,奈杰尔•艾伦(NigelAllan)编辑出版的《东方之珠:威尔康图书馆的亚洲珍宝收藏》一书,部分刊载英国伦敦威尔康图书馆(欧洲最大的关于亚洲的手稿、图书、图册的收藏地之一)收藏的三种苗图;同年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将馆藏《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以德文译本形式出版发行;美国出版的《人种志的艺术;一册中国“苗图”》一书复制了一册年代判断在1797年以后的佚名贵州苗图,并对其中文内容进行了全部的英文翻译。这些“苗图”的出版提供了不少国内从未见到有特殊价值的版本形态,特别提供了我们寻找已久的,具体的苗图编绘者,如乾隆朝鹤丽镇中营游击赵九州、乾隆年间三楚贺长庚的信息。这是我们利用国内资料,对比研究,溯本清源的契机。
通过回顾国外“苗图”的收藏与研究,我们发现:一批有价值的“苗图”珍本、孤本主要收藏在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及个人手中。除少量外,目前我们只知其目,不见真本。以国内外协作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搜集、整理流落在海外的“苗图”,使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重归故土,必将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同时,把握国外“苗图”收藏与研究动向,对于深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用“苗图”搭建起一座中国民族学与海外沟通的桥梁。
(作者简介:史晖,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Laura Hostetler,ChineseEthnography in Eighteenth Century:Miao Albums of Guizhou
Province
Thesis(ph.D)University ofPennsylvania.Ann Arbor,Mich:UMI,1995
Liscak,Vladimir,Miao Albums andTheir Study.Studien Zur Kulturgeschichte.
Frankfurt/M.Verlag für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1992.
祁庆富,2003,《绚丽多彩的清代民族画卷——“苗蛮图”研究述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2001.
Rev. E. C. Bridgman,1859,Sketchesof the Miao –tsze. Journal of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Society No.III.December.
T.M.H.Playfair,1877,The Miao Tzuof Kueichou and Yunnan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s The ChinaReview.Vol.V.
石光明,2003,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34.北京:线装书局。
Colquhoun,Archibald Ross,1883,Across chryse: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China border lands.London:Sampson Low.
Cordier, Henri,1907, LesLolos:État actuel de la question Leide : E.J. Brill.
Chang-kong Chiu,1937,Die Kulturder Miao-tse nach älteren chinesischen quellen.
Hamburg : KommissionsverlagFriederichsen, De Gruyter & co. m.b.h.
Wolfram Eberhard,1978,China undseine westlichen Nachbarn : Beitrge zur
mittelalterlichen und neurerenGeschichte Z monograph,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Nicholas Tapp and Don Chon withthe assistance of Frances Wood,2003, theTribal
Peoples of Southwest China Chineseviews of the Other Within.White Lotus Press, printed inThailand.
James A. Millward ,2002,Reviews of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3.
Monika K.Rieger,2000,Review of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artographica, Vol. 37.
Richard.J.Smith,2003,Asia and thePacific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XXXVIII
April.
Shana J. Brown ,2007,Review of Artof Ethnography :A Chinese “Miao Albu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8.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