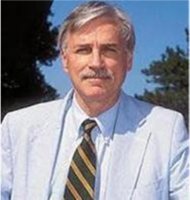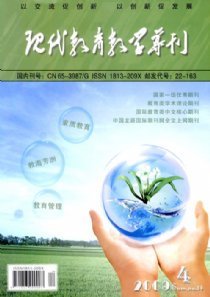第784篇: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王充的教育思想
逍遥行者
2011年4月7日
王充(公元2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年不详,据史料分析,他的卒年应在公元97—105年之间。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帝四朝,正是赤眉起义失败,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东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俗儒守文失真,方士仙士惑众,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说猖獗的时代。
王充目睹紫朱杂厕,瓦玉集糅,论说纷云,莫之所宗,“听者以为真然,说者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者不绝”,甚至“南面称师”,也诵读宣扬奸伪邪说的状况,他企图使人们“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于是以“心愤涌,笔手扰”的心情作《论衡》,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批驳虚妄伪说。范晔称他的著作能“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王充传》)。纪晓岚称王充的思想“殊有裨于风教”(《四库提要》卷一二○,子部杂家四),近人钱穆说他是“开魏晋新思想之先河。”
王充祖上曾因“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但时间不久。后来他的先世“以农桑为业”,他的祖父王汎,父亲王涌“以贾贩为事”,因与豪家丁伯结怨迁居上虞,所以,他自称出身于“细族孤门”,接近一般人民群众生活,属于下层社会,被人讥讽为“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论衡·自纪》)。他一生“仕路隔绝,志穷无如”,晚年“发白齿落,日月逾迈,寿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处境相当困难。他罢官归家以后,一面招收生徒教学授业,一面研究学问专心著述。
王充自述他对仕宦淡漠,说:“不贪富贵”,“不慕高官”,“贬黜抑屈,不恚下位。”他抱着“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的心情看待世俗人情,立定以“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的高尚情操立身处世,宁可过“处卑、位贱”的生活,也不趋炎附势(《论衡·自纪》),所以,晚年不仅物质生活极端贫困,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压抑。
从王充的《自纪篇》来看,他罢官归乡以后,以对“世书俗说”、“考论虚实”的精神著书立说,希望将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以垂教后世。他说:“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又说:“既晚无还,垂书示后”(《论衡·自纪》)。所以他的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现实问题而写的,贯穿着新鲜明朗的批判精神。王充讥恶那种“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故旧叛去”的庸俗世风人情,撰《讥俗》一书;他忧患人君治民之道,不得其宜,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作《政务》一书;痛感“俗书伪文多不诚实”,于是作《论衡》一书。晚年由于生活贫困,精神孤寂,年老体弱,作《养性》书十六篇,在著述中结束了一生。
王充的著作虽多,但现存仅《论衡》一书。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是针对当时“俗书伪文”和“俗儒守文”而发的。他以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求真理,正是非。他以科学为依据,以“证验”为尺度,对一切虚妄谬论给予无情的批判。在谶纬迷信充斥于世的条件下,他敢于公开抨击“天人感应”,“神灵怪异”,一扫汉代二百多年阴阳谶纬之风,为东汉学术另辟途径,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
《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国哲学史上掀起了一大波澜。
据《后汉书》记载,《论衡》共八十五篇,内《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实际上只有八十四篇,是他用了3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巨著。由于《论衡》直指官方神学化的儒学,因此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东汉政权瓦解后,才重见天日,但这已是王充死后百年的事了。
在《论衡》这部著作中,也谈到教育问题。如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培养中的作用;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后知”的学习论;反对呆读死记,重视实际锻炼的学习方法;反对复古,重视现实的教育内容;反对“信师是古”,提倡“问难探索”的学风,等等,这些对以后唯物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王充依据自然科学理论,吸收道家“无为自化”和荀况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
王充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天地是物质性的,宇宙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生成是自然现象。他曾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论衡·祀义》)。又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很清楚,王充把天当作自然物,不是人格化的,有意志的,有无上权力的神。所以他说:“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论衡·自然》)他以造物须用手,天没有手不可能创造各物为理由,通俗地证明天是自然物而不是神。他以“日月行有常度”,即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过程,否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可以降福佑善,下祸惩恶,谴告人事等“天人感应”的谬论。他又以鱼生水中,兽在山林来证明物各有其自然本性,所以得出结论:“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论衡·自然》)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灾变呢?他说,这乃是运行规律的失调,而非意识性的感应,就好像人生病一样,“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论衡·谴告》)。他针对人死变鬼,可以祸害生人的谬论,指出,人之生是由于夫妇合气,是自然现象。同样,人死气灭,也是自然现象,怎能变鬼?他解释说:“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论衡·论死》)。人死精神消失,骸骨归土,消亡无形,从医学生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生与死乃是普通的自然现象。王充还进一步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了形神关系,有力地驳斥了鬼神的存在,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
但是,王充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的思想,还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可能对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因而有些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他的教育思想也体现在这本书中。
1、论教育的作用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2、关于培养目标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王充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意成果。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3、学以求知
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天地之间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当然人与人的禀赋不同,但不学是不可能得知的。他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知物由学”可谓古代最有价值的认识论命题之一。
王充认为,学习应是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过程。其中耳闻目见的直接认识是基础,否则就可能被虚假浮夸的东西所迷惑。所以他强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但仅凭耳目,得到的只是表象而已,还必须将感性认知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充兼论感官与思维的作用,使古代学习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
4、问难、距师
王充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问难”精神。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提问者是经过个人思考,有自己的看法的。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他认为:“苟(如果)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真正)有传圣业之知,伐(讨伐,批评)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列举若干例证,说明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而弟子当时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为此,王充感叹:“凡学之道,距师为难。”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距师并不是拒师,王充更没有彻底否定孔子等圣贤的意思,他提倡的是追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独尊儒术及师道尊严盛行的环境下,更是具有反潮流的突出意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