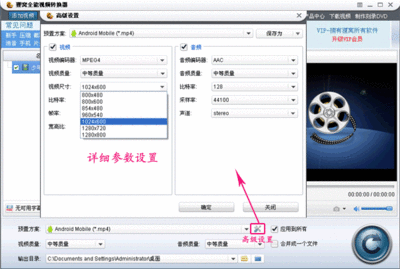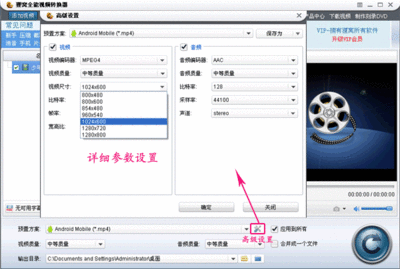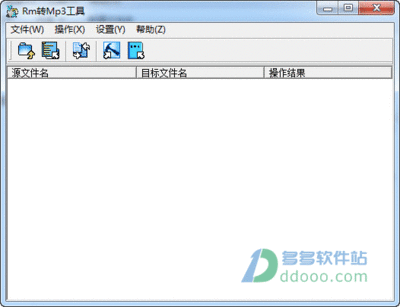9月底,我去香港参加港澳内地三地的药物滥用学术交流年会,遇到了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吕宪祥主任,他很关切地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收治泰勒宁成瘾的病例?我们正在关注这个药。”我脑海里马上想起了一个病人,阿青(化名)。
阿青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主要是三点:其一,他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术治疗后发生感染,反复手术期间长期服用镇痛药泰勒宁而上瘾,来我们这里前每天服用的剂量达50多片,换句话讲,他其实是医源性药物依赖的患者,也就是说是因为治疗疾病过程中服用药物而导致的药物成瘾,并非滥用所致;其二,他是北京人,已经30多岁,给我的感觉其毅力不亚于常人,但是在北京已经去过多家医院包括北京安定医院,都无法真正让他摆脱掉这个药物,曾经陷入绝望之中;其三,来到我们这里做完UROD以后,他感到全身非常轻松,对于治疗效果感到不可思议,一次团体时,他以“纪念白求恩”的歌曲为基调,填词,写了一首歌送给我,并让人做成一块匾,歌曲名叫“神医何日辉”,呵呵,这是对我很高的褒奖。
实际上,我在临床上碰到的医源性药物依赖的病人也不少。比如09年我曾经接诊过一个曲马多成瘾的女患者,四川人,40多岁,是由于乳腺肿瘤手术后服用曲马多镇痛而上瘾,平均每天的剂量在300mg左右,剂量并不大,但是这足以引发她出现严重的戒断症状和心理异常,因为一个戒毒所治疗错误,用美沙酮给她治疗,最后差点导致自杀,是她在广州工作的儿子带她来治疗的。治疗结束后她还曾经与我一起去过北京,接受过央视《健康之路》的采访,节目很精彩,也很震撼,遗憾的是由于节目组的领导在国庆60年大庆的压力之下,不敢播放,胎死腹中,少挽救了多少人!因为,08年走近科学对我们的采访《被药物控制的人》播出后,至今影响力仍在,前前后后近千人因为这个节目而来到我们医院就诊。
阿青与这些病人相比,他留给我的印象更深。
阿青本来只是一个腰椎间突出症的患者,在北京某医院做了手术,手术本身也很成功,没想到的是术后发生感染。伤口长久不愈,反复做了5次手术,时间长达3年,期间伤口疼痛难忍,医生给他开了泰勒宁镇痛。泰勒宁,通用名叫“氨酚羟考酮”,常用于普外科和肿瘤科,适用于术后痛、创伤痛、烧伤痛、关节痛、神经痛、头痛,缓解由扭挫伤、骨折、椎骨间盘移位等各种愿意引起的中度和中度急慢性疼痛,特别是手术后疼痛,癌痛等。主要成分是羟考酮,这是一种与吗啡作用类似的半合成的麻醉类镇痛药,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镇痛药。据国际麻管局的报道,美国处方药滥用成瘾问题很严重,而羟考酮是滥用最常见的一种处方药,而我们国家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再说阿青,3年后他的手术伤口的问题终于解决,但是他却对泰勒宁上瘾了,而且服用的剂量越来越大,最后达每天50多片。他非常痛苦,因为上瘾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脾气暴躁、不愿意与人交流,人也变得自卑起来,婚姻也出现了危机。他只能求助于医生,但原来做手术的医院的医生面对这么棘手的情况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北京一些医院的戒毒科或戒毒所,但是他们普遍的是给他服用美沙酮,美沙酮也是一种麻醉性镇痛药,换汤不换药,结果出院后因为无法忍受美沙酮的戒断症状,最终还是重新吃回泰勒宁。绝望之下,他的朋友在网上查到了我们这里,看完央视走近科学对我的采访“被药物控制的人”之后,热泪盈眶,他后来告诉我,因为他看到了希望,他知道我能够救他。于是,在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后,在朋友的陪伴下,他飞到了广州。
由于提前已经电话联系过,而且又是半个老乡(俺是北京人的女婿),加上阿青的性格本来是很开朗的,见面时我们禁不住拥抱了一下。与阿青当面交流过后,阿青安心地住了下来,开始接受系统地治疗。由于他服用的泰勒宁剂量太大,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按照常规,先用替代疗法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我们不用美沙酮(实际上,我们科室连美沙酮这个药都没有,这样我就强迫临床医生提高治疗的技术)。时间过得很快,大约10天后,阿青的戒断症状已经比较轻了。一天,阿青提出在全麻排毒前要出去一下,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是他的心瘾现在很大,试图出去服用人生最后一次泰勒宁,我遇到过不少这样心态的患者,所以,我断然拒绝,但是安慰了他一下,也告诉他我们的规定:在排毒后3天之前都不能外出。阿青显得很无奈,失望之余我感觉到他有一丝的如释重负的感觉。也许良知已经发挥作用,我们帮助他战胜了他的冲动。
UROD(全麻下超快速脱毒)当天,阿青显得既紧张有兴奋,查房的时候,他的心理医生向我汇报说,阿青的心态调整地还不错,现在已经能够接纳自己,自信心强多了,但是面临婚姻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干预,由于他的妈妈没有来,需要电话与他妈妈交流一下。UROD进行地非常顺利,结束后从UROD室出来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意识还不太清楚,但是阿青显得很安静,没有出现烦躁。大约1小时后,阿青已经很清醒,并下地走路了,他显得有些疲惫,但是可以看出来心情很轻松。
阿青的身体恢复地很快,排毒后第二天查房的时候,他自述这是3年多来第一次感到这么轻松,身心轻松。他看我的眼神,有感激,有激动,还有喜悦。我也通过电话与他的母亲交流了一下,让她真正了解这个病,了解阿青的心理状态,对我们的治疗也给予了解释,也希望阿青在回到家以后,能够得到她的更多支持,并把出院后的问题向她交代了一番。可以感觉得到,阿青的妈妈很开心,看到儿子的康复终于有眉目了,开心是很自然的反应。
阿青的心理治疗进展地很顺利。一个周五的下午,按常规是我带领患者和家属做团体的时间,在分享的环节,阿青提出来他写了一首歌送给我,并在音乐的伴奏下开始吟唱。原来他按照歌曲《纪念白求恩》的的节奏配了歌词,以此来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
“有一个山东人他不远千里来到广州,把戒毒病人的戒毒治疗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不远千里,你带着戒毒的希望。何式脱瘾法你拯救心灵的创伤。兢兢业业,你拯救了许多病人,永永远远您在我们心上。神医何日辉,全麻下超快速脱毒,神奇快速去除心瘾!”
阿青的歌声虽然并不是很动听,但是这是他的心声,唱完之后,全体人员禁不住热烈鼓掌。反而是我有些不自然了。我表达了对阿青的感谢,同时也谈了我的看法。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白求恩式的人物,因为我觉得我的付出还达不到他的程度,我也不认为自己是神医,虽然许多患者和家属对我心存感激,尤其是他们有在外面就诊不断遇到打击的经历时更是如此。我只是觉得自己特别理解这些患者和家属,特别理解他们的痛苦、无奈,甚至绝望。也了解他们内心深处对幸福的渴望。我只是利用我多学科的知识,进行整合,并以一颗真诚地心、大爱之心面对他们,并带领出一个团队共同为他们服务,终结他们的家庭痛苦,让爱在家庭中重新有秩序地流动起来,从而让他们能够真正感受到爱、亲情,感受到幸福。
几天后,阿青出院时间还没用到,但因为要解决婚姻方面的问题,他必须要回家。阿青临走之前,将这首歌曲“神医何日辉”让人做成一块匾,并做了一副锦旗送给我们,我也很感动,不是因为什么神医的称号,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流动的是真情和爱。
阿青出院了,我们按照常规为其举办了“毕业”仪式,阿青很感性,面对相伴多日的病友和我们医务人员,眼睛都湿润了。我们用力地拥抱了一下,他很坚定地看着我,表达着对我的感激之情,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兄弟,好样的,等我到北京的时候去找你!”。阿青离开了医院,他的背影看上去是那么地坚定和有力量。
我期待着到北京与他的见面,那个时候,他不再是患者,我也不再是神医,我们是兄弟,是这一生有缘分相识相知的两个灵魂,我期待着这样的相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