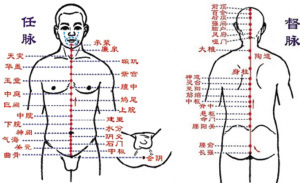故乡老屋的院子很大。五道窑洞的宽度,东西又没有盖下房。三间南窑塌毁后形成了一个高出院子二尺多的“圪塌”(朔方土语:高出平地的土台子)。出堂间的门,留两条仅容一人行走的路,一条通往西南的茅厕,一条通往东南的大门。除此,大院子的土地都物尽其用,栽种和点种着各种菜蔬或作物,郁郁葱葱,满院滴翠。沿着那两条路,用干沙棘扎起了围墙,那沙棘刺叫“圪针”(朔方土语:沙棘枝条上生长的一种刺),扎人的手上生疼生疼。鸡飞不过去,人到不了近前。沿圪针围墙的里边点种了一溜葵花。盛夏的时候,我每每放学归来走在院里的小路上,怒放的葵花含笑点头,硕大的叶片迎面招展,恰似两排战士在夹道欢迎凯旋归来的将军。
南墙下面那个圪塌子上,是我父亲的“口粮地”,年年栽种着一片小兰花。
小兰花是什么东东?它可不是供人观赏的花卉,而是我父亲一年的“口粮”。小兰花是一种旱烟叶,用它制作的烟叫旱烟,旱烟是用烟锅子抽的,我父亲把自己的烟锅子叫做小锅,这是相对于灶上的大锅而言的。我父亲常说,大锅断一两顿能“圪迁”(朔方土语:意为凑合),小锅那是一顿也不能断的。所以,小兰花是他的口粮,南圪塌就是他的口粮地。
为什么把这种旱烟叶叫做小兰花?在我们这里栽培了多久?我是一概不知的。我只是从记事起,就知道了院子里南圪塌上长着的这种有着翠绿的叶片,淡黄的小花朵,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怪味的植物叫小兰花。蜂不盯,虫不咬,鸡不啄,就连羊偶尔进去,也只是轧踩糟蹋,别说吃,闻都不闻一下。
小兰花的籽粒非常的小,小到捏在指间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清明刚过,父亲便在窗前垒就的炕大一片花池里,浇水施肥松土,而后撒播小兰花的籽粒。当然必须空出一片地方,撒播母亲交给他的茴子白籽种,小锅大锅兼顾嘛。过三天五日,籽粒发芽开始顶破土皮。哪一方是小兰花,哪一方是茴子白,这时是分不清的。待秧苗撒开三五片叶子,茴子白的小苗叶子圆而灰绿,小兰花的叶子长而翠绿。再长到一扎高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茴子白是栽到当院最肥沃的土里,而且每一苗的下面都施了黑油油的肥料,行距株距都是一尺五;小兰花照例被移栽到比较贫瘠的南圪塌上,洒些许草木料炭灰,权当肥料,而且栽的东倒西歪密密麻麻。
茴子白的小苗娇贵的很,几乎天天要浇水。而小兰花的小苗倒过秧后,就再也不需要浇水了,要么怎么叫旱烟呢?春天,太阳和风沙的密切合作,往往能使十年九旱的雁北大地赤地千里,而此时的小兰花匍匐在干瘪的土皮上,任凭阳光的烤灼和风沙的吹打,它的叶片的顶端始终保持着一抹翠绿,似乎不相信能有不下雨的老天爷。它的顽强与坚守,终于以老天爷低头为止。当它接受过一场透雨的洗礼后,就会相拥着拔地而起,一夜之间,院子里的南圪塌上满目滴翠。
当满院的蝴蝶飞舞盘旋,准备着在刚刚包住菜心的茴子白上繁衍后代的时候,已经半人高的小兰花,从枝桠上抽出了花蕾,花蕾渐渐地绽开,开出了一朵朵指甲盖大小的小黄花。小黄花呈喇叭状,单薄的有些可怜,而且没有花香,倒是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蝴蝶们不屑一顾,只有茅厕石头缝里生存着的一种叫做臭蜜蜂的昆虫,煽动着薄薄的翅膀,嗡嗡嗡地频频光顾这些采花季节本不该落魄的黄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上帝的造物就是这样地公平,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
转眼间秋霜凝露,田野大地的农作物籽粒饱叶片儿泛黄。此时的小兰花却在一场场的连绵秋雨中,杆壮叶肥,长势愈发蓬勃。已经落蕾的花骨朵后面,是一粒粒指头肚大小的果实,有的已经成熟,针尖大的细小籽粒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到了地里。而枝桠中又不断抽出新的花蕾,新花蕾又不断绽出新的小黄花,新黄花的后面又不断结出串串果实。
然而秋日的霜冻还是如期而至,尽管小兰花朴壮无比,但最怕的是霜冻,一旦受了冻,小兰花就毫无价值,用来烧火都没有火焰。父亲对霜期到来的估计那是绝对的有把握,往往赶在霜冻来的头天半下午或者傍晚,父亲便挥镰收割他的小兰花,忙不过来时就喊上我帮忙。小兰花枝干粗壮,挨着地皮的那一段有些木化,非常的坚韧。父亲再三的告我要割到地皮,茬子不能高了,我明白割的茬低了就等于撂了他的口粮,所以就挥起镰刀搽住地皮一株一株地砍。这一砍,又把上面的果实震裂了,细碎的黑色的籽粒撒了一地,父亲就又喊轻点轻点,你把兰花籽都抖落了,旱烟抽起来还能香吗?
初割倒的小兰花水分很大,但又不能直接对着太阳晾晒,那样会严重影响旱烟的质量。要将小兰花架起来,放到背阴通风的地方慢慢地荫干。地里收拾罢,场户关了门,小兰花苗也干透了。这时将它从架子上取下来,摘下叶子,摘取果核,叶子揉碎,果核碾开,又是筛又是簸,黑油油的兰花籽煞是好看。
小兰花苗全身除了根茎,它的叶子、干枝、种子,全部加入到了旱烟的成分中,而且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雁北小兰花旱烟独特的香味。这是与卷烟的最大区别,卷烟是加工烟叶使其成为烟丝,进而加入香料成为卷烟。故乡人将卷烟叫做“洋旱烟”。而小兰花旱烟不能光用叶子,一是不容易点着,二是点着后烟灰容易暴起,禁不住吸;而光有兰花秆子的旱烟过于辛辣,不太适口。
我父亲对小兰花旱烟的加工炮制,那可真是手法独到。先把兰花秆子用铡刀切成寸段,然后铺在炕头上进一步使其水分充分蒸发,一直干到用手一扳吧的一声脆响为止。这时就上碾子上去压碎,碎粒是用麻箩子筛下去的,越到最后越难压碎,一直碾压到麻箩筛子里只剩了半升一格,碾子上是实在再压不碎了,然后再放在石臼里继续捣碎。兰花籽上锅炒一下,也是放在石臼里捣碎,捣的油津油津的。这时找一个大笸箩,将粉碎的兰花秆、揉碎的兰花叶和捣成油泥的兰花籽一起搅拌,充分和匀。然后倒入一口大瓮里按实,这就是父亲一年的小锅口粮。
由于捣碎的兰花籽泥起到了粘合作用,父亲做的兰花旱烟好装好吸烟蓬也大。饭罢一锅烟,赛似活神仙。父亲一尺多长的烟锅子连同那个羊皮缝制的烟袋,整日里戴在腰间。黄铜做就的烟锅子黄灿灿,六道木磨成的烟杆子绵溜溜,玉石打磨的烟嘴子光玉玉。这套作杖,配上父亲亲自栽种炮制的小兰花旱烟,在田间地头,在街口道边,那是非常有面子的。街坊邻居,表叔大伯,不时有人上门向父亲讨要小兰花,父亲虽来者不拒,但每次都不多给。父亲平生最讨厌最看不起的,就是动不动就向别人讨要烟抽的人。在他看来,这是最没出息的事情。然而我后来才渐渐明白,父亲的认识和理解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是后话。
自小耳濡目染,我十四五岁时就学会了抽烟。旱烟水烟卷烟都抽过,算是水旱朝阳,全本武艺。我工作以后每次回去就给父亲买包烟,或者丢下钱让父亲自己去买。我总觉得应该让他抽抽洋旱烟,尤其是刚刚时兴起带过滤嘴的那几年,叼一只带把子的烟卷站在我故乡的桥头上,对一个庄户人来说那是何等的耀武扬威!但我的父亲或是抽惯了自己的小兰花,或是舍不得抽留着将来招待上门的贵客,总是一如既往地抽他喜爱的小兰花旱烟。而我每次回家,却总喜欢坐在炕头上用父亲的铜烟锅抽袋小兰花,那辛辣而充满温馨的烟味,那既苦涩又甜蜜的感受,是任何高级香烟都抽不出来的。尽管我后来戒了烟,什么豪华的烟都是一个味——呛人,但只有小兰花旱烟的香味让我陶醉,让我梦回萦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