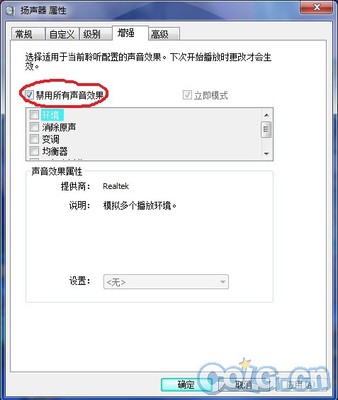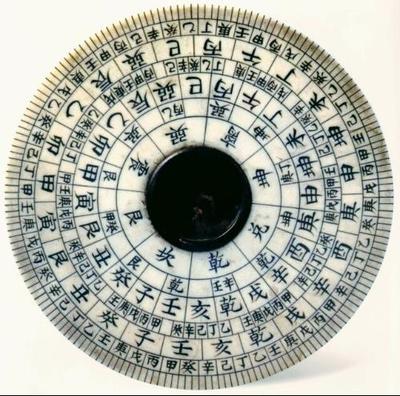禅思想的特征
“禅”原为古印度各宗教共同遵循的使心念安定的修行实践,佛教也把它作为重要的修行方法。它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或“思维修”,意指住心一境而冥想佛理。随着印度佛教传入,禅法经典也传译到中国,后汉安世高为禅教学的创始者,他所译禅法多属小乘禅法,后有后汉支娄迦谶、姚秦鸠摩罗什等译出大乘禅法。印度禅法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逐步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以“禅”思想及其修行方法为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宗派——禅宗。对于禅法思想的类别,宗密禅师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有概说:
……故三乘学人,欲求圣道,必须修禅,离此无门,离此无路……又真性则不垢不净,凡圣无差,禅则有浅有深,阶级殊等。谓带异计,欣上厌下而修者,是外道禅;正信因果,亦以欣厌而修者,是凡夫禅;悟我空法有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辗转相传者,是此禅也。④
禅为三乘学人的共法,然由于见地不一,形成不同的禅类。外道禅因执有异于佛教的计着(一般有常、断二义),且上下两隔,一心就此分裂;而凡夫禅虽不异计,而正信因果,修善断恶,然有欣悦上界厌恶下界的二相分别,上求人天善果,下厌三途恶趣,没有超出三界之外;小乘禅虽悟人我空,然对真俗二者犹有取舍;唯有达摩门下所传,是直指心源,认为众生自心本来清净,具备如来种种智能德相,众生如能念念于此自心相应,无有取舍,则能当下成就,顿同佛体,这种禅法才是禅宗所传真义,宗密定义其为如来清净禅或最上乘禅。禅宗虽在其后因宗风不同而形成不同派别,然总体看来,还是有共同特征的,大致可分三种:
一是将清净佛性置于众生的心性中,且称之为“真心”、“自性”、“自心”。这可看作是将佛之果位的涅槃境界提到因位来作修行,以佛的境界作为修境,念念与真心相应。由于自心即佛性,则佛性之德,清净无染,无有烦恼及无漏智能,在众生自心中本来具足,因此修行成佛只要体认自心,离开自心外无别佛,强调自性自度。这种即心即佛观点是禅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其他两个特征可据此而来,因为即心即佛,禅者在修行时只要直入自身心源,当下即是,这为简易的顿悟方法的提出铺垫了理论基础。且佛与众生在体性上无二差别,这在逻辑上缩短了众生与佛之间的距离,通过运用般若之智的不执空有的修行方便,便可从理路上自然推衍出无修无证的纯任自然的修行作风,以及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等诸法无二的圆融境界的观点。
二是在修行方法上,禅宗认为虽然众生心性本净,但凡夫为无明所蔽,不识自心清净本性,只有通过善知识的开示,反观自心,彻见本性,才能成佛。见性是禅宗修行方法的关键,也是凡圣之分界。禅宗内部在有关见性的方法上有南北之分:一是北宗提倡的渐修顿悟之法。它认为,禅者在顿悟见性之前,须经“凝住壁观”、“守本净心”、“拂尘看净”等的渐修功夫。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将北宗归到“息妄修心宗”之内,并将此禅法归纳为:
息妄修心宗者,说众生本有佛性,而无始无明,覆之不见,故轮回生死。诸佛已断妄想,故见性了了,出离生死,神通自在。当知凡圣功用不同,外境内心,各有分限。故须依师言教,背境观心,息灭妄念。念尽即觉悟,无所不知。如镜昏尘,须勤勤拂拭,尘尽明现,即无所不照。又须明解趣入禅境方便,远离愦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跏趺宴默,舌拄上颚,心住一境。⑤
此宗认为,众生虽本有佛性,但由于无明的障覆,则人佛两隔,凡圣二者功用不同。因此,在顿通佛体之前,需要渐修的功夫,“依师言教,背境观心,息灭妄念”、“勤勤拂拭”、“明解趣入禅境方便,远离愦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跏趺宴默,舌拄上颚,心住一境”等语,皆是顿悟前之渐修。而对见性的一刹那,北宗也是提倡顿悟的,如北宗作品《大乘无生方便门》说:“诸佛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净心,顿超佛地。”⑥但其关注点在渐修方便上,由此而定为渐修顿悟者。南宗的顿悟方法上又有两个分支:顿悟渐修和顿悟顿修。顿悟渐修以神会禅师为代表,他反对通过北宗渐次修行以达顿悟,认为顿悟见性是不立阶级的,但在顿悟以后,还须渐修。《南宗定是非论》云:
此为顿渐不同,所以不许。我六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渐阶。夫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不离是生而得解脱。譬如其母,顿生其子,与乳渐养育,去子智能,自然渐渐增长。顿悟见佛性者,亦复如是。⑦
这里批判了北宗的渐教禅法,认为见性之时是须“顿见”、“直了”、“不言渐阶”,但顿悟之后必须渐修,使顿见的佛性得以保任和长养,以求在此生中达到解脱。顿悟顿修的主张以马祖创立洪州宗以来的南宗禅为代表。宗密把此类禅法概括为“触类是道而任心”。《圆觉经大疏钞》卷3云:
起心动念,弹指、磬咳、扬眉。因所作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全体贪嗔痴,造善造恶,受苦乐,故一一皆性……或有佛刹、扬眉、动睛、笑欠、磬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故云触类是道也。
言任心者,彼息业养神之行门也,谓不起心造恶修善,亦不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也是心,不可以心断心。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名为解脱人,亦名过量人。无法可拘,无佛可作。何以故?心性之外,无一法可得。故云但任心即为修也。⑧
“触类是道”即指“即心即佛”。强调一切生活日用、善法恶法、行为动作皆是佛性的显现和作用,都是道心,无须另外求道,一切现成无须更修,由此只有“任心自在”才合于道,体悟此义,即是顿悟也是顿修,当下即是。任心的结果也造成以后禅宗的无修无整、自然任运的禅风。此一禅法对以后的禅宗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后期的禅法虽然接引手法不一,但其理路与此是一致的。
三是体现在终极境界上。禅宗的终极境界是明心见性,即清净无垢的真如本性呈露于心,此时禅者住于三昧,不见诸法有二,得到自在解脱,于一切法无有系缚,并于三昧起用,顺应世间,摄化众生,圆融无碍,达到圆满佛界。
以这三个特征为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在藏传佛教中也体现出如此的禅法特征,本文姑且称之为禅思想。但在藏地它不是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宗派形象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思想内容渗入到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教理、口诀和修法中。藏传佛教的教修可分为四大部分:事部瑜伽、行部瑜伽、瑜伽和无上瑜伽。藏传佛教的禅思想主要存在于无上瑜伽的教法中。以下从各派分别来分析藏传佛教的禅思想。
宁玛派的禅思想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其特殊的教法为大圆满法(属无上瑜伽部)。大圆满的含义为:
此法说现前无有染者之觉性、明空赤露,为大圆满。若释其字义,说现有世界,生死涅槃,所包含的一切诸法,悉在此觉性空寂之内,圆满无缺,故名圆满,再无较此更胜的解脱生死方便,故名为大。⑨
从中可以看出大圆满法的佛性说,这里称佛性为大圆满,它是没有染污的、清净的觉性,具足净、明、空三性,即指它的体、相、用三方面。宁玛派通常用三句概之:“体本清净、自性顿成、大悲周遍”。⑩体本清净是大圆满的体性,是本来清净,无生空寂的;自性顿成是相,是指空性中呈现的不灭的妙光;大悲周遍是用,指此空性能起妙用,现出种种染净之法,也即万法归于此觉性空寂之内。从中可以看出,大圆满是以空性统摄性相用三性,所以三性又分别体现出三种无别:“觉空无别”、“明空无别”、“现空无别”。[11]与内地禅宗的佛性论相比较,宁玛派佛性论也从觉性的角度来论述,认为它本来清净,无有染著,又具足万法,能现妙用。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内地禅宗很少说到佛性的明相,而宁玛派则强调了此清净明光,这也是内地佛教藏传佛教禅思想的一个主要区别。宁玛派有时又称佛性为“自然智慧”。“自然”是本有之义,指其有不假造作性,这与内地禅宗的义趣是一致的,禅宗常常以“自然天真佛”来称道佛性,也是强调它的不假造作、自然现成之义。同禅宗一样,宁玛派把佛性归结在众生自心中,说“随现何境,唯是自心,自心的心性是自然智慧,除此自然智慧外,再无余法”。[12]既然众生心性本是佛性,且万法之境也是自心所现,则修行时只要直入自身心源,即可见性成佛,这与禅宗的凡圣皆一、不假外求的即心即佛的观点相似。从此观点出发,宁玛派也主张顿悟成佛,并在此基础上提倡无修无证、宽坦任运的纯任自然的修行风格。在染与净的关系问题上,宁玛派认为,二者在相上虽不同,但在体性上是无别的,都是自心之用:
关于妄心与觉心的差别,说心是随无明之力,起种种杂念,这个客尘的分别,则名为心。不随无明之力所染,远离二取戏论,照此明空而又无可得的空寂者,名为觉性。又说心的形相,现有的部分就是轮回,心的体性,空寂的部分就是涅槃……在自心的本性空寂之中,是无分别的。[13]
众生与佛、觉心与妄心的区别只在一念之间,一念追随无明则为凡夫,一念不随无明则是佛,关键在于众生是否能够在一念中顿悟这个佛性。它与后期南宗的修法较为相近,也是强调求悟者从“用”上着手,即从现前的一念当中认识自心的实相。因为佛性的德行在众生自心中本具,则道不属修,在修行上主张无修之顿修。宁玛派教法中说,归总起来这个当下无有污垢、明空无执的自己觉性,让它宽坦任运,任它妄念境相起伏变化,都不去辨别好恶,不作破立,只保任此觉空赤露,这就是大圆满修习的心要。[14]另外,宁玛派提出有顿渐之别,渐悟是指有修行次第,不能当下觉知此明空觉性。而顿悟者则无需阶次,只要一语便可当下体悟此明空觉性。宁玛派认为:
先要知境为心,知心为空,知空为无二双融。由此理断便通达一切诸法,唯是觉空赤露,此乃渐悟者所悟觉性的程度。若不由渐次观修,而仅依上师指点此觉性,则能通达外境所现皆为觉空赤露,此乃是顿悟者所悟觉性的程度[15]。
渐悟者须经“知境为心”、“知心为空”、“知空为无二双融”的先后次第,然后才能了知一切法皆是此觉空赤露。而顿悟者不需经过这些次第观修,只要一听上师的一语指示,当下就可明白并显了此觉空赤露。但顿悟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达到的,只有上上根人才能做到。《大圆胜慧》说:

上根利智无修无证,由此而住,自见而成者名为且切;上根利智具大精进,得见自心后,勤修猛进,随修现见自性三身,空五蕴而成光明之身者,则名为妥噶。[16]
且切与妥噶是大圆满要门部的修法。“且切”,意为力断,即顿断妄念而证光明;“妥噶”意为任运超越。且切与妥噶的修行者必须是上根利智之人,这与内地禅宗所说修行禅宗法门的根器必须是上上根人的说法一致。上根智者以无修之修顿见自心,名为且切,且切的修法与顿悟顿修的修法相同,由当前一念而修。妥噶则是顿悟自心后起修、勤修自性三身、光明之身等。
噶举派的禅思想
藏传佛教另一大教派噶举派的教法、口诀中也体现出明显的禅思想特色。噶举派分为许多小派,有“四大支”、“八小支”之说,所以在见解上不尽相同,此处只取与内地禅宗相似的思想来论述。在佛性论上,噶举派与宁玛派相同,都是指觉空之心。此觉空之心即是众生之自心,也即佛性。噶举派大手印名之为如来藏,宁玛派大圆满名之为大菩提心。此心也有体、相、用三者。岗波巴大师云:
心的体性是本元俱生,心的本相是境界俱生,心的妙用是分别俱生。[17]
体是本元,相是境界,用是现起的种种分别,心的体、相、用都是俱生,同是一体,没有分别,众生本性光明。然众生虽具情净本性,但因客尘所染,众生迷其本性,流于六道轮回之中。只要一念转悟,远离客尘,即可现证法性之身。噶举派教法中说:
心之体性自性清净,然由客尘所覆障,自己之实相由于自己未能明见,一切皆依烦恼之缘起而有六种苦乐,从而呈现为轮回之相。由远离客尘而明见自身之实相,由依靠清净之缘起而现证法性胜义之身,其之显现,则呈现为色身之庄严妙幻。[18]
凡圣差别关键在于心的依缘不同,如依烦恼之缘,则为凡,现轮回之相;若依清净之缘,与自性本性相应,则为圣,现庄严之相。可以看出,噶举派在佛性观点上也是主张即心即佛、体悟自心、自度自证的。众生与佛在本性上是相同的,若要达到对自性的直观体验,对心则要采取一个无念无作的自然态度,即不追求过去的识,不迎接未来的识,不造作现在的识,在此之中无为而住,对外界的一些现象反映到自己头脑中而生起的一些善恶之念都不作任何破立取舍,让它任意浮游,任凭思维活动自行消失,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就能认识到心性本性,顿悟而住,即见法性。噶举派说:
心中若现声色等一切境相,或起善不善诸美恶妄念,都不作任何取舍,即此体相上只住心凝观,它便自行泯灭,灭后迹相了不可得,惟成空寂,从而坦然安了而住,若得如是见地,即是悟入法性,见心本性。[19]
因为妄念本性即空,妄念不碍本性清净,所以由心中所现种种境相,不要起念去除,不作任何分别取舍,而是随起随观,由此了知妄念本性空寂,了不可得,得此见地,则可彻见本性。这种修法相似于南宗的从用入手、悟入自性的禅法。噶举派的特殊修法要门为大手印法,大手印分显密二种,属显教的称“实住大手印”,属密法者有“空乐大手印”和“光明大手印”两种。而光明大手印为顿悟心性之道大手印,一般要依上师加持而得见,依上师所授口诀修禅。大手印与禅宗之禅有颇多相似之处。大手印特别强调无分别止调心得见,它认为要证悟本元自心的方法有三要:不散乱,自然放下;不整治,任运松弛;不改变,自然清澄。此三要为远离戏论分别和一切法具法性的三解脱之门,此为顿门,即直指人心,立地解脱,见性成佛,不讲烦琐的教理,全在上师直指。[20]此三要的特点全在于自然任运:不散乱为定,修定之时不要强制一心,而随念自然,观念不实;对于妄念不假整治,随念任运;也不改变妄念,而让它念起念灭,而后自然澄清。这种禅定特色与传统的印度禅定差异颇大,而与内地禅宗更为接近一些。“直指人心”、“立地解脱”、“见性成佛”直接就是禅宗之语。这种无修无整、无念无住、不作分别之禅风在噶举派大师们的道歌、口诀中多有体现。如米拉日巴道歌中说:
为顺汝劣慧,佛说一切有。若于胜义中,无魔亦无佛,无能修所修,无所行地道,无所证身智,故亦无涅槃,皆名言假立,三界情非情,无身本非有,无体无俱生,无业无异熟,故无轮回名,究竟义如是。[21]
佛所说种种名相差别,皆是对钝根人安立的,而从究竟义上来说,一切没有名相分别,皆是超越次第、离诸戏论的,轮回即涅槃,这就和禅宗一样,以中观的不立一切、不执有无的见地来指导修行实践。岗波巴大师还提出平常心是道的观点:
什么是平常心,就是当前显而空,空而显,空显(明空)不二之心,不要去修改,不要去增加,毫无功用地凭内证智自己觉知。[22]
平常心即是在妄心中的真心,所显现者本性是空,由空中而显现一切法,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若要见性,则由此空显不二之心入手,不增不减,无功用行,只管觉照。有意思的是,南宗马祖禅师也提出了“平常心是道”的命题:
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23]
平常心与道二者是不二的,以起平常之心,即是本性,没有造作、是非、取舍、断常、凡圣的区别,生活日用、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等皆同于道。由于平常心与道无二,则修道 是只要直指人心,当下现成,无修无整,所以宗密评介马祖的禅法是“触类是道而任心”。从中可看出岗波巴大师与马祖禅师的“平常心是道”的命题,不仅字词相同,其义理是完全一致的,甚而,禅宗的“烦恼即菩提”的思想在噶举派中也有体现。噶举派认为,按密宗的修行次第修炼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切妄念无明都会成为法身智能,成为解脱之道,甚至还说有多少妄念就有多少法身,这与禅宗慧能所说一切妄念都是清净体上本智的表现,妄念能证得清净佛身的观点是相呼应的。另外,烦恼不仅不要灭除,它还可以作为修道之用。噶举派说:
转妄念谓道用,转烦恼为道 用,转疾病为道用,转鬼神为道用,转痛苦为道用,转死亡为道用。[24]
“妄念、烦恼、疾病、鬼神、痛苦、死亡”等本是传统佛教必须去除的无明和业报,但噶举派却把它们作为助道之用,可见,噶举派的“烦恼即菩提”的思想已经成为指导修持的主要见地,这可以说是噶举派的特色。
萨迦派的禅思想
萨迦派是藏传佛教的一大教派,它对禅思想也多有论述。萨迦派的特殊教法为“道果见”,它的佛性论与前二者一样,也是属如来藏系统。萨迦派认为:
直指本元俱生智。此智非泛指唯认识总相的自心及迷现之心,而是要认识在因位时的明空双运、远离迷乱之心。此于显密经论中,名曰清净心、如来藏、本性光明心、心金刚等。[25]
萨迦派的佛性称为“本元俱生智”,是指远离迷乱的因位清净之心,明和空是佛性的二分——相和体,“明乃心的性相”、“空乃心的自性”。[26]此佛性也在众生心中,从本以来就是人心的本质,它本身不存在生死和涅槃、清净和污染、无明与智慧的区别,但众生却要安立种种虚妄分别,因而不能彻见佛性。如能契会此本心,则可引生利益。萨迦派说:
自心所现迷乱的俱生之心,则为客尘轮回,是它的所净,也是它的自性。此与本心,无始以来即为助伴,从前未能认识之俱生智则为涅槃,此二从本性上不可分别,是为无别。如是故名因生死涅槃无别。若契会此远离能所二取的自心,平等住于明空双运之见,此则承认去名为道位生死涅槃无别。[27]
自心分二:一是无始以来的迷乱之心;一是无始以来的俱生智慧。然二者是没有分别的,迷乱之心无始以来就与自性相伴,它本身就是清净自性,未体会前二者的无别,称为因位生死涅槃无别;若契会自心无二,没有取舍,平等安住于明空双运,因此觉见,则称为道位生死涅槃无别。道果最高的见,就是轮回涅槃无别之见。此观点也与禅宗一样自心有真妄轮涅,两者是一体二用,悟即涅槃,不悟即轮回。要获得明空之见,则须顿悟。顿悟分二:
初觅的此心,指点此心为明空双运。次于明空双运中直指体认本元俱生智慧之心,乃观其义而为修习。[28]
修习虽分两个层次,然二者都是直指,实为顿悟。第一层次悟此心为明空双运,第二层次于明空双运中直指本元之心。明空虽为佛性之两分,但修法时应具备二者都不执着的见地,萨迦派有句名言叫做“是执则非见”,意思是说不管是有或无、生死或涅槃,凡有执着即不能彻见从本以来即存于心中的佛性。因为佛性从本以来即是无生,且心性的明空双运也是离绝言诠的,如用心识去思维佛性,则成虚妄分别,因此在修持心性的明空本性时要在毫无牵挂、无有用心、无所作为的氛围中宽松任运而住,才能达到无执的境界。这与内地禅思想中因诸法真理离有绝空,只要摄心不散,不起任何思虑,无分别住,就可以与佛性自然契合的说法是相一致的。萨迦派说:
中则放任,于所见上心放任宽松而住,则以一切执著由自然解脱之门而随持之,最后或安然而住,或仍其本分……此则一切法自然归于无实,生起顿悟一切法的奥义。[29]
此“中”指萨迦派显教见方面修持的“中破我执之见”之“中”。“破我执”的方法是宽松任运之法,因执著本来无实,则它自然而灭,从而顿悟一切法的究竟之义。最后“破一切见”的修法为:“既抉择诸法无实后,即心念无实的执相部分,亦属应断。”[30]意即心中不存在任何念头,连“空无实有”之念也不应有。这即是禅思想的全无所许、无念无住的观点。它所说的“中”、“后”两悟,也同于禅宗的“小悟”、“大悟”。
藏传佛教禅思想与内地禅宗思想的区别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中也有禅思想,它和内地禅思想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为,佛性存在于人心,并强调自性自度的佛性论;在修法上,有主张渐修顿悟的禅风,有强调无修无整、毫不作意的自然禅风;有强调直指人心,彻见本元的顿悟方法;有强调圆融无碍、自在解脱的法身境界等。但藏传佛教的禅思想与内地禅思想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是表现在对身心的看法上。内地禅宗为消解对身体的执著,仅强调心性的修持,而视人身为“臭皮囊”,认为对人身的执著是影响心性得到证悟的障碍。藏传佛教则强调身心并重,除了修心性的空分外,还必须修身的明分。同时认为人身难得,它是渡向彼岸的船只,在到达彼岸之前不应丢弃,认为身心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所以藏传佛教非常强调对气、脉、明点的修持,主张身心修持不能偏废。二是两者偏重的禅思想类别不同。内地禅宗有如来禅与祖师禅两种,而不立文字、祖祖相传的祖师禅在后期日益得到重视,它侧重师徒间的以心传心,强调宗门的宗风。且以祖师禅为了义禅,如来禅为未了义禅。藏传佛教也特别强调师徒间的口耳传承,重视上师指引,但它的禅思想在风格上更偏重于如来禅,强调依据佛祖所传经教来修习佛法,且重视悟前的加行。特别在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的主要派别之后,藏传佛教便趋向于强调修行次第,以佛说经典作为修行的依据,更接近于内地禅宗的籍教悟宗的渐修顿悟的方法。三是两者对禅思想在整个佛教体系的地位看法不一。内地禅宗认为不立阶级、直入心源、任运自然的禅修法为最高的修行方法,且以它摄受其他的法门。它能即生成佛,当下直悟,瞬间彻见心性本源,获得法身成就。它是个独立而完整的体系,并以独立的宗派形式出现。藏传佛教则认为金刚乘(密乘)是最殊胜的法门,它高于小乘和大乘佛教,对心性修持的顿悟虽是金刚乘的内容,但不是最高的境界,只有外加金刚乘的修身方法,才可即身成就,一生可完成法、报、化三身。所以禅思想仅是无上瑜伽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体系,没有独立的宗派来承载它。而且它只能成就法身(即对空性的证悟),不能成就报、化两身,只有通过密乘气、脉、明点的修持(即证其明分),才能完成三身成就,四是两者的终极境界不同。内地禅宗认为彻见本源、获得法身为最高境界,只要法身成就了,则化身与报身自然成就。而藏传佛教认为,最高境界除获得法身外,报身、化身也很重要,且化身、报身有专门的修法。所以,藏传佛教认为只有成就了“三身四智”[31]才是圆满境界,而禅宗语录中对三身四智则很少论及。
一、所谓密教
密教即秘密佛教,英文EsotericBuddhism,是显教(ExotericBuddhism)的对应语。这一称呼是近代学者所创,但古梵语中似乎未见与它相对应的术语。密教又称“怛特罗佛教”(Tantricuddhism, BuddhismTantras),在密教中“怛特罗”,即“经典”,之意。在密教发展的后期,其经典确实被称作“怛特罗”,但在初期未必如此。
印度佛教自其创立者释迦牟尼时代起至13世纪初因伊斯兰教徒的侵略而灭亡,其间存在的时间超过1600年。最初的500年是从所谓的原始佛教至部派佛教的发展时期。到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密教以大乘佛教为母体孕育而生。
关于秘密佛教的“秘密”之意有两种解释:一、佛教或称显教是在所有求教者中传布的宗教,密教则只传授给通过灌顶仪式的人,因此被称为“秘密教义”。二、显教是佛祖释迦针对众生的能力临机应变所作的说法,而密教则是对语言无法表达的佛祖的觉悟所作的阐释,超越了凡人的理解,故称。
密教的最初形态于5、6世纪出现,直到13世纪佛教在印度灭亡。在印度佛教诞生发展的千余年时间里,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密教的时代。密教阐述的是语言不可表述的真理。因此,它的象征体系得到高度的发展,有代表性的如“印”、“真言”、“曼荼罗”,等,这些形式是在印度佛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二、西藏初期佛教中的密教要素
在考察西藏的初期佛教,亦即《布顿佛教史》中提到的前弘期的佛教,特别是考察密教的传播与发展的情况时会面临几个棘手的问题。第一,在佛教最初传入西藏的7、8世纪左右,正是吐蕃王朝的隆盛期。关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史料中没有详细的记录,这种情况也普遍见于其他的文化圈。第二,必须注意的是在佛教中密教首先重视的是个人的宗教体验,它同历史中代表多数派利益的从政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从政者的基本原则是尽一切努力去维持将自己置于最高位置的某一体制,而佛教中的密教则首先顾及修行者自身圣俗一致体验的获得,更极端一点说,纵使修行者的行为有悖于通常的道德准则,但在其内面若能通过全身心的体验而与圣者合而为一的话,这种实感的获得亦被视为重要的过程。但是,作为某一社会环境之中受某种制度制约的宗教,在强调个人的宗教体验的同时,又必须服从社会的安定和秩序的要求。宗教可以发挥某些推动的作用,以巫术的方式祈愿使当政者按自己的意图去控制国家,无论它以息灾的修法将灾害与疾病等社会的或个人的负面因素消减殆尽,或者以增益的修法激发丰盛与繁荣的正面因素,都必须与当政者的统治意图一致。但是一味的将政治对手的力量与运势消减,或者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诸如咒杀等,对意欲维持现状的从政者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
因此,作为与在家信者交流甚密、如实反映民众愿望的密教来说,后来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抑制。但在此之前的阶段,密教受政治权力压制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西藏,初期的佛教极为重视护政色彩较强的内容,而对个人的神秘体验和行善积德等方面的东西不甚关心,而且,像瑜伽部那样不与政局合作的态度是当政者所不喜欢的。因此,对史料中有意识忽略的事实也应予以充分的考虑。第三,关于密教史上的8、9世纪这一特殊的时代。密教学现阶段的定论认为,7世纪前后,《大日经》、《金刚顶经》等以三密行为基本特征的系统的密教经典告以完成,在此基础上具有浓厚的印度色彩的后期密教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在佛教史发展进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这一时期与西藏佛教的前弘期至后弘期的推进时间基本平行。所以,这一时期的密教即使在印度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发展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前弘期的密教最终形成的是宁玛派体系,宁玛派密教的教理最根本的理论直接来源于8、9世纪印度及西藏的密教,同时也带有伏藏、新译密教及无上瑜伽密教的影响痕迹。
佛教传入西藏的最初阶段,即摇篮期确实可信的史料极端医乏,在后世的论述中有许多属于神话式构想的成分。所以,试图从这些资料中抽取出可信度较高的有关密教发展的内容,并对此再作整理的想法决非易事。例如,在《布顿佛教史》等著作中关于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的记述中,尤其是墀尊公主奉不动金刚身、弥勒法轮像、多罗像等佛像入藏一事,在此之前还有南印度的十一面观音像传入西藏,这些说法显而易见的背景就是松赞干布乃观音菩萨化身的主题。毫无疑问它属于西藏佛教确立以后的传承,在此出现的主尊是后期大乘佛教过渡到初期密教的过程中受到重视的阿门如来、多罗佛母以及被视为变化观音之滥觞的十一面观音像。这些记载即使带有很浓的神话色彩,但在时间划分方面并非全无根据。
以上是西藏密教研究中面临的难题,此外,论及西藏密教的发展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几位重要的人物,诸如莲花生、毗玛那弥遮、毗卢遮那等,他们与密教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莲花生 西藏的初期密教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虽是古宁玛派的创始者,却赢得了密教各派的尊敬,被称为“古鲁仁布钦”。头戴独特袋状的帽子,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骷髅杯,胁挎骷髅杖的容姿明显是一副印度成就者的姿态,它见于唐卡、木版画、壁画、金铜佛像等艺术形式中。在众多神话色彩浓厚的传说中,莲花生的真实面貌确实变得模糊不清,后人只能在历史资料中寻找到一些有关莲花生身世的情况。
吐蕃的赤松德赞王皈依佛教,从印度那烂陀寺院招请了学识渊博、享誉甚高的寂护向他学习佛法。但是,逢时运不佳,天灾四起,寂护受到苯教的抵制,不得不退避尼泊尔。此后,吐蕃境内的形势逐渐稳定,为弘扬佛法寂护再度入藏。他吸取了前回入藏的经验,若使佛教体系得以确立,除了基本的教理体系外还需要咒术之类的权宜之计。因此,寂护邀请了当时印度著名的密教行者莲花生。
莲花生出生于印度东部的乌仗那,在密教修行方面成就甚高,在寂护的协助下他建立了桑耶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关于他的传说中还提到了他身边的几位明妃。莲花生精通性瑜伽,所以很有可能是把她们作为印母而与之接触的。另外,他最直接修炼的是金刚橛法,即使今天金刚橛法在宁玛派的修炼实践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布顿佛教史》还记载了莲花生在桑耶寺主持《恶趣清净怛特罗》修法的情况。《恶趣清净怛特罗》有旧译和新译两部,旧译作为“瑜伽怛特罗”收录在《布顿佛教史》中。
莲花生的密教传法包含相当可观的内容,诸如金刚橛所象征的杂密修法,《恶趣清净怛特罗》中呈列的为净化地狱等恶趣而作的仪式。这些在印度密教中也属于所作、行仪、瑜伽等低位或中位的经典内容。因此,可以说以莲花生为代表的初期密教的内容实际存在的可能性很高。从另一方面看,印母在性瑜伽中的必要存在也可从后世的传记与图象中得到证实。
无论怎样说,莲花生都堪称西藏密教史上的第一祖,他的存在超越了历史,并且具有深厚的象征意义。
毗玛那弥遮(无垢友) 据《布顿佛教史》记载,宁玛派的九乘密教分类的最高层为阿提瑜伽,这一层又分心部、界部和教诫部三部,其中心部由毗玛那弥遮及毗卢遮那创立,界部由毗卢遮那创立,教诫部由毗玛那弥遮创立。这一观点显示,九乘教判,特别是大究竟的体系成立前后,原先以独立形式活动的毗玛那弥遮和毗卢遮那组成了一个体系,这一变化对前弘期密教的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于二者的历史资料不明之处甚多,现在仅就所知的情况作一介绍。
据记载,赤松德赞除寂护和莲花生外还邀请了毗玛那弥遮、佛陀密、辛底嘎坝等人入藏,以求佛教的显密两方得以普及。毗玛那弥遮在赤松德赞殁后入藏,翻译了多部经纶。传说他是佛陀密的弟子,现存大藏经中的《金刚萨埵幻化网秘密一切显现怛特罗》、《一切如来佛顶白伞盖陀罗尼》等都是毗玛那弥遮的译作,其中,后两部陀罗尼可看作是后期陀罗尼的经典,它们有宋代和元代的汉译本。
在密教史上必须重视的经典莫过于《金刚萨埵幻化网秘密一切显现怛特罗》(《幻化网怛特罗》的旧译)。在新译密教中它为无上瑜伽部收藏,注疏部分由瑜伽部来分配使用,其内容包括大日如来中的五佛、佛眼、白衣等四明妃,《秘密集会怛特罗》中展示的尊格群,还有《秘密集会怛特罗》的先初形态,即所谓的菩提心偈,此外还包括宁玛派极为重视的十八部重要经典中的内容。
总括而论,毗玛那弥遮同《幻化网怛特罗》之间的关联包含着某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性意义。这些端绪连同当时既已形成的《秘密集会怛特罗》组成这一时期西藏密教发展的风貌。需要说明的是,毗玛那弥遮并未被吐蕃地区所接受,他壮志未酬便改道去了中原。
毗卢遮那 寂护曾赢得莫大的尊敬,被当时的人称为“菩萨”。在莲花生的协助下,仿照印度的欧丹达菩提寺(飞行寺)建成了桑耶寺。他从那烂陀寺招请了12名“说一切有部”的僧人,这列僧人之下有7名藏僧首次接受了出家受戒的仪式,他们被称为“七预人”,其中就有毗卢遮那。他在赤松德赞晚年时期留学印度,现存的大藏经中的《恐怖真言集金刚根本怛特罗》属他的译作,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怛特罗王吉祥秘密集会注释》,这是瓦吉拉哈萨为《秘密集会怛特罗》所作的注释,当然是旧译。仁钦桑布的新译经典问世以前,《秘密集会怛特罗》的一部分已经传到西藏。这部和宁玛派大瑜伽有着相应内容的著作与《幻化网怛特罗》一同构成前弘期佛教向后弘期佛教转变的重要环节。
赤松德赞时代由于密教受到压制,毗卢遮那曾被流放到四川阿坝一带,当地的佛教由他传播,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功绩,民间称他为“点燃东方明灯的人”。由此可见,在密教传入西藏的初期,密教的传播者们包括莲花生的晚年并非总是受到优待的。
《丹葛目录》 赤德松赞的治世确立以后,在吐蕃王室的保护下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获得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译经事业也得到相应的促进。与此同时,对翻译用语的统一化方面提出了要求,《翻译名义大集》借此编撰而成。关于编撰的宗旨在《二卷本译语释》中有述。在这本书的序文里作者指出,由于密教的圣典很容易被误解,所以,未经许可不能擅自翻译。对王室佛教来说,它的主旨是维护吐蕃政权的统一,而密教动辄无视伦理道德,批判惯行秩序,尤其是瑜伽级以上的怛特罗,无疑会被列为禁止的对象。但这一事实也从反面证明,当时西藏密教中已经渗入令人忧虑的成分。
《丹葛目录》于824年编撰成书,至今尚存,通过它很容易了解到当时的佛教原貌,从目录中也可看到昔日对密教施行压制政策的影响。当然,目录中的怛特罗名未必能代表当时密教的全貌,但反过来我们可将收录在目录中的圣典称为“被容许的密教圣典”。在《丹葛目录》的《真言怛特罗》部分中收有九种怛特罗,其中只有《恶趣清净怛特罗》属于后来怛特罗四分法中的瑜伽怛特罗,秘密瑜伽的成分很少,也就是说,目录对地狱等的恶趣净化的内容更为重视,在死者供养方面给予后世以极大影响。
除此以外的怛特罗基本上属于所作和行仪之类的怛特罗,其中还有《大日经》以及《大日经》的先行圣典《金刚手怛特罗》。通过这些经典可以了解当时吐蕃政权对密教的具体要求和宽限程度。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佛陀密对《大日经》、《恶趣清净怛特罗》及《上禅定品》三部怛特罗所作的注释。
在考蔡前弘期密教发展情况的时候,有一位人物非常值得注意,他其实并未去过西藏,但结果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就是佛陀密。这位8世纪后期的密教学僧不仅通晓所作、行仪及瑜伽等三部怛特罗,而且还写过多部有关这三部怛特罗的注释书,同时还摸索出了怛特罗二分法和三分法,给后世的密教分类法以诸多影响。此外《丹葛目录》也收录了佛陀密的三部注释著作。他还精通印度佛教唯识派的思想,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西藏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的所求与志向。
除以上经典外,《丹葛目录》还设立了《孔雀佛母陀罗尼》等“五护陀罗尼”及“大小杂陀罗尼”的题目,内容大部分属于陀罗尼经典,在三密行中重点放在了口密之上。
由此可见,《丹葛目录》是据吐蕃当政者的意志收录的密教经论,但其中也夹有《秘密集会怛特罗》的有力思想家佛陀鸠尼亚那帕达的著作,这一现象也不可忽视。
以上通过三位密教者及《丹葛目录》的情况,大致勾画出所谓前弘期密教的基本轮廓。正像文章开头处所提示的,试图呈现8、9世纪时西藏密教的全貌的做法并非容易之举。如果完全默认后世的传承,就有可能使西藏密教蒙受性瑜伽及咒杀之名。
三、新译密教的传入
赤松德赞及其弟弟的相继过世象征着吐蕃佛教的崩溃,届此西藏佛教在9世纪后半期以后的近百年时间里至少在历史的表层面上看不到任何显著的活动迹象。但据推测这其中咒术色彩较强的密教部派在无适当指导的情况下汇入民间礼仪,并在当地扎根,但从史料中寻找不到有关的情况。到了10世纪,随着政情开始稳定,在西藏周边地区出现了渴望佛教复兴的势头,为顺应这种要求,西藏与印度的二位密教者也开始在西藏传播密教,他们是仁钦桑布和弥底尊者。
仁钦桑布 毫无疑问,仁钦桑布在西藏佛教发展史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将从密教史的角度总结一下他的密教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当时西藏阿里地区的意希沃主张重盛佛教,他派遣了21名年轻的僧人出国学习,但由于疾病和事故,最后只有仁钦桑布和另外一人完成了使命,顺利返藏。仁钦桑布在克什米尔滞留了7年,受教于体拉达卡拉瓦鲁曼及卡玛拉古普塔,尤其是前者系印度后期佛教大家拉陀那卡拉香提的弟子,他著有后期佛教的概说著作《无上瑜伽怛特罗义入》,他的思想对仁钦桑布的影响很大。
仁钦桑布前后三次出国,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使命,为西部佛教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仁钦桑布返回阿里后即在普兰、古格及拉达克等地建成许多寺院。史料中有记载的寺名21座,若加上一些较小规模的寺院,据称共建有108座寺院,同时为安置寺内的佛像及设计内装,他曾再度前往克什米尔,6年后带回32名克什米尔艺人,组织完成了寺院的装缮工作。其次,仁钦桑布毕生致力于圣典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为后世奉为范本。西藏密教史将他之前所译的密教经典称作“旧密咒’,,而把他及其以后的译经称作“新密咒”。
由于他的卓越功绩,当时继任的阿里古格王拉德尊称他为“金刚阿黎”。他的翻译著作内容涉及经典、仪轨及经论等诸多领域。他的贡献在于系统地向西藏介绍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上瑜伽密教,这得意于他在瑜伽怛特罗方面的精湛的学识。晚年时拜阿底峡为师,译出诸多经论,其中以无上瑜伽怛特罗系统的密教仪轨为主。
仁钦桑布对密教经典的和诠释基于他对瑜伽怛特罗的独到理解,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他对瑜伽怛特罗的理解基于印度学者阿难陀嘉拔的论说。关于阿难陀嘉拔的生涯与思想至今没有定论,但根据布顿的看法,他应被列为与佛陀密齐名的学者。仁钦桑布在翻译了多部主要的瑜伽怛特罗的同时还翻译了阿难陀嘉拔对这些经典的注释书,例如,他翻译了瑜伽怛特罗的最核心的著作《真实摄怛特罗》(即《处会金刚顶经》),以及阿难陀嘉拔的力作《真实的灯明》。在这部注释书中他论及了原经典中未曾提到的大圆镜智等五智。他还翻译了《一切金刚出现》,这部著作是在综合了《真实摄怛特罗》及其注释书《金刚顶怛特罗》(即《第三会金刚顶经》)的基础上成书的。此外还有《理趣经》的一种《最胜本初怛特罗》,仁钦桑布在阿难陀嘉拔注释的基础上作了翻译。除上述译著外,还翻译了阿难陀嘉拔为《幻化网怛特罗》(它是从瑜伽怛特罗向无上瑜伽怛特罗过渡时的重要经典)所作的注释以及许多其他的瑜伽怛特罗。与旧译密教相比,仁钦桑布对阿难陀嘉拔的解释学尤为重视,也可以说这是他在教学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
仁钦桑布的瑜伽怛特罗观的第二个特点可以从他对《恶趣清净怛特罗》的评价中得出。这部经典的基础是《真实摄怛特罗》,同时也受到了《毗卢遮那现等觉》(《大日经》)的影响。从内容上看,它论及了地狱、饿鬼、畜生等恶趣净化的思想与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多在葬礼上诵读。在仁钦桑布翻译的许多无上瑜伽怛特罗及关联性的仪轨中还包括为噶举派所重视的《七部成就书》之一印德拉布提的《知惠成就》,但最具有意义的是他翻译介绍了密教的最高经典《秘密集会怛特罗》。后来围绕这部经典形成了两个流派:鸠尼亚那帕达流派和圣者父子流派。他对本经及两个流派的主要经论都作了介绍,其中包括关于圣者父子流派的基本文献生死次第的经论《要集成就法》,论及究竟次第的《五次第》,阿里亚德瓦的《行和集灯》以及《灯作明》等。他的译作促成了后世圣者流派的流行。此外他还翻译了鸠尼亚那帕达的《普贤成就法》。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仁钦桑布对《秘密集会怛特罗》抱着极大的关心。
弥底尊者 这一时期的密教史中仅次于仁钦桑布的人物是弥底尊者,但是他的运势不佳,未能像仁钦桑布那样为后世留下丰硕的成果,他的影响仅限于西藏东部的康区。
弥底尊者从印度出发,最初到达阿里,不幸的是陪同他的译师尼泊尔人白玛汝措因病死去。由于语言不通,他到处流浪,据说曾给人放过羊。后来有幸遇到甲色扎哇·索朗降称,被他邀请到麦隆地方说法。后来尊者设立了《俱舍论》的讲座,精通藏语后还翻译了《文殊明智法门》、《四天女请问怛特罗》、《四支成就法》等经典。在西藏佛教史上由他所传的怛特罗体系被称为“康派”。
弥底尊者的漂泊并非只是运气不佳所致,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西藏地方割据政权仍对密教的传入抱有慎重态度的缘故,即使对稍后入藏的密教大师阿底峡也采取了相当的限制。由于仁钦桑布及弥底尊者的努力,无上瑜伽部的密教才得以在西藏的许多地区传播,但普遍受容的时机尚未成熟。从另一方面看,二人在避开地方政权的控制后翻译出大量密教经典,成为后来以阿底峡和玛尔巴为代表的宗派密教形成的远因,也促使西藏佛教走上显密结合的发展道路。
四、阿底峡与玛尔巴的密教
后期密教俗称“怛特罗佛教”,它在印度的鼎盛期为9~10世纪,其部分思想通过仁钦桑布和弥底尊者传入西藏,但最终未能形成教理和实践统一完备的宗派。然而,到了11世纪中叶,密教的大部分思想由当时活跃的印度僧和藏僧介绍到西藏,其中的几支形成了后来的宗派。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为阿底峡和玛尔巴。
阿底峡 在西藏佛教走向复兴的道路上,阿底峡起到了过渡性的作用,他的入藏决定了后来噶举派的创建。关于他的生涯与思想及其弟子仲敦巴的情况在此不作赘述,只对他在密教史上的成就作一个简要介绍。
阿底峡生于982年,是东印度萨贺国善祥王的次子,在那烂陀及超岩寺等钻研各派教典,是当时活跃的著名学者。这一时期正值“超岩寺六贤门”的后期时代。当时的印度佛教融汇了小乘、大乘以及大乘中原本就有的异质的思想,更有甚者有时还借用印度教的尊格和礼仪,真称得上是复合佛教的时代。这些情况如实地记录在同时代的一部佛教资料《善说集》中。
阿底峡入藏以后,应当时古格王的请求写了《菩提道灯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划分了“三士道”的次第。他阐述佛法的修行是由个人的权宜不等而分次第,发大心者为大乘,发出离心者为小乘。因此,同样是修布施和戒、定、慧等,但结果会有所不同。然而,人的根机胜劣依修习而成,而非不可改变的种姓所致。至于修行的次序,也就应该是循序渐进,否则不能生起无上的功德。所谓“下士”是凡夫行,“中士”为而乘行,惟有“上士”是菩萨行。
仅就密教方面而言,通过考察《大藏经》、《阿底峡小部集》以及他的翻译著作,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有关密教方面的内容比想象的要多,而且正像布顿的四分类法所说的,它涉及到所作、行仪、瑜伽及无上瑜伽等各个阶段。此外,关于怛特罗的分类法,他在《菩提道灯论自注》中提出了七分类法,即所作、行仪、仪轨、两俱、瑜伽、大瑜伽、无上瑜伽。第二,阿底峡的密教涉及范围广泛,他重视密教的尊格,并为保持与显教的整合性而费尽心血。根据七分类法,他为大瑜伽配置了父系怛特罗的代表经典《秘密集会怛特罗》,为最高位的无上瑜伽怛特罗优先配置了性及生理因素比较明显的母系怛特罗。实际上阿底峡所传的《胜乐系怛特罗》接受了成就者路易巴的系统,在西藏被称为“阿底峡流派”。作为胜乐五大流派之一,它对后世产生了影响。第三,关于阿底峡的多重性格,从否定的角度讲,象征其折衷主义特征的当属菩提心说。他对当时在印度流行一时的俱生的实体性本有主义以及在行法中极力排除人为构想作用的无作为主义都倾注了极大的关心。但是这些观点同《修习次第》所论的传统的菩萨行相比非属同类,或根本是两立不能的。然而,很多密教者或密教论著都很注意“菩提心”这个概念。所谓的“菩提心”原本的意思是追求最高境界的正觉,但“菩提”这个概念具有对实在的象征作用,对圣俗一致为前提的密教来说,“心”为一个足场,与“菩提”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菩提心”的内容在论说“空”的同时,又把它看作是一个实体,再进一步“菩提心”便成为性行法中的男性要素(精液),或男女两要素合一的生理行法的组合。
据说阿底峡的无上瑜伽密教思想曾受到过他的西藏弟子仲敦巴的谏止,他对“菩提心”的重视目的在于调停显密之间的冲突,这番苦心可谓当时密教者身上的共同的特征。
玛尔巴 噶举派被称为密教的双璧之一,创建者为塔波拉杰,但渊源出自玛尔巴和米拉日巴。玛尔巴本名却吉罗追,出身于山南地区的封建农奴主家庭,幼年时向卓弥大师学习梵文。他曾三度游学印度,向那若巴、弥勒巴等著名密教者学习。《大藏经》中有数量很多的关于《胜乐怛特罗》的注释书和成就书,署名为玛尔巴之作,但属他人之作的可能性很大。他自身整理的著作并未传下来。因此,想完整地再现他的密教思想非常困难。噶举派的教义重视“大手印法”和“那若六法”。在考察玛尔巴与麦陀利巴的关系时可以看到,那若巴与麦陀利巴皆属于11世纪前半期的密教者,二者与《时轮怛特罗》是否有关尚无确说,但他们无疑都属母系怛特罗。那若巴作为“超岩寺六贤门”之一,被看作是北门的守护者。然而,与他同时代、占对等以上位置的麦陀利巴(别名为阿德巴亚巴吉拉)被有意识地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最终成为了一名实践的密教者。从传统的波罗密道教义来看,麦陀利巴所写的《真理的宝环》一书依据的是中观派中“一切诸法无住派”的理论,其影响涉及的范围甚广。
虽然如此,由于他在包含了性瑜伽在内的无上瑜伽的密教实践方面本领超群,据说甚至连超岩寺实力最大的拉陀那卡拉香提(香提巴)也未敢轻视这个旗鼓相当的对立者。
通过阿底峡和玛尔巴,本文对印度后期密教,特别是母系怛特罗传入西藏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11世纪印度迎来了无上瑜伽的最后一个高峰,但不能忽视的是,正是由于阿底峡传仲敦巴、玛尔巴传米拉日巴及其后的塔波拉杰·索南仁钦,才使各宗派得以确立。可以说这些传播者试图通过显教成分的导入,努力使印度密教中的过强的个人色彩多少变得缓和一些。相比而言,印度密教的个人影响力很强,尽管如此,却没有形成宗派或教团。使密教宗派化的功绩应归属西藏僧人,这或许是因为密教与特定的氏族相结合而获得的助力导致了这一结果。
五、玛尔巴以后的西藏密教
新密教或称新译密教不仅影响了噶当派及噶举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萨迦派和息结派。在新密教兴盛的11世纪,印度的后期密教大量传入西藏。在考察其后的密教发展流脉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二三个显著的对应特点:
第一,从数量到内容,在广泛的领域内对密教经论进行了分类,这些分类整理的成果可从一部分怛特罗中观察到。印度的密教者,比如佛陀密、阿底峡等都创造了各自不同的分类法。在西藏,宁玛派有九乘分类法,布顿创立了四分类法,它后来成为密教论说的坐标轴。
再者,布顿创立了夏鲁派,又称“布顿派”,他对密教理论具有精深的理解,在西藏密教教学的道路上留下了不朽的足迹,特别是《驶入瑜伽怛特罗之海的船》和《时轮史》等瑜伽怛特罗以及各种对《时轮怛特罗》的解说。另外,《怛特罗概说》、《开启秘密之门》等密教概说书都给予后世极大的影响。
第二,不仅在密教的内部范围,而且在佛教整体的范围内都确立了密教的地位。有史以来,学术界对佛教史上有关密教的评价各持己见,虽然在此我们无法对这一问题作详尽的论述,但可以肯定地说,密教确实包含与佛教相异的因素。因此在包括无上瑜伽怛特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密教最后完成的时间里(10~11世纪),在印度,关于传统佛教(波罗密道)是如何与新兴密教(真言道)的复合成分发生联系的问题,以及如何重新对佛教作出全面整理等问题,都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前文提到的麦陀利巴的《真理的宝环》,拉陀那卡拉香提的《三乘建立》以及作者不详的《善说集》等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包括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也是在同样的目的下写成的。
在论及印度和西藏的显密关系时,特里毗塔卡玛拉所作的《三理趣灯明》中的几句话常被引用:
即使是抱有相同目的者,因为没有昏迷,方便诸多,又非难行,只要根机优异便为有资格者。所以真言论典更胜一筹。
《善说集》将这段话奉为圣言,并将中观归谬论证派所说的“空性”定义为般若。因此真言论典根据个人的志向将生死次第和究竟次第区别开来的理论包含了更多的方便。在这里,“方便”被认为是后半部密教的特征。通过将般若和方便的合一,而完成了密教的统一。
众所周知,关于特里毗塔卡玛拉的四句教判,西藏佛教的集大成者宗喀巴及其后继者还有宁玛派的代表人物们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作过详细的论述。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真言道次第广论》这两部著作无疑是针对显密之间的关系而作的。
第三,关于根机的问题。这一问题与显密对比论有着相应的关系。关于怛特罗中“根机”的问题,应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教中有名的兽性、勇性和神性的所谓三性说,佛教有笑、视、握手、拥抱等四种行相,简而言之,只在字面意义上理解密教理论的愚钝者必专注于所作、行仪等低层次的怛特罗,与此同时他也有可能向一尊瑜伽的高度提升。另一方面,具备相当理解力与意志力的人在一尊瑜伽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获许参与以性的成分为特征的无上瑜伽密教的实践。但是,从代表母系怛特罗的《嘿金刚怛特罗》(又称《大悲空智金刚王经》)中可以了解到,在秘密、般若等以性瑜伽为特征的第二、第三灌顶之后又设立了性力思想浓厚的第四灌顶。《善说集》中“智印”一语反映了印度密教中已经确立起来的精神的女性原理。然而,在性力思想并不显著的西藏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深刻。就性的风俗习惯而言,只要人仍属动物的一种,性便是无法忌避的实际问题。因此,一旦轻易地接受了性力思想的影响,它便会迅速地向民众阶层渗透。但是,这是否牵涉到本质性的问题还另当别论。
上述三个特点是12、13世纪以后西藏密教的主要特征,不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特征是在印度密教的土壤中孕育萌芽的。
在西藏,对无上瑜伽密教的教理和实践重新作出解释的是格鲁派。自宗喀巴始,格鲁派为重建正统的佛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宗喀巴是西藏佛教的集大成者,他的登场使西藏密教脱离了一味地承袭印度密教的轨迹,建立起西藏独自的密教体系。关于他的生平,著述繁多,最翔实的该属一世班禅克珠杰·格勒巴桑撰写的《宗喀巴传》,在此恕不赘言。宗喀巴的最显著的业绩是将显密二宗作为相互补充的体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西藏佛教虽人才辈出,诸如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布顿等。但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学问只是以显教为中心,而布顿明显将重点放在密教方面。另外,即使同为密教者,擅长“究竟次第”系统瑜伽的密教行者重神秘体验而轻“生死次第”;显教的学者虽精通“生死次第”,但究明“究竟次第”之奥义者甚少。
青年时代的宗喀巴游学四方,钻研各种经典,其中包括《大印密法》、《弥勒五法》、《现观庄严论》、《阿毗达摩俱舍论》、《那若六法》、《西藏大藏经》等。宗喀巴在34岁时开始学习密教,谙熟重要的密教经典,如《秘密集会怛特罗》、《时轮怛特罗》、《初会金刚顶经》等。像当时的新萨迦派一样,他属于通过辩论的方式来修习佛教教理的学者,但是他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将佛教的全部体系整理统合,于是,他从阿底峡的著作中找到统合大小乘、显密等佛教整体的典范,并通过《菩提道次第广论》具体地作了阐述。宗喀巴在显教方面的最高成就即他的中观派学说,在密教方面获得的最高评价是《秘密集会怛特罗》的“圣者流”,的立场,而这二者反映的是一种共同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宗喀巴实现了他对显密二者的统合。
虽然通过宗喀巴精妙的构筑,在阿底峡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统合西藏佛教的大业,但今天透过科学的研究,我们还是发现了他的体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例如,中观派的龙树与《秘密集会》“圣者流”的圣龙树虽然名字相同,但他们在时间上相隔了700年以上,另外,《菩提道灯论》的著者阿底峡本是《秘密集会》的大家,但他不属于“圣者流”,而是属于“鸠尼亚那帕达”。尽管如此,他在建立独自的佛教体系方面创立了不朽的业绩。
以上通过对各个时期重要的密教者的简要介绍,概观性地回溯了西藏密教的发展脉络。由于篇幅的关系,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未能提及,在许多关键的理论问题上也未能展开论述,这些有待于日后更为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