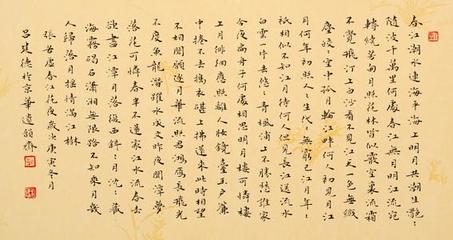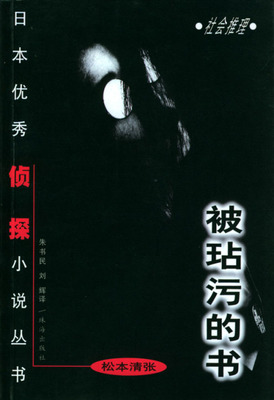
在被官方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文学界也释放出了活力,至少在“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10年(1978-1988)呈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潮流更迭,作家云涌。在林林总总的写作潮流中涌现出一批批各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中有一部分在80年代便成绩斐然,而此后又不断地拓展写作领域或转变创作风格,艺术日臻成熟,成为近三十年贯穿性的重要作家。
由于文学界在“文革”期间饱受政治禁锢之苦,“新时期文学”一开始仿佛就是站在政治的对立面的。然而,至少在最初几年,政治化的写作模式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中,“政治性”仍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主导性的作家王蒙(1934- )本身就是一位“政治人物”,早年投身中共革命,1956年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遭受批判,次年被打为“右派”,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79年,从劳动改造了十数年的边疆重返北京,作为一朵“重放的鲜花”,迅速占据文坛的中心位置,一度官至文化部长,却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下台。从这样的人生履历出发,我们不难理解,“革命”二字何以成为王蒙创作中的关键词,即使是在那些具有形式探索意味的所谓“东方意识流”的小说中,也是如此。在他最为著名的几个中短篇,比如《布礼》《蝴蝶》中,既有劫后余生的革命者对于革命的思考,对于历史的反思,亦有他们不死的革命理想与信仰。在90年代创作的“季节”系列长篇中,这一写作路数仍在延续。出版于1986年的《活动变人形》是王蒙的长篇小说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一部,通过塑造新旧之交年代的知识分子倪吾诚这一形象,作者触及到“启蒙者”的悲剧命运,并给以深刻反省。
张洁(1937- )起初的创作也与政治纠缠不清。批判“旧”的经济体质,呼唤改革,也呈现改革进程艰难的长篇《沉重的翅膀》,其所引起的震荡甚至远远超出了文学界。除此之外,凭借那些表现知识女性婚恋生活的创作,在80年代,她的影响力超出其他女作家。《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是大陆“文革”后第一篇“婚外恋”题材的小说,在发表后立即引起一场关于婚姻伦理道德观的大讨论。其后发表的中篇《方舟》(1982),表现了三个离异单身的女人的现实困窘和激愤,被视为当代中国文坛第一篇“女权主义”小说。在《祖母绿》(1984)中,这种愤怒被平息与超越,取而代之的是宽恕与一种永恒而空泛的爱。然而,作者的愤怒却难以平息,在其后数年的创作中,贯穿着对现实,对人性,特别是对男性的抨击、嘲讽。三卷本《无字》(2002)是张洁后期最重要的作品,以男女情爱穿起各自家族的命运,也穿起百年的中国历史风云。这是作者深刻历史反思与自我清理,是她对于前期理想的一次较为彻底的颠覆与解构。
大致是从1985年开始,大陆的当代文学才获得了一种“文的自觉”,启动了所谓“纯文学”的步伐。一面是“现代派”西风袭来,一面是植根于本土的“寻根”热潮掀起,向中国传统、民族传统寻找文化之根。有人将汪曾祺(1920-1997)的创作视为寻根文学的前奏。早年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其恬淡、豁达、诗意盎然的汉语小说风格本来是京派小说的不绝余韵,却与有意为之的寻根小说不谋而合。他早于寻根口号提出之前的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以田园牧歌的笔调抒写世外桃源般的美好生活,模糊了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唯一鲜明的是心灵、青春、人情的美好,深得乃师沈从文建希腊小庙供奉永恒人性之真传。随后,他又写出《大淖记事》,仍然是充满诗意的汉语小说,到1985年寻根文学出,汪曾祺被认为开风气之先者。有评论家认为,在摆脱一度统治大陆的“毛(泽东)文体”的过程中,汪曾祺是一个关键性的作家。90年代以后,汪曾祺的小说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其作品成为“文革”后小说唯美化的艺术标杆,这与大陆文风的演进不无关系。
而韩少功(1953- )却是以“寻根文学”发轫者之一而闻名文坛。“寻根文学”是80年代明确提出了口号的一支文学脉络,这个口号多多少少来自于韩少功1985年写下的随笔《文学的根》。在拉美文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激励下,“寻根文学”一度被视为是一种可复制的、打入世界文学之林的路径。韩少功的《爸爸爸》(1985)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展示了民族文化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一面。此后,寻根之风沉寂,而韩少功的创作却向前迈进,长篇小说《马桥词典》(1995),以词条连缀的方式,展现出蕴含在民间词语下面丰富的生命和生活;以一个个不被主流文学所记录的口头词语,记录了一方土地的历史。无论是小说形式还是思想深度,都达到了其创作生涯的又一高峰,而对民间、乡村生活的执着探索中也可见当年寻根理想的影子。出版于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暗示》(2002)呈现出一种混杂的文体特征,也显露出作者的“思想”气质。
1985年声势浩大的“寻根文学”标志着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式浮出水面,进入文坛中心,这就是“知青”作家群。“寻根”文学潮流中的代表作家,如韩少功、阿城、郑捷生、郑义等人都是“知青”。还有两位“女知青”日后成为蜚声文坛的女作家。王安忆(1956- )最初的创作表现回城“知青”困惑与希望交织的新生活,如《雨,沙沙沙》《本地列车的终点》。1985年,从美国归来后创作《小鲍庄》,以一次自我飞越,正式奠定了她的文学地位。随后发表的“三恋”以其细致入微的性心理描写引发争议。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与政治事件,对王安忆构成了心灵上的极大冲击,使其感受到一次信仰的坍塌与幻灭。发表于1990年的中篇《叔叔的故事》通过一种元叙事的手法,拆解了“叔叔”这一辈作家的“神话”,反思了一个时代的虚妄的热情与信仰。而同期发表的《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又似乎在营造一座新的“精神之塔”。长篇小说《长恨歌》(1995)获得了持续的关注,这部以一个人(王琦瑶)来表现一座城市(上海)的力作,使王安忆获封为“海派传人”。但她的野心绝不止于此,“比张爱玲宽阔”是她的自信所在。她的目光并未停留于“海上繁华梦”,甚至早年的知青生活在她的笔下也获得新的审美观照。
而曾在河北农村插队的铁凝(1957- )则与另一个文学流派联系在一起。在她早期那些单纯明朗的小说中,不难发现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的影响——抒情的笔触,诗意的氛围,优美的女性,以及对心灵美的开掘。在成名作《哦,香雪》(1982)中,以上因素得到了较好的融合。一条铁路改变了台儿沟人的生活,那个唤作“香雪”的女孩儿,以她攒下的鸡蛋要换取“城里人”的一只铅笔盒,那是她对于“文明”的向往。将“物质”寄寓“精神”意义的做法,在80年代的中国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发表于1988年的长篇《玫瑰门》,代表了铁凝艺术上的深化,以一种恶的透视取代了善的呼唤,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不过,铁凝后来依然回归到优美和谐的美学志趣。在中篇《永远有多远》(1999)中,借助一个北京女孩白大省的人生挫败,为丧失中的老北京精神唱了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2006年底,作为已故的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巴金的继任者,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成为这一位置上的第一位女性。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与先锋文学共同汇聚成大陆文学的创新潮流。这一阶段,在“文体自觉”的意义上,马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其小说中的“叙事圈套”为人津津乐道。其后,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叶兆言等人共同推进了大陆当代文学的一次“叙事革命”。反对传统现实主义追求的那种客观现实,转向人类的内心是先锋作家们共有的思想向度。这种真实观的转变深刻影响了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余华(1960- )的小说创造出一种“虚伪的形式”以展现个体精神的真实。在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1987)中,他扮演了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如荒诞梦境般的叙事情境中,一个涉世之初的青年感受到了来自成人世界的暴力侵犯。对暴力与死亡的沉迷,贯穿在他随后的一些重要作品,如《一九八六》《往事与刑罚》《现实一种》中,发展为一种“残忍的才华”。发表于1992年的《呼喊与细雨》(后更名为《在细雨中呼喊》)在对苦难和孤独极为平静的叙述中笼罩着一层忧伤又和煦的温情之光,已透露出作者转变的讯息。在随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正式宣布他与生活的“和解”,“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在先锋作家群体中,余华的转变是具有代表性的。停笔十年之后,2006年出版的长篇《兄弟》在评论界引发争议。
“江南才子”苏童(1963- )以其独特的韵致加入到先锋作家的行列。在他最具“先锋”特征的小说,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中,性、本能、死亡、衰败等等“颓废”的主题被置于叙事中心。但苏童式的颓废却并非习自西方,而是滋生于江南水乡、秦淮世家,别具阴柔绮糜的东方情调。在书写故乡——“香椿树街”的故事中,读者能嗅到一种市井文明烂熟的气息,那是“南方的堕落与诱惑”。其间,有青春期的躁动,危机四伏的成长;也有成人不竭的欲望涌动。而另一类小说如《妻妾成群》《红粉》,无论主题、情调,还是叙事风格,都不无来自传统文人小说的影响。苏童长于中短篇小说创作,长篇小说则似乎稍逊一筹。近年在稳定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之外,亦有长篇《碧奴》(2006)和《河岸》(2009)面世。
80年代中后期,几乎是在先锋文学同时,一种与之相背的创作潮流兴起。这种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努力挣脱“革命现实主义”的影响,直面琐屑的日常生活。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作家。刘震云(1958- )的小说《一地鸡毛》(1991)以“一地鸡毛”来形容日常生活的平庸零碎的情状,形容在褪去了诗意与理想的光圈之后,生活的“本来”面目。这也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陆社会精神状况的表征。这篇小说连同《单位》《官场》《官人》,表现大陆“机关单位”的工作环境、生存环境对于人物的种种制约,种种逼迫,以及种种人性的扭曲。它们也是大陆较早透露官场“潜规则”的小说。作者对这种种荒诞生存施以无奈的嘲讽。另一方面,刘震云也是一位重要的乡土小说家,90年代相继出版了表现乡村生活的长篇巨制《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这方面的努力在新世纪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出版于2009年的长篇《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广受好评的小说。这部作品不仅继续了作者此前对于孤独、交流、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探讨,也被评论家认为开启了中国当代乡土叙事的新面向。
乡土叙事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条主要的文学脉络,从鲁迅开创的乡土小说,到沈从文、废名、师陀等人的京派小说,到1949年后蔚为壮观的“农村题材小说”,再到“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以及邓友梅、冯骥才等人的风俗乡土小说,乡土小说几乎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来自西方乡村的贾平凹(1952- )是当代最重要的乡土小说写作者之一。80年代创作的取材于故乡生活的“商州系列”,如《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天狗》《黑氏》《浮躁》,提供了具有陕南山区地域特色的描摹,反映在社会变革时代里乡土社会的世相和人心的浮动。引发巨大争议的长篇小说《废都》表现古城西京文人的“颓废”生活,在90年代初出版,深具转型时代的文化症候。书中大量直露的性描写,以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而保留在书中的方框(代表被删去的性文字)也是引发非议的焦点,并导致最终被官方查禁。近年出版的长篇《秦腔》(2005)则获得了评论界较为一致的肯定。作品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乡土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为处于崩解颓败中的乡土社会,深情地献上了一曲挽歌。从“废都”到“废乡”,贾平凹或许是中国当代最具有“世纪末”颓废意识的作家。
莫言(1956- )是另一位重要的乡土小说写作者。与贾平凹对西北古老乡村的书写不同,莫言的山东高密乡是其文学创作中魂牵梦绕的乡土世界。1985年以《透明的红萝卜》进入文坛视野,其出色的视觉感官书写为人称道,评论家也不难发现彼时风靡大陆文坛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他造成的影响。随后发表的《红高粱》系列,写的便是发生在高密大地的祖祖辈辈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以祖辈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优根”,来表达、发泄对“我们”这些丧失了血性的懦弱的不肖子孙的轻蔑,因此莫言也常常被视作为“寻根文学”的一员重将。在90年代以后,莫言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等,成为大陆产量最为丰厚,才华也最为横溢的作家之一。如果说,贾平凹书写的是古老乡土中国处于“现代性”压力下的命运,那么,莫言则执着于寻找故乡深处孕育生命、支撑历史的永恒不息的“民间”力量。奔放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感官意象,成为莫言风格的标识。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大陆,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随着经济体质改革的继续推进,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之下,市民文化、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造成了空前的冲击,纯文学的世袭领地不断丧失。这是一个文化溃败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王朔(1958- )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早在80年代中期,王朔就发表了《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橡皮人》等尚带纯情的作品,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青年特有的精神风貌;1987年发表的《顽主》以其“调侃”的语言风格和略带荒诞的笔调表现转型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和心态;带有北京市井特色的“顽主”人物序列堪称最早从大陆当代主流体制中流离出来的“多余人”。90年以后,王朔在文坛的形象更为飞扬跋扈,“过把瘾就死”、“我是流氓我是谁”都成为其代表性语言。这个时期,王朔开始向影视编剧方向发展,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后获得巨大成功,其“痞子式”的自我定位恰好为文学脱离精英化、进入大众文化市场开风气之先。在一些人看来,王朔堪称“躲避崇高”的“反体制”的“平民文化英雄”;而在1993年的那场“人文精神讨论”中,王朔则因其对于“崇高”的戏谑,作为丧失“人文精神”的典型而遭受批判。
王小波(1952~1997)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推进了中国大陆“个人化”的写作潮流。与王朔一样,王小波也是上升成为“文化符号”的作家,其作品讥诮反讽、特立独行、天马行空,被看作是“自由精神”的代言人。其重要作品触及性与政治权力关系的独特思考。《黄金时代》《红拂夜奔》《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等可读性较强的作品受到热烈追捧,而艺术成就较高的《黑铁时代》反倒曲高和寡,较受冷落,这也几乎是“文化符号”的必然命运。王小波死后,这个出身干部家庭、受过毛泽东接见、“三反”中遭过殃、在云南插过队、工厂做过工、赴美留过学、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任过教、又辞职做自由撰稿人的知识分子,与其说被当做一位“作家”,倒不如说是被当作“自由主义斗士”被公众悼念。
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信息和资讯时代,网络的普及造成了新的文化景观。大众文化日益发达,客观上说,纯文学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另一方面,大陆当代文学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艺术上已渐入佳境。一些重要的作家都推出了他们的成熟之作,而一批新锐的作家也在走向成熟。作为所谓“晚生代”作家的代表,毕飞宇(1964- )的写作功力引人瞩目。代表作《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等,以细腻的感受力、精致的文字显示出不凡潜质。创作手法虽不乏先锋性的探索,但并不过分,也融合了传统的因素,叙事流利。2005年,毕飞宇推出长篇小说《平原》,描写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苏北平原的农村生活,其扎实的写实功力为人称道,出色的细节描写仍然是其最拿手处。2009年,又有长篇小说《推拿》问世。
同样出生于60年代,“东北才女”迟子建(1964- )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她的文字朴素干净,携带着一种诗意的温暖,这在早期的《北极村童话》中已有表现,奇异的东北极地的风景与人伦被成功编织进了小说的美学世界,《逝川》《亲亲土豆》《雾月牛栏》等都是她代表性的作品。近年的创作则淡化了“童话”意味,而增添了更多的“现实”内涵,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与《踏着月光的行板》,对社会“底层”生活有了较为深刻的揭示,但也仍然不乏“辛酸的浪漫”。《伪满洲国》(2000)和《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是迟子建重要长篇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前文以简短的篇幅,勾勒了近三十年大陆小说的主要流派与发展脉络,对其中涌现出来的代表性作家的创作历程和艺术特色也给予概述。由于篇幅与笔者能力所限,另一些并非不重要的作家尚未论及,这些名字至少应包括:高晓声、陆文夫、张贤亮、冯骥才、张炜、张承志、史铁生、阿城、池莉、方方、刘恒、陈染、林白、阎连科。这些作家共同构造了大陆当代文学的银河星系。而同样由于笔者的眼界或者偏见所致,在新世纪渐成气候的“80后”作家,如韩寒、郭敬明,以及浩如烟海的网络小说家也未曾提及。他们会将中国文学推向何处,是一件尚需要再观察论证的事情。至少在一个主流文坛的圈子范围内部,严肃文学作家及他们所表现的艺术水准才真正代表着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艺术高度。
(原载台湾《联合文学》2010年第3期。本文系与师妹燕娟合作,师弟治臣对王小波一节进行了修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