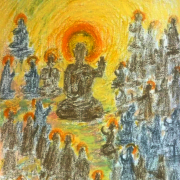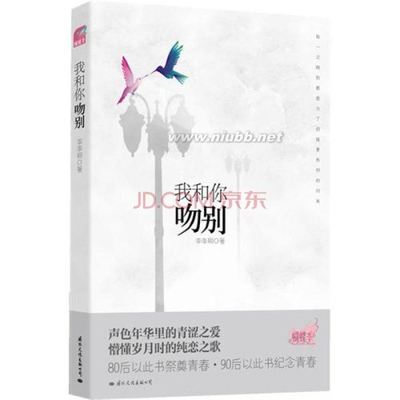我和《奔流》
田中禾
1959年春天,我还在郑州七中读书。寒假里写了一部童话长诗。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天,我拿上诗稿到工人新村的省文联去。办公室里一个戴眼镜的人值班。他举止斯文,谈吐儒雅,面对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像和蔼的师长一样用低沉的声音和我交谈,讨论诗歌,讲卞之琳,讲艾青,和我谈了两个小时。他叫丁琳,是《奔流》杂志的编委。一星期后,我接到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信,说我的长诗太长,《奔流》无法发表,丁琳老师推荐给他们,他们已经读过,决定出版,要我到出版社去一趟。这年“六一”,这部诗出版了。它就是我的处女作《仙丹花》。当年被选入《河南建国十周年儿童文学选》,第二年,由文化部选送参加“巴黎儿童读物博览会”,这部书的稿费是我入大学的路费和学费。我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丁琳成了我终生的师友,《奔流》成为我文学道路上的重要园地。
丁琳先生的一生随着《奔流》起落,他的身影与《奔流》联为一体,伴着它的始终。文革中《奔流》停刊,1979年《奔流》复刊,我在故乡县城一个街道小厂里。写了一组诗寄给他,丁琳先生马上给我回信,鼓励我继续写作。后来我到了县文化馆,发表了《五月》,丁琳请我和乔典运来,住在文联招待所写稿子。当年心目中崇拜的老师,以一副谦恭的态度殷勤地招待我,每天到楼上来看望,让我心下十分不安。此后,我的《春日》《椿谷谷》《娃娃川》都由《奔流》推出。《春日》获了那一届的“奔流奖”。《奔流》1990年再度停刊后,丁琳先生退休,我每年春节去看他,坐在他的小卧室里和他叙旧,直到先生去世。他的宽厚、仁爱、敬业、爱才,对我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在《奔流》结识的另一位长者、仁者是庞嘉季先生。我从大学退学后,生活和人生遭遇了一波又一波挫折,1963年夏天寄寓在西郊一个出租屋里。从邻居那儿借了一本《奔流》1963年上半年合订本,读过之后,写了一篇《奔流1963年上半年小说纵横评》,那时已很久没与丁琳联系,就把文章寄给了奔流编辑部。几天后,收到“奔流评论组”的回信,赞扬文章写得好,问作者的情况,希望作者到编辑部去见见面。第一次见到庞先生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时他是评论组组长。嘉季老师满头银发,穿着尖头皮鞋,满面笑容,一副风流潇洒的样子,从外面一进来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你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当时还有一位年轻编辑在场,他忙着给我让坐,倒水,——他就是后来主编《故事家》的杜道恒。那是我生活最窘迫、潦倒的时候,庞先生和道恒的勉励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此后,嘉季先生一直关注着我的情况,常向文学界的老师们介绍我。1985年在洛阳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他向南丁推荐我大会发言,见人就说:“田中禾很有才华,很有潜力。”其实,那时我发表的作品很少,他的话对我是很大的鞭策。那次会后,我写了《五月》,算是对老师们的厚望的报答。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奔流》在我心中依然有着神圣的记忆。丁琳老师作古了,他倾注于《奔流》的精神依然温暖着我。
《奔流》现在再一次复刊,使这本源远流长的刊物能够继续发挥品牌效应。这对文学界是件好事。对老一辈的作者是历史的延续,对新的作者是又一个崭露头角的园地。祝贺之余,感慨良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