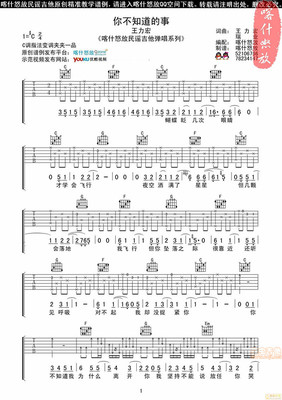《实验室的普罗米修斯之一》这篇文章大概是一年前翻译的化学家传记,不是很成熟。自己中英文都不够好,里面还是有严重的翻译腔,而且我只是一个化工的本科生,还是大学渣,所以里面可能有一些常识的错误。但是就贴出来请各位指正了。之所以翻译这篇大概是因为帕特森以一个人的研究对抗整个宇宙的勇气鼓舞了我。今天乔北兄转了一篇报道,说起今天沸沸扬扬的氢氟酸和科学素养的问题,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这个。从不敢示人的QQ空间挑出来。在翻译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虽然翻译过来略显生硬,但是原文还是相当生动的。这篇传记有上中下三篇。(收藏人:木立2013-12-29)
卡莱尔·C·帕特森和他的无铅汽油(上)
(1922年6月2日—1995年12月5日)
最伟大的科学家
总是抛弃那舒适的生活
只为一丝照亮未来的光芒
去践行那看似不可能的道路
是什么使他们前行?
因为在科学的处女地
能发掘到人生的美和意义
于是他们甘心被它奴役
护卫着人类的命运
卡莱尔·C·帕特森
1981年8月23日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富铅的世界之中。他们的汽油采用了铅作为稳定剂,他们的牛奶装在含铅的罐头里,他们的水流经镀铅的水管,储存在衬铅的水桶中。牙膏管是鍍铅的,葡萄酒的软木塞上也有一层铅皮。就连天然的水果上也有砷酸铅的农药残留,而在入口之前,它们还得装在上了釉彩的盘子中,而那些釉彩也含有一定的铅。
一年下来,美国人一共吸收了大约20吨的铅,其中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铅(其残留程度由摄入的铅的物理化学状态决定)会残留在人体内。铅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危害极大,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危害中枢神经系统,造血系统和肠胃系统,严重的可致死亡。尽管人们知道大剂量的铅危害极大,但关于低水平的铅含量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性,始终也没有大规模的研究,所以他们对于少量的铅摄入却怀着错误的看法,认为少量的铅的摄入是无害的。
作为一位地球化学家,卡莱尔·帕特森曾经通过铅的测定确定了地球乃至太阳系的年龄,之后更是孤身一人对抗大型工业和政府的双重压力,甚至包括其他并不了解铅危害的同行们,历尽艰辛把铅污染从汽油和厨房中驱除。帕特森对于全球性的污染做了一些调查,并把评判环境污染的方法告诉其他化学家。他发展了微量化学分析的手段,为地球化学家和海洋化学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并且开发了超净的收集设备和技术。通过推动对于铅的药理研究和提升自身的学术能力,他使得公众相信,即使是少量的铅存在于环境中,其危害也是不容小视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带头反对在汽油中加入四乙基铅。汽油中不再有四乙基铅之后,美国人体内的血铅含量下降了80%。
帕特森在1922年生于衣阿华州的米切尔维尔,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叛逆的”本性。他形容的的家乡是一个“只因为创造力托生于日常生活之中才得以不被践踏”的地方。他的大学是在附近的格林内尔大学度过的,在那里充满了废奴主义者和公理教会的信众,社交生活一派繁荣。大学里,六尺四寸高的帕特森总是晃荡着两条长长的胳膊,但是内心却是敏感而瘦弱的,也不甚理解幽默的意义。他总是很诚实,透明的像一块水晶,这一点总是让人又爱又恨。他的同学,他以后的妻子罗娜·“洛莉”·麦克利里,说他“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想法。”拿到学位之后,帕特森和洛莉一道加入了芝加哥大学的“曼哈顿计划”,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做起了原子弹的研究。
在橡树岭,帕特森接触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技术。为了给原子弹注满燃料,实验室采用质谱仪进行同位素分离,将铀-235从铀-238中分离出来。所谓的同位素是指同种元素因为中子数不同而具有不同质量的原子。正如帕特森所解释的“通过电场对原子核样本加速,然后让其通过磁场,更轻的原子会划出一道更小的圆,更重的原子则会划出一道更大的圆,于是同位素就得到了分离。”
和他许多在橡树岭工作的同事一样,帕特森也向曼哈顿工程请愿,希望那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能够先投放在日本乡村,而不是瞄准人口众多的城市。在曼哈顿计划的产物在广岛上空爆炸之后,帕特森把这一他投入巨大精力的工程称为“科学史上最严重的犯罪”,“我们活活的杀死了十万日本人…我们是帮凶。”因此,他之后关于铅污染的研究以及和日本科学家的合作都被他认为是对曼哈顿计划的赎罪。
当世界重归和平之后,帕特森以一名化学专业毕业生的身份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的美国大学,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正在大规模的将战时的技术应用于新出现的问题。当时芝加哥大学探索科学时采取的跨学科方法吸引了一大批的科学巨星,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埃里克·费米,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里和威拉德·利比。地球科学和同位素研究更是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在战时人们向水文学和气象学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帕特森由此认为进行地质学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将会揭开这一领域的面纱,看到“壮美的新景象”。而关于同位素的大量信息也在迅速的积累着。通过研究天然的碳的同位素碳-14的衰变查出年代,利比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而另一位助理教授哈里森·布朗,希望通过检测铅的同位素,从这种黯淡无光的金属中找到地球年龄的奥秘。
许多科学家认为地球早在3.3亿年前就已经诞生,只是他们的证据有些令人疑惑,且不能相互印证。他们知道有一些铅是自地球诞生以来就已经存在,而另一些则是由铀和钍在日后衰变而来。铀的不同同位素具有不同的半衰期,也形成了铅的两种不同的同位素,铅-206和铅-207.此外,钍则衰变成铅208。因此,铅的同位素的组成总是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而历经千百万年之后不同地区的铅的同位素比例,也是解密地球过去历史的关键。通过对比地球表面的铅的同位素比例和陨石中铅同位素的比例,可以推测出地球的年龄。早期的地球科学家得出了关于地球年龄的公式,但是却无法知道地球最初的铅的同位素的比例。一旦这个比例得到确定,整个方程就变得可解,然后“扑零一下”,正如帕特森说的那样“地球的年龄之谜就被揭开了。”
哈里森·布朗对于地球化学自然是十分了解的,于是他意识到,在陨铁之中的铅含量就是太阳系中最原始的含量。因此他找到了一位熟稔质谱分析学生来分析古代陨铁和现代陨铁中的铅含量。他找到了帕特森。
作为探测地球年龄的第一步,帕特森首先测量了锆石中的铅的含量。锆石是一种在火山岩中常见的矿石,常常用于制作珠宝。作为一位化学家,帕特森并不知道地质学或是有关矿物分离的知识。但是无论是普通的火山岩结晶,还是由岩浆中结晶而成,锆石的组成都几乎毫无差别。最开始锆石之中含有铀,其中的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中的铀会缓慢的转化成铅。为了测量“现代”岩石中铅同位素的比例,布朗让帕特森测量锆石中的铅同位素的比例和丰度。他们手上只有极少的可以通过放射线探测年龄的矿石样品,这些都是从珍惜的铀矿石之中得来的,以克为单位计的稀少样品。而每一块锆石晶体样品则更是只有针尖大小,每一个针尖大小的样品上更是只有几百万个铀原子,自然衰变得到的铅原子数目就更少了,相对于当时所有的测量水平,帕特森只有把测量极限再缩小一千倍才能够测得结果。
“帕蒂,”布朗鼓励他说“在你成功的测量出这些锆石中的铅同位素丰度之后,你就能采用相同的方法测量陨铁中的铅同位素丰度。你会一举成名的,因为你将会是测出地球年龄的那个人。”
“听起来不错,那我答应你好了。”帕特森回答道。
“哈,我相信这对你不过是小菜一碟。”布朗很高兴他能答应下来,“我看好你。”
于是,为了做出这碟小菜,帕特森整整花了七年。
“布朗教授认为这不过是缩小了测量规模的问题…确实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所在,我确实把测量规模缩小了一千倍。这只花去了我一年的时间。”帕特森这样说道。真正的问题是他的实验室本身,帕特森的实验室在整个学校最年久失修的那栋楼,环境也堪称脏乱。环境中的铅含量比他要测量的那一丁点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他并没有今天实验室那样的清洁设备,比如防铅的特氟龙容器,经过过滤的,比外界压力更高的空气,或是浸浴在经过过滤之后的空气中的层流工作站,以及保证在提纯之前不会有液滴飞溅的高档蒸馏设备。然而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帕特森还是以高超的手段和技巧筛选并清除了残留于他实验室管道,试剂,电学装置,金属和玻璃仪器中的大部分的铅,甚至包括空气中和水中的铅。“除铅运动”所消耗的时间远远比分析锆石的时间要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帕特森发现迄今为止发表的上万份有关于日常生活中的铅含量的数据是错误的:日常生活中的铅污染远比我们所认为的要严重。
帕特森认识到铅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污染的时候,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它在我们身边的存在。1951年帕特森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这是他对于实验室的打扫也颇有进展——他的实验室中只含有百万分之一克的铅。在当时可谓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现在的大多数的超净实验室中的杂质都只有万亿分之一克了。
帕特森的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关于亿万年前的前寒武纪矿石中的铅同位素的,如今这篇论文已经被视为是地球化学这一学科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了。这篇他和物理学家马克·英格拉汉姆以及地球化学家乔治·蒂尔顿共同完成的论文所采用的铅同位素研究技术,发现了地球化学的新天地。地质学家们此后终于可以测量普通火山岩和沉积岩中的铅同位素含量了。再加上锆石中铅的丰度,他们可以推测出地球上任意一块花岗岩的年龄。最重要并不是这个,而是论文中通过微量化学分析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帕特森和他的同行们一起努力,使得微量测量达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水平,推动了许多化学技术的进步。大多数的化学家都能够“奢侈”的采用相对较大的样品来解开自己的谜团,但是地质学家只能从极小极少量的样品中找寻地球的奥秘。帕特森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便是他在学术研究中的特质。他认为科学家应当不遗余力的把数据做到完美,他们注定得小心翼翼的迈出每一步。
然而此时,尽管已经小有成就,可是那碟布朗教授让他做的“小菜”却仍在烹饪之中。他还是没有能测出地球的年龄。于是他先是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后,再在1952年去往帕萨迪纳市的加州理工学院,再为之辛苦工作了两年。
作为一名在地质学教学楼工作的化学家,帕特森需要搭建一间自己的化学实验室。为此他迅速的向原子能机构申请资金,在加州理工学院里搭建一间清洁实验室,来测定地球的年龄。但是原子能机构似乎对这项太过学院派的项目并不感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给他出难题的布朗教授此时已经是一项筹款运动的主事人了,他帮助帕特森搞定了一切。此时的布朗也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他告诉原子能机构说帕特森正在研究花岗岩中的铀,并且一吨花岗岩粉末中的铀能够产生和几十万吨标准煤相当的能量。此话一出,钱很快就到账了。于是帕特森建立了铅同位素研究所用的第一间清洁实验室。然而有点讽刺的是,他是在这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做到这一点的。背靠着落基山脉,帕萨迪纳几乎收纳了整个洛杉矶盆地的烟雾。
直到1953年,帕特森终于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超净的原生铅样本,这样他就可以测量地球的年龄了。他来到了芝加哥旁边的一片麦田中,在那里有着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带着他的珍贵样品来到了阿尔贡国家实验室的质谱仪前。测量是一件精细而耗时的工程,他一直工作到深夜,整个实验室都变得一片寂静。当他终于走出实验室,伊利诺伊斯的星空分外明亮,他知道他已经探知了流星,地球,和整个太阳系的一个秘密——45亿年。七年磨一剑,如今他终于确定了太阳系年龄的范围。第二天帕特森开车去衣阿华州的父母家,他过于激动,以至于他以为自己患了心脏病,于是他到家之后,赶紧让他妈妈送他去医院——抢救。
数年之后,他说起这段时光,“科学发现让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在那时候,我只是不停地想大声告诉世界‘你们看,我做到了!’”然而现实却是在“科学神圣庄严的小世界里,如果说‘我’让人觉得孤独”他本能的大喊“我们做到了”。当他意识到人类能够探索到地球的奥秘之时,浑身就像通过了一股电流,他感到了先前的科学家们赋予他的责任。“那是一种荣耀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以后慢慢熔铸进帕特森的灵魂,赋予了他持久的热情,哺育了他善良的心灵。经过了在阿尔贡的那个夜晚,帕特森感觉到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科学家。
在1953年11月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帕特森公布了他的发现,三年之后,他把地球的年龄修正为45.5亿年,这个精确的数字在五十年的时间里都未被超越。正如他自己所说“给出的地球年龄的准确毋庸置疑,我对于这个数字信心十足,这就像罗德岛上维斯特里小镇上的花岗岩中的铝含量一样确信无疑。”
然而让帕特森失望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拿到诺贝尔奖。当时的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都没有把目光投向地质学领域,而跨学科领域的成就也常常被评委会所忽略。而更重要的是,除了新兴的核地质化学的小圈子,当时只有少部分的圈外科学家能够理解他是如何计算出地球年龄的。当时大多数的地质学研究都是描述性的,尚未以数理学科为基础。“直到十几年之后这个数字才被放进地质学教科书之中。”帕特森之后说道。而即便如此,也少有人提起这是帕特森的成就。一份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过去三十年中超过50本的教科书中,只有四本在说起地球年龄时提到帕特森。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早认识到帕特森成就的人之中,有一位在帕萨迪纳极具权势的神创论者。于是广播和电视节目中的布道者赶到加州理工,咒骂着说他会下地狱,饱受地火煎熬。
等到其他科学家蜂拥而至,想要重新确认或是颠覆帕特森的这项研究时,他却翩然转身,“我不愿再做这项工作了。”二战之后,许多自然科学家收集了浩如烟海的数据,降雨,河流,温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及在海洋和湖泊之中的二氧化碳沉积。这些年所收集到的关于全球雨水中的元素分配的数据,在之后80年代的酸雨研究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作为历史的的探路者,帕特森决定去测量全球地表的铅同位素比率。当岩石不断被侵蚀的时候,其中的矿物质在海洋中再次混合并富集。于是他们决定在沉积层采样。帕特森为此设计了一个宏大的测量的计划,去测量不同深度的海水和海底沉积中的铅同位素比例。
为了收集到美国整条海岸线沙滩的沙子,帕特森给海岸线的几乎每一个邮局都写了信,从东海岸一直到南方,每隔30英里,就会有一家邮局收到他的信,附上一个包裹和他自己的地址,他希望他们能够帮他在袋子里装上1磅半的沙子,然后寄回加州理工。他和洛莉则带上孩子,从加州一直自驾到温哥华,一路收集西海岸的沙子。
为了给帕特森提供资助,哈里森·布朗再次向美国石油基金会“鼓吹”说帕特森对海底沉积的研究会帮助定位石油的所在。“哈里森每年都帮我从那里搞到许多钱来维持实验室的运转,但我做的研究和石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帕特森说“其实我在欺骗人家…额,一个小小的欺骗。”但是够意思的哈里森·布朗还是接着资助了他好几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帕特森和他的博士后搭档周才骅(音译)发现了他们检测的从河流流入海洋的沉积样品中铅含量在现代突然激增。为了对比海洋沉积物中本应该含有多少铅,他决定迂回出击,去分析另一种元素,钡,因为钡和铅有许多相似之处,却没有被大规模的投入工业使用。于是存在于岩石和海洋沉积之中的钡的含量就成为了一把标尺,帕特森可以借此来衡量在一个没有铅污染的世界中,铅含量究竟是多少。他们发现钡在深层海水中含量较多而铅则富集在水体表面。帕特森和周才骅近一步惊讶的发现,加州南部的海水表面的铅含量超过了地表和火山岩侵蚀的八十倍还多。“为什么铅含量会这么高呢?”帕特森疑惑不解。“如今的海水还没能快速的混合,浮在表面的海水比深海之中的海水远为‘年轻’。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融合在一起。”
帕特森认为现在他可以确定这污染的罪魁祸首了:“如果我们测得的样本中的高铅含量是整个北半球的普遍状况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含铅汽油便是污染的源头。”虽然帕特森尚未公布他的假设,但是他还是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个结果对于社会的爆炸性影响。汽车所排放的铅是以可溶性的卤化物颗粒物存在的,因而极容易被人和其他哺乳动物吸收。当1962年,他最终把自己45页的海洋沉积物研究报告发表的时候,他把副本给了他的同事,说道“读读它吧,它很重要。”
为了确定他所采集的样本是否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他联系了一位日本的同行,Mitsunobu Tatsumoto,接着对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域中的海水层中的铅含量进行进一步研究。但是一直和海洋打交道的帕特森却十分讨厌跨洋的旅行,因为他晕船十分严重,以至于有一次他不得不去吸氧才能缓解症状。而且因为轮船也涂上了含铅的涂料,所以如何采样也是一件特别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必须避免涂料中的铅溶于水的影响。而跨越了这些艰难险阻之后,帕特森发现,铅也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上层海水中富集。

考虑到水循环中,是由雨雪天气补充表层海水的,于是帕特森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在降水和大气环流中的铅含量究竟是正常范围之内,还是在那时就已经高到不正常了。正常情况下,未被污染的空气中只含有极少量的铅,都是一些火山喷发或者是森林火灾之类的产物。于是帕特森登上了远在洛杉矶烟雾以北500英里的,拉森火山国家公园的高山草地。这又是一次开创性的研究,他把他在地球年龄实验中采用的超净实验室技术推广到了户外环境中。为了避免含铅汽油的影响,他特别找到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自从今年的第一场雪之后就一直没有通车,他收集了干净的积雪样品,但却惊讶的发现,即使是在保护区的山谷里,他也检测到了超量的铅,而且比自然的大气环流中的铅含量高了一万倍!事实上我们后来知道,积雪中的铅含量通常比海水中的高出10到100倍。所以即便不用考虑自然的大气环流中的含铅量,几年积累下来,积雪中的含铅量也足够解释海水中铅超标的问题了。于是一切的矛头都慢慢的指向了含铅汽油。
帕特森在对于沉积物的研究慢慢成型之时,简洁的阐述了他的结果“我们发现在积雪中发现的铅元素的存在形式和近10万年来在海底沉积的铅元素的存在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在拉森火山国家公园中,铅同位素的比例,充分地说明这是一种“人类从不同的铅矿中得到的混合物,而不是一种来自地表的天然化合物。”
《自然》在1963年发表了帕特森关于工业铅污染的论文。在这篇论文的脚注中提到了美国石油基金会赞助了此项研究。拥有这样的赞助人,却写出了这样的论文,即便是身为理想主义者的帕特森也都意识到,“我们摊上事儿了。”当他日后忆及这段经历的时候,“我用美国石油基金会的钱写了一篇发给《自然》论文,告诉他们‘污染来自含铅汽油喔’,呵呵…”于是不久之后,铅工业果然开始注意到他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