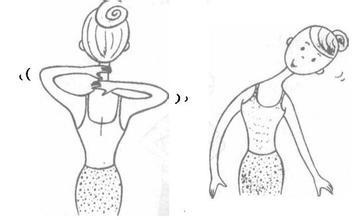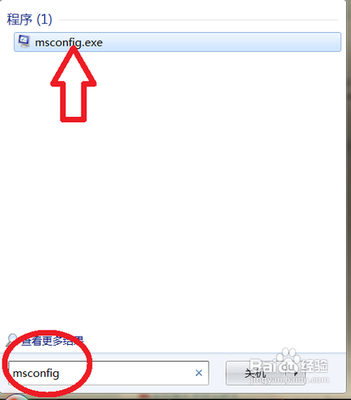朋友问我,你为什么最近如此喜欢,这些古典的美术和音乐作品?想起两年前第一次面对传说中的吕楠,他对@lens杂志 说的话:“看历史上那些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会让人踏实。会使自己保持一种状态,一种精神上的高度。”
他坐在北京“七九八艺术区”其中一间画廊的咖啡桌前。外面的阳光直直地泻到地面,透过落地窗映在他光亮的头上。此时,距离他拍摄中国精神病人已经20年,距离最近一部作品完成已经三年。他靠在沙发上,展开粗壮的四肢,用镜片后很审慎的微笑等待着记者的问题。这些年过去,到底如何评价这个人呢,以及他的作品?对面的吕楠,谦卑中带着不屑、羞涩处透出狂放……
精神病院的大教室里,吕楠收起相机准备离开。窗边那个大个子听到快门声,突然转身,直奔他而来,脚步重重、愣愣地握拳而来。大个子比他高一头,逃跑是来不及了,吕楠本能地半蹲下、背靠墙、胳膊护着两个相机,心想这一拳别打得自己脑震荡了。闭上眼、飚着劲,等着那一下子……
没有比画少女的红更难的了

《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的生存状况》,吕楠1989年到1990年的作品。那是辞去公职后的两年,“在养爷的地方干一辈子,我还不如吊死呢”。27岁,他开始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29岁,拍完病房里的病号、街头的流浪狂人、家庭中的无助肢体……吕楠停手了。因为他觉得完整了,以他当时的能力,再拍就重复了。于是,中国精神病的黑白世界,“吕楠三部曲”的开篇完成。
那个精神病院里的大个子冲过来的时候,吕楠脑子里一片空白。等他缓缓睁开眼的时候,看见的是对方直直伸过来的一只手,一只等待他回握的手,善良而粗壮有力。那是他在精神病院的第一次拍摄经历,也正是那次“历险”,使他义无反顾地深入一个个被我们遗忘的世界:乡村的天主教、西藏的农民、缅甸的戒毒所……其中的艰辛与收获,远非言语可及。
拍天主教,从县城下到一个有教民的村落,引起怀疑,村干部连夜骑自行车60公里到县公安局举报。结果人被请回县城,相机被没收;
拍西藏农民,在高原连续呆了九个月,从秋收拍到春播。等回到家,放完11乘14的片子,兜里真的没钱时,心里明白这可能成为最后一次的进藏……
吕楠所有的作品一应黑白,因为在他看来:黑白更适于表达严肃和永恒,没有颜色反倒更易达到深层的意义。但这也带来过麻烦,他曾用很蹩脚的藏语向藏族妇女解释,为什么她的BANG--DIAN(藏语:已婚妇女的围裙)在照片上没有颜色?结果很难说明白。他给你举画家夏尔丹的例子,“就像夏尔丹的那幅《家庭教师》,多少人临摹过,但那少女脸上的红就是画不出来。藏族人脸上就是那种黑中透出的红,想拍得好,没有比这更难的了。”吕楠每次进藏随身一台柯尼卡小相机,十卷富士的彩色负片,给藏族拍人像,自己从来不留,到县城洗出来,给藏民寄过去。西藏农民是“吕楠三部曲”的收山之作,从1996年到2004年,拍了八年。虽是黑白,但饱有感情,没有感伤。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承载着生活的快乐与艰辛。
吕楠1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黑白三部曲”。20多到40多岁,一段并不短暂,甚至略带艰辛的人生路。因为他的内心总对自己这样说----‘如果靠你的学识、你的良知,选择了一条路,而且你认为是正确的,走下去就完了,不要考虑它能带来什么报酬’。
他最常引用歌德的那句话是,“只要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冥冥中总有只手会帮助你。”而他在兄弟间讲出的原话则是:“(我的片子)你他妈爱用不用!只是他们,恰好就特喜欢,就用了。
摄影是瞬间的艺术?胡扯八道
“我有个请求,凡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话,一概不用。批评别人的,不要写。”吕楠如是说。我们答应了这个请求,因为席间三个小时的访谈,我们听不到什么贬低他人的话,那些话也不符合吕楠的人格和风格。如果我们以下引用的原话竟然令一些人不入耳,那一定是轻者自轻的选择。
2004年,吕楠最后一次从西藏回来的那天,包里塞满了900卷底片。休整了两天,开始自己配药。一天冲大约60个胶卷,凉干。六张一条,剪好、包起来、编号,显影、印片,主题归类、粗看一遍。拿出五倍或十倍的放大镜看细节,筛片……这样的速度,两个半月终于完成900卷的工作量。最后,把那几个自己吃不准的片子都放大,给马格南寄去。看看离下次出发还有一周的时间,开始手缠新胶卷,用吸尘器吸、刷子刷暗盒。一切就绪后,如果还有时间,就看书,看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使自己保持一种状态,保持一种精神的高度。”
吕楠是乐于引用名人名言的少数几个中国摄影师之一,可以想见的原因是,在孤独行走的15年里,他随身携带着很多艺术巨匠的作品。在这些大师多年的浸淫、感召之下,任何人都会拥有一颗脱俗桀傲的心灵。他拜读普鲁斯特十年,喜欢歌德、托尔斯泰,始终在研究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的不朽之谜,“这两个人的价值没有因时代的趣味转变而有丝毫的减损。因为他们笔下的人物代表着一类人,而非单独的个体”。
吕楠有三个住处,北京西单母亲家、丰台姐姐家,云南昆明自己的工作室,所有房间的书架上都找不到活人的作品,因为“看完伟大的东西后,会让你踏实。那些不到位的东西,更显得微不足道,真的不想看了。”
作为一名摄影师,你请他谈对中国摄影界的看法?“你要让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凡是与我工作无关的人和事,我一概不闻不问。中国的摄影界:我不了解,也不关注。”
你请他说说摄影的瞬间艺术,他找出早期在北京胡同里的一张抓拍的图片,“你知道我从不裁片子,当时我能感到有个孩子要经过镜头,我不能让他出画面,而且对面的那个跳皮筋的小孩又要正好跳起来……完全是经验判断,我抓到了这个画面。拍完这张片子,我马上觉得瞬间真是狗屎不如,毫无意义!我再也不触及所谓的瞬间了。”然后他给你耐心讲解布列松所处的那个印象主义时代,现在“摄影是瞬间艺术”的论调如何的不合时宜,如何胡扯八道。其实“吕楠三部曲”也是瞬间的集合,只不过我们在里面会看到更多的永恒。
你问他对摄影的摆拍怎么看?他的声调一下子提高三倍:“摆拍?这是个很脏的词。是一个弱智的、偏靶的伪问题,真正要探讨的是真实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呢?只要揭示、反映了生活的实质就是好的作品。最怕的就是不好不坏的作品,它们带给你的只能是困惑,学不到东西!”
天天网上扎堆秀自己照片的人,比80岁还老
吕楠1994年加入玛格南,成为玛格南在中国大陆的惟一摄影师,这个惟一一直保持到今天。而这一被众多媒体过分渲染的身份,却也是吕楠所刻意回避的。“你最好别提马格南的事,真的。我们中国人看这些东西是失常的,玛格南就是一个很光荣的图片社而已。”然后他会为你很耐心地讲解马格南的结构、分成方式,自己的通讯员、而非成员身份。“通讯员只要马格南过半数成员同意就可以了,好像是I打头的一个单词。台湾的美籍华人张乾琦就是正式成员,要三分之二成员通过才行。”前后讲十分钟,其谦谦的态度,令人唏嘘赞叹。
由于过于低调的风格,使媒体对他有无数的误读。比如说他的摄影受米勒和伦勃朗的影响,说他为生计接受各种企业的拍摄委托……而实际上它的家里没有一副米勒或者伦勃朗的画作,他从没有为生计发过愁,八年拍摄西藏农民,前后花费80万,从没有一次因为钱而耽误行程。因为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冥冥中总有只手会帮助他。当然,这些钱只能让他完成他的工作,“想腐化一把,没戏。有人说,先挣够钱,回来再搞艺术,你的质量已经下去了,你的精神高度再也回不来了。”
他认为自己的低调,是因为“有比抛头露面更重要的事情做”。他几乎拒绝在媒体上刊登自己的照片,因为“不想让已很丑陋的世界更加难看”。等真的见到本人时,我们确实产生迷惑,这个面貌并不和善的光头大汉凭什么赢得拍摄对象的信任?那些西藏农民、天主教徒,甚至精神病人、毒品贩子。吕楠最新的《缅北监狱》,在异国环境的成功深入,获得马格南成员的一致好评。用他的话讲:“不在熟悉的中国,我也能拍到,而且从容不迫、随心所欲。给了西方摄影师一个大耳瓜子!”其实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人的心里有他人,出于爱的作品一定比其出于恨的要持久。
2006年《缅北监狱》拍摄期间,吕楠与吸毒者、毒品贩子耳鬓厮磨了半年之久,没有做过危险的尝试,因为“尝了毒品睡不着觉,而我第二天还要干活。”他有太多想拍的东西,譬如家庭、譬如城市……“像普鲁斯特、乔伊斯这样的人,一本书就可以画个完美的句号。而我不行,我不能停。你知道,卖菜的也能说一句格言似的话,甚至一句真理,但不能说他就是先知。写博客的可能有一篇好文章,但有一连串的好作品才称得上作家。我还不想回忆,那些天天网上扎堆秀自己照片的人,比80岁的还老!”
然而今天,他开始出现在图片展的发布会上,开始不那么拒绝记者伸向自己的镜头,开始接受各类采访,甚至开始与朋友谋划城市题材的拍摄……我们惊喜地意识到:那个精神病院、天主教堂和青藏高原的吕楠,正在“回归”我们的视线,要以某一种身份介入这个华丽的社会了。毕竟,2006年到今天,他已经休息,或者说思考了太长时间,是出发的时候了
。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