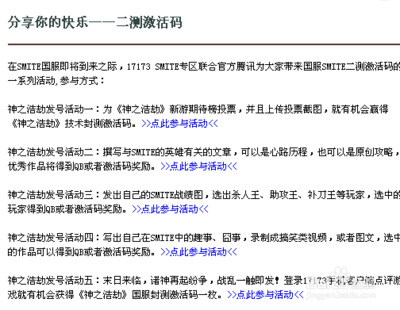司法如何获得国民的信赖
——评孙伟铭案判决
贺卫方

不独立的司法只能处于权力与民意的双重挤压中,无从前行
经过成都中院一审、四川高院二审,孙伟铭因为无照醉酒驾车导致四死一重伤而先判死刑,终审改为无期徒刑。二审宣判之后,最高法院马上表达对于判决的支持,并要求今后遇到此类案件将依照此例统一适用法律,均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
尽管本案受害人值得同情,醉酒驾车肇事也亟待加以惩罚和遏制,但是,法院对任何犯罪的处罚都必须严格依据法律,不可混淆有罪与无罪的界限,也不可在此罪与彼罪之间含糊其辞。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更是通过法治保障人权的制度前提。
遗憾的是,本案的审判正显示出我们的司法决策尚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在一些论者质疑的基础上,我们不妨再作出几点进一步的分析。
“交通肇事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的标题,该章涵盖跟危害公共安全相关的四十余种罪名,第一三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正是其中的一种。严格地说,“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一种类的概括或曰类罪名。请注意刑法的措辞:
第一一四条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破坏工厂、矿场、油田、港口、河流、水源、仓库、住宅、森林、农场、谷场、牧场、重要管道、公共建筑物或者其他公私财产,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一五条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二款略。)
从立法技术而言,这里采取了两类列举,一是对犯罪方法的列举,一是对犯罪对象或客体的列举。看上去有些笨拙,例如仓库很可能也是公共建筑物,不过列举本身就是限制,这也可以理解为显示了立法者力求防止扩大解释的意图。在放火等罪名之后用了“或者其他危险方法”的表述,是因为立法者无法做到穷尽所有犯罪手段,于是只好用这样的兜底或俗称的“麻袋条款”以便将未列举者包罗其中。当然,这里存在着某种与罪行法定原则相背离的倾向。所以,如果要将某一种行为纳入其中,需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其他危险方法”必须与本条已经列出者即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的危险性相当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另外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限定是,本章已经列有专门罪名的犯罪不得移花接木地纳入本条治罪。例如,刑法有专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
第一三三条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很明显,从分类学上说,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畴,但除非在某些完全突破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导致不特定人员死伤的犯罪才可以纳入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前最高法院副院长、著名刑法学专家刘家琛主编的一本权威的刑法解释著作举了这样的例子:
承德地区的一个汽车修理工李某,因犯罪误受了处分,心怀不满,在1983年7月的一天,将一辆大卡车开到剧院前,见剧院散场,就驾车向人群冲撞,当场轧死20人,重伤23人,轻伤5人,撞毁自行车29辆。(《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页445)
这的确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无疑超越了交通肇事罪的范畴,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无异议。但是,孙伟铭案件却与这种情况完全不同。
孙伟铭案完全符合交通肇事罪的要件
买车半年多了,他一直没有办驾照。平常请一名司机开车,同时也学会了开车,于是就经常无照上路。虽然也有过一些违章记录,但万幸尚没有出过大事。那一天他与父母亲一起参加一位友人的寿宴,喝酒不少。不过,散席后,他还是开车把父母亲送到火车站。离开车站后他的车就有些失控,超过规定时速一倍,与一辆车发生过追尾,但是并未停车,而是超车高速前行,很快就冲过道路中心双实线,与不远处的几辆车撞到了一起,现场一片混乱。头部受伤的他从副驾驶门出来,看到自己闯下的大祸,急忙呼喊,希望围观者中的医生赶快抢救……
现在,站在法庭上的孙伟铭面临着检方的严厉指控,他构成的不是交通肇事罪,而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证驾驶,酒后开车,超速一倍多,这些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最难以确定的被告人的心理状态:他对于最终的危害结果是积极追求或放任其发生,还是应当预见这样的后果但疏忽大意或轻信可以避免?前者就是故意犯罪,或者那种跟过失之间差异极其微妙的所谓“间接故意犯罪”,但后者就是过失犯罪。前者属于可以判处最高达死刑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后者则是最高七年刑期的交通肇事罪。
很清楚,无证驾驶、酒后驾车以及超速行驶都是导致交通肇事的常见情节。与此同时,本案中的一些情节足以表明孙伟铭不存在放任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他酒后驾车的目的是送他的父母亲到火车站,如果不是自信可以避免危害,他实际就是完全无视其父母及本人的生命,而检方根本没有证明孙伟铭有此心态。假如事故发生在到达火车站之前,假如其父母也在事故中伤亡,我们是否还如此信誓旦旦地确认孙伟铭属于故意犯罪?在审理中,检方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孙伟铭在其父母下车之后心态上有所变化,相反,当发生事故后,孙伟铭呼叫救人的事实却是毫无疑问的。招呼救人意味着他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从反面证明对他放任危害发生的指控不成立。
因为有关鉴定证明孙伟铭血液中乙醇含量已经达到醉酒的程度,而醉酒后驾车,控制能力当然就下降,也就是说会出现主观愿望与实际后果之间的差距。例如,对于车速的判断错误,对于某些正常状态下可以觉察的异常情况浑然不觉。如果追尾以及加速行驶都是由于孙伟铭已经处于醉酒后无法自控,那么所谓间接故意也是无从谈起的。人醉酒后的判断力会出现错误,侯宝林相声里的那个令人捧腹的故事讲两个醉鬼都不承认自己已经喝醉,都认为对方喝醉了:
甲“没喝醉?没喝醉,你来这个。”
乙 什么东西啊?
甲从兜里头啊,把手电筒掏出来啦!
乙 手电棒。
甲 往桌子上一搁。
乙 干吗呀?
甲一按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乙 哎,那光出来啦。
甲“你看这个,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
乙 那柱子啊?
甲 “你爬!”
乙 那个怎么样啊?
甲那个也不含糊啊。“行!这算得了什么啊,爬这柱子啊?你甭来这套。”
乙 嗯?
甲“我懂,我爬上去?我爬那半道儿,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呀?”
虽然有些艺术的夸张,但未必没有事实的依据。
对于辩护人在法庭上出示的孙伟铭所在单位同事、朋友、其资助对象的证明和证言,判决书说“与本案事实及定罪量刑无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本案的关键之一就是查证孙伟铭是否存在着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动机,他如果像前面举的承德李某的例子那样,存在着反社会的心理,或者对父母怀恨在心,或者有严重的轻生倾向,那么案件的性质就可能不一样。辩护人出示的这些品行证据对于本案事实认定以及定罪量刑大有关联,至少从辩方的立场看,它们可以证明孙伟铭不可能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故意。假如检方有异议,他们有责任作出相反的证明。
此外,对于本案二审时辩护人提供的“天网”视屏,法院拒绝接受,理由只是“视屏资料及相关分析不能确认孙伟铭所驾车辆在案发前与白色微型车发生过擦刮,也没有白色车车主的报案及相关痕迹勘验,确认该情节的依据不足”。但是,“天网”监控录像正是权威的证据,是否发生过擦刮、孙车是否因为擦刮受力而改变方向、孙伟铭是否因为躲避行人而急打方向盘从而闯入反向车道导致惨剧,对于这个关键情节,法院理当通过庭审一一澄清。假如辩护人所请专家不够权威,法院可以邀请权威专家作出分析。白色车车主没有报案,可以推迟审判,通过公告等方式寻找车主。事关事实真相,甚至关乎孙伟铭是否被判死刑,法院何必如此匆忙定谳?
粗糙的法律推理
更可奇的是,二审判决作出的下述怪异推理:
过于自信的过失是一种有认识的过失,即应当避免而没有避免。应当避免是避免义务与避免能力的统一。虽有避免义务,但没有避免能力,仍属于缺乏应当避免这一要件。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认为凭借自己娴熟的技术、敏捷的动作、高超的技能、丰富的经验、有效的规范,完全可以避免发生危害结果,但实际上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而未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在本案中,孙伟铭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也没有通过国家专门部门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更没有长期丰富的经验取得熟练的技术及意外处置能力,其酒后高速驾车之行为不仅完全丧失对危害的有效防范,而且也大大降低其驾驶危险交通工具的能力。因此,孙伟铭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避免能力,其无证、醉酒、高速驾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重大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必然的,其主观心理状态上的自信没有客观依据。
这段话有些绕,不妨仔细梳理一下。首先,法官认为,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有避免危害结果的能力是构成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的前提。但是,某些人会“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用“力量”一词有些奇怪,姑且不论),因而就发生了危害结果。这里说的还是一种心理状态,即行为人是否意识到自己有避免危害的能力。但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认识错误,错误的认识也是一种认识,基于错误认识产生的自信就是所谓过于自信。因此,与其说“应当避免是避免义务与避免能力的统一”,不如说是两者的不统一。那么,问题马上就会提出来:为什么孙伟铭无照酒后驾车就不属于基于对自己能力的过于自信?
法官接着要论证“孙伟铭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避免能力”,但是逻辑的前提是要证明孙伟铭对自己的无能力的无认识。但是,证明心理状态的方法却是无证因而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和缺乏长期的驾驶经验等。但是,即便孙伟铭确实因此而处理意外情况的能力低下,这并不影响他很可能恰好属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的那类人。况且驾龄短未必一定毫无能力,法官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许忘记了判决书前面引述孙伟铭的供述,他曾驾车沿高速公路从成都到重庆!我曾乘车走过那条路况不甚好的成渝高速公路,那可是需要相当驾驶技术和意外处置能力的行程呢。那么远的高速公路都可以平安而归,为什么他在成都市区开车反而没有了自信,而且还彻底丧失了产生过于自信心态的能力?
当然,还有醉酒,法官说,“酒后高速驾车之行为不仅完全丧失对危害的有效防范,而且也大大降低其驾驶危险交通工具的能力。”“完全丧失”的说法缺少法律人言说应有的严谨,能力降低倒是没有疑问。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不正是孙伟铭盲目自信以及愿望与结果之间发生落差的原因么?
这段推理的结论是:孙伟铭“无证、醉酒、高速驾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重大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必然的,其主观心理状态上的自信没有客观依据。”言之凿凿的语气掩盖不了其间的逻辑混乱和论证乏力。醉酒高速驾车极易发生事故是事实,但说是“必然的”,不知道法官的这一结论又有怎样的客观依据?
“辱己以正天下”的司法
人类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是否拥有公正的司法制度,是一国能否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以及增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前提。司法制度的公正无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揭示案件事实真相,法庭理性的态度、对双方举证等程序权利的保障、对证据的细致审查和审慎判断等。另一方面是法院忠诚于法律,在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上诚心正意,不屈法,不妄断,以维护法治的尊严。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司法的独立性。不独立,则必然受制于法外的权力,扭曲法律,导致司法的恣意和随意。与此同时,不独立,也会削弱法官的责任心。某些判决书之所以论证漏洞百出,甚至文字都不通,也许并非由于法官的能力低下,而是因为某些案件法官和一般公众都知道,案件的结果并非法庭上同时也是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所为。既然决策责任不在自己,用心较劲,精益求精都是没有必要的。
鉴于时下醉酒驾车导致重大惨剧频频发生,不少人认为现行刑法对于交通肇事罪所规定处罚太轻,不足以遏制此类犯罪,也难以补偿受害人及其家人所遭受的苦难。实际上,这种以重刑阻却犯罪的思路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贝卡利亚早就讲过这样的道理,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严厉,而在于违法行为都会得到制裁。相反,“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犯罪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一次犯罪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也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不仅如此,即便刑法规定的刑罚偏轻,法官也不可依据他们自己对正义标准的理解,超越法律判决案件,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惟一的解决之道只能是立法机关修订法律,而且修订之后的法律也只能适用于新法生效后发生的案件,否则就违反了法治的另一准则:法不追溯既往。
最后,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细节也值得略加讨论:孙伟铭案二审在成都开庭并宣判的当日,远隔千山万水的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尔梅表态支持四川高院的判决,并表示今后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结果发生,造成重大伤亡者均依刑法第一一五条第一款定罪处罚云云。从时间上判断,最高法院根本不可能在对于四川高院的审判过程进行仔细了解和分析之后再做出评论,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四川高院二审之前已就判决结果请示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实际上就是最高法院,虽然名义上是四川高院。当然,与此相对应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四川高院的审判属于典型的先判后审,所谓审理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可怜两位辩护律师还提交新证据,与检察官激烈辩论,苦心孤诣,力图说服法庭改变案件的定性,殊不知一切都在此前确定,律师所作所为皆是无用功。连最高法院都无视下级法院基本的独立性,践踏程序正义,如此司法如何可以获得国民的信赖,如何能够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判决?
孟子曰:“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罔顾法律准则,自坏正当程序,迎合非法干预,我们的法院就是在枉法辱己。希望这样的法院实现社会正义,真正是只好等待黄河清了。
原载《西部法学评论》(甘肃政法学院主办)2010年第3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