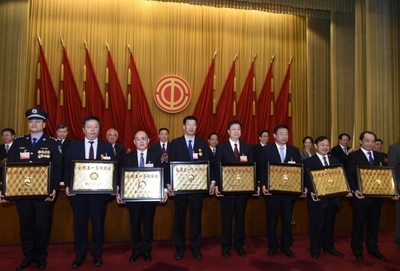《飞行少年》是部入围台北电影节台北电影奖纪录类组的影片,纪录一群失亲失养、遭家庭或学校遗弃、身心都伤痕累累的孩子们,在他们冷漠淡然的眼神、桀骜不驯的态度、佯装坚强的外表之下,只有一颗期待被关怀、被注意的心!这群孩子,来自花莲信望爱少年学园…。
甫以《飞行少年》一片获得余纪忠文教基会「映像公与义」纪录片首奖的纪录片导演黄嘉俊,花了一整年的时间跟著一群处在社会缘缘的孩子生活,纪录他们骑单轮车环岛的壮举,也见证了这群孩子愈挫愈勇、跌倒了再爬起来的成长历程。「纪录片工作者似乎一直在等待事件发生,我很幸运的面对一群每天都有事发生的孩子,只怕我不在现场而已。」
「飞行」少年意指行为偏差、失亲失怙、被家庭或学校遗弃的「非行」少年,他们在花莲信望爱少年学园接受辅导教育,随时准备重新回归正常教育体系。二○○六年的夏天,在观护人卢苏伟、黄明镇牧师及老师们的陪同下,三十个小朋友花了二十天的时间,骑著单轮车环岛一千公里,在当时成为新闻焦点。
黄嘉俊并未用使用过度煽情的剪接,只是冷眼记录一群孩子努力学习重回社会的奋斗过程,平凡间存在几许老练世故,多少跟他的人生历练有关。
《飞行少年》 -导演
《飞行少年》 -导演现年三十五岁的黄嘉俊,在家中排行老大,国中毕业后便一个人前来到台北念国四班,之后升上高中,并在世新大学念了四年电影。「父亲对我们几个兄弟非常信任,他说我们不管做什事他都不会阻止,只要自己能负责。」有这么大的包容的空间,让黄嘉俊的学习之路走得比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更宽广,求学阶段热中文学、绘画与爵士乐,还曾到乐器行兼差教学,大二开始就开始当接案导演,入伍前更考上「最爽的单位」国防部示范乐队,才华洋溢的黄嘉俊「等著继续过著白天当兵吹乐器,晚上四处闲逛的悠哉生活。」
没想到因为兵役单位的疏失,竟让黄嘉俊被转到最操的战斗部队,从天堂掉到地狱,「前半年的魔鬼训练让我非常不快乐,感觉自由自在的心灵被囚禁了,一身的才艺无法发挥。」生命无端被消耗,让黄嘉俊的生命陷入最低潮,「那时还有看到别的弟兄被不当管教,拳打脚踢的,现在想起来还不敢相信那是发生在九○年代末的事情。」
不过一九九九年一场九二一地震,完全改变了黄嘉俊对生命的看法。凌晨两点地震过后,他与营区弟兄接到指令进入台中新社灾区展开救灾工作,「我到现在还记得与另一位弟兄从瓦砾堆中抬著第一具尸体出来的感觉,那位阿伯的身体还是温的。」他们陆续将尸体运至营区的餐厅,或将伤者送至临时安置中心,转眼不过四个小时,餐厅已摆满了一百五十具尸体。
「我还曾经眼睁睁看著一位被救出来的伤者,看来并无大碍,却在喝了一口水过后,就在我面前死掉了。」面对生命的脆弱及无常,原本被囚禁的心灵反而释放了,接下来的救灾工程毕竟是有意义的,不必操练,不必看长官脸色,加上与重建区的民众朝夕相处长达一年之久,日子反而过得相当充实。「晚上跟著弟兄喝著维士比加咖啡提神,听受灾户讲故事,感觉好像在很多时间经历了每个人的生命。」

退伍之后,黄嘉俊先是在咖啡店上班学习煮咖啡,后来有机会参与瞿友宁(原误植为曲佑宁,谨此更正道歉,并感谢网友指正)导演《人生剧展》的工作团队,开始回到当初所学的专业,不过两年时间下来,他发现这样的工作型态似乎只有导演最有成就感,其他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过得不开心,甚至必须扭曲自己的性格来面对工作,让他很不自己。于是他便离开工作,一个人到尼泊尔旅行一个月,「我发现那个地方的人很穷,但人人都很快乐,这又让我想到生命的本质,我开始去思考我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怎样的我才会快乐。」
回国以后,黄嘉俊到三立电视台担任《中国那么大》的编导工作,到处旅行,后来又参与公共电视《古典魔力克》、《下课花路米》、《非常有艺思》等节目,并获得广播电视小金钟最佳导演的荣耀。黄嘉俊的能力逐渐受到肯定,也因为制作相关儿童节目,让想要拍《飞行少年》故事的团队找上他,开启另一段参与别人生命历程的神奇之旅。
《飞行少年》 - 花絮
一开始与这项计画的策画人卢苏伟及黄明镇讨论时,还一直犹豫是否要让孩子们入镜,如何入镜,要不要打码赛克等细节伤脑筋,直到几位孩子打断他们的对话:「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被拍?我们也很想当主角耶!」于是在征询学员及家长的同意之后,影片顺利开拍。片中最令人震撼的一幕,莫过于一开始镜头扫过学园每一间寝室,时间彷佛长达一世纪之久,令人鼻酸这个社会竟有这么多的苦命儿。不过习于正思考的黄嘉俊,看到的却是这些孩子悲惨故事背后的坚强,当他们挥洒汗水与眼泪,镜头也跟著起雾,而每一次摔倒在地的画面,其实也都撞击著包括导演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心。有趣的是进入环岛行程之后,每个人的喜悦写在脸上,这不只是自我挑战的严格考严,许多从小到大未曾旅行的孩子,想到的尽是书本上看到的美丽景点,与未曾谋面的花花世界。而到后来项计画受到媒体关注,每天都有媒体前来采访,而每个人的心情又都各自不同,大家期待自己能上镜头,「为何他可以上镜头,我不行?」「如果上镜头要讲些什么?」严重干扰他们的行程,以致后来完全拒绝接受媒体访问。
「我后来还跟著他们跑遍了全台湾各大监狱作经验分享,看到的景像更震撼,这些人几乎完全被人遗忘,彷佛不存在一样。」这也促使黄嘉俊完成「监狱三部曲」的拍摄念头,在《飞行少年》之后,他打算接著拍更生人与受刑人的故事,拜访这些被禁锢而渴求自由的心灵。
历经才华受到肯定、彷若天之骄子的轻狂岁月,继而接受军旅生涯的残酷考验,让黄嘉俊的心情犹如洗三温暖,九二一地震之后,则让黄嘉俊对人生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现在我很喜欢引用黄明镇牧师的口头禅:『一切自有上帝安排。』」黄嘉俊用自己的方式维持兴趣与志业,并持续用镜头关怀这个社会,在数度「飞行」之后,显然已找到自己生命的节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