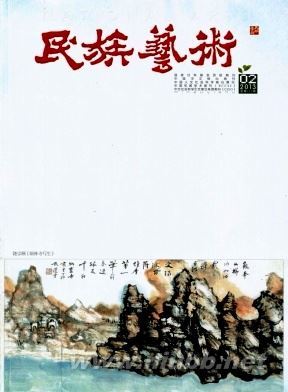影响与借鉴——略谈两篇《狂人日记》
1834年的俄国和1918年的中国,分别诞生了两部名字相同、文体相同、人物相同、风格相同的作品———《狂人日记》。由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在前,中国作家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后,因此,自鲁迅的《狂人日记》问世之日起,关于两部小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研究就从未终止过。老愤青在参阅专家学者相关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简要谈谈这两篇小说,主要谈谈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主要谈谈它们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什么联系呢?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又说: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鲁迅的这段话表达了以下含义:其一,他的《狂人日记》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影响的结果。其二,他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其三,他日后的作品“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艺术上更加成熟,但热情却减弱了,读者关注的程度也有所下降。这一切都验证了鲁迅所主张的“拿来主义”的思想: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一、两篇《狂人日记》之间的联系
两部一样名字的佳作:《狂人日记》。两部一样文体的作品:日记体小说。
当我们面对“日记体小说”这个文体的时候,却发现它不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产物。中国小说的典型形式是以故事情节为框架、以人物刻画为目的的章回体。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等,都是章回体小说的杰出范例。即便在现当代,也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缘》、《金陵春梦》、《林海雪原》、《烈火金刚》,乃至金庸等创作的章回体小说出现。日记体小说的母体是日记。西方文学中,日记是“一种自传性文体,为作者本人对每日发生事件的观察,或这些事件与他的关系的记录。”日记盛行于文艺复兴末期,繁荣于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一些作家的日记不仅是后人走进他们心灵世界的钥匙,也是研究其文学创作的珍贵资料。日记体小说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日记的日记体裁的小说。
从形式上看,它好像与日记不无两样,而从实质上看,它是地道的小说,是日记与小说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日记体小说就兼有日记与小说两种文类的特征。从日记体小说的源头上看,可追溯到日记十分盛行的18世纪的欧洲。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就已经具备了日记体小说的某些基本特征。之后,这种“偏重于抒发作者强烈奔放的主观感情,着重描写对事物的内心反应和情绪体验。……摆脱故事的束缚,有利于作者进行自我表白和情绪宣泄”,有利于“作家直接抒发感情”的“最便捷的方式”,一直受到西方作家的青睐。时至上个世纪,仍有萨特的日记体小说《恶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浸润着西方文坛。
中国的日记体小说开始于鲁迅的《狂人日记》。这部由13则日记构成的小说,不仅拉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序幕,开创了中国小说的新局面,而且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发出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线,一大批日记体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石评梅的《林楠的日记》,乃至茅盾的《腐蚀》等,形成了一种魅力独特的文学时尚。在上述日记体小说中,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独占鳌头,而且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腐蚀》一道,构成了中国日记体小说的三座高峰,并由此而奠定了自身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它“在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不可磨灭的地位,它博大的历史内涵、伟大的思想意义,以及艺术上的独创性”等都不容质疑地被学术界所一致认可。
然而,从世界文学的发展来看,鲁迅的这部划时代的杰作,又恰恰是俄国文学直接影响的结果。这样一来,鲁迅的某些独创就不能视为独创了。因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使用的文体,果戈理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就已经使用过了。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脱胎而出,能够记在鲁迅同名小说功劳簿上的,恐怕就只有“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这一个方面了。这应当是对鲁迅及其《狂人日记》的一种相对客观的评价。
从文体的角度上看,果戈理的小说是“日记”,鲁迅的小说也是“日记”;果戈理小说中的“日记”为“狂人”所写,鲁迅小说中的“日记”也是“狂人”所为;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为第一人称,鲁迅的《狂人日记》也不例外;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按照日记的要求记述了“我”在当天的所见所闻,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记录了“我”对当天经历的所感所思。虽然在时间上有较大幅度的跳跃,没有那么连贯,但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进行的,对当天事件的记载还是具体的,从“日记体”的角度上,这无可厚非。
从篇幅上看,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20则,鲁迅的《狂人日记》有13则。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每则都有明确的日期,从相对具体的10月3日、4日开始,历经11月和12月的数天,再跳跃到2000年3月43日和3月86日,乃至后来无法辨别的某月、某日等,尽管有些荒唐,但依旧符合“日记”的特征。相比之下,鲁迅的《狂人日记》并没有明确地标明日期,而是用中国数字的“一”、“二”、“三”……来表示,尽管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表现出一点差异,但仍未超出“日记”的文体范畴。从文学角度上看,两部作品又不仅仅是“日记”,而且还是小说。因为每则日记并非对“我”当天所经历的事件的简单记叙,同时还夹杂着深层次的思考。单纯的日记一般一日一记,一事一记,前后并无大的关联,而两部《狂人日记》联起来可以构成一个整体,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人物形象。
在文体结构上,如果说要寻找两部作品的不同的话,那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尝试,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点。”正是鲁迅的这一独创之举,使借用于果戈理的“外来”文体本土化了,使“日记体小说这种‘舶来品’完全民族化了。”
二、两篇小说的人物
两部小说,一样的文体:日记。两部小说,一样的人物:狂人。
如果说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对鲁迅的同名小说在文体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果戈理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对鲁迅的同名小说中人物的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果戈理的文体是日记,鲁迅的文体也是日记;果戈理的小说是“狂人”的日记,鲁迅的小说也是“狂人”的日记;果戈理笔下的主人公是“狂人”,鲁迅笔下的主人公也是“狂人”。果戈理笔下的“狂人”叫波普里希钦,他是一个小职员,一个九等文官。要论工作嘛,还算清闲:为他的领导———司长削鹅毛笔。而论起在司里的地位来,就十分寒酸。司长瞧不起他,把他当仆人使唤;科长瞧不起他,有机会就对他训斥;司长的仆人也瞧不起他,对他时时加以怠慢;司长女儿的狗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说他是一个丑陋的人,头发像干草,活像一个套在肥大衣服里的乌龟。然而,在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心灵深处,也有美好的精神追求,也有幸福的爱情憧憬。他爱恋司长的女儿,只要这个女孩出现,他就魂不守舍。为此,他想象司长女儿的生活,想象她的客厅、她的卧室,想象她穿衣时的情景。当他觉得光凭想象也无法解决自己的思恋之情时,就利用自己能够听懂狗的语言,看懂狗的文字的“特异”功能,试图从司长女儿的狗那里着手。于是,他偷来了狗的信件,在阅读中满足自己的欲望。从狗的信件中,他知道了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从狗的信件中,他知道了自己在这条狗眼中的形象;从狗的信件中,他知道司长的女儿在恋爱;最后,从狗的信件中,他得知司长的女儿要结婚了,她的爸爸希望女儿嫁给一位将军,或宫廷侍从官,或上校。至此,波普里希钦的心灵世界彻底崩溃了:“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不是被宫廷侍从官们就是被将军们捞去了。”他心中所刚刚幻想得到的东西,也被宫廷侍从官或将军们抢走了!波普里希钦疯了!他不断地为自己升官,在幻觉中觉得自己当上了西班牙皇帝。他大胆地不去司里上班;他上了班也不把科长和司长放在眼里;他勇敢地闯进司长女儿的房间宣泄自己的情感。走在大街上,他认为自己在微服私访;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也以为到了西班牙。最后在残酷的折磨中,他终于呼喊出:“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
鲁迅笔下的“狂人”既不是小人物,也不是小职员。从尚有“佃户”的身份上看,应当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人,而且还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者”。也正是由于这种“叛逆”,使他在村子里处处碰壁,多有“杂无伦次”的“荒唐之言”,患上了“迫害狂”之病。尽管他十分小心,但不论在行走中,还是在睡梦里,都感到十分的恐怖。赵家的狗对他虎视眈眈,赵家人的眼光也格外的怪;路上的人见了他交头接耳,孩子们见了他也议论纷纷;母亲骂孩子时话中有话,家里的人见了他也视为陌路。他失去了自由,被关在家里,每日与两餐为伴。大哥请来的医生是刽子手,大哥也加入了迫害他的行列。赵家的狗又咬起来了,“我”被囚禁在“监牢”中等待不祥的命运。联想到中国数千年的吃人历史,联想到亲人的被吞噬,“我”终发出了凄惨的呼喊:“救救孩子……”。
果戈理笔下的“狂人”开始并没有“疯”。他从正常到不正常,经历了一个渐变的心理过程。从日和内容上看,他的前11则日记:10月3日、10月4日、11月6日、11月8日、11月9日、11月11日、1月12日、11月13日、12月3日、12月5日和12月8日是正常的,除了能听懂狗的语言,看懂狗的信显得有些荒诞外,还是一个意识清醒的人所为,日记中的内容还是一个理智正常的人所记载的正常件。波普里希钦发狂的转折点在第八则日记:11月13日。这篇日记记载了波普里希钦在狗的信件得知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尤其是得知他如此深爱的司长女儿索菲在谈恋爱,甚至要结婚的消息后,被压抑已久的自卑心理开始变形了。
如果说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真疯的话,那么鲁迅笔下的“狂人”则根本就没有疯。如果说果戈理笔下的“狂人”的疯是医学诊断的结果的话,那么鲁迅笔下的“狂人”的疯则是由别人,由那个社会强加的。
大哥对众人的高声吼叫无异于对“我”的一次“宣判”。果戈理笔下的“狂人”由于疯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鲁迅笔下的“狂人”则由于疯被关进了不是牢房胜似牢房的“家”。一个本是有身份的人家的人,就由于背叛了已有秩序而被视为另类,被污蔑为“迫害狂”,被指认为“疯子”。于是,这个旧秩序的叛逆者,这个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狂人”就时刻在要被他人、被亲人、被社会“吃掉”的险境中说起了真实而清醒的“疯话”。
果戈理笔下的“狂人”说的是地道的“疯话”,因为他在巨大的打击下,在精神上出了问题,他是一个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鲁迅笔下的“狂人”说的是地道的“狂话”。这个旧传统、旧道德的叛逆者,在即将被“吃”的危机时刻所讲出的“杂无伦次”的“荒唐之言”,是掷向那个社会的一杆投枪。这应当是鲁迅在接受了果戈理“狂人”影响的基础上,对“狂人”形象的升华。
三、两篇小说的风格
相同的人物:狂人。相同的艺术:讽刺。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史册上,果戈理是一位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家。这位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的奠基人,不仅继承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成就为俄罗斯文学开辟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时期———果戈理时期。谈及果戈理的艺术成就,人们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他那卓越的讽刺艺术。这种具有民族传统的艺术手段,正是在果戈理的手中得以发扬光大。也正是天才的讽刺艺术才使果戈理成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史册上,鲁迅也是一位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家。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以其强烈的叛逆精神、丰硕的文学创作、丰厚的文学译作和见地深刻的文学批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光辉的旗帜。在鲁迅的艺术成就中,讽刺艺术表现得十分鲜明。在他充满批判精神的小说中,在他言辞犀利的文学批评中,在他“痛打落水狗”般的杂文中,讽刺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一切又源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
果戈理的讽刺是幽默的讽刺,是含泪的讽刺。对此,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指出,“他的全部中篇小说都是这样:开始可笑,后来悲伤!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开始可笑,后来悲伤!”“果戈理的这种独创性,表现在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之感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里面,”使人笑中含泪。果戈理的讽刺风格对鲁迅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回忆青年时代所接受的外国作家的影响时,鲁迅深情地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
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评论家在论及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时指出:在这篇小说中,果戈理的笑声急剧地转化为眼泪。开头它是一个很可笑的故事,……而结尾时却是一位无名的母亲在哭自己的儿子。他大声呼唤着要回到母亲的身边,并且听到“雾霭中的琴弦”的声音。当读者走进《狂人日记》的故事时,除了“可笑”之外,并没有感觉到弦外之音。波普里希钦的傻里傻气,对周围一切的荒唐感受,对司长女儿的单相思,以及听得懂狗的语言、看得懂狗的信件的“特异功能”,会不时地引来读者的笑声。这是幽默的笑、嘲讽的笑。然而,当波普里希钦得知司长的女儿要嫁人,天下的好处都要被上等人抢走而发怒发疯时,人们的心头就不免一颤。“为什么我是个九等文官?”
不仅在折磨着波普里希钦,也在敲击着读者的心弦。最后,当波普里希钦被关进精神病院还以为去了西班牙,被残忍地折磨还以为是西班牙的风俗时,人们的心就在发抖。当痛苦不堪的波普里希钦发出:“妈妈,……把可怜的孤儿搂在你的怀里吧!……妈妈!可怜可怜你的病孩子吧!”的呼叫的时候,眼泪会不由自主地从读者的双眸中流出。这“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将这个小人物的悲剧推向了高峰。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狂人”就是“疯子”或“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词。尤其是鲁迅在序言中用近乎“病历”的格式和“迫害狂”、“供医家研究”等描述性词句后,人们对“狂人=疯子”的看法已坚定不移。既然是疯子,那么必然要产生荒唐的举动。在“狂人”的眼中,人人都想“吃”他,甚至包括赵家的狗。大人要“吃”他,孩子也要“吃”他;邻居要“吃”他,佃户也要“吃”他;医生要“吃”他,哥哥也要“吃”他;医学上有“吃”人肉治病的药方,书上有“易子而食”的历史;妹妹被哥哥“吃”了的时候,幼小的“我”也许跟着“吃”了一片……通篇都是“吃人”的描述,通篇都是要被“吃”的恐惧。既然“疯子有什么好看?”那么“疯话有什么好听?”既然是“迫害狂”患者的“狂言”,那么人们就只能权当茶余饭后的一柄笑料了。然而,当我们循着“狂人”关于“吃人”的“狂语”一步步走下去的时候,当“狂人”纵古论今将“吃人”的历史一一掠过的时候,当“狂人”在犹疑的语气之中说到“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并且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的时候,人们方才领悟到那句曾经被看作“狂言”的讽刺与批判的力量:
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鞭挞和揭露,就这样被鲁迅借助“狂人”之病言,“迫害狂”之病语,在“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之中,发人深省地展示出来。果戈理对鲁迅的影响是直接的,但鲁迅的同名小说并非对俄国前辈的“克隆”,而是在借鉴和模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拿来主义”原则,将外来养分有机地融化在自己的创新之中。
四:赘语
我们前边主要谈了谈这两篇小说之间的联系,谈了它们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其实,这两篇小说还有很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是两者的文化语境、文化意识的不同,鲁迅先生的小说侧重体现的是“治国教化”,而果戈理的小说离不开东正教这一重要的文化语境,因而,他的小说侧重体现的是“自我救赎”。其次,两位大作家的哲学观念不同,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期,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尼采的哲学,而果戈理的哲学思想渊源则主要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和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所借鉴,更有创新,至关重要的是拿来之后,可以用来医治我们自身的顽疾,并开一代小说之风,这恐怕是鲁迅先生之最伟大之处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