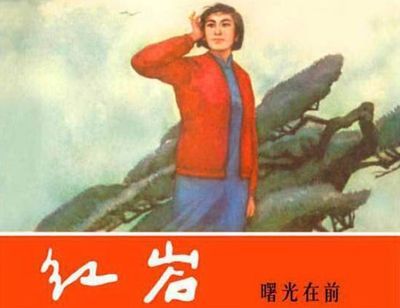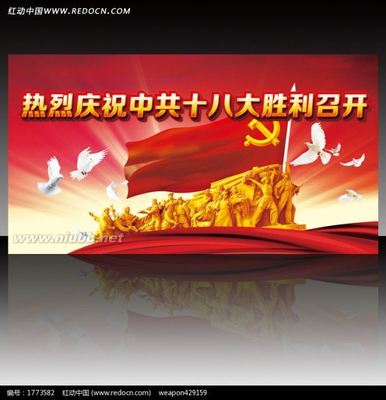郦道元《三峡》完成的历史过程
手记:
不少赏析郦道元《三峡》的文章,均认同《三峡》“自然美”的反映说,等而下之的甚至坐实到“实感”上去。其实,三峡的美的性质是由人的情志决定的,郦道元《三峡》的语言经历了上百年的积累、提炼才成为经典,在中国古典散文史上,罕有超越者。直至二十世纪有了现代性的发展:刘白羽以政治哲理,南帆以质疑解构,楼肇明以冷漠“丑化”,余秋雨以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的互释延续着艺术的探险历程……
这是一篇经典性的散文,已经有了不少的赏析文章,但是没有令人满意的。原因在于,此类文字,一味限于赞赏。试举一例:
先从大处着笔,本百里三峡……正面描写,巧用夸饰,极山高,再状夏日江流,以日行千里的江舟作侧面描写,对比衬托,春水大流急,令人惊心动魄。仰视高山,俯瞰急流,体物妙笔,将巫峡山水描写得生动逼真。(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5001年,第521页。)
这并不是此类所谓赏析文章中水平特别低的,但是在观念上,方法上、文风上可以说具有普遍的代表性。通篇文章可以说完全是废话,没有一点具体分析。原因是作者的观念僵化,文章的观点落实在“体物”“逼真”上,与《三峡》的文本的精彩根本不沾边。
其实,《三峡》的描绘的景观并不以逼真取胜。首先“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就不能算是逼真的。到过三峡的人都知道,三峡的两岸并不是七百里都是同样高度的悬崖绝壁,高低起伏是山之所以为山的特点,不可能是“略无阙处”。中午才能见到太阳,午夜才能见到月亮,也只是部分航程如此。其次,“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也不是写实的。一般情况下行舟是很慢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写到三峡的黄牛滩曰:
江水又东,径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两(四库本作“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经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1]
舟行三峡不但是很慢的,而且是很凶险的。当年三峡有礁石,尤其瞿塘峡,那里的礁石相当可怕。文献记载很多。杜甫晚年的《秋兴》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白牢关。”
作者论定郦道元此文写得“逼真”,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前提:郦氏亲临其境。其实是糊涂的想象,当时南北朝分治,郦道元在北朝为官,蓦然到南朝辖治下的三峡旅游,肯定要当俘虏。把郦道元的成就,归功于亲历的观察从而产生逼真的效果,暴露了作者在观念上的两大局限,第一,对机械唯物论的拘守,第二,对审美价值的无知。
其实,就是亲临其境,也未必能写出这样的经典名文来。郦道元《水经注》中“三峡”注文中就有袁山松的文章:
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有称山水之美也。[2]
袁山松明确指出,多少年来,口传和书面记载,出自一些亲临的人士:从来没有提及这里的山水的美好(“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相反倒是,“悉以临惧相戒”,全都是以可怕相告诫。如果是逼真的,那也是可怕的。而这个袁山松先生恰恰相反:
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故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3]
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难道那些把山水之美看得很可怕的人们,他们的感知难道不是“逼真”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山川,袁山松却能“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毫无生命受到威胁的感觉?这是因为,恐惧的感觉,生命受到威胁的感觉,属于实用理性,但是情感与理性是一对矛盾,情感超越了实用理性的才能进入想象的、假定的境界,也就是超越了“逼真”的境界,情感获得了自由,从而进入“审美”境界,对这个境界,袁山松这样称述:
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4]
无生命的山水,被假定,被想象为“有灵”,不但有灵,而且成为他的“千古”“知己”,这明显是从“逼真”上升到“想象”。因为一味追求现实的“逼真”,就不能不陷入被动,变成现象的罗列,越是追求“逼真”,越是芜杂。想象越是超越了“逼真”,情感越是超越了实用,才可能对现象进行选择和同化,使物象与情志统一,构成形象感染力。
而赏析文章的作者,用了一系列流行的套语:“大处着笔”,“体物妙笔”,“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对比衬托”,“令人惊心动魄”,都是废话。原因盖在于作者内心的有一种于被动体物,机械模写为上的准则。殊不知文学性的形象,都是虚实相生的,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早就说过,艺术乃是“逼真的幻觉”,只有通过假定才能达到表现审美情志的真诚。
从思想方法上说,作者行文不着边际的原因还在于,文章号称赏析,当以“析”为核心。“析”乃分析,分析的对象乃是矛盾/差异,可通篇没有接触到《三峡》文本的内在和外在矛盾,因而无从分析,也就不能深化,只能在文章表面滑行。
其实,矛盾明摆着:郦道元根本没有去过三峡: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二十五.地理类二.水经注》卷六十九中这样说“后魏郦道元”
至塞外群流,江南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经。纪载传闻,间或失实,流传既久,引用相仍,则姑仍旧文,不复改易焉。[5]
一个从未到过三峡的人居然写出表现三峡的绝世名文,完全是靠想象吗?想象也是可以分析的。
一方面,通过想象写出经典散文并不是个别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就并没有直接到现场观察,而是在河南邓州想象的。另一方面,想象也有胡思乱想,架空的可能。就算不架空,光是在想象中把自由的情感转化为艺术的语言,也可能失败。因为情感是无序的,而且往往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并不是在心有情,发言就一定成文的。从想象、情感到语言的艺术化,既是灵魂的升华,也是语言的探险,其间要经历许多艰险。
郦道元这所以获得如此的成功,关键是在他以前,众多文献在语言上,已经有了许多历险的记录,多种版本为他准备了精彩的素材,主要是袁山松(?--401)的《宜都记》和盛弘之[6]的《荆州记》。有人因而认为郦道元不过照搬了他们(尤其是盛弘之)的文字。[7]这个说法是不够全面的。且看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袁山松的《宜都记》中对三峡的描写:
峡中猿鸣至清,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为三声泪沾衣。[8]
自西陵溯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山行周围,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曰月也。[9]
这个袁山松很有情感的超越性,他笔下的三峡,前一段写猿鸣,可谓秀美,其情调乃是悲;后一段写江岸,宏伟森严,可谓壮美,其格调乃是雄。但二者不相连属。而我们今天从郦道元的《水经注》中看到的文字,是出自《荆州记》(成书约于432—439年间),《荆州记》目前原书虽失,但其描绘三峡的语句仍然存在于一些古籍中。据稍后于盛弘之三十年左右的刘孝标(462—521年)注《世说新语·黜免篇二十八》所引,盛弘之的文字是这样的:
峡长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绝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10]
显然,盛弘之把袁山松的山行旅游(“行三十里入峡”“复通高山”)改写成“两岸连山,略无绝处”,造成舟行的感觉,把“重嶂”改成“重岩叠嶂,隐天蔽日”不但提高了意象的密度,而且在节奏上也变得严整。而到了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里,《宜都记》中对于三峡两岸的描写(自西陵溯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山行周围,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曰月也。)则变成了: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郦道元把“日中夜半”改成“亭午夜分”,把“日月”改成“曦月”口语性质的白话因用了典故(日神羲和)而变得高雅。本来袁山松的原文直接从“高山重嶂”转入“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多少有些突兀,郦道元增加了“隐天蔽日”,为下面的“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提供了自然的过渡,意脉更加流畅。
在袁山松《宜都记》中,也写到猿:“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是相当精炼的,但是,其基本格调,聚焦在“清”和“泠”。对于袁山松的描述,盛弘之可能不太满意,把“猿鸣至清”改成了“高猿长啸”,一个“啸”字,就把清冷(凄凉)带上了凄厉的意味。盛弘之又把袁山松的“泠泠不绝”(不断)变成了“属引清远”,意味就多了一层:猿声相互连续,此起彼落,“清远”就不仅仅是不断,而且是越来越远,愈远愈弱,然而愈弱愈“清”。民歌的词语也有改动,袁山松记载的是:“巴东三峡猿鸣悲”,与下句的“猿为三声”有重复。盛弘之还把“猿鸣悲”改成了“巫峡长”,这一改改出了意境,原来只是猿鸣不断,只是时间的延续,改后变成此起彼落,又有了巫峡悠长,猿声是在巫峡漫长的空间中回荡的,其效果,就由内心的悲凉,泪沾裳成为递增的效果。
把外在的景观定性为悲凉的意象群落,应该说,盛弘之是很有才情的。但是,和郦道元《水经注》描写三峡的文章,相比就相去甚远了。[11]
郦道元的贡献除了前文指出的还在于,第一,很有气魄地暂且把猿鸣之悲,放在一边,留到最后,一开头集中写其山之雄伟。这就是说,郦道元的目的是在结构上是以情绪的有序性为纲领来展开山水之美的。
第二,在“高猿长啸”前面增加了:“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期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这样的语句,强调的是水的险而豪,风驰电掣,一日千里,和前面表现山之雄伟,相得益彰,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是潜在的豪迈的情调。
接下去增写的山水之美,就不停留在壮美上,而转向秀美,在情调上就更是别开生面了:
春冬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怕。悬泉瀑布飞其间,清荣峻茂,良多雅趣。[12]
“回清倒影”是静态的,而“悬泉瀑布”,是动态的,动静相宜,与绝壁之怪怕反衬,统一于“清荣峻茂”。清荣,是透明清冽,而“峻茂”则有棱角,有风骨,和前文壮美相比,则是秀美,而情调上,则是凝神的欣赏,是物我两忘的快慰。最后两个字“雅趣”点明了情调的特点,豪迈的情调一变而为雅致。
“素湍绿潭”“回清倒影”“清荣峻茂”的妙处,与其说是对长江三峡的景观的描述,不如说是在情调上和朝发暮至,乘奔御风的豪情的对比。郦道元没有直接游历过三峡,这样的增写显然出于想象,长江三峡江流急流(在李白笔下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怎么可能在春冬之际变成“素湍绿潭”,甚至水清到有“倒影”的效果?而到了秋季水竟枯到“林寒涧肃”的程度,看这里的关键词“湍”、“潭”和“涧”怎么可能是江,连河都很难算得上!
但是,千年以来,读者对这样的“不真实”熟视无睹,居然无人发出严正的质疑。原因是郦道元的文章太漂亮了,虽为地理实用文体,但是其“逼真的幻觉”,审美想象超越了机械的真,把读者带到忘我、忘真的境界,这也许就是叔本华的审美“自失”,[13]实用性的地理文献,不期而变为抒情诗化的审美散文。
郦道元不但在袁山松和盛弘之精彩的语言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的语言,将不同的语言转化为不同的情调,最重要的是,将不同的情调和谐地统一起来。
但是他遇到的难度是,不同的情调、情趣,在性质上差异甚大,生硬地联系在一起,跳跃性过大,意脉可能断裂。第一,江山之雄与山水之秀,不能贯通,第二,豪迈之气与悲凉之韵不相连续。郦道元的才气在于,对无序的素材作了大幅度的调整,以有序的意脉把反差强烈的意趣统一起来,在情趣上达到统一而丰富。
为了达到意脉上的和谐统一,郦道元的艺术气魄还表现在季节上作了不着痕迹的调整。在概述了两岸连山之后,其立意本是把三峡的自然景观,按不同季节分别显示其变幻。但是,并没有按春夏秋冬的时序展开,而是先写夏(夏水襄陵)再写春冬,最后写秋。这一点,一般读者被应接不暇的丰富景观骗过了。如果从春冬之际写起,突出了“林寒涧肃”,和“朝发白帝,暮至江陵”“乘奔御风”就接不上气了。
而写“夏水襄陵”江水暴涨。表面上和第一段没有关系,但是这种美,和前面的山之美,有内在的统一性,具体来说,也就是因果关系。因果之一,正因为江岸狭窄而高峻,江水才容易暴涨,涨到“襄陵”的程度;如果是平原,就是浩浩淼淼,横无崖际的景象了。因果之二,正因为夏天洪水猛涨,航路不通。一旦有最高当局的命令要紧急传达,也有例外,那就是顺流而下,速度就很惊人:“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这和前面所写的江岸之美,是另一种范畴,但其间的内在联系,是很紧密的。三峡的地形特点蕴含着双重内在的逻辑:一,江水暴涨,是江岸狭窄高峻的结果;二,航行如此超凡的迅猛,又是江流暴涨结果。
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这样的描写,并不是很现实的。朝发白帝,暮到江陵,风驰电掣,一日千里,乘风御奔。肯定是有些夸张的,不过是为了在情调上显示出豪迈之气。
结束了夏水之美以后,作者并没有按时节顺序写秋,而是接着表现“春冬之时”,这是因为一下子写秋之瑟肃,猿之悲鸣,和前面江山雄伟、情致豪迈在意脉上不能融通。表面上,从夏到春冬在时序上是跳跃的,但是,其实在逻辑上是对比的。夏天江水的特点是洪水汹涌澎湃,滔滔滚滚。而春天和冬天,则相反,水浅而宁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素湍,是清的,应该是比较浅的、才是透明的;而绿潭,则是比较深的地方。水中有倒影,说明水十分清澈,而且宁静。这一笔和夏水襄陵显然是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是很强烈的,但是,又是很和谐的,因为对比在外在景观上有过渡:“绝巘(写作“山献”)多生怪柏”,而在趣味上,则是“清荣峻茂”的风骨,不但趣味有渐变之妙,而且有从豪迈向猿鸣之悲的过渡的功能。
把猿鸣之悲和秋天的景观,放到最后去,避免了在意脉上突兀和生硬。
写完了夏、春、冬,最后一段“晴初霜旦”,肯定是秋天的特点。其“林寒涧肃”和“清荣峻茂”是自然贯穿的,表现了自然景观之美的高度统一。但是在表现情感方面,却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虽然短短几句,然其间感触程序甚为精致:感之则寒,视之则肃,初闻之凄异,静聆之则哀转久绝,写出被吸引而凝神动性,构成了一种凄美、凄迷的情调。“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并不完全是对民歌客观的称引,而是从雄豪的极至,转化为悲凄的极至。其动人就不完全在自然景观,而在于情志的变化而又和谐地统一。在差不多同时代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中写到猿就不是悲凉的(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为什么在如此美好的景观之中,有这样悲凄的情感?这里,值得注意是,“渔者歌曰”。三峡之舟行虽十分凶险,对于旅行者,如袁山松来说,乃是自由的选择,而以渔为生者,则是别无选择的生计。乐府诗集晋诗有渔民的歌谣:
滟预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预大如猴,瞿塘不可游;滟预大如黾,瞿塘不可回;滟预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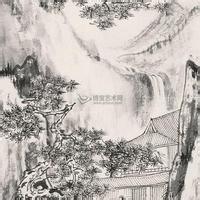
这是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三峡之美,这是一种凄美,一种悲情,这既有别于“乘奔御风”的壮美的豪情,又有别于“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的秀美和“清荣峻茂”的雅致。在强烈的反差中表现出某种递进的层次。
由此可见,在时序上将秋放在春冬之后,在情趣上将猿鸣之悲放在结尾,实际上,是反差与递进的统一,也是意脉的高潮。豪情之美、雅趣之美和悲凉之美乃构成三峡之美的主题的三重变奏。
从袁山松(?--401)的审美情趣经过盛弘之《荆州记》(成书约于432—439年间)的积累,再到郦道元(约470—527)的《水经注·江水》,古代中国作家呕心沥血,前赴后继,竟然不惜化了上百年工夫,才成就了这一段经典在情感上的有序和语言上的成熟。
正是因为这样,三峡,或者以三峡为代表的《水经注》中的山水散文,成为中国散文史奇峰突起,得到后世的极高的评价,将其成就放在柳宗元之上。明人张岱曰“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袁中郎”(琅環文集卷五)。[14]正是郦道元的成就如此之高,给后世写三峡的作家出了难题。以致余秋雨在《三峡》中这样感叹:“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
余秋雨这样说应该有真诚的一面,光从自然景观和语言上着眼,的确再高的才华也很难有超越的余地。如果真这样想,那余秋雨为什么还在写他的《三峡》呢?细读余秋雨不难理解,他心里酝酿着一个办法,一个不同于郦道元的办法,用来写三峡,虽然不可能超过郦道元,但也不至于对郦道元作疲惫的追踪。其实,在余秋雨以前,早就有现代作家,用自己的三峡之文,对郦道元发出质疑乃至挑战。
*本文在在引用文献资料方面得到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镁硒的大力帮助,特此鸣谢。
[1]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页512上。
[2]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73册,512页下。
[3]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73册,512页下。
[4]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73册,512页下。
[5]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版,上册第945~946页。
[6]盛弘之生平不可考。仅知是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侍郎,一说,元嘉十四年(437年)撰成《荆州记》三卷。一说成书于成书约于432—439年间。
[7]《水经·江水注巫峡那段非郦道元作》,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8]《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888册,905页下。
[9]《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87册,241页下。
[10]《世说新语》卷下之下,《四部丛刊·世说新语三》。
[11]当然,也有人引《太平御鉴.地部》盛弘之写三峡的文章,和郦道元几乎相同,但是,《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晚于盛弘之《荆州记》五百余年年,晚于《水经注》四百余年,且只比盛弘之晚生三十年的“书痴”刘孝标(462—521年)注《世说新语·黜免篇》所引只有“峡长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绝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刘孝标未见之文,四百年后何以得见?《太平御览》所引不足为据。
[12]《水经注》卷三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73册,510页上。
原文是:[13]不是让抽象的思维、理性的概念盘踞着意识,而代替这一切的却是把人的全副精神能力献给直观,浸沉于直观,并使全部意识为宁静地观审恰在眼前的自然对象所充满,不管这对象是风景,是树木,是岩石,是建筑物或其他什么。人在这时,按一句有意味的德国成语来说,就是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了(原著“自失”一词之下有着重号),所以人们也不能再把直观者【其人】和直观【本身】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却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24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4]另,清刘熙载《艺概.文概》卷一评云:“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可备一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