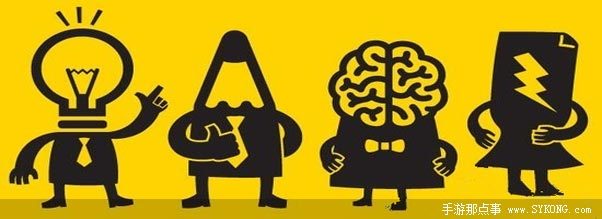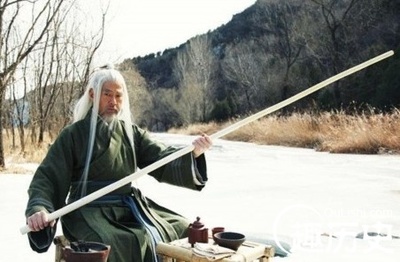我与周韶华最初见面,是好多年前在他的画友仇德树家。近年他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大型个展,却是通过国家画院邀约我写文章。因邀约拐了弯,我在讲好之际便斗胆不讳其短。当今评画文差不多都只说好的、不讲差的——扬长避短;要讲了差的,那还有谁来请你写?写了也通不过呀!令人称奇的是,周老竟包容了我的唐突,不但将此文交雅昌网发表,后美术报又刊登,皆未删所论其短。我感佩周老胸襟,据雅昌网记载,此文当时点击率甚高。这是我评画文中唯一一篇长短皆论的文章,因此它亦是我相当珍视的一篇评画文。
燃烧生命的血性呈现
——漫论周韶华的水墨风格
舒士俊
不期而遇的印象串连
我与周韶华先生原本不熟。先前关于他的大型研讨会,我一个亦未参与。不过我曾执编的《朵云》,很早便发过他之《再论全方位观照》。我当时感觉,他在现代画家中是位罕见的思绪广阔的画家。
谁知之后竟陆续有缘,使我对他产生了印象叠加:
一次在山东石岛参加学术会,主办方安排去参观设在荣成博物馆内的周韶华艺术馆。我记得那儿的建筑环境较暗,但见到一大批周韶华水墨之作,立刻感觉好似“混沌里放出光明”(石涛《画语录》中名句),竟有种生命光焰放出异彩之感。周韶华的水墨画,往往文化哲理之异彩与生命光焰交炽,象征与抒情意味交映生辉,如其名作《黄河魂》。不过就个人而言,我倒更偏爱其纯抒情之作,印象中那批作品便属此类,其中一幅荒漠耗牛多少年后仍念念不忘,是我所见个人艺术馆中最为精彩的。
之后不久,我与一友人同赴台湾,被刘国松先生热情邀住他家。在刘府,意外见到周韶华早年所著《刘国松的艺术构成》,听刘太太谈起上世纪80年代他们住香港,周韶华与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那书中,周韶华赞许刘“把时代的意义化为精神世界,把一切审美体验集中在个人的经验里,把你的心境变成画境,用你自己研究过的纯粹的形式来结构你的艺术世界”,这应是周韶华对绘画不同凡俗的挈领提纲之悟。谈及台湾“五月画会”,他感慨地说:“一切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伴随着一场大喊大叫。新的艺术主张只有宣传出去人家才知道,在宣传的过程中还会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清晰和深化。不然的话,谁知道你在干什么想什么?我觉得创作和理论研究要双轨同步。”显然,这是两位新水墨大将在相互砥砺。而“创作和理论研究要双轨同步”,——而今看来,那竟是周对日后自己发展的精准预言呵!
在那书中周韶华还问刘国松:“心灵里的闪光不是预先就能设计好的,头脑里的熔岩如果没有喷射口也不能迸发。创作过程多半是边画边深入,在取势、求势,因势利导,顺乎自然,改变意图,在边画边想的过程中,就像蚕吐丝一样,从自己体内抽绎出自己的灵感、沉思和想象,如果落实到纸上,并把这幅画完成,连自己也会奇怪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意念!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形?”显然,这是周韶华作画不可自遏的经验自道。在画完成后,他竟也会“奇怪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意念”!——说明虽创作理念倔执,他作画却是顺乎自然、随机而成,且亦颇善自省。
又数年,其“汉唐雄风”巡展至上海。我趁观众较少时特意去观摹,当时不知他有“三大战役”之构想,对其题材变迁之大颇感惊异。
周韶华前期引人瞩目的《大河寻源》,题材是山水造化,其用笔“写”中寓“工”,“放”中含“收”,于含蓄蕴藉中见深沉激越。而这时的《汉唐雄风》,是与山水迥异的溯古象征题材,其用笔明显以“工”和“收”为主,原来《大河寻源》中蕴藉深沉的激情已相对淡然。生命与艺术,原本皆会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他前后期笔性之变迁,题材选择之变似更为主因。其后期所画大量器饰塑像,让人想到传统题材之器玩清供,其题材本身之静物性,决定了在抒写中情感更为深含不露。不过尽管如此,其所作尺幅之巨,气息之幽,决非传统清供画所能企及。我颇钦佩他能将大幅染得不腻不滞那么深厚,整幅气色变幻能于厚中见灵,这在当代中国画家中,绝少有人能及。在展厅我向他讨教染法,归后又特向卢辅圣推荐,因卢当时正画一批巨幅古贤,其法亦以染为主。
再以后,便是我被中国画研究院(国家画院前身)邀编6卷本《当代中国画品》中之《雄浑刚健》分卷,周韶华正好入选于该卷。当时入选有好些名家,但有的好像刚健味有些,要说雄浑却够不上,要硬按上“雄浑刚健”,总觉有些勉强。最能与“雄浑刚健”合拍的,我记得是周韶华。当时为数个画家选撰文作者亦颇费心,我邀于洋为周韶华写《民族魂源与水墨雄风》一文。回忆起来,那是该卷中写画家最精彩的一篇。
现代大写意之风格归属
周韶华早年写的那本书,将“与刘国松探讨艺术技巧”设为第一章。他很欣赏刘如此说:“不能了解真正艺术技巧的人,就不能把握住真正艺术的本质;没有真正技巧的人,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这种技法研究至上的见解,与我意甚合。可能是担心后学过份执著于技会陷于形而下,在周后来丰厚的理论著述中,论及技法的已相对较少,但他绝对是位对技法孜孜以求的画家。在文革中,他竟独自赶赴李可染下放之干校,渴望见其一面,便显示他对大师画艺极其倾慕。
除了曾为刘国松著书,周韶华极欣赏并亲自撰《大风吹宇宙——论石鲁》。他极为精辟地写道:
“所谓风格,就是一个艺术家真正找到了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表达自己感情的独特语言。风格就是他的纯洁心灵和本质力量的结晶。”
“以意念创造为中心的石鲁画,追求的是寓意象征的内在精神,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全面展示。他的长处是能把内在精神潜藏于艺术世界,把对整体的把握渗透到形象底蕴的精微表现上,使一切精神内涵都蕴含于可视的美感形式中,抓住自然的灵气,把生活和情感的要素突现出来,以呈现精神之光。”
“他的意象构成的精彩处,是形象的生命运动和形象的诗意,是更高层次的‘第二自然’,是‘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的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
周韶华还指出,石鲁后来放弃早年代表作《古长城外》那种叙事写实方式,“着力于诗意的追求和意象的表现,自觉如梦初醒,顿开颖悟,找到了中国画特有的语言”。他极欣赏石鲁之张扬个性,赞其“满纸是结构的旋律,果敢的笔触,准确、豪放的力线,是气与血的痕迹,清白纯正的人品风骨的象征。”
以上这些话,可说是周韶华借论石鲁,来吐自己心中块垒。周韶华以写意抒情象征为其风格追求,石鲁可说是让其顿开颖悟之人。也见有人将他的写意抒情象征风格,与清代大写意派中抒情象征特征极为突出的八大相比。从八大、石鲁到周韶华可看出,简笔大写意自具抒情象征之优势,是不言自明的。
颇可玩味的是,石鲁早年甚而用放大镜临过吴昌硕之印刷品,其笔墨精神曾深受吴影响。又据周韶华自述,在上世纪70年代他与上海大写意画家林曦明时有过从,亦曾为其画册作序,对之颇为欣赏。而林曦明,曾跟王个簃(吴昌硕弟子)学笔墨,又深受林风眠影响。林风眠则极欣赏齐白石,而齐与吴昌硕显然有师法关系。其实即便是刘国松,观念技法似背离传统,其用炮筒阔笔之草书笔意,亦并非与大写意无涉。而后周韶华甚欣赏并亦为之作序的何海霞,其泼彩山水有张大千之师承启迪;而大千泼墨泼彩山水由其泼墨荷花转换而来,亦属大写意无疑。近现代上述的几位突出画家,竟皆归现代大写意之麾下而各呈其异彩,这也是颇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现象。
一个成功的画家不可能全然空所依傍。周韶华自我风格之形成自然有多方面影响,包括他曾从事过的水彩和版画;但在笔墨精神因素方面,其主体风格应属现代大写意之血脉。我甚至以为,周韶华之彰显清朗骨力精神,和他以排比阔笔来形影交融地显现弥满的整体氛围,其中显然有得自石鲁和林风眠两家的微妙感染。甚或可说周韶华所作之佳者,乃取石鲁之骨,融林风眠之体,显自我张扬之魂。
燃烧生命的血性呈现
与林风眠、石鲁一样,周韶华曾有过悲催的往事记忆。童年极其孤独的不幸,与其后军旅生涯及革命英雄主义象征之潜在印痕,这些特异的人生经历,在山东大汉刚毅血性的心里,皆成其后艺术之异彩折射,使他尤能通过积健为雄之坚毅不懈,来充实和张扬笔力。
周韶华说石鲁“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情感驾驭画笔,他追求的是精诚之至的情感注入”,此话亦可移用来评他自己。他尤欣赏庄子《渔父》这段话: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周韶华说石鲁笔触果敢,乃“气与血的痕迹”;而他自己所孜孜以求的,亦正是如此。故其《博峰日照》《大风起兮云飞扬》等作,下笔一任性情苍莽老辣,气质俱盛,直与吴昌硕、黄宾虹之率意笔性相通;其笔力之遒健沉厚,在同辈颇有盛名的画家之中,几乎无人可及之。
刘骁纯发现,周韶华“创立了以浓重的黑红两色冲突为基调的个人色彩风格”。这黑红两色显现的浓郁血性,是石鲁和周韶华两人特殊的人生及个性,与革命经历交并碰撞而产生的,周韶华则更将之推至浓烈沉郁,故我称其为生命燃烧,——那燃烧,亦是黑红两色之激烈冲突呵!
出生于大海之滨的周韶华,如此形容晚霞在大海燃烧:
“西天燃烧着一片片朱红色晚霞与太阳浑然一体,缓缓地沉没在海中,但浪峰上的霞光依然壮观,一片片燃烧着的火焰,时而滚动,时而闪烁。”
大海被霞光燃烧的印象自童年至晚年,在周韶华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不仅其一生被这激情燃烧所鼓催,它也渗透到其作品的笔触和调子里。尤值得一提是,他竟将血性燃烧之气色,融入其画调子之幻变,可谓独臻其妙处。
现代研究已认为光色与燃烧之温度相关。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发现,黑体物质若吸收热量,会因受热高低而变成不同的颜色。当黑体受热达500—550摄氏度时,就会变成暗红色;达1050-1150摄氏度时,就变成黄色;温度再继续升高,就会呈现蓝色。而天空在阴或晴,日出或日落时,色温之变化极大,亦是色温越高,光色越偏蓝,越低则偏红。因而燃烧的云霞,其色温变异所带来色彩之演绎眩变,尤为丰富微妙。
周韶华在水墨中体现黑红两色之冲突,正与光色燃烧之奥妙相通。对霞光燃烧之迷恋和激赏,加之他早期的水彩画修为,使周韶华对熹微光色(气色)之演绎眩变尤其敏感。有个电脑软件可摹拟白昼夜晚光线之幻化演变,对图像光色之演绎作微妙反应。我曾以周韶华有些画作试之,竟出现意想不到的美幻(这也说明其山水画有被继续挖掘的丰富潜能,——图见2013.7.30笔者之新浪博客),可见他对光色(气色)调子之微妙把控,确有卓异超人之处。
(上图左为周韶华原作,右为我作的电脑幻变图)
周韶华懂得通过积健为雄来彰显笔力;但过于概括象征之笔法,有时难免笔气太盛却显简略而空。而其对熹微气色之捕捉和铺染演绎,恰恰可令其铮铮铁骨之笔力与氤氲柔润之渲染相扶持,使积健为雄复归返虚入浑,从而形成他截景特写式、大气包蕴的雄浑山水面目。旷达的笔力,沉郁的墨气,绵密的情思,其笔下佳作由机神凑会而生,亦可谓不可多得也!
未想其后题材之变迁,周韶华又拓展至“三大战役”。他说:“思想有多深,成就便有多远;思想有多远,目标就有多么远大。思想愈拓宽,心灵便愈开阔,便愈有大思维、大视野、大结构、大气象。”“辽阔的心理空间能扩大语境空间,打破以往对意境的种种界定。”大概不愿被已有的大写意格调所限,他遂上溯汉唐乃至彩陶纹样及岩画等原始艺术,以冀涉猎广阔,博观而约取。不过我注意到他之后的想法,与他曾说过的以下这些话,还是有所不同:
“在一段时期内,你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去一步一步地接近终极目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漫天撒网。首先要把对生活的直接感受转译为对专题性的独特空间构造,逐渐形成自己的形式系统。对形式系统的追寻要有高度自觉,这是取得终极成果的捷径。”
上述这段话,应是他对中国画的睿智卓识。其实从原始艺术到工笔、小写意再到大写意,这一步步的历史拓展,中国艺术之各个阶段虽各有不同,但仍含其内在之衍生关联性;而大写意,作为各个阶段发展至近现代之最后一站,其所含的当代精神气质应是最强的。它尤适合周韶华那血性燃烧之个性融入于山水,会焕发出绚丽异彩,相得而益彰。倘若他能穷形极相地将其大气包蕴的截景特写式山水样式继续开发深化,以形成灵变的自我形式系统,那他无疑将在山水画领域赫然成为傲视群雄的大家。而其之后之题材变迁,虽亦注意专题性之限定,毕竟所涉太广,精神之背负亦太重。他那血性燃烧之个性面对溯古象征题材,难免形隔势禁,有所逊色。我猜他后来或亦有所省悟,乃向大海回归,——这是他一路西向溯源之后的东归,亦为向原来的大写意与山水题材回归也!
尽管艺术跋涉难免曲折,但把周韶华毕生孜孜以求的探索视作燃烧生命,我仍以为非常贴切:因血性之燃烧,既会闪烁绚丽光焰,亦会随生黯然之景。即便是大家之毕生所作,亦难免时有高低,又哪能皆在一个水平?但作为新水墨营垒中最有文化学养、最善哲思的一员大将,周韶华那饱含血性燃烧个性、大气包蕴的截景特写式山水,无疑将在现代山水画变革史上,留下其浓重的一笔。
2013炎夏于海上龙柏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