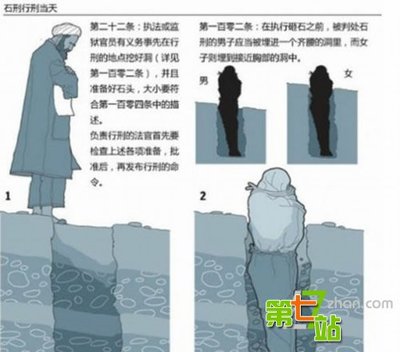上小学时,读过一则典故,讥讽“指鹿为马”的荒诞不经,那时候很天真,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世上会有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怪事。长大后经历了许多,慢慢体会到这则典故的精妙之处。
1971年在洛东水电站工地上,由于几家医院一连串荒唐误诊,我服用了过量对肠胃有强烈刺激的治疗肺结核的药物,结果患上了胃病。1976年,我的胃病已相当严重,稍不注意就有可能穿孔,引起更严重的腹膜炎,危及到生命。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咨询了医生意见后,我作出了当时看来最勇敢的决定,就像山姆大叔03年对付独裁者萨达姆那样,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在胃溃疡未穿孔前,果断施行胃大切手术,将病灶从自己肌体上彻底干净清除掉。
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挨刀子是很痛的,更何况开膛破肚。众所周知,义和团虽有刀枪不入的神功,在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前,不照样被打得丢盔弃甲人仰马翻;世人顶礼膜拜的英雄关大圣人,在华佗神医刮骨治疗时,虽面不改色,却也免不了紧咬牙关大汗淋漓,更何况我等凡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埸史无先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势有如排山倒海,所到之处,一切传统观念陈规陋习均在荡涤之列。医疗战线自然不能置身其外,在冠冕堂皇地执行主席革命路线口号下,反对崇洋迷外宏扬中华民族优秀医药文化就成了医疗战线最重要的任务。

当时,有人提出为了宏扬中华民族医药文化,给病人开刀时,不准使用西药麻醉,在病人痛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用老祖宗留下的神针,对准乱七八糟的穴位扎上几针就OK了。值得指出的是,竟有不少“专家”也跟着鹦鹉学舌,糊涂到认为不用药麻手术后恢复会更“佳”,这些所谓的专家只考虑到药麻给患者带来的附作用,却没有顾及到,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用药麻客观上虽可减少一些附作用,但手术中所带来的那种令常人难以忍受的剧痛,给患者生理和心理上带来的伤害,对其术后康复是绝对不利的。
对如此荒唐的做法,人们心里是不会苟同的,但在那个倒行逆施的癫狂年代谁也奈何不了。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一个个患者如同一个个践行“伟大思想”的先行者,不得不像唐吉诃德般,拿着意识形态的“盾牌与弓箭”,乖乖躺在手术台上,任人活生生宰割,即便痛得死去活来,还不能忘记要及时为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大唱颂歌。手术终了时,每位患者都成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好汉”,成了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先进分子”。而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疼痛难忍所表现出来的狼狈不堪像,从此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至今仍有某些范例在民间流传着,成了中国式的天方夜谭。
主刀冯大夫告诉我,像我这类尚满脸通红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做胃大切手术,按规定是不允许用西药麻醉的,手术中的麻醉,只能采用传统的针麻。医师知道,针麻尚在实验阶段,在大手术中实在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大势所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就是瞧着患者痛得嗷嗷大叫也无能为力。他鼓励我要做好思想准备,在手术中充分发扬先辈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咬紧牙关硬撑几个小时,实在受不了就大喊几声,纵使操医生的娘医生也不会怪罪你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分散患者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不过关键还得靠你本人,能否硬顶下去,配合好医生使手术尽快完成。
听了大夫一席话,我不免有些胆怯,但出于对生命的担忧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的鼓舞,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9月初,忐忑不安的我住进医院。听从医师的安排,我边检查身体,边等待手术。9月9日,毛泽东主席突然病故,巨星陨落,全国人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所有机关、医院、学校和企业根据上级指示都设置了灵堂,供人们吊唁,以寄托哀思,许多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下,医院也不能例外,我的手术只好往后推。
在忧心与悲痛中,渡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9月23日终于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动手术。
24日,一大早,两名芳龄护士前来为我作术前准备,她俩端着一大盘瓶瓶罐罐来到病榻前,用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我。这时己孤立无援的我,不得不乖乖从命,老老实实把自己裤子解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少女毫无遮拦地敞开肚皮。正当我还在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己青春酮体时。一名护士,十分利索地从盘子里操起一把明晃晃的剃刀,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迅速而准确地降落在我的肚皮上,娴熟的在小肚与胸脯间来回飞舞。只一会功夫,以往那些汗毛丛生之处,己被毫不留情地铲得干干净净寸草不留。紧接着,另一名护士迫不及待操起一大团吸饱了酒精的棉球,仿佛饿虎扑食般在我已被修理得光滑如镜的肚皮上来回涂抹,唯恐漏掉一只病菌病毒。刹那间,我感到火辣辣的难以忍受的刺痛,光鲜的肚皮上,只见肌肉一阵一阵痉挛,肚皮下仿佛潜藏着无数条蚂蟥,正在进行着殊死的翻滚。尽管难受,我还放不下男子汉的架子,故作镇定地调侃道:“涂涂酒精就这么疼,等下挨刀子不像杀猪才怪”,护士不搭理我,噘起嘴,偷偷相视一笑。
十点正,在一名护士导引下,我强打笑脸,佯装自如地走进手术室。手术台位于室内正中位置,顶部罩着一盏又大又圆的无影灯,仿佛罩着一付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阴森而恐怖。十多位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手术台四周,有的忙着消毒,有的忙着整理手术器械。看到我这位自投罗网的“优等实验品”,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洋溢着怪异而滑稽的笑容。
一躺上手术台,几名护士就将我团团围住,生怕我这位不请自来的“优等实验品”会突然间蒸发掉,紧接着两名护士娴熟地用胶带绑住我的踝关节和手腕,不一会功夫,就把我捆得严严实实。此时从无影灯中看到的我,是多么可怜,多么无奈,昔日那种气宇轩昂的红卫兵小将风度,不知跑哪儿去了。
忽然,冯大夫带领大家齐声朗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严严实实地罩上了大白口罩。
手术第一步,负责麻醉的医师、护士,七手八脚在我的手、足、头、背、腹部等处,扎上一根又一根又粗又长的银针,每一根银针又通过导线连上直流电源。这时的我,如同一只被捆得严严实实的肉猪,在绝望地等待着大屠杀的开始。忽然间电流接通了,只见银针不停在抖动,强大的电流一阵紧似一阵冲击着全身,顿时四肢就像灌满了铅似的,很快就麻木了,如果说原先还有点担心与恐惧,此刻,随着一阵阵电麻,我不得不暗暗佩服起针灸的神奇效应,感谢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动刀前,冯大夫再次提醒我应注意的事项,并反复交待我,要尽量配合好医生,实在受不了时可以喊叫,但要注意把握分寸,不要得寸进尺,动辄就大喊大叫,干扰医师注意,影响到手术成败。听了大夫的话,刚刚还在暗自钦佩的我,又把心倒提了过来。
忽然,冯的右手在半空中猛地划了一下,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犀利的刀子己从胸口左下方一直至肚脐眼,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从裂口处湧岀,护士忙着用棉球吸取。一种从没感受过的剧痛,一种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剧痛,像钻透了心窝,一阵阵袭来,使你无法自制。而十数根通着电流的银针压根就没产生任何麻醉。这时候,不要说医师的循循善诱,就是伟人的金玉良言,我也顾不得了。“妈呀、天呀,”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惨叫中,还不时夹杂着龌龊的操娘声。
这惨叫声,像鬼哭狼嚎,又像被宰杀的肉猪,拼着老命发出长长的哀鸣。这惨叫声,穿透了手术室,穿透了住院部,传遍了四周的民居。
很快我就昏死过去,朦胧中听医师说:“刚开始就喊这么凶,等下要你够受的”。果如其言,不久后,更难以忍受的剧痛排山倒海般袭来,根本就不顾及到人类的承受能力。
苏醒后,我极力挣脱羁绊,但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针灸对创口虽无麻醉作用,但四肢却着实被它麻痹得难以动弹,不管我怎样惨叫,也不管我怎样挣扎,手术仍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医师打开腹腔后,仔细清理了腹内污秽,小心翼翼剔除了胃与其它内脏器官的粘连物,然后从腹腔中将整个胃掏出,盛放在一只白色的瓷盘里。放眼望去,我的那只可怜的胃,就如同闹热的集市上摆放在肉案上的一只新鲜猪肚,在等待着众多饥肠辘辘的食客来瓜分。冯大夫翻来覆去仔细端详着我那只任他宰割的胃,仿佛在欣赏一件将要由他进行粗加工的工艺品。
一名护士贴着我的耳朵轻声说:“等下要尽量忍一忍,不要喊得太难听。”话音未停,冯从护士手中接过手术刀,毫不犹豫地将我的胃迅速切开,接着用双手把胃撑大,将右手伸进胃里,这里摸摸,那里捏捏,翻来覆去,反复掏弄。刹那间,一阵紧似一阵的剧痛,又一次排山倒海般而来。这一阵阵剧痛,撕心裂肺般剌入全身每一个细胞里;这一阵阵剧痛,比起先前的要强上十倍百倍;这一阵阵剧痛,根本是人类无法承受的;这一阵阵剧痛,就是穷尽人类最生动最形象的语言也难以描绘。
我痛得死去活来,不顾一切地发出新一轮惨叫,这一轮惨叫比之先前的更为惨烈、更为恐怖。在一阵阵剧痛中,不知昏死了多少次,最终由于体能大量消耗,我的惨叫声渐渐地渐渐地越来越弱。忽然间,感觉到腹腔内好像被谁一下就掏空了。
我再一次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一名护士坐在身旁。因为不停地嘶喊,夏日饱满红润的双唇,己裂开道道口子,从裂口处不断渗出殷红的鲜血,护士不时用吸饱水的棉球,往我的唇上轻轻涂抹,倒流入口的血水带有浓浓的血腥味。护士告诉我,医护人员都到隔壁吃饭休息了。看着自己完全暴露的腹腔,看着盛放在盘子里己明显缩小的胃,看着空旷的手术室,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孤独与恐惧。
这时,一名护士端着一只盘子姗姗走来,洁白的瓷盘上盛着一团新鲜而又血淋淋的肉块,护士对我轻轻耳语:
“这是你切下的胃”。
“大约有多少”,我好奇地问。
“百分之六十四”,护士高声答。
“天呀,今后我用什么地方装吃的东西”。
“打算怎么处置它”,我接着又问。
“当然是扔了”,护士无所顾忌地回道。
我惊呆了,不由自主大叫一声:“妈呀”。结果又引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手术渐渐接近尾声,快缝合腹部了。谁知道,又一波绝不亚于上一波的剧痛再次袭来。
腹部缝合需分两次完成,先是缝合腹膜,然后再缝合肚皮。由于腹膜弹性强,切开腹腔时,腹膜已缩到腹腔深处,缝合时,要撑开腹腔,将带钩的长针伸进腹腔,钩住腹膜用力拉至切口处,每拉一次都会引起一阵剧烈疼痛,而且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能成功,往往失败的一次引起的疼痛更大,前前后后要缝二十多针,每缝一针都要拉两次,加上失败的,绝不少于五、六十次,试想,倒霉的我要承受多大的疼痛。
不过这一轮,我不再喊叫,也不再咬紧牙关,因为精疲力竭的我,已无力再喊,也无力再咬。
下午三点多,手术终于结束,前后近六个小时。
我被推出手术室,病友们簇拥过来,一阵喧哗,仿佛在迎接凯旋归来的凯撒。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阉了老半天,真是活受罪,换谁也受不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狗股仔(意为年轻力壮者),你真行,喊得够大声了,搞得一整栋楼的病人,一整天都休息不了。”一位老者伸出拇指夸奖我说。
术后七天拆线,第二天在办公室开了个短会,总结手术成功的经验,不知为什么,院方特邀我参加。会上大家异口同声,纷纷赞扬针灸麻醉的优越性,颂扬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主持会议的人让我也说几句,碍于医师面子和当时的形势,我只好说了几句,尽管针麻于我已是不寒而慄,但人性的弱点使我还是违心地肯定了针麻的“优点”,最后话锋一转便调侃起来:“针麻好是好,但美中不足的是,该麻的地方不麻,不该麻的地方却麻得要命,今后要能反过来更好。”
不久后我康复出院。九十年代初在一次出差途中,与已调至柳州市某医院的冯大夫不期而遇。谈及此次手术,他告诉我,在手术过程中,在我喊叫最厉害时,他曾违规吩咐麻醉师,给我注射了一支局部麻醉剂盐酸普鲁卡因,以减少我的疼痛,要不然会更痛,后来他还因此受到批判,差点就丢掉了饭碗。
听了冯的话,我受到极大震撼,除了感激外,我沉默不语无言以对。在那个指鹿为马黑白不分的年代,还有人敢冒反对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滔天罪名,为一位素昧平生地位卑微的人伸出援手。
1976年10月6日,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不久后,外科手术中的针灸麻醉即被叫停。
几年以后,被割掉的胃慢慢长大,渐渐地饮食也恢复了正常。有了这次经历,从此后,一般的疼痛,我不再当回事。
如今每谈及此事,听者除了捧腹大笑之外,往往会发问:真的有这码子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等荒唐的事。是啊,我也闹不明白,好端端一个国家,好端端一个民族,怎会发生这等荒唐的事,而且还上了瘾,接二连三,一次比一次更荒唐,一次比一次更残酷,每次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这就让人不好理解了。后来尽管也进行了一些反思,可是都不怎么令人信服。
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哪一个国家,谁要是选择了个人崇拜,或是被个人崇拜所选择,那么许多匪夷所思的荒诞事,甚至像饥荒、迫害之类的大事件,将不可避免,无一例外。
最近一段时间,从权威的医学杂志上看到,这类胃大切手术会给患者留下不少隐患,其中最大的隐患就是有可能造成胆汁回流,回流的胆汁经年累月不断地浸润与腐蚀吻合口,先是在吻合口处引发糜烂性胃炎,最后突变为胃癌。
所以当年我的选择尽管很勇敢,但一点也不明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