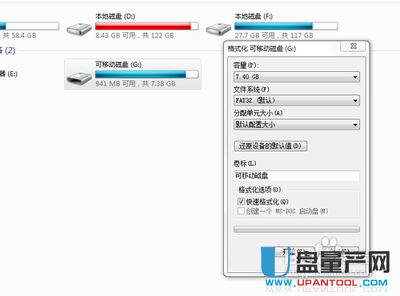去年9月读了Arthur Wolf的Gods, Ghosts, andAncestors。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ArthurWolf根据在台北市郊三峡乡村所做的田野调查而完成的。这篇论文认为中国农人的超自然的世界是他们社会图景的忠实复制。神是官员;鬼是土匪和乞丐;祖先是父母、祖父母。ArthurWolf关注的神灵主要是灶神、土地公和城隍。他在文中谈到:
One ofthese is placed in a niche outside the back door for the benefit ofwandering ghosts; one is dedicated to the stove god, whose imageresides above the large brick structure on which all meals areprepared; and the third is placed in a burner before the tablets ofthe family’s immediate ancestors.[1]
在中国社会中,灶是家的象征,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灶神自然就是超自然官僚系统中等级最低的官员。一般农人都把灶神看作是警察和告密者,如果对其祭供不周,灶神在新年就会向上天告发家人在道德上的不端行为。这是在家的层面上国家通过象征手段维持正统道德和政治秩序。而在村落和街坊的层面上,土地公则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土地公是地区的官员,他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对鬼的管理与监督;二是记录人的行为,并定期向他的上级汇报。土地公的直接上级是居住在城镇的城隍,他通常被看作是士大夫、一个获得过功名的官员;他穿着官服,旁边站着幕僚和执法官;他的庙宇与当地的衙门并排在一起,,红墙绿瓦,门口立着旗杆。在许多城市,城隍一年之中要举行三次过境仪式,巡查他所管辖的边界。
在ArthurWolf那里,把神灵解释成官员意味着:1神灵皆为官员。2神灵等级是多层次的。3除最高级的神灵外,所有神灵的权威均来自外部,由一位比他高级的神灵授权。4世人与神灵权威打交道是间接的,既可通过较低层次的神灵,也可以借助职业宗教人士;前者沟通世人与较高级神灵的关系,后者则无所不包,甚至可以做世人与最低层次神灵之间的中介。5神灵与特定地点、居民之间的联系是暂时的,是任命所致,而不是神灵本身形成的或它们自身选择的结果。
ArthurWolf的这种解释能不能充分说明中国民间神灵的象征意义?神灵仅仅是传统中国正式制度和正统秩序的唯一表达吗?不管是ArthurWolf,还是Emily M.Ahern以及StephanFeuchtwang等人都从文化象征的角度,探讨并构建中国民间宗教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EmilyM.Ahern认为,民间宗教中的仪式乃是对帝国官僚体系及其权威展现方式的模仿。StephanFeuchtwang则提出imperial metaphorical domination[2]之说,认为民间宗教虽不纯粹是模仿官僚体制,如民间仪式的实践具有地域性,但仍很大程度反映了集权权威及帝国官僚体制的意识形态逻辑。(其实这这仅仅适合用在部分神灵的身上。中国的天既不是政治秩序消极的隐喻,也不是社会等级的简单具体化。相反,天表达了社会的张力。中国的神灵以某种方式镜像了存在的秩序,但也会雕刻它、弥补它和改变它。)这些观点具有某些共通之处,其一,认为中国民间宗教反映了信徒的社会观;其二,注意帝制时代地方与中央的衔接,并构思神灵与帝国科层体系的对等关系,认为神具有科层的性格并发挥科层性职能。ArthurWolf尤其坚信神灵世界的科层特征,他说:“视神界如科层体系的观点具有如此强的说服力,以致任何反面的争论也均以科层体系词汇来解释”[3]。而同样是以台湾汉人社区为田野经验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在中国,超自然存在的整个系统并非只有某一神主司人类行为的考核,而是全部的神统构成层层互相监督复核的系统,即使最低层的神如灶君司命或土地公福德神等,也都负有考核人类行为是否中规中矩的责任,然后层层转报以作为最后审决的依据”[4]这种研究进路的选择,使他们倾向于将汉人观念中的鬼神世界秩序化。
问题是,中国民间宗教信徒的社会观不一定就包含有对科层化帝国的认识,因为在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欠缺的帝制时代,在无数相对孤立及边缘化的乡村社区里,人们无从感受到一个科层化帝国的存在,这样,所谓“中国民间宗教反映了信徒的社会观”从何谈起?神灵世界的科层秩序又从何构建?。R.Hymes在《道与庶道》一书中集中表达了“个人模式”的解释。作者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道教天心派、三仙信仰为例,并糅合了当代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资料,指出汉人眼中的神灵除了“官僚模式”外,还存在“个人模式”的解释。R.Hymes肯定了“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在中国宗教中同时得到了表述。这两个模式都不完全是独立的,而是紧密相连、异轨合辙,是宗教实践者以不同的、灵活的,有时甚至是以商业的或个人的方式加以援用的资源。“个人模式”弥补了“官僚模式”的不足。ArthurWolf仅仅看到公开的“正式制度”的表达,而忽略了私下的社会潜规则在象征层面能与“正式制度”一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仪式过程。如此理解中国社会神灵的象征意义似乎穷尽了人类学的想象力。对中国社会神灵象征意义的理解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路径?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官僚模式”还是“个人模式”,都承认和接受现成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只不过“个人模式”是以个人的方式来接近权威,从而形成庇护——依赖的关系。在这里看不到质疑与反抗的影子,政治与道德的合法性没有遭到挑战。但是ArthurWolf注意到一笔带过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者”和他们动用的象征符号该如何理解呢?
于是就有了一个异端模式。汉人社会神灵的多样性无疑来源于宗教类型的多样性。在传统中国主要有道教、佛教、国家崇拜和大众宗教,相应的就有四种类型的神灵。但这些神的界线并不是那么清楚,它们可能被四种宗教互相借用或共同分享。这极大地挑战了先前ArthurWolf对中国神灵种类认识的局限性。
许多学者早已注意到中国神灵的能动性以及所表征的复杂权力结构。最明显的例子是佛教的神灵。比如作为神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最后只能借助如来佛祖的力量镇压了这个造反的猴子。神灵的反正统性无疑揭示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内部的张力。在国家力量薄弱的地区和时期,一些反国家的宗教就有可能占据信仰的中心。比如,晚清时期在广西流行的“甘王”崇拜,就对应于该时期国家对该地区控制的倒塌。这些反对力量从更宽泛的层面来说,还可以被解释为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平衡。而在恰当的时机,反抗性质的象征符号又会转化为真正的造反动的资源。女神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的观音不论是佛教、道教还是民间信仰都没有把其看做是一个官员。尽管女神不是官员,但在民间宗教中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女神凌驾于男神之上的权力结构无疑打乱了传统中国正统的伦理秩序和性别等级。许多女神还藐视儒家伦理拒绝结婚,作为观音化身的妙善公主、妈祖和无生老母都没有结婚,这极大地威胁了父系社会的男性权威。女神是一个特别的宗教现象,在它们身上体现了“纯洁”与“污染”的吊诡与辩证法。
ArthurWolf对鬼和祖先作了区分,他说“‘鬼’的范畴应该包括家族以外所有死者的灵魂”[5],某人家已逝的祖先就是别人家的“鬼”,对特定家户来说,祖先与鬼的区别是清楚的。不过在中国文化的“小传统”[6]中,在概念上,鬼与祖先往往是含混的,如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其所谓的鬼就是指祖先。而在“大传统”上,ArthurWolf区分鬼与祖先的办法也不一定可行,因为汉人社区大多为家族聚居社区,有时,同一社区就是同一祖先同一家族,那么,“家族”的“内”与“外”又如何区分得清呢?是不是这个社区里死去的人都不是这个社区的鬼?推而广之,是不是同姓亡魂都不是同姓生人的鬼?所以,需对“家族”的范围作条件限制,否则,ArthurWolf对鬼与祖先所作的区分就不可行。
ArthurWolf提出“神”与“鬼”另外一个区别在于:“神”被崇拜,而“鬼”被驱赶。据此逻辑,死后转换为神灵的人生前一般来说都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典范。但是一些神灵却拒绝接受社会的规范,这反映在它们“鬼”的起源上。非正常死亡与暴力死亡是成为“鬼”的条件之一,但关公却是被他的敌人斩首而死的,这并不妨碍他死后成为一个神。有的神还被同时崇拜和驱赶,比如台湾地区的“王爷神”常常带来疾病,人们向它提供祭品的同时把它的神像放在船上烧掉驱赶出社区。
ArthurWolf还说:“鬼的性格全视其社会和经济环境而定”[7],有子孙定时供奉的就对人类满意,否则就具恶意。以是否有子孙定时供奉作为区分善鬼与恶鬼的依据,这大体是符合实际而且是有意义的。问题是,如果是无子孙定时供奉(并非无后嗣)的祖先(如三代以上的祖先往往无人供奉),这个“祖先”所呈现出的性格便可能与鬼相当。所以,与其将“鬼”对应于阳间的“陌生人”并定义为“家族以外所有死者的灵魂”,不如将“鬼”对应于阳间的“流浪汉”并定义为“无子孙供奉(无后嗣)、子孙无供奉(有子孙而不供奉)以及子孙供奉不到(非正常死亡或客死异乡)的所有亡魂”。“无子孙供奉”、“子孙无供奉”及“子孙供奉不到”三种情况可归结为“未收到来自子孙定时供奉”,这样,就可以将“鬼”定义为“未收到来自子孙定时供奉的亡魂”。因此,所谓“鬼”,就是指“野鬼”,不必再分出善意的鬼和恶意的鬼。这样,也许更符合人们对鬼的理解与想象,也可避免ArthurWolf区分鬼与祖先时衍生的问题。
[1] Arthur Wolf,Gods, Ghosts, and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 byArthur Wol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pp.131-182.
[2] Stephan Feuchtwang,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1992.
[3] Arthur Wolf,Gods, Ghosts, and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 byArthur Wol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pp.131-182.
[4] 李亦园,《宗教与神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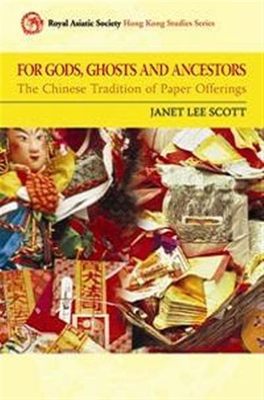
[5] Arthur Wolf,Gods, Ghosts, and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 byArthur Wol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pp.131-182.
[6] 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说法是50年代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芮斐德(RobertRedfield)首先提出来的。台湾李亦园教授对此曾有专文介绍,据他说所谓大传统是指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的文化(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大众文化,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的生活文化(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精英文化与生活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ghand low culture).
[7] Arthur Wolf,Gods, Ghosts, and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 byArthur Wol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pp.131-182.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