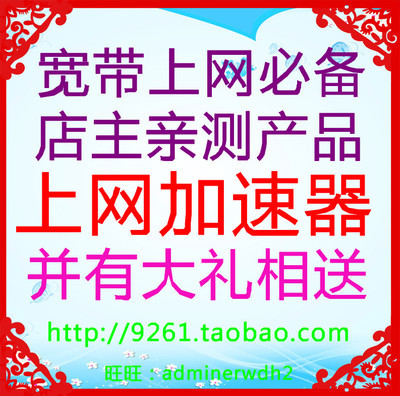洗荞麦皮是受电视生活节目的引导,教给用洗衣机洗的方法,于是勾起我也想试试的冲动。
选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周末,拆卸完枕头,将荞麦皮装入纱布袋子里……。可是,当要放入洗衣机里时就畏缩了——直怕甩洗时打散在机器里,不是就会“皮”“机”双亡了吗?
踌蹉之间,拆散的荞麦皮就摊在了那里,是洗是扔我在犹豫。还是老公行,他说,你别管了,我来。
于是,不久,门口刚翻修好的小花园里,成了我家荞麦皮的晾晒场。
手工清洗、人工晾晒,忙乎完毕后,我俩坐在沙发上休息,他说,知道咋回事吗,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看见我奶奶就是这样洗啊晾的。七十年代我家添置的牡丹牌缝纫机
其实我在犹豫没舍得把荞麦皮扔掉也是有原因的。看见这几个荞麦皮的枕头,我就会想起母亲。当年,完全是在母亲的指导下,从买荞麦皮和枕头布料开始,到一针针用缝纫机扎上成为了枕头。所以要让我将荞麦皮像撒烟花似地扔掉,真的有些舍不得哪,甘愿用这种古老的办法清洗出来,还能接茬用。
频繁的出入家门到院子里晾晒荞麦皮,遇见街坊四邻的机会就多起来。对门楼的王老师怎么拄着拐了?和她聊起,原来是门口电缆改造挖沟时,出门被绊倒摔了一跤,更换了 股骨头,一共花了5万八,股骨头材料花了4万,里面是美国的,外壳是德国的。和她从住院手术一直聊到原来的同学老师,又说起我的父母去世的早,一下让我的眼圈泛了红,她赶忙岔开了话头,说到她侄女嫁给的德国人,最终又扯到每年她们要回趟婆家扬州上海等地祭拜走访,以及婆家与江泽民、胡景涛都是老乡的家常趣事。直到站的时间太长,换了股骨头的腿招架不住,我俩这磕儿才算唠一段落,足有两个多小时,站在门口的道儿上。
再次出去翻晒时,跑过来一个两岁孩子,伸手拔拉着荞麦皮玩,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随后赶来制止他,她说她是孩子的小姨。孩子问小姨:这是嘛啊?小姨说: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他们这是荞麦皮。呵呵,仅此而已,此交谈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因为无形的代沟之深也,貌似会形成隔空对话的态势。
下午,日头西沉,小花园有了荫凉,前后楼的老街坊又聚拢过来,坐到了花园的椅子上,围在荞麦皮左右。这时遇到了姚琳的奶奶,姚奶奶把我叫到跟前问我儿子的情况,我看到她原来胖胖的体型变瘦了,问起,她说:老头没了,姚琳结婚了,结完婚20天她妈也没了,她妈就是想看见闺女结婚,要求的。
和老街坊聊天,好久的事,好多的话积攒在了一起,总是让人有世事沧桑的感觉。
晚上,去超市买了些干花,香香的,我想拿来放在新装的枕头里,好能日日枕着沁香入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