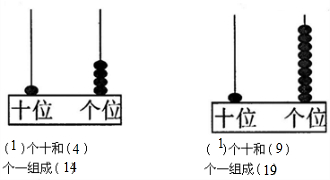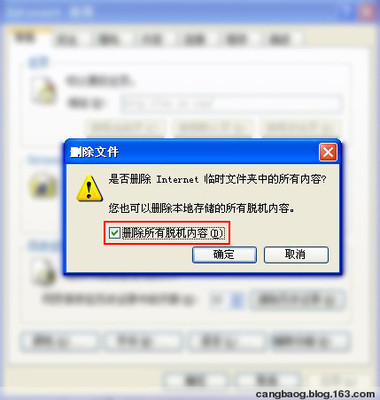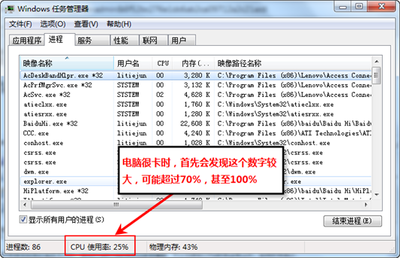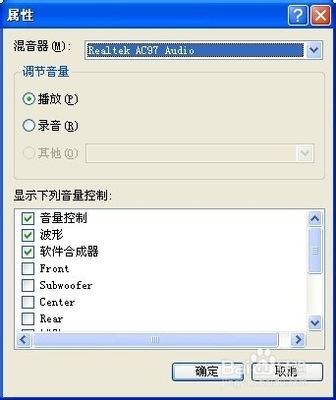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答《长江日报》记者刘功虎先生
问:《西州月》的书名富有诗意,为什么要改回《朝夕之间》?
答:《朝夕之间》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原名,这次恢复原名是想还原历史真相。熟悉我创作的读者都知道,《朝夕之间》出版不久因故停印。这是我自己很满意的一部长篇,不能让更多的读者读到,我心有不甘。过了几年,我找了个机会瞒天过海,改名《西州月》把这部小说重新出版了。当初改名的时候,曾有读者误解,说我把旧小说冒充新书出版,有欺诈之嫌。我为此专门撰文澄清过,并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这事很快就让读者朋友们理解了,更让我庆幸的是这部小说很受读者喜爱,不少读者认为它比《国画》更蕴藉、更温婉、更敦厚,艺术必更加纯正。可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书名。《西州月》是当时为了出版顺利临时凑合的,我不太满意。我喜欢《朝夕之间》这个书名,它包含着小说的重要主旨,就是小说主人公关隐达对人生的叹惋。这次湖南文艺出版社把我的9部作品重新推出,我当即决定恢复旧书名。
问:您的小说充满儒家情怀,主旨叫人向善,为什么社会上却有些人视为“官场必读”、“官场进阶”读物?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心理因素?
答:我作为作家,或者我的作品,一直是被严重误读的。比方所谓官场小说的说法,本身就是对我这个作家和我的作品的误读。我并不介意别人对我的所谓官场小说的类型化界定,知道自己的争辩也是徒劳的。有时我会调侃:假如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成立,那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渔业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犯罪小说,《红楼梦》则是青春小说,《西游记》则是穿越小说。
我觉得自己的小说满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显示着凌厉的批判锋芒,但有人觉得我的小说是官场教科书,我似乎成了教人学坏的黑暗教主。这既违背我小说创作的初衷,也并非读者阅读的真实体验。我从真正读过我的小说,或者真正读懂了我的小说的读者那里,得到的是深度的共鸣。指责我污化现实的人,指责我是黑暗教主的人,要么是没有读过我小说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的人。我曾公开表示过,因我的小说而非议我的,只有两类人:不正派的,不开明的。
我听不下一百位大学生,不下十几位大学教师说过,大学生快毕业的时候,有些老师会 着重推荐学生看看我的小说。我相信,老师的愿望是务实而善良的,他们想让学生通过我的小说了解一下社会,免得走上社会一头雾水,反而陷入恐惧和迷茫。这里体现的是我小说在真实反应生活方面的认识价值,老师并没有想把学生教坏的意思。事实上,一部小说就教坏了一个人,没有那么简单。哪怕真是一部坏小说,也未必就有这么大的功力。一个人读了十几年正经的好书,结果一本坏书就让所有的正面教育归零了,那么所谓的正面教育是否太脆弱、太虚假?
问:从《国画》到《苍黄》已过去十余年,您长期以其为剖析对象的官民生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您是否从中发现了让人感到欣喜的苗头?
答: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很多方面的问题几乎陷入僵局,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过去总是说发展中的问题,依靠发展才能解决。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过于依赖这条法宝了。很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不仅没有在发展中得民解决,反而是发展中没有协调好各种关系而带来的。比如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机会不均、价值混乱、道德沦丧、官场腐败、草根阶层上升通道越来越狭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并雄居社会金字塔顶端、权贵阶层同草根阶层甚至形成利益冲突和情绪对立,等等。这些问题都纠结在一起,一团乱麻。我没有从现实生活中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很多问题还在不断加剧。不重视这些问题,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会出大事。
问:不少读者喜欢使用“西州无好人”、“《苍黄》无好人”之类语言表达对您所刻画世界的读后感。我倒是觉得,您并不希望给任何人贴上简单的道德标签。在《苍黄》一书中您用艺术的方式揭示了体制的“无常”、不确定性,及其对人的异化力量。熊雄绝非人格分裂患者,也非多重人格。他就是他。前后一直是同一个人。我的理解对吗?
答:我的小说,不论是《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还是《苍黄》,都不是绝对灰色的,更不是黑色的。我的所有小说中都有很温暖的人物,如《国画》中的梅玉琴、曾俚、卜未之,《朝夕之间》里的关隐达、陶凡,《苍黄》里的李济运、朱芝,等等,都是可亲、可爱的。《苍黄》中的熊雄前后判如两人,事实上仍是一个人。他是体制人的典型形象,失去独立人格,服从游戏规则。惟其如此,他才能在官场混下去,才能如鱼得水,才能飞黄腾达。现实的强大,令个体显得相当渺小,相当脆弱,相当无助。行使着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场中人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情何以堪!
问:体制土壤里的病毒如何感染人,人在其中如何异化,行为突变,《苍黄》提供了精彩的“样本”。我能够理解熊雄的“突变”,禁不住希望看见更多有关他心理嬗变的细节描写,想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压力和权衡。我以为这也许是权力最为核心的秘密所在。但是您略去了没写,因而造成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观感觉。请问这是您有意追求的艺术效果吗?
答: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很能理解“两个熊雄”的现象,无需作过多的交待。当然,也许把熊雄心理嬗就的过程写细致些,可能是另外一种艺术效果。倘若再有机会,我可以尝试着把熊雄的变化重新写一下,我也相信这种补白会做得很成功。对此,我成竹在胸。
问:《苍黄》对无所不在的“利维坦怪兽”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剖析,对李济运等人的处境表示了同情,也营造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氛围。有读者表示,如果您能够在文本中提出对理想社会图景的期望,或许更有助于提升全书的主题。对此您是怎么想的?
答:描写理想社会图景,这已远远超越了作家的能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有能力给人光明、正义、希望等,而要像政治家、思想家那样为未来社会搭建蓝图,似乎做不到。用某种学说去阐述未来社会可以做到,而用具体故事、形象去描绘未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外文学名上类似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著名的《乌托邦》摆在现实面前是天真幼稚的。恩格斯说过大意如此的话:一部作品如果真实的反应了现实生活,哪怕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也认为这部作品完成了它的使命。
问:您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是什么样子?
答:有一天,我听上初中的儿子背诵《礼记·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顿时悠然神往。大同世界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虽非常美好,但未能实现。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描述的“乌托邦”。我心目中,没有什么绝对的理想社会,只有相对良好的社会而已。就目前中国实际情况来说,倘能加快并落实法制化进程,社会能够依法理性运行,就算是国人之福了。
问:一方面,我们所处的世界为文学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养料;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敏感,不免会生出“生不逢时”的慨叹。您觉得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冲破这种宿命?梁漱溟先生无奈的天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您有没有自己的答案?
答: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各种矛盾,而知识分子因为思考力强、责任心强,常会有“生不逢时”之叹。这是历史规律,也可看作历史宿命。人类社会走了五六千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在探索不同的发展道理,客观上有的道路先进,有的道路落后甚至反动。超越狭隘的民族偏见、宗教偏见、政治偏见、政治利益集团偏见,寻找具有普世价值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很有可能的。
问:有观念认为:在以暴力及恐惧为后盾的社会中,官员的声望及其在同侪中的威信,全靠恐惧来维系。对民众表示人性及善意,容易被解读为要在内部规则之外寻求其他存在的基础,给自己留退路,从而遭到体制无情的淘汰。显示僵化及无情是晋升的需要,也是安全的需要。您早在《国画》中就捕捉过这种对于“恐惧”和“害怕”的体验。请问这种敏锐源自您切身的体验多一些,还是间接的认知多一些?
答:文学创作素材的具体来源说起来很复杂,有时很难说清是自己的亲身体验,还是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目前中国的各种矛盾错踪复杂,而现代传播手段相当发达,事实与传播紧紧咬合,形成一个叫人无法逃避的“场”。所谓“场”,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人都在为这个“场”贡献力量,人人都受置于这个“场”。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是如此,叫人徒叹奈何!
问:塞缪尔·约翰逊说过,“当一个人使自己变成野兽时,他就摆脱了人之为人的痛苦”。在您笔下,主人公多是难以彻底摆脱痛苦的个人。他们经常观察到野兽出没,但是无能为力。他们有时候甚至加入他们。您为什么很少直接以“野兽”为主人公?
答:野兽见得很多,我却不愿意在作品中直接描写。因为心有不忍。尽管有人指责我把生活写得颜色过重,其实我没有勇气把真实的生活感受完全呈现出来。不是出于世故的怯弱,而是自己心底不能承受。我害怕描写黑暗的过程,也不忍把所见的真实的黑暗告诉读者。有时候,我有限度地描写着生活的不堪,内心却压抑着巨大的痛苦。因为,我知道真相,却不愿意说出来。
问:您的笔触尽管冷峻、冷静,不太轻易流露个人价值判断,但是由于您的主人公多具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或道德感,心灵中往往烙有难以抹去的信念,因此您作为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十分明显。饶是如此,还是有很多读者认为看您的书容易心灰意冷。您觉得他们阅读时抱持怎样的心态最相宜?
答:我常常叹息读者的善良和天真。我只可能做到不说假话,万万做不到在小说中虚构光明和希望。我曾套用艾青的诗表达过自己的心情: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失望太深!
问:您在《苍黄》一书中,巧妙利用了不少新闻素材,将一些网络现象、故事创造性地化用到小说之中。有读者担心,您早期对官场的描写大多根据自己最直观的印象和体验写成,而新近的小说会不会为了达到某种精神高度和艺术效果,丢掉可贵的真实性?
答:我所接受到的读者反应恰恰相反,大都认为《苍黄》非常真实。我想表达一个观点,真实固然是文学的生命,但文学仅仅真实是不够的。文学可贵的是要渗透对生活的思考。我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都凝结在我的小说里。
问:您的小说景物描写越来越少,一旦出手则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苍黄》中我记得最牢固的是开头一段提到的8个字,“白云出岫,风过袖底”,简练精彩。请问您的写作风格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答:我的总体文学气质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较大,而人文精神则受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影响大。但是,很难说清楚自己受某一位作家的影响。
问:您很喜欢网络传媒,很久以前就开通了微博,热心关注层出不穷的时事热点。您说,“当年如果有微博,我敢保证鲁迅先生必定是个微博控!”有的作家压根儿“不信任”网络,很少通过网络表达意见。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网络发生兴趣的?网络有一股什么力量一直在吸引您?
答:网络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我喜欢网络。虽然网络上鱼龙混杂,但这是正常现象。社会不就是鱼龙混杂吗?现实中混杂同网上混杂有什么区别呢?网络上传达自己的声音,快捷自由。鲁迅先生爱较真,如果他的时代有网络,必定天天会在网上同人论争。客观上,网络会推动民智开发,推进社会进步,这是我对网络最感兴趣的地方。
问: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介绍,自己家乡一度“买码”和赌博严重。您觉得近年来国家对农村的管理似乎有点不用心,有些放任。这背后有没有深层的原因,比如农业税取消之后,基层干部搭车收费无以依附,不得不大面积向城镇收缩?长期看,这种放任会不会导致一些积极的后果,比如出现类似于美国乡镇自治的局面?
答:我观察,近些年政府对乡村治理的放任和不负责已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只要不出问题,政府不管乡村的事。官方说法,重点是维稳。
我不相信这种放任会滋生乡镇自治。制度设置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基层社会没有找到适合的管理模式,只会积累矛盾和问题。前几年“买码”在乡村造成灾难性后果,很多乡村被这股风潮洗劫得很贫穷。这是南方很多农村碰到过的问题,而地方政府几乎是不予管理的。
问:“有的人,一上一下就是一站;有的人,一上一下就是一生”。您从政界退出后成了一名作家,作品被一些读者视为精神上的“必需品”,必欲搜求到手一睹为快。您在“知天命”之年,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能分别说些什么吗?
答:我要声明的是我从来就没有进入所谓政界,我只是在政府机关做过十九年的小公务员。没有做过官,谈不上曾在政界。我离开官场显然是同写小说有关的。尽管中国自古官员都是文人,但现在中国官场拿某种奇怪的眼光看文人。古时候官员不会写诗做文是件很没面子的事,现在官员写诗作文反而成了没面子的事了。人在官场而爱好文学,稍有不慎就被人看作另类。
我相信中国官场这种对待文学的反智风气不会永远沿袭下去,因为现实离曾经的以“大老粗”为荣的历史越来越远。文学毕竟是高雅的,有意义的。我的小说受到很多官场中人喜爱,我想并不是因为他们想从中间看到什么秘密,而是人们需要文学的滋养。
我已是半百之人,愿意至少在我八十岁以后看到一个风气清明的官场。刚进入官场的年轻人,三十年后同我现在的年龄相当。那时候官场风气如何,就看这批年轻人了。我想对他们说:为了你的孩子上政府办事不再需要潜规则,你现在起开始做榜样。我想对同龄官员说:你已经沾染官场恶习了,不要再带坏后来的人。抛开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说,中国官场今后走势如何,最要紧的是看当今四十到五十岁的官员们的责任和良知。当然,我这些话是很幼稚的。
(发表时有删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