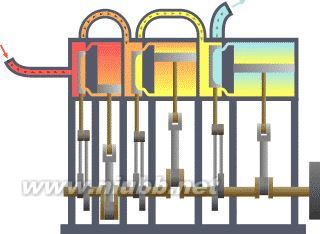但是,也有令我纳闷的,女人一经弄了文学,常常要被一些弄文学的男人宠坏了去。男人的毛病是喜欢别人就要别人和他一样,女人们因此也看不起自己,要么慢慢扭捏作态,已经是老大不小了,仍作小姑娘的天真,一尽儿卖娇,要么做个女丈夫,袒胸露乳地勇敢。放野的女人毕竟不是男人,能野到什么地方去,该遮掩的还得遮掩,于是只有一些泼。
我们面对的是文学的永恒和没有永恒的局面,而不是暂时的得失和一点虚荣.女人并不缺乏大的境界,真正的天才不需要起哄。
我在北京见过一次阿琪(本名黄少云)的,印象是很聪慧很自然,从此能记得那一副江南人说京腔的脆声。我那时并不知道她也弄文学,她是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出现的,有一个很大的背包,一说话就掏了笔和本子记录,采访得极简练,采访完了,笑一下就走了。
从北京回来,日子又平静而整齐地过去,已经有几个文友来交流读书的事,总是提到许多女作家,一日突然问:你知道有个阿琪的吗就拿了几篇阿琪的小说散文随笔让我读,但我不知道这个阿琪是不是北京见到的那个记者黄少云。
实在巧得很,三天后见过的那个黄少云竟给我寄来厚厚一沓复印件,全是她的作品,并附有一信,说她见我时,并未告诉她也是写字的,因为她还不到一见名字就知道曾写过什么的程度,但她现在却把发表过的作品集中寄来,如果能读,读后如果还有兴趣,希望我写一点序的东西。
我那时很寡地笑了,这些年里,我是为人写过一些序的,而自己的作品写得却少起来,怕正是应了“写不了作品就写创作谈,当不了作家就为作家写序”的话。我是认真地读过了她的小说,我读别人的作品,从来不是批评家,只是心态平和地等待不期而至的令我惊羡的部分。阿琪的作品确使我获得了许多启示,她的才气让我感叹,也让我生些许忌妒。
读过了,冷静作想,阿琪是属于哪一类的女作家呢尖而锐者,不是,艳而丽者,不是。她的写作时间已经好几年,现在还未惹得文坛悚动,但她的文字步步为营地发展着,其中涌动着许多青春的东西.惊涛裂岸不是她的品格,她该是轻风徐来,水波不兴.这种境界并不是清浅,它有自己的明净和温柔,有它的内涵和意义。

从它的文字里,得知了它的朴素与自然,也有了一种生气和力量,并未遭到污染.可以说,这是有出息的气象.但是,我要说的是,有了朴素和自然,有了生气和————力量,而对于种种污染,不是拒绝,应是面对和接受,然后经受污染生发出莲来。写文章需要加法,加到一定程度得用减法,加法最容易丰富我们,也最容易从此毁掉我们,而不会加法使我们永无成功的可能。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和重铸民族的传统,又藉于传统的伸展或转换以确立自身价值,这是历史转型期中我们弄文的人的既定的命运,我们须得有大的胸怀和一副好胃。
在文坛上我人微言轻,我的序是起不了当今序的作用的,这一点阿琪明白,我更明白.真正的作家是靠作品支撑的,作家的交往是建立在相互作品的理解上,我以上简单的观点,只是同志者间的交谈,我们不愿多发议论,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认认真真地依自己的人生体验走,弄好自己要写的文章,我想,艺术会亲近我们的。
(该文系阿琪《落花流水》一书的序言,该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