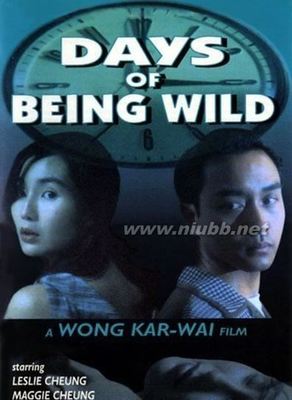电视电影《雪歌》后记
2007年春节,注定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日子!
那前后的四十多天里,我们这一小群人——电视电影《雪歌》摄制组,在中国最西最北的一个角落里,面对零下三四十度的刻骨严寒,面对说来就来的恐怖的暴风雪,连续干了三十多个大夜(通宵),此举估计前无古人,后即便有来者,也一定不会很多!
年三十休息一天,大家吃了顿有酒有肉的饭,好些人哭了!我感谢他们。
《雪歌》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灾难片,讲述一群不同经历和来路的人们遭遇同一场暴风雪,与之搏斗并最终团结起来的故事。
本子写得不错,编剧是个有才的人,美丽的雪山、善良的人们、肆虐的风雪,信手拈来,真实感人,故事紧而不乱,线索繁而不杂,但是除了剧作上的优点外,这部灾难片并没有太多令人兴奋的亮点,毕竟国内外的电影巨头们早已利用高科技把灾难片拍到了出神入化、叹为观止的水平,对于一部投资有限的电视电影,实在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弄不好,狗尾续貂,遭人嘲笑,同事受苦,领导添堵,观众想吐,何必呢。
因此刚开始,我在对这个本子表示赞赏之余,以自己有原发性高血压为名,谢绝了接手这个本子的要求。
后来接了,有人情的因素,也有(也许是更重要的)自己的因素,这个因素是:我三十七了,毛爷爷这时候已经发动秋收起义了!张艺谋这时候已经拍完〈红高粱〉了!我没有理由逃避困难、畏惧挑战!我的机会不多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去兮不回还!寒冬腊月,杀奔新疆。没打算不回还,但是拍不好就没脸回来了的想法,还是不时萦绕脑际的,算是自己给自己鼓劲儿,不敢说出来,因为真的没把握,怕将来下不了台……
弹指须臾,这部片子已经完成快一年了,在电影频道播出,也已经好几遍了,所幸的是,反响还好!对得起那些吃尽了苦头的工作人员和演员们!这一点我深感欣慰!
现在回思当时的创作过程,自然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希望和大家分享或探讨,希望将来再遇到类似的故事,会少走些弯路。
《雪歌》的创作过程中,我们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典型环境的气氛营造。
由于种种原因(当然最重要是预算的原因),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不可能获得后期支持,既不会有合成特技也不会有电脑动画,所有的暴风雪气氛都必须前期营造出来并拍摄下来,同时,这场暴风雪从无到有到大再到无,同一场景还需把握不同的风雪气氛,难度不言而喻。
天山厂的美术阿尔森拥有丰富的雪地拍摄经验,他的加盟使我们如虎添翼,著名导演高峰恰巧也在新疆拍摄一部胶片,他的经验也使我们受益匪浅。
通过学习请教,通过实地勘查,通过多次探讨和试验,我们确定了使用一台巨型鼓风机、两台中型鼓风机和两把手提式灭火器来制造暴风雪,同时我们订制了大量的苯板碎末,作为营造雪花气氛的辅助用料。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巨型鼓风机吹后景,用一台或两台中型鼓风机吹前景,手提式灭火器制造局部效果。刚下雪的气氛用真雪和碎末10:1的比例混合,暴风雪的气氛则全用真雪,顶多在前景少许飘落一些碎末,这样的配置,基本能应付从近景到中全的大多数景别的拍摄。
特写相对好办,一般不用巨型鼓风机,中型鼓风机就可以搞定,相对而言,全景和运动镜头就困难多了。
由于巨型鼓风机非常重,要10个场工一起拖拽才能移动,而它的有效范围又很有限,顺风情况下最多也就30米左右,所以我们轻易不做全景的横移或摇,实在要动,也尽量是纵向的推和拉。
鼓风机的位置和倒雪量是随机的,没有什么定论,我的印象是每个镜头都不一样,因为每次风向、照明光位、演员位置、景别都会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拍一个镜头前都多次试验,这也是我们进度缓慢的重要原因!很难忘现场制片柴兵和他率领的十几个场工,他们自封“风雪组”,他们吃的苦头只有看到的人才能体会!我看到了,可当时我不能让他们停下来,甚至,不能让他们睡个好觉,回想起来,我很难过,记得有句名言叫“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当然没到数骨头的地步,但我心里明白,我们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踩着他们的脊梁获得的。
当“风雪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鼓风机一一架起,把上百个雪包一一备好时,鼓风机就开始嘶吼起来,我们眼前就立刻一片茫茫,刚开始每到这时摄影和照明就会心痛他们辛辛苦苦整出来的后景密度,而我只有安慰他们说这是真实,后来他们也就习惯了,甚至发现拍这种暴风雪的戏后景必然是要放弃掉的——好几部美国大片也是这样的。
摄影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雪地结晶反光的问题,由于我们拍摄的地方极度寒冷,地上的雪都结成了沙子般的冰晶,反光率极高,当我们拍摄较大的景别照度较低时,地面的冰晶反光就会非常明显,严重的时候,就像满地洒满了金子,很好看,但是我们的规定情景是无法接受的,这个困难让摄影痛苦万分,苦恼了很多天,甚至有两个夜里因为这个问题而无法拍摄下去,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提高照度,因为当环境足够亮时,冰晶反光就不明显了,可是我们的灯又很有限,于是我们只好再想别的办法!
到杀青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低角度、不带雪地是实用的方法,但影响画面质量。加大风雪也可以淡化那些金光闪闪,可也没法都这么用!后来摄影师多次分析,要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使用大功率的气球灯也许是一个好办法,但这需要预算的支持!
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在六七十公分深的雪地里,我们很多的拍摄手段都只好放弃或少用了,因为无论是架轨道还是支升降,都非常困难,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时间,有一次为了铺四节直轨,我们动用了十名场工清雪,到架好整整用了两个小时,再架鼓风机再试验,拍完这个镜头,已经是四个小时后的事情了。
因为上述这些问题,我们的影像采用了一种凝重的风格,显得很纪实,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从结果来看,这一风格还是合适的,与影片整体的氛围是协调的。我的摄影师吴立晓是一位来自浙江的江南才俊,暴风雪中他常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在地狱般的严寒中,他熬了过来,用他的手中的镜头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幕幕动人心魄的画面。
美术组基本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兄弟们组成,他们的经验支撑着这部灾难片艰难前进,他们遇到的困难也许是内地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我吃惊的是,每一次,他们都顶了下来,他们的工作,获得了每一个来自内地的工作人员的敬重。
我们起初的外景地选在了新疆东部哈密地区的一座雪山上,不料我们遭遇了新疆史无前例的干旱冬天,原本应该大雪封山的雪山上居然没雪,无奈之下,我们不得不转场,这一转就是两千公里,我们来到了新疆最北边的阿勒泰地区,而我们之前搭的景全部作废。这是对美术组可怕的考验,有六辆卡车要接戏,有六匹骆驼要接戏,道班房要在几天里重新搭起,我不知道他们最终是怎样完成的,但我从美术师满脸的胡子和疲惫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
雪地拍摄最让美术组头痛的,莫过于脚印问题,由于本片的规定情景,很多场景需要人为布置,可是地下又必须是新雪,本来这件事在我们想来也不难,不就是提前准备好以后再撒上一层雪就完了吗?很简单呀,可事实并非如此。
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们碰到的情况是否是特例,但至少在我们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雪是不能碰的,只要我们碰了的雪,第二天就会硬化,硬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头天一踩上去陷到膝盖的雪,第二天就可以整个人站在上面不陷下去。
这是个可怕的问题,美术组头天布置好的景,第二天就没法用了,试想到处都是厚厚的雪,可我们的演员都像铁掌水上漂一样站在雪上不陷下去,这种景象观众能接受吗?我们不得不一次次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往往只有现场重弄,后期我们掌握了这一特点,美术组都是在我们将拍之前几小时去布置,而我们则抢在雪硬化之前拍完。
接戏是困扰美术组的大问题,窗花、冰凌、骆驼、飞雪,每天都在变化,而我们的戏规定情景是一夜之间,接戏的工作需要非常细致。无法忘记我们超勤勉的小道具师、永远美国大兵打扮的小制景、还有留着小胡子的化妆师,蹦蹦跳跳的小服装,一群不知困难永远欢笑的西部人,为我们的片子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说到现在,其实我根本没有谈艺术,没有谈我本应该谈的一切,因为我想真的没有必要了。
在这样一部片子里,导演的作用真的是有限的,这是一部团结的片子,是一部大家共同奋斗的片子,说到这里,我还要向我的演员们致敬!
宋佳伦、刘佳佳、刘思伟、林好,四位来自内地的演员,安尼瓦尔、海拉提、孙乐、贾尔斯……十几位来自新疆的演员,他们不是大腕,但他们都是优秀的有责任心的演员。寻常人在那冰天雪地中站 几分钟就会受不了,而他们,还要面对那巨大的鼓风机鼓出的风雪,我试过,站在那里,脸上像被刀子割裂一般,气都喘不过来,可是他们还要塑造人物,要表演,那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对于拍摄一部这样的灾难片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我们做出了最多只需20天在年前就可杀青的错误判断,致使所有的演职员合同都超期了,尤其是内地来的四位演员(还有摄影师),他们年后都签了新的合同,可是面对我们超期半个多月的违约情况,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理解,选择了放弃春节,选择了和我们一起奋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要求修改合同,增加酬金,虽然他们如果真的那么做,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不知道这样一股精神力量从何而来,我知道我不可以说我们的演员比别人更有道德——那样太虚伪了!但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真的这样做了,完全自愿的这样做了,也许是《雪歌》这个故事里闪耀的人性光辉感染了我们,在那遥远的冰封世界,《雪歌》剧组的全体成员,用他们自己的力量、用他们自己的心灵共同合唱着一首雪地圣歌。
我们拍出这样一部片子,毋庸置疑,它还有很多问题,很多遗憾,但是我知道,每一个《雪歌》剧组的工作人员,都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感到骄傲!
感谢把这部片子交给我们拍摄的领导和给与我们最大信任的制片人!
2008,中国电影已经有了《集结号》,有了《投名状》,有了《长江7号》,有了《大灌篮》,仰望高高在上的琼楼玉顶,我们开心,我们自豪,我们的脊梁,也已经融进了那千百万块电影大厦的基石之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