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消息在特定场合说出来有着特殊的震撼。
从南京到石台,朋友开着夜车,朋友的妻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后排。朋友的妻子是一位健谈的人,一路上说些身边发生的事情,似乎想打破深夜的寂静。
坐在后排的我,也许是着了点凉,不到一半路就有晕车的感觉,想吐又吐不出,不想说话,只是坐在后边听着别人讲,偶尔插上一句,以表示有兴趣听他们说话。
都是些家常话,女儿考上了什么学校,几位南京的老乡怎么样,南政院变得怎么样。娓娓道来,没甚新奇,却又很亲切。
“你们也许还不知道吧,你走这些年,南政院发生了许多事。”朋友妻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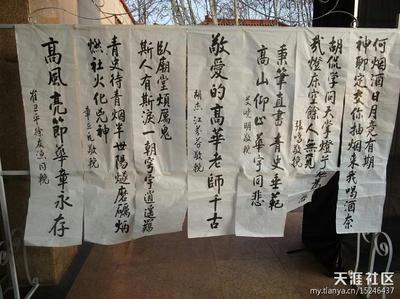
离开南京已经二十年了,小孩长成大人,大人变成老人,变化是很正常的。我心想。难道还有什么格外新奇的事吗?
“严高鸿教授去世了!”朋友的妻子不紧不慢地说。
“严高鸿去世!哪个严高鸿!”我吃了一惊。
“严教授,你还不认识?”朋友在一旁说,“前不久去世的,好像是五月份,已经成为全军学习的典型了,许多媒体都有报道。你上网肯定知道。看起来你不关心时事啊。”
“是啊,我不关心时事。可是这也太突然了,我只是不敢相信。”我支吾着。
朋友把情况跟我介绍了一番,说严教授再过一年就退休了,没想到患了心肌梗塞,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突然发作,死在工作岗位上。
听罢我良久无语。坐在一旁的妻子也无语。朋友不知道,我们与严高鸿教授有一段特殊的关系,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身为军校教员的他为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的学业,多方奔走努力……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离开南政院后,我和严教授联系并不多,有两次登稿找过他,有一年春节回家路过南京我们全家到他那去过一次。那一次他还在办公室上班,穿着军装,他喊我们吃饭,说师母不在家,他自己不会烧,只好请我们到外面吃,我们因为要急着赶路,就告辞了。
“你们的女儿真漂亮,”他赞叹道,我们正得意的时候,他笑着补充了一句:“不过,小时候漂亮,长大未必,很多小孩都是这样。”
脸膛方正、身材高大的严教授多半表情严肃,一副学者风范,很少笑。偶尔一笑,也不是那种哈哈大笑,而是嘿嘿两声,目光炯炯地瞅着对方,一副军人严谨的气质。
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妻子在南京读书到严教授家里去过两次,两次都是他爱人接待 ,也见过严教授一次。这些她回来跟我说过。
“什么时候我们到他们家去玩玩。”妻子经常说。
“好啊,哪一次我们路过南京的时候过去。”我附和道。我们在南京有许多老师和熟人,但每次回家或者不经过南京,或者虽然路过但没有停留。想见见昔日的老师是我们一桩心愿,只是每次都停留在嘴上。
没想到,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善良的长者,他还那么年轻,刚刚六十出头。
我常想,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地球上,每天大约有15万人死亡,平均每秒钟死亡1.8人。死亡是人类最平常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但是,对于严教授的噩讯,我竟是那样的惊诧,那样的心疼。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