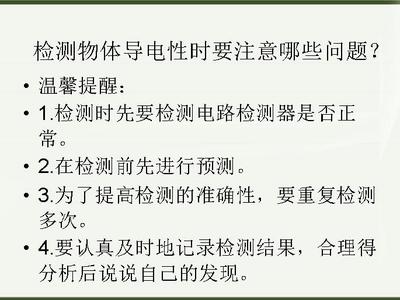杞迁小议
——兼涉笔淳于
李春颂
杞是中华大地上一个古老的国族,从夏商到战国或亡或立存续凡1500多年,它对于我国文明史的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其地位比较特殊,是曾君临天下的夏民族的后裔封国,又与周武王之母太姒有同姓的血缘关系。该国迁徙频繁,在流浪中拉得线挺长,国际关系复杂,的确是一个体现民族大融合的典型。虽然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却讲“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不足称述”倒不然,但有关杞事的史载的确太少了。特别是其迁徙路线和都城或说落脚的地望,太复杂,太朦胧,令史家大感困惑,也大感兴趣。于是,方家蜂起,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些对《春秋》《左传》的注解和后世史事爱好者撰写的某些说道,有失严谨,善意的猜测和传误,与经传原意及《史记》《汉书》等权威史籍多难契合,于是渐渐鼓胀了传世的经典谎言,混淆了人们的视听。近些年随着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相对丰富,以及治杞专家的学术研究的逐渐深入,杞国的历史真实的面纱起码是掀开了一个角儿,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本人通过学习和考察,对此也从而有了点新的认识。
一、杜注“首迁”质疑
《春秋·隐公四年》记载:“莒人伐杞,取牟娄”。时在公元前719年,这是先秦史乘所载杞国在山东最早的情况。无头无尾,可谓简约。晋代史家杜预倒有所注,于此语下称:“牟娄,杞邑,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六年,淳于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迁都淳于。”这一番详释传开来,影响很是不小。然而不小则不小矣,杜氏此“三迁”说中起码是第一迁(即首迁淳于),却与经传、事理相抵牾,产生了若干疑窦。示例如次:
一、《春秋》《左传》等典籍并未言及杞兼并淳于和紧接着定都淳于之事,杜氏根据何来?从时间和地点上说,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展示,西周中期以后,杞从河南迁来,最早是从鲁西而东移的,而杜注怎么能说杞人在春秋之初就突然出现在在齐东的淳于攻城灭国呢?
二、雍丘之杞这个在大国侵逼中挣扎求存的蕞尔小国,何能不远千有余里过来东并淳于呢?天地间有此等无可理喻的奇事吗?
三、依杜注,鲁桓公六年(前706)始自河南杞县北迁(淳于),那么,13年前“莒人伐杞,取牟娄”又作何解释?
四、中国先秦史学研究会理事孙敬明研究员质疑道:《杞乘》《杞纪》均以为杞武公初年就迁都淳于,不确。杞武公初年是公元前750年,又说淳于国亡于前707年,难道淳于亡国40余年之前杞国就过来吃掉了人家?这都是杜注惹的事儿,弄得好几个安丘老前辈算不着帐。
五、《左传·僖公三十年》说杞国受到了淮夷(即南淮夷,一说徐国)的攻击,乃迁都缘陵,据此,清代史学家沈钦韩质疑:若杞先迁都淳于,淳于在齐之东境,而淮夷在徐方,相距800余里,它怎么能侵扰着淳于呢?
与此相关联的,杜预的二、三迁也有点问题。杜注讲杞先迁淳于,然后又从淳于迁都缘陵,亦与理不通。那缘陵与淳于紧邻,二城相距不过五六十里,而且对淮夷居地徐州以南的淮河流域来讲是向西平行移动,这样如何能摆脱淮夷的追击?权威性特高的正史《汉书》《史记》分别说的杞“先春秋时徙鲁东北”和“楚灭杞……东侵广地至泗上”,此地就是杜说的齐东淳于那个所在?
杜预的“三迁”说,不管是其首还是其末,之所以出现这许多的疑点,其原因很清楚,问题就出在杜注背经离传,绎史竟乞灵于“推寻”、“似”等带盖然性、不确定性的字眼上面。唐经学家孔颖达在疏《春秋·隐公四年》时说:淳于“虽知其国灭,不知何国取之”,而“杞迁于淳于,疑不敢质,故云‘推寻事迹’,似当然也”。疑辞且自疑,当属妄测,逻辑如斯,谬不可信。无根之说岂能作信史!后世追寻杞史遇到的最大误导莫过如此,咱这里的人之所以对杞事津津乐道,就是得益于杜注的这一猜。正是古语说的:以讹传讹,流为丹青。
二、娄、诸、淳于与杞
若要追寻杞国变迁的踪迹,必先探其本源。据潍坊市博物馆孙敬明研究员考证,昌乐南邻的白浪河、丹河、朱河流域,有一个范围大遗址多的原始文化分布区,先秦时代灿烂纷呈,在古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域。昔有爽鸠氏故地,其东与斟寻相望,北与斟灌为邻,后为虞夏诸侯季荝因袭之。“杞”与“荝”古代读音两相通转,亦即“杞”乃“季荝”的合音,是一国之异名。这就是说,此一带即是早期杞氏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区域,还有人称有夏一代山东半岛大半为姒姓王室封国,而昌乐、安丘、诸城一线为中心地带。在商代《大戴礼·少间篇》载,“商汤卒受天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于杞”。不久,杞部族作为姒姓的代表逐渐南迁。商封杞于河南,迁时杞人不仅搬迁着国众以及财产,而且连同原始居住地的名称也一起搬着,于是,齐东的杞国重心“营丘”,变成了河南的“雍丘”(今杞县)。应当强调的是,这次迁徙只是部分姒姓族众的迁徙,山东诸城西部北部仍有杞人姒姓家族(或称杞夷)及诸国和娄国国族的存在。
前面提到的娄国,起初本名曰“娄”,娄即“楼”,楼是娄的后起字。《晋书·天文志》:“奎、娄、胃、徐州”,“城阳入娄九度”。城阳郡晋代时治所在诸城,与安丘同属于徐州城阳郡,故以娄星分野在牟娄。夏少康时曾封杞于娄,因而杞属姒姓娄氏。娄氏族甚古老,自西边东来居地颇广。娄国系姒姓宗室,殷末杞绝,周初求禹之后,武王从诸城一带访得东楼公,在河南就地重封之,使奉夏祀,仍沿用旧名曰“杞”。这从娄国的角度来说等于是本家近支出嗣,但其国(娄)仍自存在。娄国与在诸城、安丘一带为中心的比较强大的土著牟族交错相居,部分娄人后归牟人统治,遂合名曰“牟娄”,后为杞邑。
诸,国名,邑名。夏之斟灌、斟寻两国的直系后身,原姒姓,后为彭姓。《春秋左传》载“鲁人城诸”,即构筑诸的城邑。并且,莒县还曾出土过西周的“诸勃父匜”,可知春秋而上推西周再溯至商代,诸国为古国望族。其与亚醜方国有姻娅关系。其实诸国与杞国说起来还是老本家。其主要证据,便是上世纪30年代在益都县北苏埠屯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杞妇卣”等(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书,原藏于清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其上并有“亚醜杞妇卣”族徽,证明杞国与青州弥河流域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庞大的方国亚醜通婚一事,也说明杞国活动交往的地域远阔。在另一件垒中铭文有“者姒”字样。“者”即“诸”(如考释出的某甲盘之“诸侯”、殳季良父壶之“诸老”之“诸”,原件皆作“者”),是国号。此二字铭文与上面的“杞妇卣”合起来理解,意为:当时的诸君姓姒,故署曰“诸姒”。此杞器为媵器,随诸国贵族的一个长女他适亚醜氏的男子,身后作了殉葬品。时代为殷末。古文字学家认为“者”(诸)即山东诸城,具体来说就是娄乡(娄国)。由此可知,娄地早就有杞国的史影存在。
淳于,古国名。《春秋·桓五年》经谓“冬,州公如曹”,而《左传》云“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古文字学家王献唐考证,“州”盖“淳于”之合音,“淳于”即“州”。“州”音古隶尤部,当时缓言为“淳于”,急言为“州”。“淳于”既可合音称“州”,也可合音称“诸”。“诸”音古属鱼部,“尤”、“鱼”古音(韵)近通转,就像“洲”也可以为“渚”。“诸”其急读为本音,“州”其急读之转音,就“淳于”来追溯其源,原名当为“诸”。一地而有急读缓读二名,例证不少。
那么,《路史·国名纪》不是说州国是姜姓吗?回答是,在春秋初年当如此,要是更向上推,则是姒姓。《水经·汶水》注曰:“淳于,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续山东考古录》却谓“灌”为“寻”之误读,乃斟寻氏。但无论斟灌、斟寻,不都是姒姓吗?《史记·本纪》言:“夏之后,有斟寻氏,斟戈氏。”斟戈即斟灌。夏是娰姓。斟寻作为地名,有时只称“斟”。而“斟”与“诸”双声,音转最近,也就是说,在潍汶流域,名“斟”、名“诸”、名“州”,慢读皆音“淳于”,只不过先后以时空不同而异,其实是同指一个国。武王所封的,仍称“淳于”、“州”,而见于诸城区域者,仍称“诸”国。它们古代皆姒姓。古代一族一国先后异姓的事很正常。
看来,淳于与诸国有缘,诸国又与杞国有缘,那么杞国与淳于也就有缘。而且,后二者有缘到什么程度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们难解难分,以至同名一国。至于春秋时期淳于国都城的方位和地望所在,人们茫然无所知,专家们仰天兴叹:淳于,春秋不知何处!本刊创刊号淑耳君文《杞国三易甄微》所甄,愚认为很值得重视。关于《昌乐县志》所载北展乡七个“淳于”名村一事,历史学家赵俪生老前辈在其《说杞》文中也有提及,并为不少人所引用。赵老先生作为一个安丘子弟,却无意为乡邦争名人胜地,也并不附合《水经注》所指淳于之都在汶潍二川交汇处附近。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说那个地方是春秋杞国北迁山东的首迁地,立马吞掉了它。元代于钦的《齐乘》称之为“起城”,明代万历年间(400年前)人们就目的十分明确地改了改,书做“杞城”。退一步说,该地就算是曾做过淳于都城,也总得有点影像吧?这是需要考据证真的。治史者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文献有征,则信;无征,则不信。一位杞研究专家著文《山东新泰地区古杞国的来源和灭亡》谓:“淳于,一说为今山东安丘东北,一说为山东昌乐东南。”在考察了斟灌国的范围和北展七处淳于村后,他结论说:“可见淳于在昌乐境。”
下面引述一下文献资料和有关载录。
司马迁《史记·陈杞世家》之《索隐》引《汉书·地理志》称:“北海有营陵,淳于公之县。臣瓒曰:‘即春秋缘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州,国名,杞后改国名曰州而称淳于公。”
“淳于公之县”的“县”,即古代帝王所居之地。举例说明:《礼记·王制》:“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史记·秦始皇本纪》:“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
根据上述古史文献行文顺序,缘陵作为淳于公之都,或最早,或未另迁他处。
网络搜索:
“州亡后,州国公族定居于淳于,后来复国,名淳于国,仍为公爵,成为春秋的小国之一。再亡后,族人以国命姓,称淳于氏。”
“淳于国灭亡后,杞国迁都于其地,故后世也将杞国称淳于国,国君称淳于公。”
如此,起码在名义上,杞与淳于真的是合二而一了。这还不算完,杞国后期随着其由东西渐,新泰、泰安一带发现了很不少的“淳于”史迹,进一步明确了杞与淳于大密度的关系。(详见最后专题《仰晋回迁》专题之末)
三、都新泰有征
以前人们认识和研究杞事,往往仅限于地面上的一些历史、方志资料,所以其收获也常是些带有表面性的东西。民间搞的零零星星搜集,也与专门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人员费多少年的功夫科研出的成果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清末以来,国内众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治杞专家们,对杞国春秋之世在山东的地望的探研盛况空前,近几年来,又有了重大的突破。1999年秋,中国先秦史学会在新泰市召开了“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有12省市65位学者参加。会上群雄争鸣,发表论文50余篇,中国先秦史学会概括综合成《会议纪要》,会长李学勤先生在最后的讲话中肯定了《纪要》的核心内容:“与会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最晚自春秋时起,杞国就迁于今山东新泰定都,新泰作为两千多年前的杞国古都地位是有据可查的。”无问题,杞都并非固定一处,还有过或近或远的搬迁。《纪要》高屋建瓴,撮其精要,此其荦荦大端,简直是勾勒了一幅杞迁路线略图。与会者称,此次杞学术研讨会具有划时代意义。
杞从河南杞县迁来山东,走走停停,流浪中曾在滕县附近的邾国等地避过难栖过身,因杞、邾系婚姻之国(邾国是丈人行)。后长期居住或说重新立国的第一地点,考定为位于泰山之阳的今新泰市,确实有据可查。首先,考古发掘,功不可没。清代咸丰年间新泰出土了成组青铜器,计有:鼎2、簋5、壶1、匜1、盆1,共10件。上面的铭文基本相同,其中簋的铭文是:“杞伯每亡,作邾曹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每一篇铭文都带有“杞伯”字样。铭文与在古邾国(今滕州一带)所出土的铜鼎基本一致。这一集中出土的杞器群绝非嫁女之媵(陪送)器,而是每亡为其妻邾曹所作的礼器。这批文物的意义太重大了!杞伯每亡者,杞国之君也。清代学者许瀚先生早谓:“新泰系何国也,初无明文,今杞彝器并出其间,知班所云‘鲁东北’者,即新泰也”。从而认为新泰一带乃“杞之古都”。(转引自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卷二)许先生也够大胆的,仅凭对此器的初步研究就敲定杞国都新泰,也真有点玄。其实,如果零散出土几件青铜器,特别是再刻有“媵”字,那就不能断定该地为都。然而此处出土的明标刻着“杞伯”的青铜器成组成套成批,其规格又高,正合国君之礼制。新泰出土的八簋九鼎墓葬,常见于一般诸侯国君之礼,可见是都城之址。特别应当提及的是,在全国首届杞文化研讨会开过之后,新近有资料披露,“2002年在新泰周家庄又发现了杞国公侯贵族墓葬群,中有大型龙纹铺首和高级车马器等,如此多的杞器,为它地所罕有,而在此地集中出现,进一步证实新泰或其附近曾是杞都所在地”。
春秋之杞始都新泰,文物本已为显证,可也还有其他文献旁证:
古文字学家解读甲骨文,通过商王东征夷方往返包括杞在内的几个地方之间所用的时间,推算出杞国的方位就在泰沂南侧之新泰。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之“杞鄫何事”下注:“言杞鄫夏后,自当祀相。”从这一记载看,春秋中期(前629)之时,杞、鄫二国相距不远。临朐出土的“上曾太子簋”,说明曾(鄫)的地理位置在新泰东北邻。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以 杞封鲁”和“瘠鲁以肥杞”的记载,意思分别是因杞与晋国友好,诸侯们商议将杞国的领土割给鲁国部分和以晋为首的诸侯要鲁国归还所占杞国的领土。这两件事都说明杞与鲁国比邻。
《论语集释》之《考证》引《四书释地又续》一书云:杞国“与今之莒州及曲阜县相邻亦可知”。而新泰正处于上述两地之间。
孔子曾到杞国去观夏道,学夏礼,从而得到了夏代历法《夏小正》的史实,也说明杞离鲁不远,他绝不会跑到齐东之安丘一带来,孔圣人压根儿就没到过咱安丘。
还有杞之邑“成”·的在地,对杞国地望的确定至为关键。《左传·昭公七年》记:“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予之。”书中“杞田”下注:“前女叔侯不尽归,今公适楚,晋人恨,故复来治杞田。”书中“成”下注:“孟氏邑,本杞田。”是杞迁于缘陵之后成为鲁大夫孟孙氏的封地的。鲁定公十一年,孔子任大司寇“堕三都”时,守成城的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拒不毁其城,他说:“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杜预注:“成在鲁北境故。”足说明杞与鲁、齐密迩相邻。
《刮地志》:“成城在兖州泗水县西北五十里。”明《兖州府志》:“成城在宁阳县东北九十里。”今宁阳县境东庄乡西故城和南故城村一带有古城在,应即城邑故城。上世纪60年代新泰楼德公社西城前村(距东庄乡故城仅20公里)出土过一件殷代铜爵,铭文即“成”字,传世尚有同铭的鼎、卣等器,可证城邑确实在这一地点。城址既已定,则包括成在内的以及成邑以北、以东地区(即今新泰、宁阳、泰安三县交界地区)原应属杞国领土。许瀚根据《春秋左传》所记,推演杞国版图云:“规度杞国,成其西境,牟娄东境,北邻岱畎,南望龟阴,间于齐、鲁、莒三国,南北狭而东西长,截长补短逾百里。”学者认为这一分析大致可信。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经典史籍对杞国始迁地点和灭亡的地点的载记。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雍丘”下注杞“先春秋徙鲁东北”。汉代之鲁东北正是现在的新泰境。这“鲁东北”不可能够着咱这里的所谓淳于。《史记》载:(楚惠王)“四十四年灭杞……楚东侵,广地泗上。”新泰恰在鲁北边界的泗水上游。
总之,“鲁东北”与“泗上”实际上是一个地方——今新泰地区。这是全国研讨会《纪要》中强调的一点。
千万不能小瞧了这个新泰,它是我省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2万至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这里就曾居住着著名的“新泰人”(鲁中地区的先民),商代又曾是叔国址,新泰作为古杞国都并不奇怪。
下面顺带交代一下杞都新泰与杞邑牟娄的关系。一句话,是身子与腿的关系。隐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之时,毫无问题,杞人立都新泰已经多年了,对牟娄一直是触角所至。牟地、娄地是杞的一个祖籍地,杞夷未绝,杞邑仍存。早在殷末杞东楼公就曾经移居娄地,入周一个时期牟族被封于杞人居住区,娄、牟、杞渊源特深。杞北迁山东据新泰一带有多方面的考虑,除了与鲁、齐、卫三国间地有缘,特别是与成地人有着恩怨瓜葛外,就是想着来依靠牟人并和同姓的鄫国为邻相依。牟娄与新泰相隔固然较远,有200多里,这并不奇怪。古代以氏族统治,各国疆域自然形成相互间隔(古代国与国之间有不少的“隙地”)、犬牙交错的“插画地”和“飞地”。退一步说,即使两地有所连接,看看当世赤狄时穿不绝如缕的齐境,那么杞国国境不绝如一线也算说得过去吧?平时两地相互照应当然是会有的,但“小微”杞国的核心成员和核心国力在大西边,无法与莒的强势相抗衡,痛失牟娄一邑,也在情理之中。
四、缘陵之迁
如果说杞国从河南移山东新泰是其第一次大迁移,那么,从新泰到缘陵是第二次大搬迁,也是入山东后的第一次大的搬迁。缘陵何处?杜预《春秋左传正义》:“缘陵,杞邑,避淮夷迁都缘陵。”《汉书·地理志上》:北海郡,营陵。臣瓒曰:“营陵,春秋谓之缘陵。”于钦《齐乘》:“潍州西五十里古缘陵,春秋‘淮夷病杞’,诸侯城缘陵而迁杞。”地在今昌乐县东南50几里的营陵村。(见《嘉庆一统志·山东青州府二·古迹营陵故城·注》
学术界对上述缘陵的地望多持此议,但在杞国为什么迁都和从何处迁都等问题上,还有些分歧。让我们来介绍和理解下面几种有关资料。
《管子·大匡》:(齐桓公)“五年,宋伐杞”。时在公元前681年。杞公向齐求救,齐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曰:“夫杞,明王之后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公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鲁庄公因为与杞的土地纠纷问题,坐山观虎斗,不参与战事。齐桓公为平衡矛盾,劝杞公迁都,并将其国土暂时放弃一部分(当然尚存留一部分),鲁庄公立刻表示出积极态度。“大匡篇”又载:齐桓公遂“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甲一千”。《管子·霸形》亦如是载:“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子无事也。……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于是桓公曰:‘诺!’因命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大匡篇”又说了另一件事:“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千人。齐车千乘,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
记得有位德高望重的乡之长者有文说过的齐桓公曾两次“安杞”,大致就是上述。他在篇末写道:“《春秋》书中无此踪影,只记鲁僖公十四年(齐桓四十年,即公元前646年)有‘城缘陵’一事而已。此与《管子》所记,甚难说成是一件事,容续证而已。”这就给后来人留下了认真考证的空间。
那么,就来看看前646年“城缘陵”一事。
《公羊传》:“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谷梁传》也有僖公十四年“诸侯城缘陵”等的记述。
以上“两传”说的与《管子》“宋伐杞”是不是一回事呢?当是一事,不过有些人考证说宋伐杞的时间和到底是谁伐杞等等搞错了。并谓,《管子》乃政论之书,为战国、秦汉人所撰而非管仲自著,所记历史事件在其细节上并不严格。《大匡篇》常犯这样的毛病,如齐鲁长勺之战发生在齐桓二年,《大匡》却记在齐桓三年;所载“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时已是齐桓二十七、二十八年,《大匡》却谓事在齐桓六、七年。可见该篇所记年代的准确指数竟如此的有限。再是所谓“宋伐杞”,原是宋襄公为图霸业,背后操纵和支持徐淮集团去“病杞”的,宋没有直接干。因为齐桓公五年宋国正发生内乱,无心无力去侵略他国。再说宋国是鲁僖公十四年参与齐桓公盟会救杞的国家,《管子》说其当时会“伐杞”,也无甚可能性。
而“三传”中的最主要的一传——《左传》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所言,却是为史家多称道、史书多引述的,并且能作出较合情合理的论证。
《左传·僖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这与另外两传无别。但迁杞的原因却迥异。
《春秋·僖公十三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左传·僖公十三年》释云:“会于咸,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谷梁传》还有补充:“兵车之会也。”很清楚,快要打仗了!当年称霸诸侯的齐桓公主持了这个会,会的主题一是救杞国,二是保(周)王室。第二年,他就着手主持城缘陵而迁杞了。而那《公羊传》说“盖徐、莒胁之”,用了一个“盖”字,也是相当然的猜测之词,很不足为据。
淮夷,在金文和文献中均指(另名)“南淮夷”(古代“淮”、“潍”音同不假,但绝非我们潍河流域的什么夷)。以徐人为核心的淮夷联盟(其地在今江苏泗洪县大徐台子),一直想循淮水支流北上侵伐中原的华夏各国。古代淮、泗二水是汇流的,顺泗水河谷北攻也不算不顺。西周初年就发生过“淮夷、徐戎并兴”进犯鲁国之事。当此春秋鲁僖公时,淮夷又来进犯,因鲁强而袭击其旁的杞国,史家称为“病杞”。僖公为复仇和为华夏势力圈的安全而出兵修理淮夷。《诗经·鲁颂·泮水》歌颂其事,有“淮夷卒获”、“淮夷来同”、“莫不率从”等句,可见这次抗击是很有效的。
从淮夷的进攻路线和战略目标看,那时杞国的地理位置已清楚——泗上的新泰,受冲击之处绝不是缘陵身东不远的什么地方。从而,也让人们明白了杞国是从何处向缘陵迁都的。
杞国在鲁国和淮夷作战的前前后后,纷纷逃难,远远北迁。这次是回故乡,能在当时的齐国羽翼底下求得保护,也是缘分。齐桓公调集了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给杞国在缘陵立起都来,以保全周王朝名正言顺册封的这个宝贝国家。在今天看来,此举似无可厚非,然董仲舒谓齐桓公“擅封邢卫杞,横行中国”,讽其僭越天子之专权。杨伯峻谓“齐城之以封杞者,犹楚之迁许于叶,欲使在境内为附庸耳”。桓公的城府也够深的,霸气十足。
下面有一种说法是,其后不知什么时间,缘陵城又重修了一次,该是那“狄人伐”时曾毁坏过吧?虽然人说“伐”的是齐,但缘陵也没逃过兵灾。齐桓公再行善举,就是二次“安杞”了。
从杞成公九年(前646)迁来,到杞投奔新靠山于杞文公六年(前544)离开此地,凡120余年。
着实可叹,杞人就是华夏版的吉普赛人或犹太人,如此命途多舛,飘忽不定!
五、仰晋回迁
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杞曾经两次遭异国侵伐,只好依违于齐、鲁、晋诸大国间,日子还是很不好过。随着齐桓公的去世与齐国诸公子的争位之乱,齐国迅速从霸王地位上跌落下来。这时的齐国已无力再庇护弱杞,杞要在齐、鲁、晋众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就必须另觅更强的大国作新靠山。齐桓公辞世仅十余年,晋文公城濮一战击败强楚便取得了新的霸王宝座,这时的多数诸侯国,纷纷以晋楚为对象重新站队。鲁国首先亲楚,这就驱使长期遭鲁侵侮的杞国加入了晋国的同盟。而晋国也需要在鲁国近侧扶植一个亲晋的邻国,以与鲁楚相拒。杞入晋盟后不久,便与晋通婚,嫁杞君的女儿为晋悼公夫人而生晋平公。晋平公即位为霸主后,杞便依托晋国不断向鲁施加压力,鲁终于在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被迫归还了部分侵杞的领土;同年,“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这次由晋国首倡为杞筑城,次年连晋悼公夫人都亲自出面犒劳“舆人之城杞者”。如此兴师动众、高度重视,似乎不像是对齐东旧城的整修加固,而是异地别筑新城。就从当时的大变动、大改组的形势看,齐国已不能挺杞,而晋国又对远在东方而为齐、鲁阻隔的杞提供保护而深感鞭长莫及。弱杞若要摆脱被(齐)人裹胁的生活并得到晋国直接而有力的保护,就必须迁到与强晋相接的新泰、泰安附近地区来。
前面也已述及,在“城杞”的同时,还有“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向鲁国讨杞地)之举。可以说,“城杞”与“治杞田”是晋侯“治杞”的总体规划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对此,孔颖达似乎已洞察到了,他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疏中云:“城杞,谓筑杞城耳,下使女叔侯来治杞田,知治杞之地非独修其城也。”意思是一个目的,双管齐下。道理很简单,要想使杞在新地区站住脚,单给他修个城是不够的,还得为它尽快地扩充领土。于是,筑城的当年,便从鲁人那里为杞讨回了部分被占领土。九年后,又为杞从鲁人手里讨回了成邑。成城位于今泗水县西北50里,与新泰相邻。这样,就提升了在西部新立国的杞的国力。成地在宁阳境,新都城必也脱不出新泰、宁阳、泰安一带这个圈圈。《左传》昭公元年晋大夫祁午在追述赵文子“相晋国以为盟主”的政绩时,把晋国主持的“城杞”作“城淳于”来称述,这就向我们透露了有一个信息,即这次西迁回来的新都城叫作“淳于”。关于这个淳于,注家一般都认为是齐东与缘陵相邻的安丘东北的某个地方(原先笔者也以为是这样),实际上却不然。试想,若是如此,那楚惠王灭杞时,如果杞在齐东所谓安丘地界,楚军无由也无能跨越数国,翻过泰沂山脉和齐国为“备楚”而修筑的齐长城来灭弱杞。若一定要来的话,就必须深入齐国腹地,难免与齐国发生土地纠纷,而且与楚灭杞后“东侵广地至泗上”的记载也相悖。另外“城杞”(“城淳于”)和灭杞都与齐无利害关系,足以证明晋所城的淳于和楚灭的杞国都不会在安丘境内。那么,新筑的淳于在哪里?考古学家们基于以上史实,特别是考古新发现,认为它应是在距新泰楼德镇西北60里的泰安市满庄的淳于村一带。看来新淳于城确实在西而不在东。可不是嘛,晋国为首的诸侯国帮助杞国筑城,正是杞国西迁的产物,所筑之城是有利于加强晋杞联系而不是相反。然而正是这一回迁,后来也给楚惠王在四十四年灭杞东扩地至泗上提供了方便。
据考察,满庄镇以淳于命名的古村庄聚落,它们分别是北淳于、西淳于、中淳于和南淳于。据《泰安市志》载,靠近中淳于村,北依龙山,有一总面积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至2米的遗址,既有商周时期又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片。更为主要的是,据有关部门报道,近年又在新泰境又出土了“淳于公左造戈”、“淳于公之御戈”五件,另有“淳于杨”、“淳于云”铜印,还有一批铜兵器、贵族车马器等。专家认为,戈铭上的“淳于公”起码是杞回迁之前后的杞君之称。何林仪教授《淳于戈跋》文称:“淳于公戈应是为数不多的杞国铜器铭文中的一件标准器”。戈铭带“豫”字者,“豫”应是淳于公之名,即杞君之名,他应是战国初年的杞哀公阏路(前468——458在位)。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全国首届杞文化研讨会的会议总结(纪要)中也对此曾予以提及。事实表明,考古资料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论据,它也可以常常纠正历史文献之错误。总之,淳于戈出于新泰及附近地区,且为春秋晚战国早期器,恰与后期之杞在地域上、时间上若合符节,凡此,皆事理之使然,决非是巧合。省古文字学会会长王恩田研究员说得十分明白:“晋人祁午称‘城杞’为‘城淳于’,可见杞又名‘淳于’”。“一国二名,不足为奇”,实是不刊之论。
另外,支撑杞西迁新都淳于说的,还有淳于氏的大本营及其繁衍一节。《魏书·淳于诞传》载梁州刺史淳于诞,虽童年随父去扬州,但“其先为博人,后世居蜀汉”。博地在今泰安,西周属鲁,春秋战国为齐鲁交错地带,秦置博阳县(泰安旧县),汉初改称博县,属泰山郡,北魏博县改名为博阳县。而今泰安一带的淳于村,世传为淳于氏故地,距博平县仅十几公里。汉代名医淳于意(曾为太仓令。上书请作官婢以赎父刑的淳于缇萦是其女)的墓就在满庄镇,墓北、南,分别为北淳于、南淳于,两村之间的村为中淳于。近几年该地区一带相继出土带有铭文的兵器,如泰山附近出土了战国初年青铜器“淳于右造戈”等。这清楚地说明淳于家族长期活动在泰山一带,从而也锁定了杞国新都的地望形概。今天的泰安、新泰一带的“泰山文化圈”,确是名不虚传的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杞人尽管在“忧天”之中终失天下,但留给后世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操以及整个杞文化,与长天共永。
附:
参考文献:
(1)陈平杞史与杞文化四议》
(2)张广志《“东杞”“西杞”说》
(3)《王尹成《杞文化与新泰》
(4)王献唐《山东古国考》
(5)王恩田《从考古资料看楚灭杞国》
(6)蓝野《商周夏杞夷杞考》
(7)孙敬明《杞国考略》
(8)秦秘《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