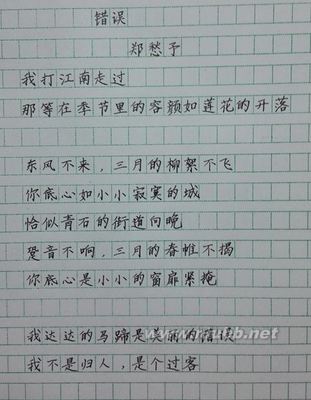昨晚写了点东西谈到了对当年清华朱令案的一些个人想法,主要是对该案当年侦办路线的质疑。文章登上博客当晚就引来激烈争议,但也引出了一些应该有一些意义的辩论与思考。于是现在把一些未必为外界广泛知晓的东西贴在这里,希望能引发更多的思考与争议,这样或许,仅仅是或许,我们会距离当年的真相更近一些。
首先,用尽量简洁而易懂的方式,把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本人认为可以得出的判断阐述清楚:孙维是朱令被投毒案件的嫌疑人,但不应是所谓的“唯一嫌疑人”,而应是一份相当长的嫌疑人名单之一。由于此案当年侦办时公安的拙劣无能,在重大关节犯了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错误,使这起案件在沦为无法挽回的悲剧的同时,沦为世界司法执法史的奇闻笑柄。前前后后,协和医院、公安保卫部门乃至清华校方都存在诸多应受指摘之处,而朱令身边很多可以为追查凶犯提供线索出力相助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而选择了“震耳欲聋的沉默”。或许,这就是人性的脆弱,或许这就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又一个活写照.....
接下来,此文的读者将要看到的一些东西,对于笔者的母校清华大学来说,或许并不是什么光辉灿烂可以拿来炫耀的。笔者在清华度过5年的青春岁月,从母校的教益中收获良多,坚定地相信此生将一直以母校为荣。然而清华不必是,不可能是,也的的确确并不是完美的。在那个永远收藏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充满了朝气与理想、信念与骄傲、睿智与拼搏的校园,有飞扬的青春,有真挚的友情,有勤奋的努力,但也曾经有过残忍的罪恶,曾经有过懦弱的逃避,曾经有过拙劣而虚伪的掩饰。或许,有些人会说没必要损害学校的声誉,但本人以为,如果为了些既莫名其妙又徒有虚名的“脸面”,有人丢了大半条性命,有人变成了网上通缉犯,有人变成了失声十几年的不解之迷,那这所谓的“脸面”还是不要也罢了。毕竟,脸面难道比人命还重要,比正义更重要,比真相还重要吗?(顺便公平地说一句,下文里即将提到的一些清华的弊病和问题,在许多国内高校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有所出入,方式也或有不同而已,所以说很多东西不仅是清华要面对的,更是国内高校要面对的,甚至是整个中国要面对的)
清华文艺社团独特的“集中班”住宿体制
昨晚写的文字里已经提到了,当年对朱令案的侦办,从开始就出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导致整个案件侦察一错再错,最终走入了死胡同,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是彻底地办砸了。由于这个巨大漏洞跟清华文艺社团专用学生宿舍的独特安排直接相关,因此必须要对此做一些介绍,让这个长期以来对外界讳莫若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清华学生当中被称为“集中班”的文艺社团专用学生宿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经非常成型,对此有所了解的同学不在少数,但却也不算非常普遍。应该说,以当时清华文艺社团的发达程度与文艺社团组织活动进行排练等各方面的需要,“集中班”的出现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以清华课程的繁重,文艺社团在白天搞这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到了晚上,学生宿舍都要按时熄灯,而且一天繁忙下来准备休息的同学们也不可能接受文艺社团的积极分子们在宿舍楼里吹吹打打鼓乐喧天。为文艺社团特别是其核心团队成员提供具有专用性的场地是必然的无法回避的要求。
按笔者的记忆,这个“集中班”的地点应该是在9号学生宿舍楼(但事隔多年,并不敢说100%是准确的,如有对此掌握得更清楚更有把握的同学请核实指正),与5号楼6号楼的女生宿舍楼“熊猫馆”距离并不远(如果没记错,应该就是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堪称清华文艺社团鼎盛时期的年代,经常喧闹无比的“集中班”是个出了许多重要成绩的地方---须知,今天的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在那个年月虽说当然是清华的主要文艺领袖之一,却也断然没有到了“一骑绝尘”的地步,那一批校园歌王舞林大侠抚琴高手的水准可想而知!然而,朱令的陨落仿佛是一种先兆,在随后并不长的时间里,随着老生毕业离校,新手应接不暇,清华文艺活动的历史高峰走入了历史。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宛如夏花般灿烂,却仿佛是在嘎然之间,便已在众人的惋惜声中如秋叶般飘落。
说句老实话,对于那段清华的文艺岁月,本人只是个站在边缘的看客。在清华的那几年,先是忙于学习,后是畅游书海,再后来就是忙着准备出国留学。但即便如此,只要身在那段时间的清华园,你根本无法置身于那股文艺热潮之外。而对于“集中班”比较近距离的了解,却是来自这样一个渠道:本人虽然是一个专注读书的“乖孩子”,却有一位“同年”是热衷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几乎一入校就开始向某社团靠拢,并且后来如愿成为其骨干队员(不过并不是朱令所在的民乐队),并由此得到了入住“集中班”的“资格”。
这位“同年”入住“集中班”后,很快就赶上了演出任务,组织排练等工作无比繁重,可以说是每天忙得连钟点都没了。如此昼夜颠倒的日子,他自然不方便深更半夜回原宿舍打扰同学,而且他所在的男生宿舍要回去也相当远,于是他索性就长住在“集中班”,一住就形成了习惯,以至于在长达几个学期的时间里很少回原来的寝室。对此本班同学是很理解的,只是遗憾晚上的“卧谈会”少了一个健谈的舍友。但时间长了,宿舍楼的管理方得知了有这么一个“铺位”常态化的空在那里。楼长老大妈和管理员们对此深为不满,但住在文艺社团“集中班”并不违反任何校规(这毕竟不是到校外去另寻住处了,跟现在的家常便饭完全不同,在那个年月是校规严厉禁止的,仅仅这一条就可以是处分劝退甚至开除的理由!),而且这位哥们虽然肯定是不能跟黄开胜朱令高晓松他们比(否则也是一名人了),但以他当时的位阶,也算得上是学生社团的一位领导了。宿舍管理方拿这位同学没什么办法,但摆出的态度足以让同学们清楚地感觉到就这样让一个宝贵的清华学生宿舍铺位空在那里是很不应该的,是对不起国家给的待遇的,是很需要深刻反省一再检讨迅速纠正的.....终于宿舍管理方抓住了一次学生宿舍调整的机会,迫不及待地把另一位同学塞进了这个宿舍(同班的而且相处得不错),让这个被革命觉悟不高的同学们遗忘了抛弃了的铺位再次迎来了让一个清华学生睡在上面的光荣。就这样总算是了了由于那位“同年”入住“集中班”引发的这一劫。(本人与这位“同年”以及他的舍友曾在一起准备出国留学必经的G托考试,相互之间极为熟悉,因此对这些掌故知情。为不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在此不愿提到他们的姓名与其他具体信息,请各位读者理解)
“集中班”如何成了清华校园的“伊甸园”
如此一个成绩斐然的“集中班”,为什么却要那样讳莫若深,以至于即便在文字里提到,也几乎全是用“乐队同学宿舍”、“XX队同学那里”、“队长同学的宿舍”等等倘若不是事先已知内情,那几乎是必定要误解为XX或XXX的“正常”学生宿舍的词语来形容呢?
那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班”里出现了一些别的东西,一些无论当事人还是学校管理当局都不愿让外界过多关注的东西。
与以“严格管理”为宗旨的绝大部分清华学生宿舍不同,特别是相比由于进出严加控制“比进日本鬼子的雕堡还难”而被誉为“熊猫馆”的女生宿舍,“集中班”的组织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集中班”出现就是为了满足文艺社团集训排练会议等等活动的需要,因此必然是以社团为单位划分,而不是如普通学生宿舍那样以系和班级为单位划分。况且各文艺社团的成员往往是个性鲜明,身份也相对复杂,至少研究生与本科生在同一个社团是很普遍的现象,而清华对研究生与本科生的管理标准又很不一样.....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中班”的寝室铺位在进行分配时随机性很强,很容易出现混乱,而且虽然寝室仍然是分男女的,但却无论如何做不到把男生寝室与女生寝室的所在区域明确而彻底地加以区分。另外,“集中班”是个时钟错乱昼夜颠倒的地方,在夜晚每每紧张忙碌热闹非凡;到了白天随着文艺社团成员们上课的去上课,自习的去自习,有事的出门去办事,不上课不自习不出门办事的则往往乘着同学去上课溜回原宿舍补觉,“集中班”反而变得比较安静,某些地段甚至完全可能白天基本没什么人。
于是,渐渐的,在当时那个一派“以德治校”风范,校领导三天两头左反西方歪风右反堕落邪气,试图以填鸭式的灌输把学生们个个都洗礼为读 圣贤书守传统道的清华园,文艺社团的“集中班”宿舍却在校领导校党委的眼皮底下变成了一个“特区”。
一开始,“集中班”里上演的不过是男生女生在一起约会谈天,然后就是很自然地一起做饭吃饭。再后来,不难想象得到,在清教徒式作风大行其道的清华园里诞生了一个男欢女爱的特区。到九十年代后期,男女生常态化地在文艺社团宿舍里共同起居已经不是非常罕见的事了。再后来恐怕是一些团委名下之类的别的可以住人的地方也开始看齐了.....
以今天的中国社会今天的中国大学,大概早不把这个当回事了;当时高喊口号的清华校领导,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短短十几年后,他们身边会是一个遍地按摩房夜总会“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的社会;但在那时节的清华园,在“集中班”享受伊甸园式快乐的男女生们却是一群“痛并快乐着的贼”:他/她们的所作所为仍然是清华的校规校纪明令禁止的。尤其是那些在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的恋情就更加危险:清华是坚决不允许本科生哪怕是考虑一下结婚的,因此即便研究生愿意把本科生娶进门(男生一般应该比女生大嘛),在清华的政策下也不具备可操作性,而未婚就混到一起,一旦爆光出来,校纪处分就等着你,下场恐怕只能是双双被劝退(不算开除就是留面子了)。
在这样的压力下,“集中班”的“文艺社团男女特区”只能是低调低调再低调,但是再低调也免不了风声四起。不过,时代毕竟是接近世纪之交了,对清教徒式作风的阳奉阴违在日益腐化堕落的校干部队伍里也渐渐蔓延开来了。作为睁只眼闭只眼的交换条件,某些担负监管职责的干部甚至是团委学生会的领导干部也在名义上加入了某某社团,但其目的是而且仅仅是在“集中班”拿到某寝室的钥匙(可以想象领导干部们要的是条件好的,而且往往是“单间”)。有了不用花钱的“长期情侣房”,学生干部们便可方便地把涉世未深的本校或外校的女同学们带进“集中班”放纵快活了。到后来,动不动就谣言四起说得有鼻子有眼,例如说学生干部XXX上周末又到X教的舞会上转来转去,而且许多人看见他带着舞会上刚认识的女同学直奔“集中班”方向而去.....
这些谣言,必须实话实说,本人是不辩真伪的。辨别真伪的成本太高,而且也没有兴趣,那时节整天忙着背英语单词还来不及呢!不过,同样可以实事求是地说的,是本人确确实实在无意中碰上了一起此类事件:那是大三军训的时候,在艰苦训练的间歇N个系聚到一起搞活动,一位极其活泼的小女生在文艺表演上大出风头让大家印象很深;后来过了大约一个半学期吧,听说已经跟某位党团委栽培的“典型榜样标兵”在一起了;再后来,偶然在距离“集中班”不远的路口碰上了骑车路过的她,当初招人喜欢的童稚般的活泼已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知该往何处去的茫然和忧伤挂上脸颊和双目的女人(当然没搭话,因为她显然是不想跟任何人搭话)。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来当事人已经各自组建家庭了吧(当年议论过此事的同学们一致认为党团标兵XXX将来信守许愿的可能性是百分之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扰,也不提那二位的姓名了吧.....
在罪恶之后,为了“脸面”,真相被可耻地牺牲了
看到这里希望一些朋友不要有所误会,另一些朋友则不要乱说乱叫,从各种公开的信息看朱令应该是一个保守的女孩,至少是没有佐证说她当年曾在“集中班”如何如何,反而有朱令即使深更半夜也要回6号楼本班女生寝室睡觉,并且还招致了室友不满之说(或许是因为看不惯“集中班”的乱象,或者“集中班”晚上的吵闹,也不是个晚间休息的好地方,不过有些让人难以信服的是,这也成了足以投毒杀人的动机)。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信息来看,朱令到“集中班”要么是乐队活动,而且这个在民乐队的后期似乎应该更多地挪到西大的艺术楼那边去了;要么是利用那里不限电煮东西,而这个更多是在白天。95年初的第二次投毒很可能就是在这个环节。
但是“集中班”愈演愈烈的混乱终于是不可收拾了,而这对于当时仍然坚持要供着礼仪德化牌坊的校方就成了个越来越头痛的问题。除了反复开会三令五申(这个从后来的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就不难想象是啥效果),用违纪处分吓唬(带头“违法乱纪”的就是学生干部,千里之堤必然溃于蚁穴,犬儒们终究是要靠“关系”混下去的),最后的“办法”就是驼鸟式的装模作样为尊者讳了。尽一切可能减少“集中班”被关注,特别是受到外界关注的机率,就成了唯一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仍然高喊口号高举牌坊的校方等于是在无奈地低声说,你们可以做,就是别让外边听到。
现在,细心一些的读者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在1995年春夏之交确认朱令铊中毒而且是被投毒之后,彻查这个案件与维持学校的那个莫名其妙而又徒有虚名的“脸面”之间已经出现了极其难以调和甚至根本无法调和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至少有理由怀疑,当年案件侦办里那个巨大的漏洞或许并不完全是偶然的。
本人并不知道,当年朱令案确认为投毒之后,校方的党政干部们有没有向即将接受警方调查的人打招呼,要他们对朱令曾在“集中班”出入并在“乐队同学宿舍”煎药的事实守口如瓶。本人也不知道,当年公安局14处的同志上门后,校方的党政干部们有没有向即将开始案件调查的人打招呼,要他们把调查限定在某个不包括“集中班”的范围以内。但本人清楚地知道的是,在一个严肃的成熟的法制国家,倘若有那样的打招呼,那只会被冠以一个称呼:妨碍司法公正(ObstructionofJustice)。在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这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在迫使尼克松引咎辞职的罪名里,就包括那么一条。
当然了,这样替他们担心大概是杞人忧天了,这样的招呼恐怕是没有打过的,因为根本没必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是犬儒主义盛行的土地,从党政干部到普通百姓,多的是重复根本就不相信的话,眼睛却盯着这些假话空话换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于是,在残忍的罪恶之后,为了那个莫名其妙而又徒有虚名的“脸面”,真相被可耻地牺牲了。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知道孙维是不是凶手;我知道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孙维是当年那个凶手的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同时我还知道,在当年的校园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嫌疑人的嫌疑是不应被排除的,他/她们的嫌疑当年被错误地排除,是因为案件的侦办建立在一个出了严重错误的假设之上。朱令被毒害,居然只是一个开始:侦办路数出了丢人现眼的巨大漏洞,为尊者讳排在了司法公正的前面,为了把已经进了死胡同的案件弄得有所交待,在学生们就要毕业(而且相当一部分很快就要远出国门)之际,硬着头皮沿着错误的侦办路线一直走到了黑,然后把既没有过硬证据又没有严密推理的“唯一嫌疑人”说成是有背景有后台查不动,接下来就是让一帮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网民定期背诵标准答案了.....“脸面”至少暂时是保住了,公安和保卫也凑合着交差了,义愤填膺的人们也有了可以宣泄仇恨和义愤的目标,简直是皆大欢喜了!不过,不知有多少人检视过,那个把嫌疑人范围从数十甚至可能要以百计一下子压缩到只有三个女生的“投毒一定在宿舍里”的基本假设到底有多靠谱?倘若,倘若这个假设出了问题,那就意味着可能,至少仅仅是可能,成了“网上通缉犯”的“唯一嫌疑人”实际上却是先被恶毒的凶犯栽赃,再被无耻的官僚机构拿来顶杠交差,接着再被一大帮网民十几年如一日地喊打喊杀.....
我知道有许多许多东西很多很多业绩是清华的荣光,我不知道,当不得不面对这一切之后,朱令案是不是应该被称作清华的耻辱。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特别是留给我的清华人同学们,而其中更要特别留给我当年一个也不认识,现在仍然一个也不认识的此案的各位当事人们,也包括那位(或许还是几位)至今仍然没有遭受应有制裁的凶犯。这个问题,请权且当作我是替默默目睹了当年这一切的清华园问的。
到如今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曾经流淌着朱令弹出的“广陵散”的校园早已物是人非,当年就被牺牲了不知多少次的真相就更是面目模糊难以辨认了。每当挣扎着伸过手去,却不得不意识到她已走得更加遥远,这让我想起了丹尼尔·伟伯斯特的一句话:我并非母校的骄傲,但我却可以听到母校用哭泣的声音说,你是我的儿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