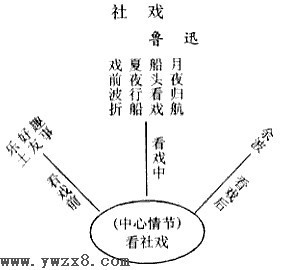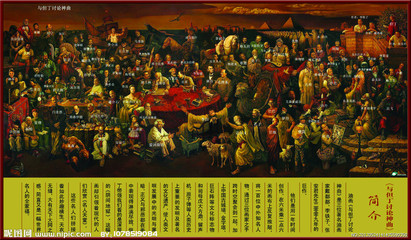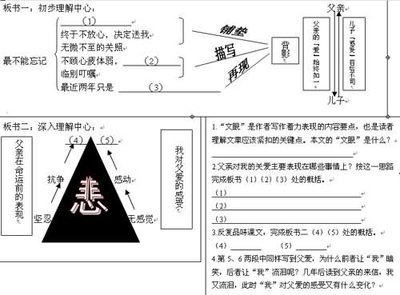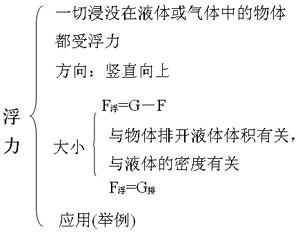严复《天演论》作意与内涵新诠
吴展良
一、引言
严复译介的《天演论》一书对于现代中国思想与学术史有划时代的影响。甲午之后,新文化运动之前,整整一代人主要透过严复的翻译去认识西方的学术与思想,而其中影响最深也最广的,莫过于《天演论》一书。甲午战后,中国知识界对于传统文化作为政治社会人生的最高指导的信心开始崩解,对西方文化也才开始有了热切的兴趣与信心。原有的学术与思想体系开始受到根本而全面性的质疑,建立新体系的要求随之而起。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史,应以此新旧体系转移之际作为断代的起点;而严复所引进阐释的天演论,则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关键时期的世界观,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的学术与思想走向。此后的变法与革命思潮、激进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斯主义、自由主义、生机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反形式理则思想、反启蒙思想、现代保守主义与其它多种主要思潮,都在天演论式的世界观与学术观之基础上继续发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原理之诸多看法,例如自然主义、唯物论、进步观、变化动进主义、世变趋繁论、本体不可知论、人与生物同原同类论、社会演化论、社会有机体论、自由竞争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都导源于严复式的天演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人文社会学界所普遍重视的发生学的方法、历史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变动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实验主义、实证主义、乃至马克斯主义方法论,也都深受天演的世界观及严复《天演论》一书中所表现的学术态度之影响。此书在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史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1]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严复《天演论》一书的作意,多偏从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危机哲学」等观点加以诠释。[2]这些说法,虽有其一定的道理,然而严译《天演论》更根本的作意,却长期为学界所忽视,因此对于本书的主要内涵,及其所表现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也有相当严重的误解。本文企图论证严译《天演论》的真正作意在于会通西方与中国的最高学理以明道救世。不明于此,我们将无法了解本书深刻的内涵与其学术及思想的特质,亦难以解释何以此书在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史上可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3]
一本书的作意与内涵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不完全相等。从定义上来说,作意是作者主观的意图,内涵则是具体成品所表现的意蕴。传统上,读者对于作品(work)内涵的诠释,主要在于解读出作者在字里行间所传达的意旨,与其所设法完成的目标。从这种角度所解读的作品内涵,其实系以作者的作意为中心,仔细检视与分析作者在作品所实际传达的主旨及其意义。在解读的过程中,固然必须注意作者是否只有单一意图、作者诸多意图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自觉的意图与实际作品之间的落差等问题,然而其研究的重心,始终环绕在作者的原有意图之上。然而新批评(newcriticism)以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研究(textural study, contextualcriticism),让我们注意到成品的文本(text)自有其生命,此生命缘自无限复杂的语言与文字世界,常超越于作者原有的意图。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声称,当书写(writing)的行为一旦开始,作者就不再直接生活或作用于实存世界,而开始进入一个语言文字的世界,也因此宣告了他自己的死亡。文本,而不是作品,才是我们应关切的重点。至于作意(intent,intention),则被归类为既不重要也无法确定的事物。[4]
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固然为文章的诠释提供了崭新的角度,却未免有过激与不适于史学研究之处,本文因此宁取较传统的观点。笔者认为,同时也透过本研究得以确认,对一个具有足够能力的作者而言,「作品」的内涵虽然可能有走失或超出作者主观预期的部份,但不致于与原作意相差太多。至于「文本」的内涵,则应放入语言文字的复杂传统作多面向的分析,同时可以因读者的不同背景而有非常不同的解读,难以有固定的说法。学术与思想史上的作品,到底不等于文学创作。文本分析的新方法,虽然早已不限于文学研究,却仍然深受文学研究观点的影响。二十世纪的主流文学批评认为文学创作的「文学性」(literariness)不在于内涵而在于形式(form),形式之基底在于语言文字,因此「文本分析」亦以语言文字的表现方式为研究重点。[5]文学创造的关键,在于表现方式的突破。然而学术与思想作品的主要价值则在于作品的内涵。作品内涵与作者意图关系密切,对此二者的研究则必需以作品分析为中心。所以就学术或思想史的研究而言,重点应该放在「作品分析」而不是「文本分析」之上。
然而若更作进一步的探讨,则「作品分析」与「文本分析」也不全然是矛盾的。当代的文本分析让我们注意到一本书的内涵有相当一部份来自他所运用的语言文字传统,而且该传统自有其无限复杂的生命。我们有关于「文本」内涵的分析,主要应循着语言分析的路线进行,以探讨此文本在无限复杂的语言世界与文字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文本中的复杂内涵为何。这种观点,非常能够让我们注意到一部著作所具有的语言文字与表现形式的各种特性,及其在广大的符号世界(worldofsignifiers)中的意义。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凡属敏锐而认真的作者,莫不细心选择并琢磨其语言,企图使其适切地表达其所要表达的意旨。严复选择高古典雅的桐城派文字进行译介,并持续地镕铸新词,这对本书的内涵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然而这个选择,原本就是本书作意的表现。语言文字的确自有其复杂的生命与规律,然而此生命与规律,又何尝不已经成为作者生命的重要组成?[6]换言之,像严复这一类对于他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高度自觉而敏锐的作者,有关其作品内涵的研究,本来就应该融入「文本分析」的部份观点。根据上述观点,本文基本上仍然采取传统「作品分析」的方式,以研究本书的作意与内涵;然而为了对于新批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文本研究的挑战有所响应,本文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也时而运用「文本分析」与「细读」(closereading)的方法去讨论严复运用语言文字的方式及其意义,以进一步深入了解本书的内涵。
「作品分析」的关切点应以作意为核心。有关作品内涵的讨论,则系以作者的作意为中心,仔细检视与分析作者在实际作品所企图传达的主旨及其意义。本文有关作意的研究,首先根据本书的序、例言,以及作者的背景与其它相关文献加以分析。序、例言可以代表作者自述的作意;对于背景与相关文献的研究,则可以进一步让我们掌握作者的真实意向。在此之后,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作为全书主体的导言与本论之内涵,以检视作者自述的作意实际落实的情形与具体作品所呈现的丰富意蕴。然而在实际研究时,有时不免引用导言与本论,来验证有关序、例言以及背景资料的诠释。而对于导言与本论的解读,其实也不免受到有关序、例言以及背景资料研究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两者的理解并不容易真正分离。两者时常构成一个诠释的循环。这种诠释的循环在「作品分析」中不仅无法避免,似乎也不应避免。因为作者一般都希望读者从整部作品,而不仅是从序言、背景分析或相关文献中来了解自己的作意。笔者的研究显示,从序例言与相关背景中所分析出的本书作意与导言与本论中所呈现的内涵相当一致,两者可以互相证成。作者自述的作意,确实已落实在其作品之中。
本书的作意相当复杂,有体有用,有本有标。本书的内涵则更为丰富,不仅有体有用,其体与用都可以分为许多的层面加以讨论。而严复对于语言文字的高度重视,又使本书的内涵,更加的深远。过去有关的研究,份量十分庞大。本文以建立本书作意与内涵的新诠释为目标,对前人研究的得失,不拟作仔细分析。既以建立新诠释为目标,所以行文时不免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于严复作意与本书内涵中救亡保种、追求富强及促进变法等层面虽亦加以讨论,却不再详细发挥。同时对于本书中所涉及的各种学说的具体内容,亦不能一一加以分疏。然而即使如此,本文的份量,已经相当繁重,由此也可见本书作意与内涵的复杂及丰富。
综合言之,本文企图论证严复译作《天演论》一书的基本作意,在于本乎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并结合中国固有的思想,以指点出人文与社会进化必须遵循的自然道理及中国文化所应发展的方向。在严复而言,能认识并遵循宇宙与人文进化所依循的根本道理,则自然能,也才可能救亡保种、获得富强、知所变革而善应危机,并进而达到长治久安。换言之,就是明道才能救世与济世。明道为体,救世、济世为用。明体可以达用,然而不明其体,则所用不成。[7]此书志在明道,内容少及于时务,虽不忘救世,然而实以明道为主。至于就著述的动力而言,追求最高的真理与大道、救亡图存以及追求长治久安,对于严复而言,都是主要的动力因。所以合而言之,本书的宗旨在于明道以救世。
二、究理极以明大道:从序例言看《天演论》的作意
严复《天演论》一书的自序应是我们了解其作意之关键。该序文辞典雅,意蕴宏深,不幸长期被人误读与曲解。原文一气呵成,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本文不避其长,先全录该文于次,而后再作分析: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着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1],据公理[2]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3]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干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干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4]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侈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光绪丙申重九严复序。[8]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提出如何能认识一国语言文字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以及该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所曾提出之最高学理的问题。由此问题出发,此序一路析论中国与西方学术的最高成就如何相通,如何可以透过西方与中国学术思想的比较而认识中国经典中隐而难明的高深道理。最后则指出西方学问实有其超越「象数形下」与功利思想的高明之处,国人大可以透过西学来认识古人难明的学问。全文宗旨在于指出真实学理本可相通,中国古典与西学中所包含的道理,正应透过比较研究,才能认识得更深透。于此同时,严复也透过这篇序言向轻视西学而崇拜古代圣人与经典的中国读书阶层提出呼吁,希望他们能了解西方学问实有其超越技艺与现实功利,而通乎古人之道的层面,必须予以重视。严复在这篇序言中以百分之九十八的篇幅讨论中国的学术走向,而只用了半行话点到「自强保种」之事。其思考的出发点与本书的基本关切点究竟为何,即此可知。[9]严复一向有「明道济世」的抱负。依照儒道两家的传统,不切实务者绝非大道。身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严复当然也有藉此书以警世的用意。只是严复从来主张真实学理为先,所以在序言中也先以绝大多数的篇幅论学论道,而后点出其中所具有的救世济时之功。序文最后几句话则说:「夏日如年,聊为侈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依然归结到以说明学理为目标的本旨。本书的宗旨既然是研讨学术上的根本性与长远性问题,所以如果时人认为此书中之所论多属学理上的空论而无助于「实政」,则他并不担心。文章以探讨「理极」始,而以恐遭空言之讥终,这篇序言的主旨、内容与其篇幅的安排,已清楚反驳了认为严复翻译《天演论》一书是主要是为了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或因应危机等目标的说法。根据这篇序文,我们只能说严复此书志在明道,而不忘救时拯溺、救亡保种。却不能颠倒其主从的次序。
这篇自序中严复同时说明了他自己所一向履行以及本书所采取的学术取径。严复所用的方法是「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亦即使用一种比较的方法,透过西方人用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确实知识与普遍公理,重新理解古书中的道理。其结果则是「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对古人的道理得到前所未有的理解。这个过程固然主要是透过西方新理去重新理解古典,然而其中也包含了相异的思想、语言与文化传统的「视域融合」(fusionofhorizon)。严复生长于旧社会,十四岁以前读的全是古籍。从学习与认知心理学、语言学、乃至神经科学的观点来看,其语言、文字、世界观乃至思维方式的原型(archetype)已经塑成。而且严复在从事于西学之后,依然深受儒学性格的影响,并持续地用功于古书,所以他的意识世界,始终深植于中国传统。正因为如此,「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才可以让他觉得「至乐」。换言之,接受了大量新思想的严复心中一直有融通中西学理的深切需要。
严复强调古人的思想既已历时久远,今人又「未尝为古人之学」,所以对于古人所得之理往往不能究明。现代西方的知识系统清楚严明,透过古书与现代西方学说的对照,正可以帮助今人了解古人。他自己的经验与穆勒氏的看法均显示,比较方法可以深化人们对于自己乃至异文化的认识。这既是他自己读书与思维的方法,也是他介绍西学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中西学理本有许多不同。此种比较理会的方法,一方面要求一种双方最高学理的会通,一方面也容易将中国原有的道理,带进他对于西方学理的理解之中。从严复在自序中所举的《易》与《春秋》的例子,可知西方学理固然明显地影响了他对于古书的认识,古人的思想亦曾经相当深刻地影响了他对西方学理的理解。[10]严复所谓「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的过程不仅是单方面地根据西方的学说来解释古人的意思,更不是妄用古人的思想去解释西方的学问,而是透过西方较清楚明白的知识体系,重新诠释中国古代的高深道理。在这重新诠释古典的过程,自然进行着视域交融,而影响了严复对于中西双方学理的认识。严复使用「证诸」二字,显示了他对于古典的信心与敬意。当代的学者,通常较注意东西双方思想文化的一些基本差异,既不会直接拿西方学理与中国学问模拟,更不敢以西学「证诸」古人所言。严复所从事的,表现了当时一种融通中西思想文化的需要。
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当时困扰学术与知识界的首要问题。张之洞于1898年所提出的「旧体为体,西学为用」说,被严复用牛体不能为马用的机体主义观点加以驳斥。[11]当时人对于西方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益发困惑不已,连严复引为生平知己的吴汝纶也不例外:
吴丈汝纶为总教习,同居京都,又复时相过从,吴丈深知中国之不可不谋新,而每忧旧学之消灭。
严复对吴汝纶的回答则是:
不然,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12]
现代西方学术与中国古代经典,是严复心中的两大宝藏。对他而言,新学与旧学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借着新学磨砺彰显出古书中隐而未明的道理,并且可以借着比较方法,显豁双方所同具的真知灼见。在《天演论》一书的序中,严复显然特别重视西方与中国学理的共通性,而并不侧重其特殊性。他相信真实学理具有普遍性,所以他认为西方与中国经典中所含藏的道理可以相通。不仅如此,透过西方的学理以及中西的比较,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固有文字、语言与学术思想的底蕴。这种取径既非汉学亦非宋学,而是开了一扇透过西方新理来重新认识古典,以及比较西方与中国文字思想的新道路。底下一代又一代的现代中国人,都不免或多或少地曾经通过西方新理以及比较中西的方法,来重新认识自己以及西方文化,并追求更高之理解。这种将西方与中国合治一炉所可能产生的非驴非马之缺点,曾遭受他自己的严厉批评。[13]然而诚如严复所言,以「他山之石」来攻深藏的固有之玉,如果运用得当,确实是了解本国学理与文化之意义的利器。
根据这篇自序,我们可以了解严复平素用心与本书作意均与西方与中国学理的互相发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绝不仅是单方面地输入西方的学理或介绍西方当代的世界观。大抵严复的中西学问俱佳,又面对西方文化对本国文明的绝大挑战,于是在平日读书时,便时时以双方所认为特别有价值的学说加以比较参证。《天演论》一书以子学与经学的用语翻译西方学理,并时时以西方与中国学理相参证,便是这种读书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西方当时流行实证主义,严复所学又植基于自然与社会科学,所以他相信真理是普遍的。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也认为大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双方之理,应可会通。所以严复认真地说了一番《易经》与《春秋》之学如何与西方「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一致,而「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的名数质力之学,又如何早已发明于《易经》之中的道理。换言之,他一方面企图输入中国所需的现代西方学理,一方面也努力进行融通西方与中国学术与思想的艰巨工作。
严复在此所采取的学术路径,表现了追求一以贯之的最高道理之传统求道特质。他在文章中说:「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明白以「考道之士」自居,主要不是为了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而研究学问,也不只是单纯地学习或引进西方的学理。此处「考道」二字,不仅是考究一般的事理,而有推究至极之义。所以他在序言中一开始便说:「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所探索的是语言、文字的究竟意蕴,以及古书中的微言大义。他企图将西方与中国学术与思想的源头接上,而不是个别思想或事物的比较与融通。[14]他要找的是西方学术与思想中最基本的原理原则,将它和中国学术与思想的根本──经学,融合在一起。所以序言从一开始便企图经由西方与中国学术思想的融合中去探索所谓「理极」、「贯天地人之理」。亦即合西方与中国学术思想之精华,研究宇宙人生的究竟道理。
严复所追求的,不在一时的应用,而在于究竟、不可动摇且一以贯之的最高道理。他当时相信:「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因为现代欧洲人发现了名理公例之极致,所以他要介绍其成就到中国来。而他同时相信世间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人所得往往在西方人之前,所以可以用中文,乃至古文介绍这些普遍的道理。严复于此序中最为称许的牛顿定律、演化理论与热力学理论,分别代表了西方当时对于物质与生物界之根本法则的最高理解,而他也分别将其与经学传统中对于大道的看法相比拟。他将牛顿力学的第一定律比拟于《易传》的「干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并认为此说一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又认为斯宾塞尔的天演说可以「贯天地人而一理之」,而其基本主张「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则与《易经》「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之说相通。至于动量与能量不灭定律,则通于《易》学的「自强不息」说;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指出的「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且不论上述的比拟是否得当,严复那种追求「贯天地人而一理之」,并且融合西方与中国最高学理的学术理想,可谓跃然纸上。而这种追求「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理想,固然曾经受到现代西方学术启发,其基本特质却非常传统。《易经》与老庄思想之精义,在于其中贯乎天地人的大道。而严复之所以特别喜爱斯宾塞,正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通乎宇宙人生而一以贯之的最高道理,而此道理又与《易》、老庄的世界观大体相通。这显示严复不仅在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上继承了求道传统,在宇宙观上也继承了以《易》、老庄为中心的传统思想。[15]
学者或许会提出质疑,认为追求一以贯之的道理何尝不是西方哲学与科学的理想及传统。然而就西方学术传统而言,获得确切不移的知识与了解现有知识的限制才是第一义。能通贯乎天地人则是个最后而遥远的理想与次要的考虑。斯宾塞式的综合哲学,在现代西方科学及哲学史上,代表了一种过份追求一以贯之,而在知识的精确性上不足的学说。然而严复因为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于一以贯之的学理似乎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从开始便特别欣赏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他早先读斯宾塞的书,便特别推许斯宾塞之学可与《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与《中庸》的致广大尽精微、无过与不及的一以贯之之道相通。此序言又以其与《易经》式的「贯乎天地人」的世界观相通。[16]严复的特殊品味,岂不由此可见。到了民国时期,国人对于同样具有一以贯之的特质之马克斯主义的强烈喜好,似乎也表现了类似的心理特质。斯宾塞与马克斯学说同属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的传统。然而当国人接受他们时,都没有真正接受他们复杂繁密的论证,而是将其一以贯之的结论,直接当作科学定律来运用。严复虽然思理精密,然而即使在他的译作里,也省略简化了不少原书的分析论证。[17]至于一般读者,更是只管他们所领略到的一以贯之的结论。国人的思维方式,由此亦可见其一斑。
学者另外可以提出异议,认为严复是因为担心当时的学界无法接受西洋学术,所以特别加了这段序言,引中国的经典以证明西洋学问的价值,以利于他引进西学来救中国的本怀。因此这篇序言只是一个导言,针对当时学术界的心理而作,未必等于全书的宗旨乃至于他的真正想法。这种怀疑似乎言之成理。然而我们如果通观全书,将发现严复引中国古书以印证西方学理是他一贯的作法。尤其在1895年所刊陕西味经售书处本,即目前存世的《天演论》最早版本之中,这种比论参证的方法,几乎无页无之。严译《天演论》的原貌,即味经本中所见内容,与通行本有重大的差异。不仅其每章的标目不同,原文更经常是每翻译一段赫胥黎的原著,便引一段中国古书或发挥一段比较中西的意见。这种大量引古书或比较发挥的情形,经友人的劝告后,在通行本的正文中已大幅减少。除大幅删去外,往往移入味经本所无,而为通行本所有的案语及夹注之中。由此可见严译《天演论》一书从一开始便以整合西方与中国学术思想为目标。今传的案语与夹注,本来是他整合西方与中国思想工作中不可分的一部份,所以其中有许多内容,原来与正文放在一起。[18]另外无论在味经本或是日后的通行本中,严复的案语或其所译的内容,也均以讨论学理为主,并大量引用中国古书中的思想与学理。其中虽然也有讨论现实问题的部份,其份量远不能与讨论学理与比较文化、思想的部份相比。严复在序言中所说的比较语言文字与学理的作法,确实已透过典雅的文言与子学与经学的词汇,落实在其翻译之中。运用古雅文言并引用古书以印证或说明西方学理,固然非常有利于严复介绍西学进入学风依然十分保守的中国,然而严复认为西学可以通于古人学理以及古文具有甚高价值的看法是真诚的。我们可以考虑他大量引经据典是否带有「方便说法」的考虑,但是不宜认为这些作法没有更积极的目的。认为本书的宗旨主要在于救亡保种等实务,而其自序讨论纯学术的部份无当于本书宗旨的说法,不但无法解释诸如「夏日如年,聊为侈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与「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这一类的话,也无法说明严复在此自序中热切真诚地欲治西方与中国学术思想于一炉的词气。而认为严复的翻译单纯是引进现代世界观以进行观念革命或思想启蒙的说法,也同样无法解释严复热衷于中西学理之印证与比较工作的事实。如果严复的目的只在于引进西方真理来取代传统的学术与思想,以进行所谓的「启蒙」工作,则他实在不必要大费周章且持续不断地「证诸古人之所传」。引进西学与现代世界观,当然是严复翻译此书的一个基本目的。然而他对于中国的未来与学术文化问题的关怀,使其翻译又进而成为一种融通西方与中国最高学理,并不断对于中国文化进行反思,以追求文化发展的大方向的一种求道的努力。
关于本书作意与基本性质的另外一段极关键而未曾为学者注意的材料,见于1898沔阳慎始基斋本《天演论》的译例言:
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徽(征)引,匡益实多。顾为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皆劝早日付梓,木斋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19]
慎始基斋本《天演论》是第一次正式出版,经严复正式认可的《天演论》版本。所以此段内容应可代表严复自己对此书性质的基本看法。[20]然而可能是因为此段涉及了较多的人事,而其所言又无助于一般的读者了解本书内容,所以后来通行的富文本与商务本中,均将此段删去。所以学者一般都不曾注意这段内容。根据这段材料,可以进一步证明严复是为了「探赜叩寂」,即研寻最深奥隐微的道理,而以之教导学生,才翻译了此书。此段译例明言此书「非当务之所亟」,所以他本来不愿将本书「问世」。是众人一再的劝说,他才答应,而实非他的本意。这是因为本书的基本性质是「理学西书」,即探讨宇宙人生之根本学理之书,「翻转不易」,有待长期研究,又「非当务之所亟」,所以他原本不想刊行。据此可见,我们长期以来认为严复翻译此书主要是为了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等现实而迫切的目的,或认为本书主要是一种「危机哲学」,基本上并不恰当。
另外在通行本的译例言中,严复说道: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21]
可见严复翻译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穷理」。穷理必须集思广益。所以他不仅综合比较斯宾塞、赫胥黎、达尔文以及西方古今各大家的思想,并时时以之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比较。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加上自己的看法,以说明他所相信的最后答案。由此亦可见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危机哲学乃至单纯引进现代世界观等说法,并不足以充分地说明本书的基本作意与主要内涵。
讨论本书作意的另外一个重要材料,便是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为本书所写的序。吴汝纶非常看重本书,曾亲自抄写副本,妥为珍藏,并说:「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亦不足为喻。[22]严复亦非常崇重吴汝纶。他曾经推许吴氏为平生除郭嵩焘之外的唯一知己,自己所译的各种书则大体都曾经先送请吴汝纶润饰。双方之互敬互重如此,吴氏又如此看重此书,此序之代表性与重要性由此可知。然而我们仔细看吴汝纶的序,将发现吴汝纶同样并未从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等角度说明此书之特色。而是从「道与文为一体」这一高度传统性而学术化的观点立论。吴汝纶在序言中首先非常精要地综述西方天演学与赫胥黎此书的精义,而后说:
凡赫胥黎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23]
在吴汝纶的眼中,严复所为乃文以载道之事,而绝不仅是一种因应时务的作为。桐城派认为,文章者得天地之英华,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文章之极至,必当与道合。此种看法,继承了《文心雕龙》的道与文为一体,与韩愈「文者载道之器」的大传统。道与天地造化为一体,[5]最好的文章应达到参天地造化,体大道流行的境界,而大道亦必需有赖于至文方能流传。从文章可以观世运,其影响至为深远。遍观历代著作,其文章若不佳,则其内容亦不能传。至于当时流行的文章,吴氏认为,其体格不出于时文、公牍、说部,内容卑靡。其道既不足,「固不足与文学之事」。[24]而一般翻译西书的人,乃以当时流行的「时文、公牍、说部之词,传而译之」,所以也不为有识之士所重。至于严复的翻译则大不同。吴氏说:「今赫胥黎氏之道,……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25]换言之,是靠了严复的文章,国人才能相信书中具有能与古人相撷抗的道理。所以诚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严译的《天演论》之所以能被当时的读书人普遍接受,与他的文章有绝对的关系。[26]而我们从吴汝纶论道与文的关系,也可以了解当时读书人之看重《天演论》一书,首先是因为相信道与文不可分离;有如此雄健高古、精深宏肆的文字,其所传的道理自然了不起。不仅如此,吴汝纶在序言中,还提出借着严复的文章,一新当时卑靡之文体,重振古文,发明道理,而开启国人智慧的意思。[27]他们所企图达成的,又岂能以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因应危机乃至介绍现代世界观为范围。所以不仅严复所引介的道理是划时代的,其上追先秦诸子的文章亦有一新风气的划时代意义。道与文,在一向特别重视文字的中国传统学人看来,有一体不可分的关系。
吴汝纶在其序言接近结尾时,也用了五、六十个字论到严译《天演论》有提醒国人应当知危知变,捍卫种族的功效。而后又结论到这仍有赖于国人能接受了解严复的「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28]吴汝纶看重此书的基本原因,在于其可大可久的道理与文章。然而吴氏也清楚了解此道理绝非空言,而有拯时救弊之功。这种一方面重视可大可久的道理,一方面企图以道理应世救时的思维方式,是儒道两家「道器不离,体用不二」的传统。古人论道从来不离实践与日用,所以先讨论普遍的道理而后指出其当代意义的写法,可使道理的价值更为彰显。吴序全文所用的笔法,与严复自序当中先学理,而后点出其时代意义,终于归本学理的写法,无论在篇幅与次序的安排上,都完全一致。由此更可确定严复此书的作意。
然而吴汝纶另外曾经写信给严复说:
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29]
这代表吴汝纶对于严复此书另一角度的理解。虽然说知交好友的看法,到底不能取代严复自己的想法。可是这段话也确实点出了严复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严复自己在《天演论》一书即将出版前写给吴汝纶的信中,亦痛陈中国人因为两千年「尊主卑民之治」,以至于「任恤与保爱同种之风扫地无余」。而今之中国,有若腐肉,其中之质点「有抵力而无吸者,与各国遇,如以利剑齿之,几何其不土崩瓦解也。」[30]他为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形,沈痛地说道:
然则三百年以往中国之所固有而所望以徐而修明者孑遗耗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此抑为复所过虑,或经物竞天择之后,吾之善与真者自存,且有以大裨[6]西治,未可知也。复每念此言,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姑为先生发此愤悱而已。[31]
严复在此信中所流露的爱国忧时、痛惜传统文化的感情,可以令人涕下。由此可见,救亡保种、保存文化与因应危机也确实是严复天演思想的重要部分。
严复对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在成年之后,有着日渐强烈的危机意识。[32]可是严复对于天演思想的信念却并不单纯地从救亡保种或危机思想而来。受到西方与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严复从早年便热心追求通贯性的学理,并相信其指导性的功能。他透过对于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而接受了天演论,而后由此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危机。换言之,是在他求学与求道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激发他进一步研寻道理的热忱。时代危机与求道有其互动的关系,然而各有渊源,不可等同为一事。严复早在光绪七、八年之交便接受了以斯宾塞哲学为中心的天演论,到了晚年依然自号天演宗哲学家,并始终以天演的概念为其一切思想的中心。这表示天演论是他毕生的真实信念,而不仅是一种「危机哲学」。然而若不是时代所带来的危机感,严复也不会如此殚精竭智地探索西方与中国思想文化中所蕴含的最高学理,企图发掘通贯乎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理,以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综合而言,严复在研穷学理、找寻中国之出路时,因其所学而认识到贯通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并由之而更深刻地体认到中国的危殆处境。甲午之后,他因此发愤为文,希望借其所明之道以救世。〈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均援引天演论以立说,原因在此。至于严复之翻译《天演论》,本来用以「日与同学诸子相课」,以深入介绍他所长期浸润,并以之贯串宇宙人生并融通西方与中国思想的天演论体系。所以其内容明显偏重学理,然而其中当然也含有救世之意。为了更深入了解严译《天演论》的作意,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严复这一段接受与宣传天演论的背景。
三、明道而以之救世:严复接受与宣传天演论的背景
严复何时开始接受天演论的思想体系?其时间不容易确定。他在英国留学时喜读各种报章书籍,应该已经接触到当时流行的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的学说。然而当时课业繁重,他未必有时间深入其学说。根据严复自己的说法,天演学说对他发生重大影响,首先在光绪七、八年之交。当时严复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席,在事业上很不得志,空有满腔救世济民的抱负与才学却无法施展,于是他本着一向爱好研究学理的个性,以及传统上论治以辨章学术为先的态度,致力于学术。[33]斯宾塞本乎天演论与实证主义的TheStudy of Sociology(严复初节译此书为《劝学篇》,后来将全书译出,并改名为《群学肄言》),便在这种情况下对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此书所论虽然关涉到中国社会在当时所面对的一个结构性的大问题──如何结合散漫的中国人以达成现代化的群治,然而在实质上却是一本研究社会学方法论的高度理论性著作。除其演化观与自由主义的原理所具有的根本性及长远性的指导功能外,并不能对于实务有立即的效用。书中所提出社会科学必需效法甚至立基于自然科学的说法,一方面与严复科技出身的背景非常相契,一方面则进一步加强他一切以学术为本的信念。我们从此书初期的译名《劝学篇》,便可认识严复的用心。[34]综合言之,这本书所揭示的基本学理与方法论,都主张采用立基于学术的根本而长远的作法。所以严复读此书后说道:
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尝言生平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义未尝晦也。其缮性Discipline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35]
此书使他看事情益发从一种根本、长远、不偏不倚的角度着眼,亦即他后来常说的以「道眼」观物。[36]并从此处领悟到中国与西方最高的学理均从可大可久、无过与不及处着眼,并都主张从格致诚正以至于治平的一以贯之之道,所以两方面的学术理想实为相通。[37]文中又特别欣赏斯宾塞此书能够发明西方学术方法的精义,可见他此时所关切的问题,超出了群学,而直指普遍的真理与学术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严复正式接受天演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辨章学术与追求普遍真理的心理下完成。其背后则表现了儒学传统从格致诚正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向往,简言之,即所谓明道之志。
我们若以严复与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相比较,便可发现严复的基本关切点与这些西方的天演大家有很大的不同。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在他们著作中所讨论的主要是物理与生物世界的因果规律问题,其精神源出于西方重视知识系统建构的大传统。严复虽然受到西方科学的知识系统之震撼与吸引,可是他所谓的「尝言生平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显然出自于一个如何治国平天下的更大考虑。《大学》之道,在于从格致诚正以至于治平。《中庸》之道,在于致中和,不「独往偏至」、无过与不及。严复的思想背景中先有了这种儒学的关怀、价值观与学术观念,才使他特别受到斯宾塞的天演世界与社会观之吸引。而他将「社会学研究」(TheStudy ofSociology)之书名译为「劝学篇」,不仅可以看出严复最看重的是如何为学的问题,更可见他继承了儒家首重为学以明道的传统。这一切种种,显示他是在传统儒学性格的巨大影响下来接受西方的天演论,所以其基本关切点与西方学者确实不同。[38]
严复具有一种强烈的儒学性格,所以他很可能是有感于中国社会的组织散漫而对西方的群学发生兴趣。他亲眼目赌西方的文明富强,对于国家的落后与国人的不知不觉也有一种深切的危机感。然而他当初之所以接受天演论,却不是因为此学说可以「救亡图存」,而是因为他确实相信其中具有融合了自然与社会科学,并可与中国经典相发明的至高道理。必须本着这种最高明也最根本的道理,才能解决中国各方面的沈痾。论者通常只就甲午之后国家危亡的情况论严复的天演论,殊不知严复自己在接受天演论时,根本没有积极用世的机会,并且带有一种「怀才不遇」、「中年蹉跎」的感慨。[39]在一种举世难寻知己的情况下,他孤独地用心研究宇宙人生与国家社会的根本道理,并痛惜国人的无知终将造成严重的灾难。甲午之前这一段长期的沈潜岁月,成功了他凡事深察其根本、不求速成的性格。他后来有感于国人,尤其是维新派,因为受到《天演论》一书的影响而日趋极端,还特别着手翻译《群学肄言》以使国人回到中庸之道。[40]由此可见严复自己所信守的天演论与流行于世的天演论中间实有重大的差距。所以难怪他一直是「孤鹤从来不得眠」了。[41]
严复这种追求一以贯之,包含一切的最高道理的学术倾向,与晚清的道器体用论,有密切的关系。道器体用论的提出,代表晚清自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以降等一系列的改良派对于如何调和中西文化的一个基本看法。它反映出中西交会之际,中国文化所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严复受过深入的西学训练,不能接受中学为道、为体,而西学为器、为用这一类流行于自强运动期间的说法。他曾经以牛体不能为马用这一有名的论点,驳斥张之洞在1898年所提出的中体西用说,并明白提出道器体用必须一以贯之的看法。既然道器体用必须一贯,所以如果不能融通中西学理而得到一个更高的综合,则只能选择全盘西化,或是全面复古的道路。全面复古既然不可行也不可欲,而尽去固有、全盘西化则无论在理智或感情上都不能为严复所接受。严复所采取的,自然是融通中西最高学理的道路。[42]他深信西方与中国的学术都有甚深奥义,足以引导中国文化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他一生的努力,正在于积极引进他所相信足以代表西方最高学理且为中国所需的学问,融入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大传统中,以形成一个道器体用一以贯之、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体系,而为中国的未来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
追求一以贯之的最高大道的学术与思想倾向其实不仅是严复个人的毕生志业,也强烈表现于同时与其后的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与新文化运动诸君身上。这一方面显示传统的学术与思想性格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晚清道器、体用讨论的一种继续发展。时代的困境与传统学术思想体系的动摇乃至崩解所造成的全面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文化的危机,是造成这种追求「新的大道」之现象的动力因。张灏先生所指出晚清学人的「方向危机」(orientationalcrisis)、「秩序的危机」(a crisis of order)、「意义的危机」(a crisis of meaning)与「存在危机」(existentialcrisis)则为此危机在思想与心理层面上的具体内容。[43]正是因为时代的危机是全面而整体性的,所以其答案也被要求为道用、体用合一,贯通自然与人文一切种种、而能达成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目标,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一贯大道。清末以降,儒学的具体内容虽然遭受到摧毁性的攻击,然而儒学理想的架构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却仍持续地发生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儒学的传统受到了全面性的挑战,所以急需一个类似的思想结构来负担儒学在过去数千年所担负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任务,及其对于世界的整体解释。即所谓新的一贯之道。[44]
更进一步分析,晚清与民初学人所面对的虽然都是全面性的冲击,然而大抵晚清学人所感受到的危机较仍较偏于政治、经济、社会、学术、世道人心等层面。同时他们虽然严厉地批评现实中的儒学与纲常名教,却对于儒学的一些核心价值与观念,以及中国学术文化中许多的小传统有很强的信心与认同感。其生活的全体与意识之大海,又深深地浸润在传统世界之中。所以即使主张激烈,仍然不会提出全盘反传统主义式的主张,也因此在文化认同上也不至于出现严重的问题。[45]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个人的生活与整体意识的背景又受到大革命的冲击,危机与怀疑感于是扩大到文化的全体,乃有全盘西化与全盘反传统主义的主张。文化认同的危机,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亦因此而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
严复出身马尾船政学堂,这是当时身家丰厚的人所不屑于就读的学校。清廷派他出国留学,其目的不过在于训练他成为一个专业的军事人才及可以传授技能的教师。然而儒家讲究「君子不器」,严复所受的教育与训练,都属于器艺或所谓「畴人」教育。而且中国自宋代以降,一直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又普遍看轻西洋文化。所以严复回国后,不为士大夫阶层接受,不受朝廷重用,甚至「举世相识如髦蛮」,只能担任一个非正途的教书匠,都是自然的结果。[46]严复不辞辛苦与讥评,三次参加科举,就是他渴望被士大夫阶层所接受的具体表现。所以严复若有所谓「认同危机」,不仅不是因为拒绝固有文化而产生的危机,反而是怕被固有文化阶层所拒斥的危机感。然而以严复天资之高,自信心之强,这种危机感并不严重,也并未对他的学术研究或判断造成扭曲。他对于传统文化既能批判又能欣赏,就是一种相当平和的心态之表现。反过来说,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强烈的尊严感与自信心,也由此可见。「文化认同危机」之说,对于晚清学人而言,并不太适用。当然,甲午之后,如一批最激进且领风骚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既已深及传统伦理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新思想对于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冲击不能说不深巨。[47]然而无论是严复或是康、谭、章、梁、刘诸人,都在严厉批评儒家传统的同时,依然肯定儒、释、道或先秦诸子中的某些核心价值。并将自己整个的学说,搭建在这核心价值的周围。[48]
甲午之后,以儒家政教伦理为中心的旧体系开始全面崩坏,建立新体系的迫切需要随之而起。这种危机与需要,是严复等晚清学人追求一以贯之的大道之主要动力。然而这一代的学人,与中国传统血脉相连的程度甚深,对旧学的知识也非后人能比,所以他们大抵均采取了保存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智能,批判其糟粕,援引各种小传统,并与西学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其学术与思想的大整合工作。而且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文化整体的危机,所以他们一生致力的几乎都是企图贯通古今中外的通人之学。然而中西两大文化交会所激起的各种问题,又岂是一、两代人所能解决。随着各种问题的层出不穷,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读书人也不断投入这个始终未竟的工作之中。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知识界,至今也未能解决。建立新体系或新的基本原则以指导文化的走向,也因此始终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根本课题。严复企图追求的致广大尽精微,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便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重要开端。
在另外一方面,严复之接受天演论,与他对于时代变局的深切感受,当有相当的关系。王尔敏先生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一文中,曾指出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变局不仅十分注意,且议论频繁。王氏统计当时论及变局者不下81人,而引用运会说以解释当前变局者又不下22人。[49]即使如此,严复仍经常指责当时的士大夫麻木不仁,昧于新知与大时代的变化,他本人对于时代的变局感受深刻,殆无疑义。[50]甲午之后,严复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世变之亟〉,并在其中运用进化论批判中国传统里面「好古而忽今」,天下「一治一乱」的思想。[51]所以严复的天演论,也是因应时代的大变局所宜有的一套新世界观。[52]
严复在甲午之后大力向国人宣讲天演论,并发布在以〈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为标题的文章中。文中时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高声向国人警示国家危殆的处境。所以时人与后人都难免从一开始便将天演论与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等说法结合在一起。激于时势,严复确实有意藉天演论以为国人之警策。可是我们如果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将会发现他同时表达了文化反思、提倡新学术、与以道济世等更深刻的思想。[53]在这些文章之中,他引用达尔文、斯宾塞的天演学说,不仅是根据科学公理以提醒国人中国在竞争激烈的现代世界中的艰危处境,更重要的是提倡新学术与新观念以便从根本解决问题。此所以他在文中不断强调中国的问题由来已久,而西方人的文明富强亦绝非短时间可致。谋国之道,必须标本兼治,尤其必须了解病原,才真正能治病。[54]
〈论世变之亟〉一文教人认识今日之大病乃长期演化而成,西方人的富强则深植于进化观、自由的精神与其「黜伪而崇真」、「屈私以为公」的态度。今日若再昧于时势,则有亡国灭种,文化灭绝的危险。[55]在〈原强〉一文中,他首先引用达尔文物竞天择的学说,以警告国人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后盛称斯宾塞立基于天演的群学。他认为斯宾塞的群学相通于《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而「精深微妙、繁富奥衍」过之。其学本于各种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与心理学,而能明察各种社会现象之演化的因果,「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吾人必须循其方法究明群学,才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换言之,他深信斯宾塞所指出的学术途径可以指向最高的道理,即使「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56]于此同时,该文中所提出的以增进民智、民德、民力为一切富强治平之根本,与反对躁进的作法,也同样源于斯宾塞的天演观。[57]〈原强续篇〉则引达尔文、斯宾塞,说明国无速化之理。他认为日本轻动躁进,违反天演的道理,所以此时尚不真正可畏。而中国既战,便应抗战到底,藉战自强,否则将有大祸。[58]〈救亡决论〉一文则要求废八股,并对传统学术思想作全面且根本性的批评,同时主张引入西方科学,彻底革新学术思想,以救危亡。[59]他在文中痛陈传统学术虚矫无用,并确切指出西方科学的长处:
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则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本无大小、久暂、贵贱、善恶之殊。庄生知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况。[60]
此处一方面引西方科学方法痛批了中国读书人之传统所学,一方面却又深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谓西方科学验于事事物物之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道通为一」,种种形容其境界的词汇,均出自《中庸》与《庄子》的道论。而所谓「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则明白将科学的最高理想与庄子的道在屎溺的齐物观合而为一。[61]换言之,是认为科学方法可以指向一以贯之的新的大道。必须掌握此大道,才能根本地改变中国的问题。
上述这些文章的总纲领,诚如严复自己所指出,是「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62]换言之,从自强运动以来,国人都以应时之务为急。而严复则指出必须以增进人民的智、德、力为改革的根本,并以科学研究所得的实理真知作施为的依据。他所期望的不仅是一时的救亡,而是长治久安之道。严复心中的道理超乎世务,然亦不离世务。明道可以救时,然而只知救时并不足以明道。他同时强调,不讲明本于格致以至于治平的大道,终究连时务都无法适当因应。[63]这种思维方式,承继了儒道两家的思维传统,相信道理无所不在,需于事事物物上讲求之,并可用之以干济实务。严复在甲午之后才开始向国人介绍天演论,这确实是受到了时代的刺激。然而其意义不仅是救亡图存,也不是提出一套计划蓝图,更重要且更根本的是寻求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法与能力,及阐明文明进化所必须依循的基本原理。严复相信必须从根本做起,才能解决中国文化中的长期病痛。必须学习掌握真理与大道,才能够与时俱进,以面对各种日新又新的问题。
这几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其主要内涵为时务评论。为求影响国人,这些文章自然以达成救亡与富强为其主要目标。然而即使在这种时论性的文章中,严复依然时时不忘提醒国人只有明道方能救亡与图强。他随后所翻译的《天演论》,不属于时论,而是探究天演学理的著作,其作意与内容更明显偏就明道这一方面。大抵严复对于知识界的呼吁已经在这几篇文章完成,他有意借着译作《天演论》一书来引介他所相信的最高学理。在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处理严复为何要选择赫胥黎这本书以介绍天演论入中国,以及严译《天演论》一书的所要表达的内涵主要为何之问题。
四、严复《天演论》的主要内涵
《天演论》一书的内容所涉及的层面极为深广复杂,限于体裁与篇幅,本文不拟对其具体的内容一一加以分析。本节的重点在于根据实际作品(work),分析其中所传达出的意蕴,以说明本书的主要内涵。不明白这些主要内涵,不仅难以掌握本书所企图传达的要旨,而且将难以理会本书的体裁、文字、以及作者为何选择本书进行译介。
前文已经指出作者志在明道而不忘救世。而其所欲明之道,则有融通西方与中国最高学理的基本特性。本节将分四个层面,进一步析论此意图如何成功地在本书中具体展现。本书最主要的内容是介绍贯串西、中、印最高学理、且贯通天人的天演思想体系。这个最主要的特质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严复为何选择赫胥黎这本书,来加以翻译及评注。在介绍一以贯之的天演思想体系的目标下,严译《天演论》同时努力融合西方天演学说,以及融西方的天演论于中国传统思想。而在阐明天演学理的基础上,严复更进一步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问题加以反思,以完成其有体有用,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严复在书中所企图引介的另外一个主要部份是西方现代世界观与学术。这一点是严复明道的大计划中的一个基本成分,本节第一与第二部份以及前文中对此有相当多的分析,而且学界在这方面论者已多,所以本节不拟特别标出讨论。[64]至于其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则同属于天演思想体系的一部份,本节中亦将加以介绍。
讨论本书的内涵,当然要涉及翻译的问题。严格来说,严复所「译作」的天演论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一种融通西方与中国思想,并企图完成天演宗「一家之言」的努力。所以他在译例言中一开始便说本书「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又说「学我者病」,明白教人这不是翻译的正途。[65]所以各种批评严复「翻译」此书的方式不佳,不能表现原书的内涵、气味与精神的说法,很大的程度上是对本书的作意与内涵缺乏了解。本节各部份对于严复如何透过且译、且作、且评的方法,来达成他明道的目标,也有详细的说明。[66]
(一)介绍一以贯之的天演大道:兼论严复为何选译赫胥黎这本书
严复在甲午之后努力介绍天演论以唤醒国人,甲午的刺激确实是他决心翻译《天演论》一书的近因。然而天演论是严复在光绪七、八年之后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他之所以介绍天演论,显然不只是因为一时的刺激。事实上远在甲午之前,严复就曾经翻译了斯宾塞《劝学篇》的一部份及柏捷特的《格致治平相关论》(PhysicsandPolitics)。[67]这两本书都根据斯宾塞的演化论立说,而且都是非常学术性而且理论性的著作。由此可见,严复所企图翻译的书,本来就以学理的考虑为第一要义。严复一向提倡自然与社会、人文科学的融合。他相信天演论代表了西方自然与社会、人文科学的最高成就,其内容贯串了物质、生命与人文界。对严复而言,作为整个西方学术界最高结晶的天演论,适足以作为指导一切的最高也最根本的一贯之道。严复推崇斯宾塞立基在天演论之上而包罗万有的综合哲学为「天人会通论」,正代表了这个态度。而他对于赫胥黎的重视,也立基于赫胥黎是一个本于演化观立论,学思体系贯串自然与人文界的学者兼思想家。
严复以天演之理为贯通宇宙人生的大道的思想,在《天演论》中几乎随处流露,以下仅举其尤为着明显者数条以为例证。《天演论》本论第一篇以「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为正文的开端。[68]然而这段「道论」意味浓厚,观念上非常具有《庄子》、《大学》、《中庸》与《易传》等书色彩的话完全不见于原文。赫胥黎的原文以杰克与豆茎的故事作开端,内容与意味均与严复之文章大为不同。[69]所以这段话完全是严复自己的发挥。他以「道论」作为《天演论》本论的第一句话,正表现了他以「道论」视天演论的基本态度。另外在导言十五「最旨」,这篇总结导言之要旨的文章中,严复开头便说:
右十四篇皆诠天演之义,得一一覆按之。第一篇明天道之常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第二篇标其大义,见其为万化之宗;第三篇专就人道言之,以异、择、争三者明治化之所以进。[70]
明白以天演之理代表天道与人道,而为所谓「万化之宗」。然而赫胥黎原书的综论方式与意味却与严复所言相当不同。赫胥黎的综合相当含蓄而谨慎,加上了许多限制条件,用意在于让读者掌握其复杂的思想理路。严复则直言天演之理为天道、人道与万化之宗,并用自己的文字与意思来作简明有力的综合论述,意在宣扬作为一贯之道的天演学理。[71]所以这些文字,也都代表了严复「道论化」的天演学说。此外关于天演说的重要性,严复曾说:
故用天演之说,则竺干天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夫拔地之木,长于一子之微;垂天之鹏,出于一卵之细,其推陈出新,逐层换体,皆衔接微分而来。又有一不易不离之理,行乎其内,有因无创,有常无奇,设宇宙必有真宰,则天演一事,即真宰之功能。[72]
以天演之事,比作宇宙的真宰神功,而为万物自微以之着的「不易不离之理」。他以此理为弥纶宇宙,一以贯之而无所不在之道的意思,亦由此可见。严复又曾说:
自吾党观之,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着,运常然也,会乃大异。假由当前一动物,远迹始初,将见逐代变体,虽至微眇,皆有可寻,迨至最初一形,乃莫定其为动为植。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随在可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73]
此致广大尽精微,包含一切物质界与生物界的变化及人文社会之沿革的「要道」,即天演是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不能不说是致广大。而「虽至微眇,皆有可寻」不能不说是尽精微。「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可以呼应他在序言中所说的「《易》本隐而之显」,又兼采《中庸》所说圣人之道「莫见乎隐」,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之意。短短一段话,融《中庸》与《易经》的甚深义理于一炉,其融通西方与中国最高学理以明道之意,诚跃然纸上。
严复在介绍天演大道的意图下译介了《天演论》,而此书的序言也用高度学术性而非时务性的角度来写。换言之,严复之所以介绍天演论给国人,固然希望此说可以有助于救亡图存,更重要的是提出他所相信的最高学理。而此道理,是严复经过三十多年学习研究中国与西方学术,长期比较中国与西方社会文化,以寻求中国之出路的总结晶。[74]它具有企图贯串西方与中国各种学理,指出人类进化与现代化的关键,及批判中国文化之根本问题的主要内涵。在思维型态上,严复所要追求的是包含古今中外,并能指导实践的大道。在这个意义上,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便成为一个极佳的选择。严复曾经指出他所翻译的《天演论》「不过赫胥黎氏绪论之一编,并非天演正学。」[75]由此更可见严复所企图藉此书所介绍的,并非严格科学意义的演化论,而是建立在天演观点上的一套世界观。
赫胥黎的原书是一本从演化论著眼,精要地析论自然与社会之基本原理虽相反却可以平衡的学理性作品。原书的主体从演讲稿改写而成,所以兼具深入浅出的特色,非常适合于教育学子与推广学理的工作。赫胥黎深信演化观,然而又深惧物竞天择说会对人类的伦理价值观产生重大的破坏,所以他企图在演化论的基础之上重新建构一套伦理学。为达到此目的,赫胥黎综合处理了古今东西各家的天演学说,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哲学、人文与社会方面的基本问题。天演学说本身可以用于宇宙人生的各种层面,而赫胥黎又企图析论自然与社会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涉及物质、生物、人类、社会、伦理、心灵、乃至轮回因果等各种层面。严复也因此可以尽情地在这本小书中,展现他自己建立在天演论上的融通西方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宏大思想体系。他在《天演论》的序言、案语与夹注中所讨论的内容,所涉及的学问门类包含了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逻辑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育种学、优生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口学、西方学术思想史、中国子学与经学传统、中国学术思想史、宗教学、婆罗门与佛学中的许多关键议题。而其所讨论的具体议题则包含生物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民权思想、自由主义、功利主义、道德情感说、人性论、天道论、上帝创世说、心物问题、启蒙运动与现代化、本体不可知论、万有恒变论、宋儒的理气及心性论、轴心时代(axialage)、运会、迷信与宗教、西学溯源等攸关人类思想大方向的关键性问题。他一方面对这些问题有直指核心的看法,一方面则以天演论贯串所有的层面,并对各家各派提出批判。所讨论的固然绝大多数为学术与思想性议题,其探索的层次亦非常深入。严复在此展现的是一个长期深入西方与中国乃至印度学术思想的学者,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一些最根本的道理之全面省思。
严复藉翻译以明道的企图,也表现在本书的译名之上。赫胥黎此书原名Evolution andEthics,然而严复的译名却只保留Evolution的意思,将伦理二字完全删去。可是Ethics一字正是赫胥黎此书所特别强调的地方。赫胥黎与斯宾塞和达尔文最不相同的地方,正在于赫胥黎重视人治与人的群性,以及建立在相感通之群性之上的伦理。然而严复对此有所不取。这固然因为严复相信斯宾塞所说的人道亦出于天演,而反对赫胥黎所说天演与伦理相对立的说法。然而这种相信一切人文还是根源于天演自然、天人一理的说法,却也表现了严复对于一以贯之之道的信念。既然严复所真正要传达的是一以贯之、既根本又普遍的大道,所以书名只标示「天演论」。如果加上伦理二字反而混淆了原来的意思。从书名的翻译,便已透露严译《天演论》所要传达的是他自己所相信的最高道理,而不是一般忠实于原文的翻译。
关于严复为何选择翻译赫胥黎此书,一直是学界一个争论不已的问题。学者最常问的问题是:既然严复最崇拜斯宾塞的学说,而且他也曾经翻译过斯宾塞部份的作品,为何在此时不翻译斯宾塞的作品以介绍天演论,却选择了一位严复对其颇有微词的赫胥黎?[76]严复为何选译赫胥黎此书的问题应当回答,然而笔者在此首先必须指出前述的问法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种问法的基本假设是:严复企图介绍西方的天演学说以唤醒国人从事救亡图存的大业,于是在西方诸天演学家著作中,寻找一个适合的对象。然而如前所述,严复的目标不只是介绍西方的天演学说,也不只是呼吁大家从事救亡图存的大业。他更根本的企图是提出以天演论为核心,融合了西方与中国各种学术思想,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况都加以深入反省,而提出的既可指导政治与文化之长远发展又有助于救亡的思想体系。用严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体有用,务本而兼顾治标之学。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严复选译此书得到更深切的理解。
严复的天演论企图说明宇宙人生最根本的道理,这个最根本的道理必须本诸自然科学,但也要含括社会人生的各种方面。它绝不仅是生物上的天演进化说,而是一种贯串宇宙人生的思想体系。这是为何严复介绍天演论时,不去翻译达尔文只谈生物演化的「物种原始」,而选择择赫胥黎这一本书的根本原因。[77]然而赫胥黎的书固然融会了宇宙、社会、人生的道理于一炉,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ASystem ofPhilosophy)岂不更能符合严复心中「贯天地人而一理之」,且涵盖一切存在层面的理想?在此我们便重新碰到严复为何舍斯宾塞而翻译赫胥黎的书这个老问题。然而此时问题的出发点,已经彻底改变了。
对于严复为何选择此书最常见的一个解释是此书的份量小,较容易翻译。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严复自己曾经说过斯宾塞之书份量繁重,「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78]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包含了「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总计数千页。其中任何一部的份量都在四、五百页到一千页左右,内容则为论证细密复杂、处理各种专门问题的学术作品。这些作品确实难以翻译,也不适合作为普及学术思想的读物。严复翻译的最终目的在于向学生与国人介绍他所相信的天演论体系,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的确难以适用,是他舍斯宾塞之皇皇巨着,而就赫胥黎这本小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严复后来所翻译的《法意》、《原富》与《穆勒名学》其份量与困难度都不在斯宾塞个别的著作之下。严复谈及翻译《天演论》的缘起时也说他本来无意于在当时出版此书。[79]所以并无一般学者所认为的为了救亡图存而必须立刻译出的时间压力。更何况严复的中心思想是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书虽然重要,在严复心中的地位还不能与斯宾塞的著作相比。既然严复可以翻译《法意》、《原富》、《穆勒名学》等大部头著作,翻译的困难度一说,似乎不足以充分说明严复之所以不翻译斯宾塞的原因。如果严复无所采取于赫胥黎此书,或是无法透过这本书以表达他以天演论为中心的一贯思想体系,他是不会选择这本书的。有关于严复所采取于赫胥黎的演化思想者究竟为何,将在下一节分析。本节将集中讨论严复在这本书中所企图展现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如前所述,赫胥黎的书讨论了东西古今各种代表性天演学说的得失,并涉及各种学术与宗教上的问题。严复则更在这个基础之上,加入了中国以《易》、老庄为首的演化观念,以及自己对于天演说的一些诠释。所以这本书其实全面探讨了来自西方、中国、印度三方面的天演论。并以天演论为中心,对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的传统与现状提出深入的批判,构成一个体大思精的体系。赫胥黎此书的导言部份以现代的演化论为中心,本文则以历史上相关的各种思想与宗教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演化论为中心,而对于东西各主要哲学与宗教均有所批评去取的思想体系。其所讨论至广,从希腊罗马各主要哲学家、基督教、婆罗门教、佛学、近现代哲学。几乎涉及所有西方与印度的主要宗教与哲学问题,而企图从一个演化思想的立场,对各家的得失提出分析,并综论自己的看法。严复之所以选择赫胥黎此书的基本原因,正在于此书有助于他提出这融会古今东西各家思想与宗教之世界观的最高学理─天演论。
严复的企图既然如此,他对这些问题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原文之外所加的大量高度学理性的案语及小注,可为证明;而其所大量使用的中国子学与经学术语及典故,也代表了一种融通西方与中国思想的努力。综合言之,严复所讨论与批注的内容,不仅包含赫胥黎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并大量加入他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佛学以及西方哲学、科学与历史的比较与省思。并企图对这些说法作一种融会贯通,提出一个他认为可以代表最深刻的最高道理的说法。所以这本书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而是一个伟大的融合与创造,其目标在于提出他自己认为最真实而深刻的世界观体系。[80]
严复在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与学说所涉及的范围至广,不可能在此一一讨论。以下仅略举数条以分析其性质。斯宾塞与赫胥黎学说的主要分歧点,在于斯宾塞主张演化论是贯通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没有例外的事物,而赫胥黎则「以感通为人道之本」。赫胥黎则认为自然界固然为自由竞争与淘汰的演化原理所主导,人类社会则建筑在人类能够相互感通爱护的本性之上。基于互助互爱本性所产生的人类伦理,正好与自然演化之理相反对。针对这个说法,严复认为:
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且以感通为人道之本,其说发于计学家亚丹斯密,亦非赫胥黎氏所独标之新理也。[81]
严复认为人道之「本」,仍是从自然到人文,从天道至人事一以贯之的天演之理。人道相感通是天演的结果。所以如果以人道感通之理来矫正天演的缺失,在严复看来即所谓「执其末以齐其本」。严复并不反对感通之说,然而他认为人道感通终究出于天演。对于「天人会通」一贯之道的爱好,使他非常不喜欢赫胥黎「天演」与「人伦」相对立的二元论:
赫胥黎氏之为此言,意欲明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也。然而其义隘矣。且其所举泰东西建言,皆非群学太平最大公例也。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用此则无前弊矣。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是例而作也。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其书五卷数十篇,大抵反复明此义耳。故道咸以来,蠲保商之法,平进出之税,而商务大兴,国民俱富。嗟呼!今然后知道若大路然,斤斤于彼己盈绌之间者之真无当也。[82]
严复之所以采取约翰穆勒、亚丹斯密与斯宾塞的「太平公例」说,认为自由的原则可以达到两利,与他对于一以贯之之道的信念,具有密切的关系。所谓「道若大路然,斤斤于彼己盈绌之间者之真无当也」,认为大道贯通人我天人,必不以彼己之间二元对立的方式呈现,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反对赫胥黎二元论的思想。
赫胥黎的认识论以事物之本体不可知论著称。《天演论》一书中曾细论婆罗门佛教的演化观与认识论,既推崇其影响与智慧,也以不可知论(agnosticism)总评其中有关究竟事物的说法。[83]严复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具有极大兴趣,所以详为解说。他根据西方哲学与物理学对于此问题下了极长的案语。尤其对于知识的界限,采取了源于笛卡尔而成于赫胥黎的「意验相符」说:
石子本体,必不可知,吾所知者,不逾意识。断断然矣。惟意可知,故惟意非幻。此特嘉尔积意成我之说,所由生也。……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如是所为,以足生事。复案:此庄子所以云心止于符也。[84]
此说源于笛卡尔、休谟、与柏克莱,在西方知识论上属于批判的唯心论(criticalidealism),与近现代物理学的认识观颇为相契,而成为严复在知识论上的基本立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终极不可知论与所知不出心识的立场,与道家的认识观非常一致。严复所下的案语:「此庄子所以云心止于符也」,确切地点出其间的关键,并清楚表现出严复融合西方与中国最高学理于一炉的企图。
从这种不可知论出发,严复继而详细申论「谈理见极」的境界:
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一言专为此设者也。佛所称涅盘,即其“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至于物理之不可思议,则如宇如宙:宇者太虚也;宙者,时也。他如万物质点、动静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讫之伦,虽在圣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实不可思议者。[85]
「谈理见极」虽必至于「不可思议」,严复对于这种究竟本体与道理的议题,其实念兹在兹,才会特别详加申论。至于人类思维如何与为何会到达「谈理见极」的地步呢?严复说:
天下事理,如木之分条,水之分派。求解则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众异而为一同。更进则此所谓同,又成为异,而与他异通于大同。当其可通,皆为可解,如是渐进,至于诸理会归最上之一理,孤立无对。既无不冒,自无与通。无与通则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议也。[86]
严复相信天下事理本来一元,万事万理如「木之分条,水之分派」。而且求「通众异而为一同」,本来是人类理解事物的根本方法,「追溯本源」则为求解的自然倾向。一路追本溯源,将达到一个超越诠解不可思议的地步。严复自己对于人类各种学术思想与宗教,也正是如是观。本于他学者与思想家的个性,他一路融会贯通,追本溯源,寻求「最上之一理」。也因此深知「谈理见极」时必至于「不可思议」之一境。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严复企图批判综汇西方、中国、印度思想的最后结果,也达于此境。
(二)融合西方天演学说
现代天演论起源于十八世纪,而大兴于十九世纪,其中所蕴含的进步、变化(becoming)、自然主义的观念以及自由竞争的意识,最能表现出西方现代,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世界观的基本特色。严复引进这套先进的世界观,注入相对停滞难前的中国文化,是件划时代的大事。中国人的世界观从此产生了巨大的变动,并掀起了一连串思想、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变革。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积极引进这种现代的天演世界观以促进变革,此事实已普受学界重视。[87]然而对于严复这套天演论思想体系如何形成,尤其是在何种学习动力与思维方式之下完成,则学界研究的仍然不够充分。救亡图存、追求富强、促进变法、危机哲学等说依然主导了绝大多数学者对于严复的天演论之内涵的理解,而限制了我们对于严复天演论思想体系的认识。以下两部份将从一个新的角度,论析严复是在何种学习动力与思维方式下融合采取西方天演学大家的学说,以完成他一以贯之的天演思想体系。同时也将指出严复所相信的,就一个严格的意义上而言,并非达尔文主义,而是斯宾塞主义,而与其说是斯宾塞主义,又不如说是融通西方天演诸大家,并与中国传统道、儒天演思想相结合的天演论思想。严复一贯的思维与学术倾向,在于融通各家学理,以成就一套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时代的刺激,固然是他学习动力的重要组成,也对他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影响,然而严复独特的学术与思想风格,却为明道的企图所决定。如果只是为了救亡图存、追求富强、促进变法、因应危机,或引入先进的世界观,严复实在不必大费周章地进行全面融合西方天演诸家以及融西方天演说入中国思想传统的工作。
西方现代天演学史上,大家辈出,严译的《天演论》,对于拉马克、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四位天演学大家的说法都有所采取。然而这四家的说法其实颇有矛盾,而严复却设法将其融于一炉,以共同完成一个他所尊信,足以贯串宇宙人生各个层面的天演论体系。这似乎表现了一种中国人所特有的「和合」性与追求一贯之道的态度。[88]在此我们首先必须研究四家之说的基本差异,才能进一步明白他采取与融合这四家学说时所表现的思维方式。
在生物演化论的传统中,达尔文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出并以大量的证据来检证自然淘汰说(naturalselection,严译为「天择」)。[89]然而严复所最推崇的斯宾塞之天演观却别有所承。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Originof Species)出版前便提倡一种普遍进化(generalevolution)的观念。[90]这种普遍进化的观念源于德国唯心论及斯宾塞对于一切物质与运动之聚合与重组的普遍规律的看法。[91]而这种渗透入一切存在的普遍进化观念,与生物学上的拉马克主义具有形态上的类似性。拉马克主义核心的观念是适应(adaptation,严复译为「体合」),认为演化机制主要并不是透过「天择」的大量淘汰,而是生命体透过意志(will)努力适应环境,代代遗传并累积其努力的结果。这种对于主体的意志与努力的强调和唯心论传统中对于心灵演化的说明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拉马克主义并不否认环境中的生存竞争与淘汰可能非常激烈,然而造成演化的核心机制,却是「适应环境」。这个观念与达尔文强调机体变异与淘汰的「天择」说,有根本性的冲突,这也是拉马克主义最后被现代生物学所扬弃的根本原因。[92]
根据拉马克的适应说,演化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个体的意志与努力在一定程度之内,可以改变其体质与命运。而达尔文结合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天择说,则将演化过程视为严酷而血淋淋的生存淘汰。斯宾塞的演化观,源于其通贯乎一切质力存在的普遍演化论,而其有关生物演化的部份,则来自拉马克。[93]然而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他划时代巨作之后,斯宾塞却又颇受达尔文天择说的影响。当时还处于演化论发展的早期,对于生物演化的许多机制都并不清楚,斯宾塞与达尔文之间也迭有论辩,互相影响。其结果是斯宾塞的学说中既有拉马克,又有达尔文主义。他相信适应说,又强调本于适应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这使得两种演化论与生物学说混杂在一起,常常难以厘清。[94]所以许多人都误认斯宾塞为达尔文的信徒,并认为他最主要的特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然而无论斯宾塞如何强调「生存竞争」(strugglefor existence, 原为《物种原始》中的一章)与「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fittest),他的基调其实一直是「适应环境」(adaptation to theenvironment)与「所获能力可遗传」说(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s, useinheritance)。两者的冲突,在1882年达尔文逝世之后,益发凸显。[95]这证明了斯宾塞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拉马克主义者。[96]在另一方面,斯宾塞又企图将达尔文主义作为他解释宇宙间一切物质与运动(matterandmotion)变化的普遍演化论的一个特例。然而这种贯串一切物质存在,背后却又带着唯心论与意志论色彩的普遍演化观,从未被达尔文所接受。斯宾塞的演化观其实自成体系,与达尔文学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至于赫胥黎本人,虽然在伦理学上别有所主张,在生物学上却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与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其为学方式与思想内容均与斯宾塞颇为不同。
严复的生物演化观,基本上来自斯宾塞与拉马克而不是达尔文与赫胥黎。我们以严复书中一段极具关键性的案语为例,可以看出严复所受斯宾塞与拉马克的深刻影响。在原书导言的接近结尾处,严复对于赫胥黎的演化观提出总评:
赫胥黎氏是书大指,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97]
赫胥黎根据达尔文与马尔萨斯,对于人口增长所造成的生存竞争问题,抱持着一种悲观的看法。然而严复与斯宾塞却相当乐观,认为「人道必成于郅治」。其所以能够如此乐观的基本原因在于他们相信拉马克式的「适应环境」说。认为在人口与其它各种生存压力之下,人类自然能够适应环境而克服各种困难:
孳乳之寖[7]多,群而不足,大争起矣。使当此之时,民之性情知能,一如其朔,则其死率,当与民数作正比例,其不无正比例者,必其食裕也,而食之所以裕者,又必其相为生养之事进而后能,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镕民生,与民生之自为体合。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98]
进化的关键,在于体合。亦即人类在天演的竞争压力底下,才智、能力、德行都会日渐进步。生存竞争,迫使人大量用脑,脑的「襞积复迭」会一直增加。而脑力发达的结果,不但会克服各种生存上的难题,也会使生育力降低,而解决人口问题。[99]乍看此说,将认为斯宾塞的说法较符合现代世界演化的实情。然而他所说的透过努力与适应环境,人类脑部与生殖力所产生的变化,其实缺乏科学的根据,而不免为一种带有唯心论色彩的主观想象。严复与斯宾塞因为「体合说」,而对演化的结果抱着高度乐观的看法。然而赫胥黎所持的演化观,正因其本于达尔文的「天择说」,所以较为悲观。
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思想界大致分成两大派,一派是自由主义,一派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派主要继承了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他们相信自由的原则终将解决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社会主义者则继承圣西门与马克斯,强调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严复与斯宾塞的乐观,让他们对于社会演化采取了自由主义的立场,相信社会尽量自由竞争,压力自然增长,人的聪明才智才会被逼得更进步,甚至于人的身体和脑部都会变化,而将各种问题都加以解决。[100]赫胥黎的悲观,则让他大声疾呼自然演化与人类伦理的道理相反。自然之道,过于惨酷,并有许多的缺憾不足。人类社会的伦理则本于人类的合群之性。必须发扬这种合群、互助、互爱之性,人类才能得到平安幸福。[101]此说法带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色彩。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立场上相通。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其说法便和赫胥黎类似,认为人有互助的本性。这种带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色彩,而又希望建基于演化论的互助合群说,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有相当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赫胥黎的悲观看法,则让他对于文明演化采取了循环论。[102]然而此说却在书中受到严复严厉的批评。[103]
达尔文与斯宾塞二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其实早已表现在斯宾塞的诸多著述,以及他对达尔文的批评之中。[104]然而对于此两位大师的学说,严复却采取了融合的立场。一方面严复对于斯宾塞、拉马克与达尔文之间的根本差异,本来似乎未曾注意。[105]另一方面他虽然明知斯宾塞的普遍天演说成于达尔文的演化论之前,却认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可以和斯宾塞的天演学说相发明。[106]对于两者立说的根源有所不同,他虽有一定的认识,却未曾深入分析其差异。更严重的是,他竟然认为「所获能力可遗传」也是达尔文的一个基本主张。[107]这种融通诸家的作法,虽然有利于完成并传扬他所相信的一以贯之的天演论思想,却不利于处处求精确,丝毫差异必究的科学研究。在这种情形之下,达尔文的学说,其实已被严复融入斯宾塞的体系。
严复所说的「天择」,其实是斯宾塞式立基于体合说的最适者生存的概念,并非达尔文天择说的原意。[108]他了解「天择」说源自达尔文学说,却认为此说与斯宾塞「最适者生存」说的意思相同,并经常加以混用:
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109]
将达尔文的天择作了斯宾塞式的诠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便成为风行全国的西方现代天演论的代名词。殊不知根据体合说的「最适者生存」,要较本于自然变异与大量淘汰的「天择」说温和而乐观。严复受限于时代与其生物学知识,也受限于他的主观企图,对此二者并不加区分。所以他一方面深有所采取两家学说所共同强调的竞争与淘汰的观念,一方面则对于演化的机制采取了「体合」说的诠释。[110]这使得他一方面可以唤醒国人,另一方面也提供国人以努力的空间与希望。严复真心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界乃至宇宙界的公理,然而他在取舍各家学说的时候,不免受到自己先入为主之所学、中国传统思维的和合性与一贯性倾向、及时代需要等因素的影响。这是他采取了斯宾塞式天演论的基本原因。
然而严复的基调虽然是斯宾塞式的天演论,他对于赫胥黎却颇有所采取。这主要是因为斯宾塞的学说具有过度偏向放任与自由,社会竞争可能因而流于过度惨酷的问题。赫胥黎强调人治与伦理,对此可以加以补正。[111]赫胥黎认为「物竞天择」的律则只适合不同的物种,不适用于同种,更不适用于人类。人群建构的基本原理并非竞争,而是彼此能相感通的群性。人群与蜂群类似,都在演化的过程中培养出群性。人类的群性使人彼此感情相通而能互助共济。人类如果过于自私则群体必然毁坏,个人也无法独存。然而人类如果完全不知为己,同样无法生存。所以为人与为己之间,必须达到一个平衡。[112]然则人群进化与否,与其中是否有少数不肖而居下位者无甚关系,所以不必在群体内施行天择淘汰的作法。[113]斯宾塞则认为社会内部有进行竞争跟淘汰的必要。「最适者生存」,既然是生物界最普遍的规律,人做为生物之一,自然也必须符合这个规律。斯宾塞的学说承认人类历史中惨酷淘汰作法的合理性。严复在这一点上,颇认同赫胥黎重视人道与伦理的说法。[114]这是他翻译赫胥黎此书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另一方面,赫胥黎又强调群体的自治跟自立,自强。这部份相当适合中国的需要。[115]严复曾熟读斯宾塞的书,对于斯宾塞有关非西方国家之命运的说法,应该很熟悉。斯宾塞认为已经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西方国家,其演化会加速进行。与非西方国家的差距会愈来愈大,所以这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基本上只有走上天演淘汰一途。这种惨淡的结果,当然不是严复所乐见。[116]所以他在自序里说:
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指出赫胥黎的主张,一方面较合乎人道,与儒家重仁义、伦理、人治的态度相符,另一方面则强调「自强保种」的道理,切合中国今日的需要。而吴汝纶在他的序言中也开宗明义地说:
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墬,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117]
清楚地点出赫胥黎强调「以人持天」、尽量发展人的天赋能力,而有利于人文进步与自强保种的价值。
然而严复虽然基本上采取了赫胥黎重人道与人治的观点,却也同时批评这种人治与天道相抗衡的二元说法。他指出赫胥黎虽注意到群性与保群的重要,却未彻底认清群道亦出于天演,而人与生物的演化均本于自求生存。[118]他同时认为赫胥黎不了解爱人与自营两原则之间,有一既利人且利己的太平公例存在,是即弥尔氏的「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119]循此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公理,则不必在群性与自营之间徘徊。换言之,他虽然对于赫胥黎有所采取,究竟而言,却依然要回到斯宾塞式「一以贯之」的天演学说与自由主义。所以他在批评了赫胥黎的二元观点之后,特别说:「今然后知道若大路然,斤斤于彼己盈绌之间者之真无当也。」[120]再次表现他追求「一以贯之」式思想的基本倾向。
严复一方面以斯宾塞式的天演说与自由主义当作一以贯之的根本学理,另一面又强调赫胥黎的互助与人治。他对于斯宾塞、赫胥黎、达尔文等人的天演观实在取舍得相当巧妙。他在最需要强调生存竞争与淘汰时,通常提出达尔文。在需要指出天演的普遍规律与进化之应有途径时,通常推崇斯宾塞。[121]然而在企图指出人类基于演化论所应持的伦理观念与所应做的努力时,则采用赫胥黎。这种斟酌取舍,在严复的书中看起来似乎非常自然。然而背后实有一番很深的智慧。严复把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三人的讲法综合起来,一方面互相证明加强,另一方面各取所长。达尔文之所长在于透过物竞与天择说证明生物演化的道理。斯宾塞之所长则在于建立一个包括物质、生物、心灵、伦理与社会的普遍演化论。赫胥黎之所长则在于提倡人治与互助。严复兼取诸家之长,而企图说明一个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天演进化说,而是一路贯穿宇宙人生各方面的根本道理。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严复对于诸家之差异,其实认识得还有限。他始终不了解斯宾塞与达尔文二人的根本差异。也因此对于赫胥黎与斯宾塞的差异,仅企图将赫胥黎之说简单地纳入斯宾塞的体系,并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天行与人治可以相辅相成等中国式的观念加以融合。这种融通诸家的中国思维方式,其实不适合用于西方的科学与哲学,却有助于严复建立一以贯之的大道。
(三)融合天演论与中国传统思想
严复以斯宾塞学说为中心的天演论,不仅融入了达尔文与赫胥黎的思想,也同时企图融入了中国学术与思想的传统,而与中国传统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以下仅就其中最重要者略加说明。严复认为西方当代的天演世界观与中国易学与老庄的思想,虽有部份不同但基本相通,所以《天演论》一书中以老庄与《易经》的道理或用语来说明天演的文字是处处可见,几乎到了无章无之的地步。而其要义,诚如严复在序言中所特别指出:
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122]
「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确实是斯宾塞在第一原理一书中所揭露的普遍演化论的核心要旨。[123]严复以之与《易经》的乾坤之道相比拟,的确有其道理。中国原有的宇宙观主要来自《易经》与道家。[124]所谓「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指向一种「始简易而终杂糅」的道理。另外《易传》所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主收聚敛藏,即严复所说此坤道之「翕以合质」。而此处所谓「静而复动」,「辟以出力」,也都用《易传》式的语言,指陈万物的动静。传统《易》、老庄一气化生,自浑沌而生生不息地发展出万事万物的世界观,本身就是一种整体观式的天演观,难怪严复会说庄子是「古之天演家也」。[125]
这种认为天地万物乃一气之化的宇宙观,使中国人在先秦便超越了神话创世的各种说法,而对于天地万物,有一种非常清明理智的观察与看法。在另一方面,这种气化的宇宙观,也与柏拉图及亚理斯多得的「理型论」化的存有观大不同。前者重变化与时间而近于现代的演化论,后者重永恒的存有实体而远于现代演化观。这一点是西方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最重要的一个差别。严复一再地引《易经》与道家与现代的天演观相比,的确有其深识。[126]中国传统主张气化观而没有造世主的观念,而中世纪以降的西方文化则以基督教创世的上帝为万有乃至一切价值的基础。当生命是经由自然、生物演化而成的理论出现,便与宗教形成极强烈的冲突。然而中国人根据《易经》、道家本来便主张人从自然之中化生,因此当人与万物都是由「天」演化而来的天演论输入时,很容易便被中国人所接受。[127]与此同时,天演观作为一种世界观本与中国传统根源于《易》、老庄的世界观有很大的类似性,所以天演论的学理容易在中国风行。[128]严复不断以两者相比,一方面是他很早便看出二者相似之处,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如何融通西方与中国之最高学理,以成其一以贯之之道。
严复融西方学理入中国学术及思想传统的另外一个重要例证,在于他的译法。他一方面使用源出子学与经学的高古文言来翻译,同时还大量地引经据典以直接说明西方学理如何与我古人的道理相通。有关使用源出子学与经学的高古文言来翻译所涉及的「文道合一」的问题,已经讨论于前。而从当代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文字与思想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高古的文言翻译西学,本身便不可能不涉及「视域融合」与再创造的问题。严复当时从实证主义出发,相信西方与中国之理可以会通,所以对于中西学理的差异性,有时并未给予充分的注意。也因此更使他的翻译工作,从头开始便偏于西方与中国思想的大融合与交会。我们从以下有关严复引经据典的情形之讨论,更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
严复大量引经据典的情形,除见于现有通行本之外,在本书最早的味经本中,更是多到惊人的地步。我们以《天演论》本论的第一章为例,特别可以看出这个情形。通行本正文的文字,几乎均从味经本删节而来,而其案语,则多系新增。其所删节的部份,大体都是引据中国的经典与史实以印证西学的地方。这一点上,严复接受了吴汝纶的劝告,将中国经典与史实的部份,或加以删节以避免误会,或尽量放入夹注、案语以与翻译的正文分开。[129]就保持原著之原貌的观点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然而「味经本」的内容,才更接近严复原始的作意以及他理解原书的方式,殆无可疑。综观全书,味经本征引传统学说的数量与范围都到了惊人的地步,由此可见严复在初译《天演论》时,所做的根本就是一种比较与融通西方与中国思想,以成一家之言的工作,绝不能以一般的翻译释之。而这种取向,即使在大量删节之后的通行本的正文、夹注与案语中,仍然大体保存。我们谨以此书本论论一的〈能实篇〉为例,先分析其通行本,再研究其味经本。〈能实篇〉的通行本开宗明义便说:
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骛远穷高然后为大乎?[130]
如本节第一部份所述,本句不见于赫胥黎原文,完全是严复自己所加。「道每下而愈况」出于《庄子‧知北游》。「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的观念出于《中庸》与《孟子》。「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的观念出于《大学》,尤其是朱子的《大学》格物说。[131]换言之全书本论的首句便综合了《庄子》、《中庸》、《孟子》与《大学》中论学与论道的看法,而以之说明原书中所要提倡的培根式的科学精神。严复而后指出一般人对于周遭习见的现象不能深察,所以「此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所以众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一句,出于《孟子‧尽心》,意谓道无所不在,吾人当即物而穷其里。而后此文再以《庄子‧齐物论》的「特无为而成,有真宰而不得其朕尔」形容「天则」与「天工」之幽深难见而井然不可乱。之后再论天行往复、生理盈虚的道理,则直接以「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来形容。至于原书论及古希腊哲学家额拉吉来图(Heraclitus)借水流不止,以比喻时间恒移,万有常变的说法,严复则引宋代理学家最喜欢引的「仲尼川上之叹」与「回也见新交臂已故」的典故来印证,并说「东西微言其同若此。今然后知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隐隐与太极图说「静极复动」,《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看法相发明。最后以「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乎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名,不可道,以为是变者根耶?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作结。「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乎主而有觉知」的句法与语意出于《庄子‧齐物论》,「不可名,不可道,以为是变者根耶」变自《老子》第一章。均指出名、色、相、知之无常,唯变与易方为万事万物之根源。而除了以上所举至为明显的例子外,本篇的文字,均使用出自以子学为主的高古文言,所以字字句句往往都有其典故,在此更无法详举。整体而言,严复这种处处引经据典的「翻译」,本身就是中国与西方思想,乃至其中最高哲理的一次大融合。[132]
「通行本」引经据典的情况已经如此普遍,我们如果再对勘目前能够找到最早的《天演论》版本──味经本,更可发现严复对西方学理的理解与翻译与他所受中国经典的训练难以分离。味经本正文的内容大体与通行本类同,但是多了许多直接引用古书的字句。其中比较重要的,首先是他在析论万物形制之巧密,而上天却似乎不甚珍惜,任其凋落,而成为所谓「存者仅如他日所收之实」的情况之后,加上「复以函将然未然之生机,用以显太极无极之能事」一句。[133]此处用《易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八卦以至于万物,以及周敦颐与朱子「万物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与「无极而太极」的道理,来印证西学所谓实存事物形制虽极巧妙,终为次要,而其中所函之理与生机方为造化之根本的说法,下语既精且妙。
另外在论拋物线先上行而后下坠之「从虚而息,由息乃盈,从盈得消,由消反虚」一段后,严复加上「星命家所谓生旺墓绝者,亦此志也。故天演如网如箑,始以一本,散成万殊,以一本含万殊之能,以万殊极一本之致」[134]一段。星命家「生旺墓绝」,所论乃盈虚之理,通于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之说。「一本万殊」,即宋朝人最喜言之「万物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之说。严复用这些极传统的语言来说明天演的道理,更可见他是在《易经》的宇宙观之基础上,融合并理解西方的天演学说。所以他认为天演的道理,如同「易道周流,耗息迭用」。其重点在于说明万物如何迁变不已,生生不息。
另外在讨论希腊哲学家时间恒移,万有常变之说时,通行本所置于夹注中的「子在川上曰:水哉水哉。又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东西微言,其同如是。」一小段,原属味经本的正文。换言之,严复原来思考与翻译此部份时,本来是一段希腊哲学,紧接着便是一段对照的中国思想。与其说他是翻译,不如说他在比较印证西方与中国思想,同时借着中国的传统,让学者更容易掌握西方的思想。这个现象在「其同如是」一句下面的一段,看得更为清楚,他说:
今然后知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暄之争也。当其发见,目击道存,要皆群力交推,屈伸相报,万(众)流汇激,胜负迭乘,大(广)宇长(悠)宙之间,常此摩荡运〔《严复合集》作「远」,盖误〕行而已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精(幽)之而为神为虑,显之而为气为力。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夫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道,不可名,(以是为变者根耶,亦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而为是蕃变者固耶?万世之后,而有触通其故者,犹旦暮遇之矣
引文中划底线者,为味经本所有而通行本所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一句,出自《易‧系辞》。「万世之后,而有触通其故者,犹旦暮遇之矣!」一句之用法,出自《庄子‧齐物论》,以喻此道理之难得解人。「目击道存」,典出《庄子‧大宗师》,意谓忘言得道,世所稀有。另外味经与通行本的引文中都有的「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夫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道,不可名,以是为变者根耶,亦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全为老庄书中论道与自然之言,亦无庸置论。由此可知,严复此段以《易》、老庄的世界观,来印证说明西方的天演论。而其关键,则在于将此通乎万变,无定形无定名的「天演」之理,比作《易》、老庄所论之道。
此论的案语翻译自原著的注一,而严复未曾注出。然而在翻译斯宾塞畅论生命代续之理的一大段话之后,味经本的《天演论》于最后加上「又,储能效实,乃力学理学家常语,即中(《严复合集》作「史」,盖误)庸之中和。」[136]一句话。大体以储能为未发之中,效实为发而中节之和。此说诚如其文中所引,其实通于《易经》的乾坤翕辟之道。至于其它用词用语之所涉及各种经学与子学的典故,实在不胜枚举。而严复融通中国与西方的企图与思维方式,也由此跃然纸上。
严复融通中西的各种说法是否恰当,必须另外作深入与仔细的分析,不适合在此讨论。然而严复的基本意图与作法,经由以上的对比,以及本文中其它的相关分析,已经相当清楚。大抵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讨论宇宙观与认识论时所引证的以《易传》、《老子》、《庄子》、《中庸》等书最多,在讨论学术方法与为学目标时,则以《大学》、《中庸》、老庄、与朱子较多。另外较常引用的包括宋明理学、《孟子》与佛学,较特殊的则包含星命家。《易传》与《中庸》都带有相当浓厚的道家色彩,是儒道两家结合下的产物。宋明理学的宇宙观则承继先秦,以儒道两家为主,同时受到佛学的影响。星命家之说,源于易学,通于道家。所以严复的宇宙观与认识观大抵以道家为中心,并融合了《易传》、《中庸》、《孟子》、宋明理学等儒家的说法。对于佛学,则主要采取其可通于道、儒、天演与西方哲学的说法。[137]至于严复的学术方法与为学目标,则以《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理想为中心,同时也深受道家式认识观的影响。其社会、伦理与政治观,则以道家自然、无为等观念为中心,然而不废儒家重人治与慈孝仁义之说,可以与其宇宙观的取向相发明。换言之,严复虽然引进了新学说,也提出了进化、自由、平等与物竞天择等传统所没有或不重视的思想,他却时时用心于新学说与旧传统的结合。其学术的基本取向与思想中的基本观点,均带有浓厚的道家与儒家特色。
严复曾经明白指出斯宾塞的学说基本上近于黄老、以及赫胥黎的学说基本上近于唐人刘禹锡、柳宗元。[138]手稿本的《天演论》的案语中更长篇引刘禹锡的〈天论〉,认为其说法与斯宾塞极为类似。刘禹锡认为「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而「天与人交相胜」,各有所不能。他并且特别提出在历史上「世道兴衰,视法制为消长」,草昧之时天胜,城郛文明之后人胜的说法,以突出人为的重要,其态度属于儒家。[139]然而严复虽用赫胥黎类似儒家重人治的说法以救「持斯宾塞学说而过者」所可能产生「任天为治」的流弊,其所宗主却仍然是斯宾塞「任天而人事为之辅」,近于黄老一派的说法。[140]严复又特别评点了《老子》与《庄子》,并常引用老庄以批评儒学之拘执而不自由。大抵严复一生偏好老庄与黄老之学,虽然从未严词批评孔孟,却直至晚年才较常称美孔孟仁义之说。在作《天演论》一书时,严复的世界观尤其明显偏重斯宾塞、老庄与黄老。然而严复于此书中又特尊《易经》,《易》为群经之首,尊《易经》则可继承儒家传统的世界观。严复在此书中于世界观又兼取刘、柳、《中庸》、宋明理学诸家之说。其于治学方法与为学目标上,更是以儒学为主。除此之外,严复并且指出赫胥黎认为政治与社会要上轨道,首先必须去除假借,使贤者自然在上不贤者自然在下的说法,与墨、法两家「尚贤课名实」的学说一致。[141]换言之,严复虽然偏重道家,却兼取儒、墨、法、释诸家的思想,而全书文字又用心于继承整个子学与经学的传统。其斟酌损益,不专守一家,唯问其宜的精神,亦由此可见。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严复评此章则说:「此章形容道体,盖道之为物,本无从形容也」。[142]冲虚应物,本不可拘执,亦难以形容,严复学术与思想的究竟追求与境界,似乎亦当作如是观。
严复融会贯通各家而成的天演思想体系,企图兼有斯宾塞、赫胥黎、达尔文、古典自由主义以及中国道、儒与诸子学之长,并反映现代世界的世界观与基本精神。所涉及的范围则从深遂的哲理、复杂的科学一直到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当他立论为文时,所采取的学理上下古今,纵横百家,而出之以极精审之文字。这种心胸、才学与严谨,不仅当世无双,百余年来,亦罕有其匹。吴汝纶说他:「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锺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143]这番话虽然成之于中西尚未普遍交通时,求之于中西大通之后,能够兼通中西而融会其精义于一炉,并形之于精妙之文章者,亦难得其人。严复求道心切,所以其所论说得以体大、思精、义深而且立言一丝不苟。如果只是为了 救一时之危亡,势必不能完成上述的宏大体系。[144]
综合上述三部份的论述,可见严复的译介,所尝试的其实是一种介绍西方最新学理并融通西方与中国思想以明道的工作。这种融通采取的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学术与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追求致广大、尽精微,综融合会的一以贯之之道的学术与思想企图。这种企图为儒、道两家所共具,而在前述「追求致广大、尽精微,综融合会之道」的意义下,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庸的态度。关于严复企图融合西方与中国并具有儒学与中庸的特质这些方面,前辈学人郭正昭先生也早有论述。其观点颇有一部份可与本文的内容相发明,然而其具体的说法则与本文大为不同,在此必须加以讨论。[145]郭正昭在他的〈达尔文主义与中国〉曾指出「严复所从事的不是翻译,而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文化的整合和重建的工作。」[146]对于此结论笔者自无异义,然而其诠释的具体内容却有许多严重的问题。郭正昭对于严复如何整合西方与中国学说的分析,是从严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的前提出发。可是严复所相信的与其说是达尔文主义,不如说是斯宾塞主义;又与其说是斯宾塞主义,则不如说是融合了西方与中国各家思想的天演论。所以绝不能简单地用「达尔文主义者」来论定严复的主要内涵。郭正昭对于严复的这项论断,是因为他的研究是从「达尔文主义与中国」这一问题出发,所以他一切的思考都不免偏向达尔文主义这一中心点。郭正昭认为作为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的严复「往往以法家取譬赫胥黎,以道家取譬斯宾塞,为了统合这两个学派的两极性矛盾,他的思维归宿必须走向中庸之道之儒家,别无选择。」[147]这个说法虽然正确地指出严复具有「中庸之道之儒家」的性质,却也因为一切从「达尔文主义者」的前提出发,而忽略了严复的儒学思想自有其「主体性」,而不是在接受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下,企图折衷对立的两派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逻辑的必然」。[148]换言之,严复的「中庸」意涵深远,与儒、道两家的精义密不可分,而不仅是一种折衷于对立两派西方学说的作法。何况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对于斯宾塞学说的捍卫始终不遗余力,并不与赫胥黎的学说置于同级的地位。郭正昭所谓严复将近于道家的斯宾塞与所谓近于法家的赫胥黎综合,而得出其儒家立场的说法,在证据上难以成立。郭正昭在这一点上企图与史华兹立异。然而史华兹认为严复一生以斯宾塞为大师(master)的说法虽有缺点,却较郭正昭之说近于实情。[149]同时严复虽然认为斯宾塞之学近于黄老,却从一开始便认为斯宾塞之书兼具《大学》、《中庸》的精义,并通于《易经》,所以其学说也不能仅以「道家」视之。严复在此书中以刘禹锡、柳宗元的天论比赫胥黎的「尚德人治」之说,刘柳虽重法制,却仍属儒家的范围。严复又认为赫胥黎论性与天道近于周敦颐,陆象山而远于荀子。所以赫胥黎之书也不能以法家视之。[150]凡此种种,都使郭氏的论证方式陷入困难。
学界多年来已经承认严复在译介《天演论》与其它西方学理时具有融通西方与中国思想的企图。然而此种融通工作对于严复的意义,以及严复从何种出发点与方式进行融通,则学者之所见甚为不同。不同的诠释,代表了学者对于严复治学的动力、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等基本问题的不同认知。本文的重点,正在于对于上述基本问题提出新的诠释。郭正昭认为严复翻译此书的主要意图在于引进「达尔文主义」以救亡与图强,而在企图兼取赫胥黎式近乎法家的达尔文主义与斯宾塞式近乎道家的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下,他只好走上了儒家的中庸之道。这种诠释方式虽然不无所见,却对严复的儒学与求道性格缺乏深入理解。严复的儒学性格与中庸的态度,被贬抑成在介绍达尔文主义之前提下的折衷产物。这说明了郭正昭先生对于严复治学的动力、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缺乏深入的探讨,而犯了「忽略被研究者主体性」的老问题。[151]
郭正昭对严复的诠释,与他「危机论下的综合哲学」说不可分。他从达尔文主义何以能够被中国人迅速接受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了「危机哲学」说:
严复的思想归宿,即非由激进而保守,而终其一生,其思维模式始终守住中庸之道的儒家观念,并没有转向西方传统,更没有一边倒地归皈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之服膺演化论,是基于危机感的爱国情操和政治觉悟。处在那样一个危疑震憾的时代环境,他迫切地企图要建立一种综合的危机哲学,任何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学说,能解决他的认同危机的思想理论,都是他探究和综合的脚注。[152]
这段结论式的文字,在论证上有许多问题。首先,达尔文主义与斯宾塞主义本身都不是危机哲学,至少不是「危疑震憾的时代环境」中的危机哲学。[153]斯宾塞主义对于演化的前景非常乐观,而严复对达尔文主义也早已作了斯宾塞主义式的乐观诠释。严复虽然有鉴于中国的危机而引入了天演论,却并不表示他是为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学说,能解决他的认同危机」而「研究」天演论。相反的,是斯宾塞的学说,让他一反「独往偏至之论」,复归于中庸之道,不至于有过激的作为。而不是像郭氏所言,是因为他笃守儒家中庸之道,从来不激进,因此不皈依斯宾塞过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事实上严复对斯宾塞始终推崇不遗余力,从来也未曾将斯宾塞简单地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郭正昭同时还从「反传统」这个角度来诠释达尔文主义对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意义。他认为达尔文主义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正能适合身处危机时代而需要颠覆传统的一代人的需要,而「这种危机哲学的本质是认同的危机」。[154]此说亦有其所见。然而我们如果以严复为例,便可见严复虽然曾强烈批判中国传统,却不曾「反传统」。同时因为他对于传统的精华之信心与认同感都非常真挚而坚强,所以也不甚具有文化或心理上「认同危机」的问题。郭氏的说法,用之于下一辈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许更适合。
综合言之,郭正昭所谓「任何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学说,能解决他的认同危机的思想理论,都是他探究和综合的脚注」这一说法,其实植基于「救亡保种」与Levenson式「文化认同危机」之旧说,而严重低估了严复求道的努力。他根据此一说法所建立的有关严复如何「守住中庸之道的儒家观念」之诠释,也忽视了严复的儒学性格与中庸思想之深刻内涵。因此对于严复如何融通中西学理以完成其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未能做出适当的诠释。然而本文虽然不采取郭氏「危机哲学」的说法,却同意严复之所以能够如此致力于尽精微与致广大的道理之研究,与时代危机的刺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思想体系受到了整体性的挑战,才逼使得严复更要「究其理极」,以找到中国的出路。严复的天演思想,源自他对于最高学理的探讨。时代的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而不是唯一的动力因。而动力因并不等于内容。我们不宜简单地将严复的天演思想视为「危机哲学」。
(四)对救亡图存的讨论与中国文化的反思
严复在此书中所做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便是本于天演论,对于救亡与图强的现实问题提出讨论,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加以深刻的反思。他在这两方面着墨虽然不多,却往往是微言大义,几句话就将他所要传达的意思表现出来。有关于文化的反思,严复用语通常较为间接,很少特别提出来专门加以申论。严复讨论较多,下语也较直截明白的,首先是救亡保种的现实问题。他曾仔细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明生物的数量以几何级数成长所造成生存竞争的惨烈。不同的人种之间,其竞争亦如是。「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所以「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155]竞争的胜负既然根据物种的能力质量,而不是数目的多寡。中国人口虽多,然而「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156]西方人文化发达,而中国人素质不如人,所以处处被人奴役压迫:
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矣。吾闽、粤民走南洋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157]
凡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下语均极为沈痛,可以想见严复当时的心情。对严复而言,天演论所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普遍真理,第一个实际运用的对象,就是中国的存亡问题。他当然不免于「惊心动魄」,而致力于「保群进化」。
从天演学的观点,严复特别注意到「国种」的素质,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盛衰强弱。他指出浅演之民「武健侠烈」,而「变质尚文」之后,则「良懦俭啬计深虑远之民多」。从历史上看,中国历代与戎狄相竞争,唐以前尚有力量,南宋则孱弱。至于当今西方之民,「好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日本人则「轻生好勇、死党好名」。[158]而中国之人久已「变质尚文」,个性「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驯服」,民风「无耻尚利,贪生守雌」,一旦「不幸而遇外雠,驱而縻之,犹羊豕尔」,[159]其「隐忧之大,可胜言哉」。[160]这些话对于中国国民性的缺点,批评得入木三分,对中国当时的危险处境,也有清楚的说明。让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内在问题与中国的前途,不禁有深切的反省。
针对这种情形,严复主张中国社会必须根据天演的道理,以及斯宾塞、亚当斯密、穆勒诸人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竞争中激发个人的德、智、力,充分发挥人民的一切潜能,根本改变人民的素质与风气,才能适应与争存于这个不断进步的现代世界。这些目标中,尤其以提升人民的智识,为一切根本。他说:
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161]
对中国的几千年一治一乱之局深为不满,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民智太低、基础太差的缘故。在人民素质太差的情况下,「以有限之地产,供无穷之孳生,不足则争,干戈又动,周而复始,循若无端,此天下之生所以一治而一乱也。」[162]一切便只好服从自然界规律,无法透过文明进化,去解决人口增生所造成的压力,于是只能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同时也因为不知道好好地教育人民,只能落于「苟且之治」:
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163]
「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一句,虽未明言,却直接批评到孔子的菁英主义,而指向民主政治。认为儒家这种政治思想,只能算是应付落后局面的苟且作法,无法适应竞争激烈的现代世界。
于此同时,本于天演论与自由主义,严复又提倡功利主义,而对儒家仁义之说有所批评:
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从自营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此道之所以不测也。[164]
「仁之本」既从「自营之私而起」,则「自营」才是人道的根本。「自营」的基本方向在于去苦求乐,所以「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165]儒家传统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严复根据天演论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166]
严复又赞成西方的民主与民权思想,认为「今者民权日伸,公治日出,此欧洲政治所以非余洲之所及也。」[167]透过天演论有关如何提升群体质量的讨论,他指出「世治之最不幸在于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而「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积弊。[168]并同时指出「英伦民气最伸」,能够尚贤而责实,去除政治上的各种病象。中国用儒家亲亲尊尊的道理,所以自中古以来就很少能够做到「尚贤课名实」。两国一强一弱,一进步一落后的关键固然在于是否能够「尚贤课名实」,然而严复显然认为民主制度较儒家更能达到这种政治理想。[169]
儒学的政教体系在进化论、自由主义、民主与民权思想、功利主义的批评下,受到根本而全面性的打击。严复透过天演论所批判的不是一枝一叶,而是对于儒学从来修齐治平的方式,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都发生了怀疑。他所主张的,是一个根据现代西方文化而建立的新模型。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学术、思想、教育以及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必须作根本性的改革。而其根据,则在于天演进化论是贯串宇宙、生物、人生、社会的根本道理。顺此道理者昌,逆此道理者亡。中国必须根据这个新的,一以贯之而无所不在的道理,重塑其文化的一切内容。严复全面批判了旧的体系,并提出了新时代所当依循的一贯之道。然而其内容虽然新颖,其追求「一以贯之的大道」之思维方式却仍然非常传统。所谓「旧槽装新酒」,正可以形容这种情形。
五、结论
学界长久以来认为严复在一种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与因应当时危机的心理之下译介了《天演论》,引入先进的西方观念,从而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这种「现实取向」与「拿来主义」式的诠释,严重低估了严复天演论的深度。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白严译《天演论》不仅介绍了西方的天演学说,并且深刻地反映了传统的学术性格、思维方式与世界观。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学术与文化传统的国家,严复又深深浸润在这个学术与文化传统之中。他对于天演学说的译介,绝不仅是为了现实的需求,而向西方拿来一些他所认识到的最先进知识。本文仔细考察了严译《天演论》的作意与内涵,发现严复研究、接受与发扬阐释天演学说时,处处均表现出一种追求一以贯之之道的传统心态。其天演思想又与中国传统以《易》、老庄为中心的世界观有不可划分的关系。换言之,严复其实是在一种相当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基础上,吸收译介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世界观与相关学说。他以高古的文字与子学、经学的术语来翻译西方思想,不仅表现出他融通中国与西方学术与思想的努力,也让深受传统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影响的清末读书人,得以接上最先进的西方学理。进化论在西方发表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国却是风行草偃,不到几年便流布全国。其流行的原因相当复杂,然而其中一个基本而经常为人所忽略的原因便是经过严复所重新诠释的天演论,其实深深契合传统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严复所阐发的天演论,是在契合了传统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深层基础上,又进而符合救亡图存、追求富强的显性需要,所以才能席卷当时的学术思想界。[170]
严复所引进的天演学说确实符合了救亡图存、追求富强等时代迫切的显性需要,这也是学界长期以来主要用救亡图存这一类实务取向的观点来诠释《天演论》一书的主要原因。可是一本书所以风行的原因,尤其如果只是众人意识中的显性原因,并不就等于原著的真正作意与内涵。[171]严复本人译作《天演论》的真正用意不仅在于满足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或因应危机等一时的目标,而更在于本乎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并结合中国固有的道理,以指点出人文演化必须遵循的自然道理与中国文化所应发展的方向。在严复而言,能认识并遵循人类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根本道理,自然能也才可能救亡保种、获得富强、促进变革并因应危机。然而若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道理,则无论如何跳踉号呼,也终究不能解决问题。国人对中国在现代世界的处境原来茫昧不知,于是他在甲午之后首先发表了〈救亡决论〉等一系列的文章,根据学理提醒国人国家处境之落后、危殆与天演淘汰之危机;并进而译介《天演论》一书,以说明通贯乎天地人之道而可以救世的天演学理。前者重在于提醒国人当前危殆的局面,后者则着重于高深学理的介绍,教人必先明道才能救国。然而国人对于严复所提出天演学说的深远内涵,从开始便缺乏足够的了解。年轻新锐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一旦觉醒后,心情激动,不学无术却日日从事于极端之事。严复深恐国人循此一切求变求新的偏激心态,必将酿成大祸,于是他在《天演论》出版后的两年之内,又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从天演的观点,详述人群进化以渐不以骤的道理。并特别强调必须先以谨慎、平静、客观的心,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究明人群结合与进化的道理,才能因应复杂困难的人群之事。[172]严复终生强调凡事必须本于「真学实理」,并将他自己的一生主要奉献给学术。[173]他非常厌恶行事不根据学理、不审乎时势之人。也因此对于戊戌变法、革命党与晚清的各种激进的潮流都有深刻的批评。然而严复一生所学终究不为国人所知,包括最风行的《天演论》一书也只获得表面的理解,所以他始终痛感寂寞。更让他难过的是,国家终究在国人德慧术智均有所不足的情形下,一路走上激进的道路,而莫之能救。[174]
除了根据天演论的影响立论,学者也经常举出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之前后所发表的言论与《天演论》一书的内容,以证明严复译此书的宗旨在于救亡保种或追求富强。不能否认这些目标也的确是严复翻译此书的重要因素,然而细绎《天演论》一书,笔者发现学者所能举证出来的文字,其实只占全书内容的一小部分。而严复在甲午战后所发表一系列藉天演说以救亡的言论,也只是他明道以救世的长期努力中的一部份。本文透过了针对《天演论》文本与其写作背景的详细分析,证明严复翻译此书更主要且根本的用意在于「明道」,救世则为明道所当有之用。就严复而言,明道为体,救世为用,明体方能达用,务本才能治标。他其实是经过了长期的努力求得了他所认为的最高而普遍的道理,并相信只有借着这种「真实学理」,才能解决问题。这个最高而普遍的真实学理,就是他认为足以代表当代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而又通贯乎古今中外之最高学理的天演学说。他企图藉此来指导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从而逐渐而根本地解决中国文化的内在问题与外在困境。他相信中国文化当前所面对的内部问题,源头甚为久远,绝非一时所能解决。而西方的挑战,则有悠久博大的文明与高深的学理为后盾,亦绝非一时就能克服。中国人唯有明白这一切问题与正确道理的本原,才能逐渐解决中国所面对各种危机与问题。如果不能究明正确的道理及问题的根源就鲁莽从事于救国的工作,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他非常反对革命派与康梁激进的作法,就是这个缘故。
严复这种追求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理以指导文化发展的态度,有其深厚的学术与文化根源,这是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超越现实考虑的根本原因。严复在追求真确知识这一方面固然表现了西方的科学态度,然而就其追求一以贯之的最高道理以指导文化的发展而言,则深刻展现了一种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的「求道精神」。虽然这两者之间有相当的紧张甚至矛盾性,然而严复却一直试图将其加以融合。中国儒道两家在传统上均以追求一以贯之之道为学问的最高鹄的。这不仅是传统学术与思想的核心精神,在历史上它也担负著作为一切人文活动最高指导的重责大任。作为一个宗教色彩不浓厚的文明,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与意义系统,基本上建立在以儒家为主,释道两家为辅的世界观与价值系统之上。这个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体系对于天道与人道的诠释维系了数千年,却在清末遭受严重的挑战。而严复正是全中国最早也最深切了解西方学术与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所构成的全面挑战之先知先觉。严复出身海军,深受西方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及科学精神的影响。然而他虽然大力提倡科学,其本人所表现的学术性格,却又绝非典型的西方学者或科学家性格,而是相当传统的儒学性格。他在早年便不只用心于自然与军事科学,而对于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学术、文化与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处处留心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持续钻研西方的整个学术传统,并藉此反省自己国家的学术、文化与制度。他的国学基础雄厚,笃好道家思想,并对儒、释两家以及整个子学传统都相当深入的了解与敬意。生长任职于旧社会,严复一生的志业与作为,明显表现出传统儒者企图明道救世,一匡天下的特色。在个人长期不得志与时代危机的刺激之下,他深深地探索一切有关中国与西方文化比较与中国前途的问题,并终于在以天演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中,提出其答案。他的思想体系包含了天文、地质、生物、脑质、社会、人文演化的一以贯之的基本原理,而企图对文明演化必须遵循的自然道理与中国文化所应发展的方向提出完整的看法。其答案的具体内容固然主要得自于斯宾塞、赫胥黎等西方天演学者,其内涵则深具以道家与《易经》为中心的传统世界观之特色,而其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与所表现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则表现了以儒道两家为中心的传统求道特质。
参 考 书目
严复著作
严复着,王庆成、叶文心、林载爵编,《严复合集》(台北: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
严复着,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1986)
严复,《严译名著丛刊》(上海:商务,1931)
严复,《侯官严氏丛刻》(南昌:读有用书之斋,1901。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八辑)
严复,《严几道先生遗着》(新加坡:南洋学会,1959)
严复,《严几道文钞》(台北:世界,1971)
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台北:文海,1969)
严复译,赫胥黎着,《天演论》(台北:台湾商务,1969;案:本书版本甚多,请参见本文注8)
严复译,赫胥黎着,《天演论》(郑州:中州古籍,1998)
严复译,亚当‧斯密着,《原富》(台北:台湾商务,1977;北京:商务,1981)
严复译,孟德斯鸠着,《法意》(北京:商务,1981)
严复译,耶方斯着,《名学浅说》(台北:台湾商务,1966)
严复译,斯宾塞着,《群学肄言》(台北:台湾商务,1970)
严复译,甄克思着,《社会通诠》(台北:台湾商务,1977)
严复译,穆勒着,《群己权界论》(台北:台湾商务,1966)
严复译,穆勒着,《穆勒名学》(台北:台湾商务,1965)
严复,《侯官严氏评点老子》(台北:海军总部,1964)
严复,《侯官严氏评点庄子》(台北:海军总部,1964)
严复,《严氏评点王临川诗集》(台北:海军总部,1964)
研究文献:
中日文部份
小野川秀美着,林明德、黄福庆译,《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时报文化,1982)
中下正治,〈晚年严复〉,《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32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严复与家乡》(福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9)
毛以亨,《一代新锐梁任公》(台北:河洛图书,1979)
牛仰山、孙鸿霓编,《严复研究资料》(福州:海峡文艺,1990)
王中江,《严复》(台北:东大,1997)
王中江,《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河南大学,1991)
王世昭,〈近代翻译界三先生〉,《中国文人新论》(香港:新世纪,1953)
王民,〈谈谈严复研究中的几处疏误〉,《历史教学》第5期(1983,天津)
王民,〈严复出生年月与赴英留学时间的订正〉,《福建论坛》第3期(1982,福州)
王宏志,〈翻译与政治:有关严复的翻译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通讯》第21期(1992,台北)
王家俭,〈严复与伊藤博文轶文订误〉,《中央日报》(1978年7月25日,台北)
王栻,〈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思想与活动〉,《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1956,南京)
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1982)
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人民,1986)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初版1957,再版1975)
王梓良,〈严复〉,《珠海学报》5期(1963,香港九龙)
王盛涛,〈严复与伊藤博文〉,《艺文志》131期(1976,台北)
王煜,〈严几道谈伦理政治与中国文化〉,《孔孟月刊》30:3=351(1991,台北)
王道还译,Jonathan Howard着,《达尔文》(台北:联经,1986)
王寿南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台北:台湾商务,1978)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1995)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1995)
王宪明,〈严复《民国初建》诗「美人」新解〉,《近代史研究》5期(1996,台北)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郑州:中州古籍,1998)
王觉源,《忘机随笔》(台北:东大,1993)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1936)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1999)
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台北:文津,1994)
史华慈等着,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文化文化,1980)
左舜生,《中国近代史话初集》(台北:传记文学,1970)
田默迪,〈由严复《天演论》的翻译特色论科学精神的问题〉,《中国近代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严复》(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编辑;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
田默迪,〈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之研究与检讨:与赫胥黎原文之对照比较〉,《哲学与文化》第19、20期(1975,台北)
伍稼青,〈严几道先生的生平〉,《畅流》32:6~7(1965,台北)
朱传誉,《严复传记资料》(台北:天一,1985)
何家炳,〈严几道先生小传〉,《人间世》24期(1959,上海)
余英时,〈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严复思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1999.7.11。
吴相湘,〈孙逸仙近代思想与郑观应、容闳、严复、胡适之比较〉,《传记文学》69:6(1996,台北)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1979)第一册
吴康,〈晚清学界之进化思想〉,《晚清思想》(台北:时报文化,1980)
吴万颂,〈严复的教育思想〉,《新时代》11:12(1971,台北)
李承贵,〈五十年来严复思想研究述评〉,《中国文化月刊》第204期(1997,台北)
李承贵,〈自由的经济与自然的经济:严复经济思想的中西比较与结合〉,《鹅湖月刊》第18期(1997,台北)
李承贵,〈严复文化观研究〉,《哲学与文化》24:12=283(1997,台北)
李承贵,〈严复对中西哲学的会通〉,《中国文化月刊》第194期(1995,台北)
李承贵,《中西文化之会通:严复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思想研究》(南昌:江西人民,1997)
李牧华,〈翻译西洋学术著作的第一人:严复〉,《今日中国》第20期(1972,台北)
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上海:学林,1993)
李春生,《天演论书后》(福州:美华,1907)。
李洵、薛虹等编,《清代全史》(沈阳:辽宁人民,1991)
李荆,〈严几道别传〉,《中央日报》(1958.10.19,台北)
李猷,〈严复传〉,《国史馆馆刊》第7期(1989,台北)
李渔叔,〈严又陵及其译着〉,《鱼干里斋随笔》卷八,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3辑(台北:文海,1981)
利瓦伊武,《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湖南教育,1991)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风云时代,1990)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台北:文海,1962)
沈寂,〈严复为安徽高等学堂的”礼聘”与”辞馆”〉,《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1994,合肥)
沈云龙,〈严复晚年之政论〉,《传记文学》39:1~2(1981,台北)
沛莲,〈严几道的生平与学术〉,《世华金融》第82期(1985,台北)
汪一驹着、梅寅生译,〈严复的政治思想〉,《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台北:久大,1991)
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析论〉,《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北:时报文化,1980)
汪荣祖,〈郭嵩焘、严复、曾纪泽连环叙〉,《历史月刊》第80期(1994,台北)
汪荣祖,〈严复的翻译〉,《中国文化》第9期(1994,台北)
汪荣祖,〈严复新论〉,《历史月刊》第89期(1995,台北)
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1979)
周弘然,〈康有为和严复的民主思想〉,《政治评论》6卷8期。
周邦道,〈严复、张柏苓、梅贻琦:当代教育先进传之十四〉,《中外杂志》22卷6期(1977,台北)
周邦道,〈严复传略:当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稿之一〉,《华学月刊》第74期(1978,台北)
周昌龙,〈严复自由观的三层意义〉,《汉学研究》13:1(1995,台北)
周振甫,〈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东方杂志》34:1(1937,台北)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上海:中华书局,1936)
官桂铨,〈严复世系简说〉,《文献》第4期(1989,台北)
房德邻,〈严复与西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1985,北京)
林安梧,〈个性自由与社会权限:以穆勒(J. S.Mill)「自由论」为中心的考察兼及于严复译「群己权界论」之对比省思〉,《思与言》27:1(1989,台北)
林保淳,〈天演宗哲学家严复: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幼狮月刊》第419期(1987,台北)
林保淳,〈严复与西学〉,《知识分子的良心:张季鸾、严复、连横》(台北:文讯杂志,1991)
林保淳,《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台北:幼狮,1988)
林国清、林萌依,《严复》(福建:福建教育,1989)
林启彦,〈五四时期严复的中西文化观〉,《汉学研究》4:2(1996,台北)
林启彦,〈论严复的保守思想:「政治讲义」的剖析〉,《香港浸会学院学报》第13期(1986,香港)
林博文、王家俭,〈关于严复的生年及其它〉,《中央日报》(1978.9.26,台北)。
林景渊,〈严复、福泽谕吉对于促进中、日近代化之比较〉,《共同学科期刊》第1期(1989,台北)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新华,1988)
林载爵,〈严复的终极关怀:新出土的严复〉,《当代》第37期(1989,台北)
林载爵,〈严复对自由的理解〉,《东海大学历史学报》第5期(1982,台中)
邵镜人,〈严复〉,《同光风云录》(台北:文海,1983)。
俞政,〈析严译《原富》按语中的富国策〉,《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1995,苏州)。
俞政,〈严译《原富》的社会反应〉,收入《「严复与中国近代化研讨会」会议论文》(福州:严复与中国近代化研讨会,1997)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
胡映芬,〈介绍《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华文化复兴月刊》7:12(1974,台北)
胡楚生,〈严几道「庄子评点」要义阐释〉,《中兴大学文史学报》第21期(1991,台中)
胡楚生,〈严几道对于庄子思想的批评〉《中国书目季刊》24:3(1990,台北)
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1905。收入《胡汉民先生文集(一)》(台北党史会,1978)
胡适,〈严复与林纾〉,收入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1986)第一集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
夏志清着、张汉良译,〈中国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幼狮月刊》42:4(1975,台北)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2)
夏敬观,〈严复传〉,《国史馆馆刊》1:2(1948,台北)
孙小着,〈从严译名著按语试探严复的改革思想〉,《近代史研究》5期(1994,台北)
徐元民,〈严复的体育思想〉,《体育学报》第18期(1994,台中)
徐立亭,《严复》(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
徐高阮,〈严复型的权威主义及其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周阳山等编,台北:时报文化,1980)
殷善培,〈启民智:严复的理想与悲情〉,《问学集》第1期(1990,北京)
耘农,〈严复晚年之政论〉,《新中国评论》13:2~3(1957,台北)
马克锋,〈严复与袁世凯〉,《福建论坛》,第6期,1994。
高大威,〈严复对老庄思想的诠释〉,《中国近代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严复》(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6)
高大威,《严复思想研究》(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2)
高拜石,〈严几道评传〉,《古春风楼琐记》(台北:台湾新生报,1962)
高惠群,乌传衮,《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外语教育,1992)
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编辑,《中国近代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严复》(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6)
崔运武,《严复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1993)
康有为着,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1990)
张士楚,〈严复的进化论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文集》(长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1983)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1963)
张立文编,《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1)
张立文编,《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89)
张志建,《严复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1995)
张志建、董志铁,〈试论严复对我国逻辑学研究的贡献〉,《中国逻辑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2)
张瑞德,〈严复对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介绍与曲解〉,《大陆杂志》57:4(1978,台北)
张瑛,〈严译《天演论》与中国近代文化〉,《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1985,贵阳)
张嘉森,〈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家学说及西洋哲学之变迁〉,收入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
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北:时报文化,1980)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1989)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台北:联经,1988)
张灏着,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南京:江苏人民,1993)
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北京:人民,1998)
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1989)卷八
连士升,〈严几道先生遗着序〉,《中国一周》565期(1961,台北)
郭正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晚清学会运动(1895-1911)-近代科学思潮社会冲击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1972,台北)
郭正昭,〈从演化论探析严复型危机感的意理结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台北)
郭正昭,〈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书评书目》14:56期(1977,台北)
郭正昭,〈达尔文主义与中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北:时报文化,1980)
郭正昭,〈严复〉,《中国历代思想家》(王寿南主编,台北:台湾商务,1978)第八册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郭良玉,《严复评传》(台北:兰台,1998)
郭湛波,《近代中国思想史》(香港:龙门,197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1984)
郭嵩焘着,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沈阳:辽宁人民,1994)
郭嵩焘着,杨坚点校,《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1984)
陈木杉,〈大陆学者对严复之评价〉,《共党问题研究》12:1(1986,台北)
陈越光、陈小雅,《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与道路》(台北:谷风,1987)
陈敬之,〈严复〉,《畅流》43卷10-11期(1971,台北市)
陈鹏翔主编,《翻译史‧翻译论》(台北:弘道文化,1975)
陈麒元,〈严又陵「评点老子」初探〉,《辅大中研所学刊》第3期(1994,台北)
陶菊隐,〈严几道与林琴南〉,《六君子传》,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续编》第八十辑(台北市:文海,1981)
章士钊(笔名秋桐),〈读严几道民约平议〉,《甲寅杂志》1:1(1914,北京)
章士钊,〈读严几道民约平议〉,《甲寅杂志》1:1(1914,北京)
章太炎,《章氏丛书》(台北:世界书局,1982)
章斗航,〈海军先贤严几道先生传〉,《中国海军》16:5(1974,高雄)
章开沅主编,易升运着,《西学东渐与自由意识》(湖南:湖南人民,1988)
曾克端,〈严几道先生──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的第一人〉,《大学生活》1:7(1955,香港)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1985)
曾纪泽,《曾纪泽日记》(长沙:岳麓,1998)
曾纪泽、李凤苞等,《使欧日记》(台北:黎明文化,1988)
汤志均编,〈严复(1853-1921)〉,《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篇》3卷,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二辑(台北市 : 文海,1976)
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22:21(1925,台北)
项退结,〈当代中国哲学述要:替中国打强心针的严复〉,《哲学与文化》7:9(1980,台北)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北京:人民,1989)
冯保善,《严复传》(北京:团结,1998)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郑州:中州古籍,1998)
黄大受,〈翻译大师严复〉,《传记文学》9卷4期(1966,台北)
黄玉芬,〈翻译前辈严复〉,《畅流》60:4(1979,台北)
黄克武,〈发明与想象的延伸:严复与西方的再思索〉,《思与言》36:1(1998,台北)
黄克武,〈严复研究的新趋向:记近年来三次有关严复的研讨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台北)
黄克武,〈严复晚年思想的一个侧面: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之会通〉,《思与言》34:3(1996,台北)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1998)
黄志辉,《我国近现代之交的中西文化论战》(广东:广东高等教育,1992)
黄见德,《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湖南:湖南教育,1998)
黄征,〈严复参与辛亥革命南北和议的补证〉,《南京大学学报》第3期(1980,南京)
黄保万,〈严复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特色〉,《福建学刊》第3期(1994,福州)
黄康显,〈严复所承受赫胥黎的变的观念:维新运动的原动力〉,《大陆杂志》66:6(1983,台北)
杨正典,《严复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7)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94)
翦伯赞主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台北:鼎文翻印,1973)
杨国荣,《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台北:五南,1995)
杨肃献,〈严复与近代中国思想界〉,《明道文艺》第42期(1979,台北)
杨儒宾、黄俊杰编,《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探索》(台北:正中,1996)
万尚庆,〈恩铭被刺不是严复辞职离皖的原因〉,《近代史研究》第3期(1993,北京)
叶文心,〈孤鹤从来不得眠〉,中国时报,1999.7.10,11版。
雷慧儿,〈富强之道:严复的威权政治理想与困境〉,《思与言》30:3(1992,台北)
福州市纪念严复诞辰140周年活动筹备组,《严复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专辑》(福州市纪念严复诞辰140周年活动筹备组,1994)
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编,《严复与中国近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
绪形康,〈严复之翻译论〉,《爱知大学文学论丛》,(丰桥 : 1989.7)
刘小枫、林立伟编,《经济伦理与近现代中国社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
刘富本,《严复的富强思想》(台北:文景,1977)
刘靖之主编,《翻译论集》(香港:三联,1981)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南昌: 百花洲文艺, 1994)
潘潮玄,〈严复与福州〉,《发展研究》第6期(1994,福州)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1964)
郑永福、田海林,〈《天演论》探微〉,《近代史研究》第3期(1985,北京)
郑师渠,〈严复与鲁索的《民约论》〉,《福建论坛》第2期(1995,福州)
郑康民,〈严复与黑格尔〉,《学人》23期(1957,台北中央日报社)
郑学稼,〈严侯官先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建设月刊》1卷12期(1935,上海)
郑学稼,〈严复先生之生平及其思想〉,《民主评论》5:22、24(1954,台北)
郑观应,《盛世危言》(台北:学术出版社影印,1965)
黎建球、邬昆如,〈严复〉,《中西两百位哲学家》(台北:东大,1978)。
黎难秋,《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3)
萧功秦,〈严复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思潮〉,《中国研究》2:3=15(1996,台北)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上海:三联,1999)
赖建诚,〈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汉学研究》7:2=14(1989,台北)
钱公博,《经济思想论集》(台北:学生,1973)
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台北:明伦,1972)
钱履周着,何桂春整理,〈严复年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1984,福州)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与文化》(台北:联经,1980)。
钱穆,《钱宾四生全集》(台北:联经,1998)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1984)
谢小芬,〈西学中译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中央月刊》23:9(1990,台北)
瞿立鹤,《清末西艺教育思潮》(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1)
瞿立鹤,《清末留学教育》(台北:三民,1973)
罗耀九,〈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学术月刊》(1985,上海)
谭慧生,〈林纾、严复、辜鸿铭〉,《民国伟人传记》(高雄:百成,1976)。
严秋尘,〈发现严几道先生寿言稿后的回忆〉,《人间世》27期(1960,上海)
严秋尘,〈严复〉,《民国文人》(台北:长河,1977)
严家理,〈严复先生及其家庭〉,《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福建:人民,1981)第5辑
严家理,〈严复与二林〉,《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福建:人民,1981)第5辑
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编,《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海峡文艺,1995)
西文部份
Abrams, M. H.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Fort Worth: Harcourt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Allinson, Robert E. e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 HongKong: Oxford UP, 1989.
Barthes, Rol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The Rustle ofLanguage . tran.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1984.
Boorman, Howard L. ed. 〈YEN FU〉,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Republican China Ⅲ.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Bowler, Peter J.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Chang, H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71.
Darwin, Charles. The Origin of Species. Middlesex: PenguinBooks, 1982.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83.
Fairbank, John 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Hardy, Alister. Darwin and the Spirit of Man. London: WilliamCollins Sons & Co Ltd, 1984.
Henderson, John B.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Cosm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4.
Hudson, William Hen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Herbert Spencer. New York: Haskell House, 1974.
Huxley, Thomas Henry. Evolution and Ethics. London: Macmillan,1893-94.
Huxley, Thomas Henry. Evolution and Ethics.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Kennedy, James G. Herbert Spencer.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1932.
Lai, Cheng chung. “Adam Smith and Yen Fu: Western Economics inChine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Vol.182. Fall, 1989.
Li, Qiang.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Righteousness: Yen Fu and Utilitarianism in Modern China,”Utilitas. 81, March 1996.
Macpherson, Hector.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and His Work.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imited, 1901.
Mill, John Stuart. Three Essays. Oxford,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75.
Mill, John Stuart. A System of Logic.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874.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 by Thomas Nugent. NewYork: Hafner Press, 1949.
Palmer, Richard E.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ell, J. D. Y. Herbert Spencer on Social Evolution. Chicago andLondon: Chicago UP, 1972.
Pusey, James R.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Harvard UP, 1983.
Scarre, Geoffrey. Logic and Real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JohnStuart Mill.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the Wes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1964.
Skorupski, Joh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il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of Nations. Indianapolis : Liberty Classics, 1981.
Smith, Richard J., and D. W. Y. Kwok, ed. Cosmology, Ontology,and Human Efficacy: Essays in Chinese Though. Honolulu: Universityof Hawaii Press, 1993.
Spencer, Herbert. First Principles. London: Watts, 1937.
Spencer, Herbert.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Indianapolis:Liberty Press, 1981.
Spencer, Herbert.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London: Longman,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5.
Spencer, Herbert.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D.Appleton and Company, 1906~07.
Spencer, Herbert. The Study of Sociology. Ann Arbor: Universityof Michigan Press, 1961.
Stanislav, Andresk, ed. Herbert Spencer: Structure, Function andEvolution. Great Britain: Nelson UP 1972.
Tillett, Alfred W. Spencer’s Synthetic Philosophy. London: P. S.King & Son, 1914.
Venn, John. The Principles of Empirical or Inductive Logic.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4.
Wang, Y. C. “The Influence of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on the‘San Min Chu I’”,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 34, 1965.
Wilbur, C. Martin. “Schwartz’s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 24, 1, 1964.
Wu, Chan-liang. "The Cosmo-ontological View of Becoming inAncient Chinese Taoism", Historical Inquiry.(台大历史学报) V.19,1996.
Xiao, Xiaosui. “China Encounters Darwinism: A Case ofIntercultural Rhetoric “,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81,Issue 1, Feb. 1995.
Yang, Dayong. “Yen Fu's Philosophy of Evolution and the Thoughtof Lao Zi and Zhuang Zi”, Chin Stud Phil. 241, Fall, 1992.
徐兆镛. ”Yen Fu and Lin Shu:Two Translators Who Helped ChangeChinese Thinking”, Sino-American Relations. 20:3、22:4, 1996.
赵世玮. ”Yen Fu and the Liberal Thought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36:2, 1995.
发表时间:1999.12
[1]各家所取于《天演论》者,未必符合其本旨,但莫不受其影响。有关天演学说对于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史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还并不充分。已有的研究可参看:JamesR.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1983);李泽厚,〈论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风云时代,1990);萧功秦,〈严复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思潮〉,《中国研究》2卷3期(1996,台北);杨国荣,《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台北:五南,1995),98-103;吴展良,〈梁漱溟的生生思想及其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1915-23)〉,及〈傅斯年学术观念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皆收于本论集中;郭正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晚清学会运动(1895-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1972,台北);利瓦伊武,《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湖南教育,1991),96-162。
[2] A. 主张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为了追求富强的首推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Mass.: Harvard UP,1964);史华兹「追求富强」的说法一出,学者普遍地采用它来诠释严复的《天演论》及其整体思想。例如:刘富本,《严复的富强思想》(台北:文景,1977);雷慧儿,〈富强之道:严复的威权政治理想与困境〉,《思与言》30:3(1992,台北);徐高阮,〈严复型的权威主义及其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周阳山等编,台北:时报文化,1980),140-42;林保淳,〈严复与西学〉,《知识分子的良心:张季鸾、严复、连横》(台北:文讯杂志,1991),96、98;钱公博,《经济思想论集》(台北:学生,1973),170。B.主张救亡图存说的包括: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1957),33-37;林载爵,〈严复对自由的理解〉,《东海大学历史学报》第5期(1982,台中),95-96;张志建,《严复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1995),29-31、89-96。小野川秀美着,林明德,黄福庆译,《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时报,1982),269-270;杨正典,《严复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7),26。C.主张严复翻译此书是为了变法维新的包括:黄康显,〈严复所承受赫胥黎的变的观念:维新运动的原动力〉,《大陆杂志》66:6(1983,台北),28-38;黄保万,〈严复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特色〉,《福建学刊》3期(1994,福州),74。D.以危机哲学来诠释严译《天演论》的首推:郭正昭,〈严复〉,《中国历代思想家》(王寿南主编,台北:台湾商务,1978)第八册,105-115;郭正昭,〈从演化论探析严复型危机感的意理结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台北),527-555;同时见于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湖南:湖南教育,1998),31。有相当一部份的学者同时主张两种以上的原因。
[3]上述的各种主义、思想及学术态度固然主要学自西方,却大多与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传统有其「亲合性」,所以容易在中国的土地上蔚为潮流。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相当成功地指出中西最高学理的许多相通之处,正可以说明其中的消息。同时因为他所要介绍的是最高学理,所以其影响才能深远。学界一般只注意到天演学说适合时代需要的一方面。这方面固然重要,却不足以充分说明此说在中国现代思想及学术史上的意义。
[4]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Hill and Wang, 1984),49-55.另外诠释学者亦主张作意(intention)不重要也无法确定,真正重要的是作品本身。(Richard E. Palmer,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69],246.)笔者则主张绝对客观的知识虽不可得,充分掌握作品并深入现有的相关材料,却仍然可以让我们对于作意达到相当程度的真切理解。而有关作品内涵的解读,固然可以有无穷多的面向,并且视读者而不同,却仍应以了解原书所传达的主要意旨与所企图完成的目标为依归。
[5] 参见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Oxford:Blackwell, 1983), 1-17, 95-97, 134-141; M. H. Abrams, Glossary ofLiterary Term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3), 120-121, 246-248, 273-275, 284-286.
[6] 以上系针对于R.Barthes所提出的部份观点加以反思。当代有关文本的研究,急欲完全脱离传统的「作品分析」而独立,所以非常强调两者的对立性。研究文本时,要将作者的一切与该书的外缘及影响置诸脑后。「文本分析」固然急欲独立,然而笔者则以为「作品分析」不妨开放心胸,兼取「文本分析」之长。(参见R.Barthes, The Rustle of Language, 50-55。)
[7]严复在《原富》的案语中说:「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严复集》,859。王栻主编,北京:中华,1986。)指出明道不但不与兴利、救世冲突,反而是后两者的必要基础。而就他自己的学习过程与教人的方法而言,则明显是以明道为先。
[8]严复,《天演论》(长沙:商务万有文库本,1939;台湾商务的人人文库本系景印此本而成;译自Thomas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London: Macmillan,1893-94]),自序全文,1-3。 案:1.万有文库本系根据商务严译名著丛刊第一种(上海: 商务,1931)重排,虽不尽为善本,然通行最广。严译《天演论》的版本甚多。其中通行最广者为各种商务本(商务于严译名著丛刊本之前另有排本,最早出版于1905年),其次为慎始基斋本(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1898),二者的差异很少,均为严复反复修订后的定本。另外有富文本(富文书局,1901),也是严复改定的善本,内容与商务本相当接近。然而其它的早期版本,例如手稿本(收藏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1896-97)与味经本(陕西: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1895),其内容与前述定本则有重大差异。本文所有引文的页码以商务万有文库本为准,以方便学者参照。其内容则本于商务万有文库本并曾参校商务严译名著丛刊本、富文本(收于林载爵等编,《严复合集》[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及慎始基斋本(收于王栻,《严复集》)。2.此序作于光绪丙申(1896)重九,并于次年有所删改。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天演论》手稿本(收于《严复合集》),其内容与商务本及慎始基斋本略有差异。本文所引则根据商务与慎始基斋本。
[9]文章的重点固然不能纯以篇幅论,然而篇幅自然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严复在序言中以绝大多数的篇幅讨论中国的学术走向问题,不能不说这是他的基本关切点。学者固然可以质疑他在接近结尾的地方以半行话点到「自强保种」之事,是否用了画龙点睛或让全篇结穴于此的笔法?然而我们细读其原文,便可知他虽然在接近结尾时提到「自强保种」之事,观其前后文气只是要人特别注意到赫胥黎的学说在这一方面的意义,却并无结穴于此之意。
[10]严复论「《易》本隐而之显」与「《春秋》推见至隐」一段,最容易引起现代学者的批评。然而我们如果从一种同情的眼光来看,则可见严复所言确有其理致。《易经》结构谨严、自太极阴阳以至于万事万物,用一以贯之的道理说明各类事物在不同时位中的种种变化。以简御繁,以一寓万,所以太史公所说的「《易》本隐而之显」,确实与西方的演绎法有一定的类似性。至于《春秋》的褒贬则于纷繁的史事当中立下普遍的规范。立法极严,丝毫不可假借,所谓推见至隐,故近于归纳。当然,这种说法也有其勉强之处。《易》学、《春秋》学中所表现的思维方式虽然确有合于演绎、归纳思维之处,然而演译、归纳的逻辑方法不真能代表《易经》与《春秋》作者的思维方式。
[11] 《严复集》,558-560。
[12]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1549。
[13]如其讨论时人著作时有云:「复近晤曾重伯,其议论大抵学穗卿,而傅会过之。渠有《重电合理》,一作,类谭复生之《仁学》,四五读不得头脑。渠欲复评点,复据实批驳,不留余地。中国学者,于科学绝未问津,而开口辄曰吾旧有之,一味傅会;此为一时风气,然其语近诬,诬则讨厌,我曹当引以为戒也。」(严复,〈与张元济书〉20封之13,《严复集》,550。)
[14] 《天演论》本论七又曰:「考道穷神之士」,有穷尽事理于事事物物之意。(《天演论》,论,16)
[15]序中只言《易》。有关严复爱重老庄思想这一点,详见本文对于「严译《天演论》的主要内涵」之讨论。
[16]严复,《群学肄言》(上海:文明译书局原刊,1903;台北:台湾商务新刊,1970),译余赘语,2-3。
[17]严复翻译《天演论》时,省略了许多复杂的论证,而有不充分重视科学精神与方法之嫌。请参见田默迪,〈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之研究与检讨:与赫胥黎原文之对照比较〉,《哲学与文化》第19、20期(1975,台北),4-18,49-58;田默迪,〈由严复《天演论》的翻译特色论科学精神的问题〉,《中国近代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严复》(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编辑;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117-126。
[18]参见本文第三节的讨论与注8。又案:严复一旦将案语独立出来后,所发挥的内容乃至方向,已大幅超过味经本于正文中所加入的部份。然而《天演论》一书案语的来源,却不得不追溯到严复大量引用古书以说明、参证、与比较西方与中国思想的原始企图。
[19] 《严复集》,1323。
[20]此段内容也保留于同年(1898)严复自己刊印的嗜奇精舍本中。(参见《严复集》,1323。)
[21] 《天演论》,例言,3。
[22] 《严复集》,1560。
[23] 《天演论》,吴序,1。
[24] 《天演论》,吴序,2。
[25] 《天演论》,吴序,2。
[26]余英时,〈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严复思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1999.7.11,台北),20-24。
[27] 《天演论》,吴序,2-3。
[28] 《天演论》,吴序,3。
[29] 《严复集》,1560。
[30] 《严复集》,521。
[31] 《严复集》,521。
[32]观察严复与郭嵩焘在英国时期的有关讨论,可知他当时对于中国的未来,尚未具有强烈的危亡意识。然而回国后,目睹国内落后而不知改革的情形,他的危机意识便日渐增强。认为中国如此因循,终将为外国所驱役。(参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449-450、511、562、647、664、696、846、885、1010;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1936],8。)然而他在洋务运动时期,依然努力从事于科举与矿务,又企图将斯宾塞立足于天演思想上的TheStudy ofSociology翻译成所谓《劝学篇》(日后译为《群学肄言》)。可见严复在中年之前的危亡意识并不非常强烈。所走的反而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路径,对于学术与仕途等有较高的兴趣。至于他所从事的矿务,固然表现出他特殊的背景,却也不出自强运动的范围。
[33] 参见吴展良,〈严复早期的求道之旅〉(收入本论集),38-42。
[34]严复似乎到1901年仍称此书为《劝学篇》。见:《严复集》,507-508,及欧阳哲生,《严复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1994),68。
[35] 《群学肄言》,译余赘语,2-3。
[36] 〈救亡决论〉,《严复集》,45-46;又参见《天演论》,论,1-3。
[37]1.西方人格致的方法与内容与中国传统所谓的格致颇为不同,严复自然深知。此处他所谓的格致,主要是科学地「追求真理」的意思,然而也继承了朱子「格物穷理」的精神。(〈侯官严先生年谱〉于乙酉(1885)年下注「府君自由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竺旧,鄙夷新知,余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严复集》,1547。]此所以严复深为推崇朱子格物之学,并批评陆王学。参见〈原强〉一文对陆王学的严厉批评。[《严复集》,43-47。])至于两者的不同处,则严复并不深论。这种宁取其同的作法,可以见出他企图融合西学入中国传统的心理。2. 斯宾塞的作品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
[38]然而此不同点不是史华兹先生所谓:严复基本上是在一种追求富强的目标下来探讨西方学问。参见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39] 参见本论集,〈严复早期的求道之旅〉,37-39。《严复集》,360。
[40] 《严复集》,678。
[41]参见叶文心,〈孤鹤从来不得眠〉,中国时报,1999.7.10,11版。叶教授系严复的外孙女,该文虽未针对《天演论》而言,却通论严复一生,故特为引出。
[42]当时并没有多元并存的观念。事实上,所谓多元并存,本身也必须先证明其所涉及的多元可以并存。现代的多元并存主义,其实是在「自由主义」与「法治」可以有效运行的前提下进行,并非完全没有前提或其所依存的社会体系。
[43]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risis (Berkeley: Uni.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5-10,对于晚清的思想与心理危机有深入的分析。张先生以寻求「秩序与意义」为晚清学人面对这些时代危机的反应一说,确实是深具卓识。然而追求「秩序与意义」虽具有对应危机的普遍性,却似乎未能表现出中国固有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的特殊性。本文则企图指出追求致广大尽精微、格致以至于治平的一以贯之大道,才更能反映晚清学人的学术性格、思维方式与其整体的追求。
[4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严复的思想具有「危机哲学」的成分。然而却不是为了救亡图存、追求富强而产生的危机哲学,也不是因为危机所以便采取了达尔文主义。请参见本文有关郭正昭先生「危机哲学」说的讨论,46-51。
[45] 张灏先生在其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risis一书中,也指出Levenson式的「文化认同」说,对于解释晚清思想的功能有限。(Hao Chang, ChineseIntellectuals in Crisis, 9, 65.)
[46] 《严复集》,361。
[47]参见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周阳山等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北:时报文化,1980),30-31。
[48]例如康有为的「大同说」、「公羊三世进化观」、「天人观」;谭嗣同的「仁学」;章太炎之于荀卿韩非、道家、魏晋之学与佛学;刘师培之于道家、原始儒家、晚汉魏晋思想;梁启超思想多变,然而他三十之前在大同说、公羊学、阳明学、中国经史、经世及义理之学所打下的基础,对他仍有终身的影响。
[49]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商务,1995),386、399-400、419、424、433-34。两种统计均包含严复。
[50]此说亦可参见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析论〉,《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87-110。
[51] 《严复集》,1。
[52]至于公羊三世进化的说法,虽然对于天演论的流布有所帮助,却并非严复接受天演论的原因。参见:郭正昭,〈达尔文主义与中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680。
[53] 参见吴展良,〈严复早期的求道之旅〉,本论集44-56。
[54] 《严复集》,1-5、12-14、31-32、35、36-37。
[55] 《严复集》,1-5。
[56] 《严复集》,7。
[57] 〈喻术第三〉,《群学肄言》,40-60。
[58] 《严复集》,38-40。
[59] 《严复集》,40-54。
[60] 〈救亡决论〉,《严复集》,45-46。并参见同篇,48-52。
[61] 〈救亡决论〉,《严复集》,46。
[62] 〈与梁启超书〉,《严复集》,514。
[63]所以他在这些文章中一在强调必须标本兼治。然而他所说的本,不仅需要长期培养,而且需要甚深学养才能明白。当时国人却对此可谓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始终无法真正接受他的意思。参见:《严复集》,14、30-32、36。
[64] 请参看李泽厚,〈论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65] 《天演论》,译例言,1。
[66]《天演论》在严复的译作中是一个特例,不能用此书来范围其它的译作。然而诸如企图明道、融通西方诸家、融入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传统与现实加以反思等性质,在严复其它的译作中,也依然存在。然而因为这些目标而扭曲改易原作的情形,要较本书轻微得多。
[67]王蘧常,《严几道年谱》,9;《群学肄言》译余赘语,2;《天演论》,导言,31、39。
[68] 《天演论》,论,1。
[69]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London:Pilot Press, 1947), 104.
[70] 《天演论》,导言,35。
[71]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91.
[72] 《天演论》,导言,5。
[73] 《天演论》,导言,4-5。
[74]此处所谓的「总结晶」是指此书中所表现的思想体系,乃严复在此之前长期研究所得之总结。并不表示严复的思想从此不再改变或进步。事实上严复的思想体系,随着他翻译事业的进展与年龄的增长,仍不断扩充改进、日益完整。然而其核心的观念,包括严复对于名学、群学、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学理的重视与基本看法,却已成形于此时。严复后期思想最重要的变化或许是对于功利与自由竞争主义的批判,然而即使如此,他仍然笃信天演的基本原理,并自号「天演宗哲学家」。(参见《天演论》自序1-2,译例1-2,导言32-33、34、45、47-48,《严复集》,692,与下文之相关讨论。)
[75] 《严复集》,525。
[76]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98-104.
[77]有的学者认为达尔文原书的生物学名词太多,学理太专门而难以翻译,所以严复没翻译该书。这大抵是不了解严复的志业所产生的误解。(郭正昭,〈达尔文主义与中国〉,677。)
[78] 《严复集》,507、1327。
[79] 《严复集》,1323。
[80]前人如郭正昭也曾经指出严复所从事的是一种融通西方与中国思想文化的伟大创造工作,然而其立论的出发点与诠释的角度与本文颇为不同。请参见本节第三部份的有关讨论。
[81] 《天演论》,导言,32-33。
[82] 《天演论》,导言,34。
[83] 《天演论》,论,14-26。
[84] 《天演论》,论,24-25。
[85] 《天演论》,论,27。
[86] 《天演论》,论,28-29。
[87]严复所引进的新世界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究竟意义为何,仍留有许多讨论的空间。但学界对于严复引进了这套现代世界观的重要性,已有初步共识。请参见李泽厚,〈论严复〉;杨正典,《严复评传》,140-205。
[88]关于中国人的思想性格中所特具的「和合性」,请参看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与文化》(台北:联经,1980)。
[89] Peter J. Bowler, Evolution (Berkeley: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55-164.
[90] 斯宾塞自己特别强调这一点。参见:Herbert Spencer, Prefaceto the Fourth Edition, First Principles (New York: A. L. BurtCompany, [Pref. 1880]) , iii-iv.
[91] James G. Kennedy, Herbert Spencer(Boston: Twayne, 1978), 35-61.
[92] Peter J. Bowler, Evolution, 76-84.
[93] Kennedy, Herbert Spencer, 19, 70-71, 79;Bowler, Evolution, 239.
[94] Kennedy, Herbert Spencer, 70-82.
[95] Kennedy, Herbert Spencer, 82-86.
[96]斯宾塞对于拉马克亦有所批评,然而这并不害于他基本上仍然是个拉马克主义者。参见Kennedy,Herbert Spencer, 19, 70, 77, 79.
[97] 《天演论》,导言,36。
[98] 《天演论》,导言,36-37。
[99] 《天演论》,导言,37-39。
[100] 《天演论》,导言、34,37-39。
[101]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84-98.
[102]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103.
[103] 《天演论》,导言,32、34、36-37。
[104] Kennedy, Herbert Spencer, 79-83.
[105]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写到斯宾塞之于达尔文,「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严复集》,6。)可见他认为二人学说基本上是一贯的。而在〈原强〉修订稿中,他进一步指出斯宾塞之说成于达尔文出书之前,所以将此句修正为「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却依然未曾分析二人学说的差异。(《严复集》,16。)另外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严复常用二人的学说互相参证。(《严复集》,5-7、9、13、15-17;《天演论》,导言,3-4)却均未曾分析其中差异。换言之,严复虽然认识到两人所言似乎各有偏重,却一心以二人所说互相发明,阐扬天演学说。对于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始终未曾觉察。严复称拉马克为「兰麻客」,对于达尔文与拉马克之间的差异,也未曾析论。(《天演论》,导言,3-4)
[106] 《严复集》,16、309。
[107] 《严复集》,309。
[108] 斯宾塞也强调naturalselection的重要,却将其纳入适应说与普遍演化论的体系。而在该体系中,此说仅具有第二义的价值。同时因为斯宾塞一直企图用「最适者生存」说解释「天择」说,而达尔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这种解释。(Kennedy,Herbert Spencer, 78-79)严复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所以未曾深究其间的差异。(《严复集》,309)
[109] 《天演论》,导言,3。
[110] 《天演论》,导言,37。
[111] 《天演论》,导言,15。
[112] 《天演论》,导言,28-34。
[113] 《天演论》,导言,39-45。
[114] 《天演论》,导言,32、39-45。
[115] 参见郭正昭,〈达尔文主义与中国〉,678-679。
[116]在这个意义上,一般人认为斯宾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不是偶然的。从其名言「最适者生存」而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即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族群与每一个个人都必须面对不断的竞争,而适应不良者,便自然淘汰。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成为一种严酷的主义,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也成为一种自然的规律。强者获得各式各样的资源,弱者或者奋力适应,或者遭到欺凌淘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许多西方人受此影响,认为西方人宰制非西方世界,白种人宰制其它肤色的民族是合乎自然法则的。
[117] 《天演论》,吴序,1。
[118] 《天演论》,导言,32。
[119] 《天演论》,导言,34。
[120] 《天演论》,导言,34。
[121]所谓「将锡彭塞之说未行,而达尔文之理先信。」(《严复集》,9)。同时可参见《严复集》,5-7、9、13、15-17。
[122] 《天演论》,序言,2-3。
[123] Kennedy, Herbert Spencer, 35-45; Herbert Spencer, FirstPrinciples, 199-249, 281-288, 394.
[124]参见:钱穆,〈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1998),第18册;钱穆,《庄老通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7册。
[125]严复着,《侯官严氏评点庄子》(台北:海军总部,1964),〈齐物论〉人籁地籁天籁一段中「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一句之眉批。
[126] 请参见:吴展良,”The Cosmo-ontological View of Becoming in AncientChinese Taoism,” 《台大历史学报》第十九期(1996,台北)。
[127] 参见James R.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60-61。极少数批评的意见,大抵来自宗教界。例如台湾的思想家李春生对演化论曾大肆批评,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信仰基督教。参见:李春生,《天演论书后》(福州:美华,1907)。
[128]郭正昭先生分析达尔文主义为何席卷现代中国时,举出不少重要的原因,却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参见:郭正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晚清学会运动(1895-1911)〉,566-571;郭正昭,〈达尔文主义与中国〉,680;郭正昭,〈严复〉,110。
[129] 《严复集》,520-521。
[130] 《天演论》,论一,1。
[131] 严复论《大学》,颇推重朱子的格物说,而不喜阳明。参见《严复集》,29、45-46。
[132] 《天演论》,论,1-3。
[133]《天演论》味经本,《严复合集》,34。通行本将「复以函将然未然之生机」一句改为「复以函生机于无穷」。《天演论》,论,2。
[134] 《严复合集》,34。
[135] 《严复合集》,35。
[136] 《严复合集》,35。
[137]严复对于佛学中所蕴含的深邃哲理非常有兴趣,然而他在此时仍然而是个自然主义者,并不相信灵魂转世与万法唯心的说法。因此他基本上仍然用道、儒、天演、与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诠释佛学。(《天演论》,论,14-28。)
[138] 《天演论》,导言,15;《天演论》,论,47-48。
[139] 《天演论》手稿本,《严复集》,1471-73;并参见《天演论》,论,47-48。
[140] 《天演论》,导言,15;自序,3。
[141]《天演论》,导言,43-45。严复说:「去其所傅者,最为有国者所难能。能则其国无不强,其群无不进者。此质家亲亲,必不能也。文家尊尊,亦不能也。惟尚贤课名实者能之。」《天演论》,45。
[142] 《严复集》,1077。
[143] 《严复集》,1559。
[144]融通中西学术与思想,兼取中西文化之长的工作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与应当如何进行的问题,绝非任何个人所能回答。在历史上这一类的问题通常需要一整个时代,至少数百年的时间,才能有初步的结论。严复虽然提出许多非常精彩的说法,却仍然有不少地方可以批评或有待研究。本文主旨在于阐述严复所企图处理的问题、所采取的途径及其主要的说法,并不能真正处理评价的问题。然而对于严复的用心、努力与「工作质量」,不能不生出赞叹之情。
[145]本文以建立新诠释为其主要目标,对于前人说法的得失,原本不拟加以论列。然而本文的基本论点与郭正昭先生的部份说法有其表面的类似性,有必要在此加以澄清,兼以回答本文的一位评审人所提出的质疑。
[146] 郭正昭,〈达尔文主义与中国〉,684。
[147] 郭正昭,〈严复〉,《中国历代思想家》,114。
[148] 郭正昭,〈严复〉,《中国历代思想家》,114-15。
[149]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98, 111.
[150] 《天演论》,47-48;《天演论》手稿本,《严复集》,1471-73。
[151] 请参见本论集,〈严复早期的求道之旅〉,17-18。
[152] 郭正昭,〈严复〉,《中国历代思想家》,115。
[153]郭正昭对「达尔文主义」之作为危机哲学并未加以论证,却立刻引史宾格勒的学说,作为「达尔文主义」可以视为危机哲学的左证。史宾格勒相信文化同生物体一般有其生老病死,并认为欧洲文化已经老化而接近死亡。然而这属于他个人独特的说法,与达尔文与斯宾塞的进化论相差甚远。达尔文与斯宾塞的书出版于维多利亚的盛世,史宾格勒的书出版于一战结束之时的悲观情绪之中,两者的内容与时代,都有巨大的差异。(郭正昭,〈严复〉,108-111。)
[154] 郭正昭,〈严复〉,110-111。
[155] 《天演论》,导言,11。
[156] 《天演论》,导言,14。
[157] 《天演论》,导言,20。
[158] 《天演论》,论,41。
[159] 同前注。严复文中只说「变质尚文」之民有如是的缺点,然而其言下所指,昭然若揭。
[160] 《天演论》,论,42。
[161] 《天演论》,导言, 22。
[162] 《天演论》,导言,23-24。
[163] 《天演论》,导言,23。
[164] 《天演论》,导言,31。
[165] 《天演论》,导言,47。
[166] 《天演论》,论,47。
[167] 《天演论》,论,11。
[168] 《天演论》,导言,44。
[169] 《天演论》,导言,45。

[170]本书在晚清之所以风行的原因非常复杂,无法在本文中仔细讨论。大体而言,提出救亡保种的呼吁并满足变法与追求富强的需要,是本书之所以风行的主要显性原因。符合传统以儒道两家为中心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而满足在危机时代建立一以贯之的新思想体系之求道要求,是本书之所以风行的主要深层原因。子学的复兴、新文体的需要、理性主义与存疑论的文化背景、朴学实证的遗风与公羊学的兴起等因素,则是本书之所以风行的其它较为隐性或所谓背景因素。(此处所谓隐性因素,指大多数读者不会自觉的因素。有关理性主义的文化背景、朴学实证的遗风与公羊学的兴起等因素,请参考郭正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晚清学会运动(1895-1911)〉。郭先生所说的理性主义与存疑论,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儒道两家思维方式的部分特质。)至于时人对于社会与儒家传统的不满、新学术与思想本身的吸引力、科学的号召等因素,也是本书所以风行的重要原因。其性质则似乎在隐显之间,因读者而有所不同,难以正确估量。
[171]一本书风行的原因往往相当复杂,其中有部份与原书的作意与内涵关系密切,但也有部份几乎无关乎或严重改变了原书的作意与内涵。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严译《天演论》一书的作意,多偏从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与促进变法等观点加以诠释,其实是专从本书之所以成为流行思潮的「主要显性因素」立论。这种方法既难以真正掌握到严复本人的作意与本书的内涵,也多半未能深入探索本书之所以风行的诸多隐性因素(请参看前注)。一般提倡这个观点的学者,最常引用的便是胡适先生的一番话:「《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中国屡次战败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1986],第一集,53-55。)我们细读这段话便会发现这里只说明了中学生与一般人的第一反应,这种反应的确是《天演论》一书之所以风行的首要原因,然而并不等于严复自己的作意与本书的基本内涵。胡适自己后来读书渐多,便了解到「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的贡献」,并终身服膺赫胥黎的思想,然而这并不是他作中学生时便懂得的。换言之,读者对这本书的理解与其所以重视这本书的原因,与个人的学力、见识与时代大环境有关。中国当时所遭遇到的首要现实问题,确实是救亡图存的挑战,一般人既无暇也无力于从事高深的学问,对于《天演论》的解读自然偏从救亡保种这一方面入手。然而这并不等于本书的作意与其基本内涵。
[172] 《群学肄言》全书均致力于阐明此义。
[173]《天演论》最后一章接近结尾时说:「居今之日,藉真学实理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惟去畏难苟安之心,而勿以宴安偷乐为的者,乃能得耳。」(《天演论》,论,50。)此句不见于原文,是为严复的「夫子自道」。
[174] 《严复集》,565、631-633、648、684。
[1](手稿本作「外导」)
[2](手稿本作「大法」)
[3](手稿本作自「在在见极」以下作:「而吾《易》之所著,则往往先之。不肖于《易》至浅,且尝知傅会者学术之大禁,尤不愿躬蹈之以欺世也。」)
[4](呜呼!古人之作为是说者,岂偶然哉!夫以不肖浅学,而其所窥及者尚如此已,则因彼悟此之事将无穷也。)
[5]再考
[6]会 卑
[7](水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