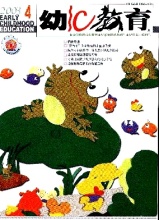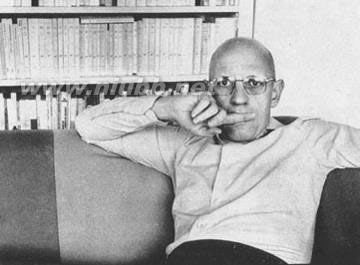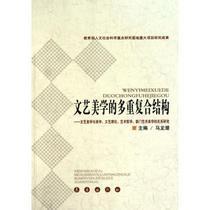认知语言学(cognitivelinguistics)是一门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1]其基本观念是认为语言和语法是不自足的,力图通过认知和功能来解释语言现象,有时还试图通过语言的历时发展来解释共时现象。有人认为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认知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认知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是由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组成的交叉学科,从多个角度探索思维的奥秘。也有人认为认知语言学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当代语言学的一个学派,属于广义的功能主义语言学。
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
(一)认知语言学兴起的过程
虽然认知语言学真正的历史只有约三十年,但作为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言理论的反动,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心理学、认知科学对认知的早期研究,其认知结构完形的组织原则来源于格式塔心理学,其主客观互动的信念来自皮亚杰的心理发展的相互作用论,不过一直处于酝酿期。
认知语言学的诞生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三部认知语言学专著的出版:约翰逊(M. Johnson)《心中之身》(1987)、雷可夫(G. Lakoff)《女人,火,危险事物——范畴揭示了思维的什么奥秘》(1987)和兰盖克(R. Langacker)《认知语法基础》(1987);二是1989年春,在德国的杜伊斯堡(Duisbury)举行的认知语言学专题讨论会。会后,出版了《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 Linguistics),并成立了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ICLA: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Association),还出版了认知语言学研究(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系列丛书。此后,《语用学与认知》杂志于1993年由约翰•本杰明斯出版公司发行。[2]20世纪90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在欧美语言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认知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兰盖克、雷可夫、杰肯道夫(Jackendoff)、泰勒(Taylor)、塔尔米(Talmy)等。
(二)认知语言学兴起的原因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语言学流派资料]认知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94345t016986ec3914b69c98.jpg)
首先,起因于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批评。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中期,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作为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直雄霸美国语言学。美国描写语言学专注于语言形式的描写,忽视对意义的研究,属于形式主义语言学。20世纪50年代中期,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继承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形式主义传统,并把形式主义发展到极至。转换生成语言学极力强调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要求对语言寻求“内部的解释”,并尽可能形式化。然而物极必反,乔姆斯基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暴露出许多问题,引来许多学者的批评,强调对语言意义、认知和功能的研究。
其次,语言学史上,一直就有重视意义和功能的传统。古代的修辞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使用功能的学问。结构主义学派之一的布拉格功能学派既重视语言的结构,又重视语言的功能。我国古代更是注重意义的研究,结合意义和文化来研究语言是汉语语言学的传统,正是由于国内语言学的这种学术传统,认知语言学引入国内后便风靡一时,而在国际上影响甚大的形式语言学在国内却一直没能成为统治中国语言学的霸主。
再次,20世纪下半叶以来,涌现出很多新的语言学科或交叉学科(外部语言学),如语用学、语言哲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等。其中大多研究兴趣在语义、功能、言语、篇章上,自觉不自觉地否定了语言的自足性,积极从语言系统的外部来解释语言现象,形成了功能主义的新潮流。
最后,认知语言学兴起的直接原因是以雷可夫、麦考莱为代表的生成语义学的兴起以及语用学的发展。[3]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认为大脑有一种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认为语言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语言能力及其深层结构,以此揭示习得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还认为自然语言的句法是“自足的”,不受语义因素的影响,雷可夫、麦考莱在语义问题上率先对生成语法发难,提出语义是语言系统的核心和基础,语义具有生成性,与乔姆斯基分道扬镳,后来走上认知语言学的道路。语用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认为语义研究必须结合语言的使用者和具体的语境。正是因为语用学注重对意义的推导,而意义与人的认知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语用学研究最终也走上了认知研究的道路。
二、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
形式与功能是语言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研究语言的形式和功能是语言学的两大任务,当代语言学中的各种流派大体可以归入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大阵营,认知语言学是功能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形式语言学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形式化的原则和规则系统,从语言结构内部来解释语言现象;认知语言学理论主要是通过心理、认知分析的手段,从语言外部来解释语言现象。认知语言学在语言观上与形式语言学有较大的区别,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语言能力与认知能力相关
认知语言学认为,自然语言既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又是认知活动的工具,自然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是人类一般认知活动的结果和反映。人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能力,而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紧密相关,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能力跟一般认知能力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语言能力的发展跟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例如,一个女子长得漂亮,人们常说“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而不会说“她有一双漂亮的手”或“她有一个漂亮的后背”,这是因为我们认识一个人的长相总是先观察他的脸部而不是别的部位。可见,“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这样的“转喻”说法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跟人的认知方式密切相关。[4]
(二)句法不自足
在形式语言学看来,句法是自足的(autonomous),是语法和语言的核心,是体现人类语言能力的最重要的方面。认知语言学却认为,句法作为语言结构的一部分不是自足的,句法跟语言的词汇部分、语义部分和语用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并没有明确的界线。认知语言学还认为,形式语言学把句法独立出来甚至作为核心自足系统,再分成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等不同的部分,完全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例如“四级还没有通过呢,就别提六级了”,这个句子中的副词“还”具有语用意义,是在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这个“还”字句表明,句法处理离不开“还”字的语用意义。可见,在表达和理解语句时,句法、语义、语用三者并没有明确的分界,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三者交织在一起。[5]从词法到句法到语义再到语用,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认知语言学并不把语言现象区分为音位、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层次,而是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
正是因为形式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在句法地位认识上的不同,导致它们在对待形式化的态度上也不一样。形式语言学认为句法是自足的,力求用数理逻辑对句法及其生成过程进行形式化的描写;而认知语言学认为句法是不自足的,因为句法涉及很多语用因素和认知因素,这些因素是难以形式化的。
(三)语言范畴是非离散范畴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的各种范畴都是非离散的,边界是不明确的。形式语言学和传统语言学持一种离散范畴观,认为每个范畴有自己的特定内在特征,符合某些特定内在特征的就成为某一范畴的成员,反之则不然,并且特定内在特征为范畴所有成员共有,因此范畴内部各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认知语言学则认为语言范畴大多是“典型范畴”(prototype-based category)而不是离散范畴。以“鸟”范畴为例。“鸟”包括“生蛋”、“有喙”、“有双翼和双腿”、“有羽毛”等十多种属性,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具有这些属性。鸟范畴内各成员的典型性不一样,各成员的地位也不平等,有的是范畴的典型成员,有的是非典型成员。例如,知更鸟、麻雀、燕子、喜鹊等是“鸟”这个范畴的典型成员,鸵鸟和企鹅则是这个范畴的非典型成员,“鸟”因此是个典型范畴。这种根据与典型事例类比而得出的范畴就是典型范畴。这种理论有以下假定:第一,实体是根据它们的属性来加以范畴化的,但这些属性并不是离散范畴理论中的那种两分的理论,而经常是个连续的过程;第二,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不固定的;第三,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在说话人的心目中地位并不相等,有较好的样本与较差的样本之分,即成员资格有等级之分,较好的样本是这一范畴的典型成员,较差的样本是这一范畴的非典型成员。[6]
汉语的词类就是一种典型范畴,要想找出为某个词类所有而为其他词类所无的语法特征,实际上很难做到。认知语言学认为,词类是人们根据词与词之间在分布上的相似性而聚集成类的。属于同一词类的词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别,典型成员是一类词的原型,是非典型成员归类时的参照标准。以名词为例,如果从语义范畴上看,最典型的名词是“可数的具体的物件”,由此扩展到“不可数的抽象的非物件”,如“爱情”、“信仰”等;如果从句法功能上看,典型名词经常做典型主语(施事主语)和典型宾语(受事宾语、结果宾语),还能做定语直接修饰名词;一般不能做状语和补语,一般不受副词修饰;只有一小部分名词可以做谓语,但不能做典型的谓语。这就是名词的典型特征,说某个词是名词或者不是名词,最多说这个词在多大程度上像是典型的名词。
三、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内容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较广,涉及象似性、语法化、隐喻和转喻、主观性和主观化、意象图式和认知模式、典型范畴和基本层次范畴等内容,这里主要讲述象似性、语法化、隐喻和转喻。
(一)象似性
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认知语言学则认为语言符号及其组合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认知的制约,具有象似性(iconicity)。象似性指人类语言的结构与人类所认识到的世界的结构恰好对应。象似包括两种类型:肖像象似和图式象似。肖像象似(imagic iconicity)指肖像与所指事物之间简单的、感官的或模仿性的象似,如拟音词的声音与所拟的声音之间具有象似性,独体的象形汉字与所指事物的整体轮廓象似。图式象似(diagrammatic iconicity)指图式自身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与所表现对象各个部分之间关系性的或结构性的象似。图式的每一构成成分与所指之间也许没有象似性,但是图式中各构成成分间的关系却与这些成分所指间的关系具有象似性,如地图、建筑物平面图、线路图、语言结构等。在语言结构中,成分象似和关系象似对应于肖像象似和图式象似。成分象似对应于肖像象似,指各种句法成分与各种概念相对应;关系象似对应于图式象似,指句法关系与经验结构的成分之间的关系相对应。就关系象似而言,主要原则有三:距离象似原则;顺序象似原则;数量象似原则。[7]
1. 距离象似原则
距离象似原则指语言单位的距离象似于概念之间的距离,即在功能、概念以及认知方面关系越近的概念,在语表上就靠得越近;联系越不紧密的概念就分得越开。比如“小张不认为他明天以前会离去”比“小张认为他明天以前不会离去”否定程度较弱,因为前一句中的否定成分“不”离“会离去”较远。
多项定语的语序体现了距离象似原则。以汉语为例,当多个不带“的”的定语修饰一个中心语时,一般的排列顺序是:领属性的名词或代词——数量词——形容词——表性质的名词,例如“一双白棉袜”、“一件黑大衣”等。这种排列顺序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语表距离取决于它们所代表的概念之间的距离,越是表现事物本质属性的定语就越靠近中心语,相反,那些表示事物临时的、非本质属性的定语则离中心语较远。
语言中的领属结构也体现了距离象似原则。领属关系反映的是领属者和领属物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可让渡”和“不可让渡”两种,它们在不少语言里都有形式上的区别。汉语表领属关系的定中短语具有这一鲜明特征。例如:“他的爸爸”“你的哥哥”可以说成“他爸爸”“你哥哥”,但“他的书包”“你的水壶”却不能说成“他书包”“你水壶”。这是因为“爸爸”“哥哥”和“书包”“水壶”比起来,不可让渡的程度更高一些,即“爸爸”“哥哥”所表示的概念与领属者的距离较“书包”“水壶”要近,所以前者在语言形式上可以不用“的”,这样语表距离更近、更紧密。
又如英语中限制性定语从句与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差异也是距离象似性的表现。限制性定语从句与先行词靠得近,而且在同一语调组内,因为它们在概念意义上较近。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与先行词之间用逗号隔开,而且形成自己的语调,语表距离相对较远,因为它们在概念意义上不很紧密。
2. 顺序象似原则
顺序象似原则指语言单位的顺序象似于实际状态或事件的先后顺序。时间概念是人类认知系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语言符号的排列顺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概念的先后顺序,恺撒的名言“veni, vidi, vici”(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例如“我去北京坐飞机”与“我坐飞机去北京”就是不同动作次序在句法形式上的直接投射,前者是先去再坐,后者是先坐再去。
汉语复合句中的因果关系和条件关系复句,一般是以原因和条件在前,结果在后。这正好符合认知世界的先因后果的次序。当然,汉语中也有原因和条件在后的句子,但在现代汉语中,这些例外一般都有形式标志。复合句中的顺承关系也体现了顺序象似性原则,这类复句没有主从关系,但有着严格的先后相继的关系,其显著特点是循序渐进,依次顺延,所以也称为“连贯式”,典型标志是“就、才、然后、于是”等关联词语。这种复句反映了客观世界、认知和语言的一致性。
3. 数量象似原则
数量象似原则指语言单位的数量象似于所表概念的量和复杂程度。语言单位的数量与所表示概念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成正比,即语言倾向于用更多的形式来表达更多的概念;语言单位的数量与可预测度成反比,在语言交际中,对于那些量大的信息,说话人觉得重要的信息,对听话者较难预测、理解的信息,想间接表达的信息,表达它们的句法成分也相应增多,句法结构也相对复杂。
例如英语中复数形式一般是在单数形式的基础上加复数标记-s或其他形式形成的,复数比单数形式长,所表达的概念量也就大。英语中形容词、副词的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所指的概念程度渐升,语言形式也渐多,从零词尾,到-er(两个字母表示比较),再到-est(三个字母表示最高级)。又如下面两个例子:
(1)a.This guy is getting on my nerves.
b.This impertinent egghead is getting on my nerves.
(2)a. Onthe Brighten train from Victoria, I met her.
b.On the Brighten train from Victoria, I met this fairhaired, fragileand beautiful creature.
这两个例子中b组不仅信息量大,而且也突出了主语(1b)和宾语(2b)在概念上的重要性和不可预测性。[8]
(二)语法化
1. 语法化的定义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即实词虚化。实词虚化这种现象中国学者在13世纪就提出来了,元朝的周伯琦在《六书正伪》中说:“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是元末卢以纬《助语辞》,清代袁仁林的《虚字说》则是我国传统语文学研究实词虚化的专著。如汉语“把”、“被”、“从”等原来都是有实义的动词,现已虚化为介词。实词虚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虚化有程度的差别,实词变为虚词是虚化,虚词变为更虚的成分(如词缀和屈折形态)也是虚化。例如动词“在”变为介词“在”是虚化;从表示地点的介词到表示时间、范围、性质、原因等的介词,这种变化则是由虚变得更虚。语法化研究的最大特色是打破共时和历时的界限,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语法系统的形成过程,解答人类语言的语法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人类语言的语法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构造的。
2. 语法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语法化主要研究词汇的语法化、短语的词汇化、语用法的语法化以及篇章的语法化等内容。
词汇的语法化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实义向虚义的变化;二是不太虚向更虚义变化。实义向虚义的变化一般是指名、动、形三类实词虚化成介词、动态助词等意义比较虚的词,例如近代汉语动态助词“将”、“着”等是由动词演变而来。不太虚向更虚义变化指词汇由助动词等较虚的成分向副词、助词等更虚的成分演变,例如表“可、能、会”的助动词“敢”虚化为反话副词“敢”等。
短语的词汇化是指一个短语或其他句法单位演变成一个稳固词汇单位的过程。“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说的就是有些词汇成分来自早期的句法结构。例如“恨不得”本是一个短语,在古代汉语中结构可以切分为(以S为陈述对象):(S)恨|(S)不‖得,在这里,“得”是实义动词,表示获得,后面带宾语,“不”否定“得”字短语,然后,“不”和“得”字短语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句法单位再接在“恨”的后面。在一个合适的语境,情况可能发生某种变化,当“恨不得”由表示现实心境重新分析为未来事实,用来表示某种主观愿望时,这时“恨不得”就由短语“恨|不‖得VP”词汇化为一个固定词汇单位“恨不得|VP”了。[9]
语用法的语法化包括两个意思。一是用语用原则来解释某些语法结构的差异现象,例如以下两个英文例子:
(3)a.Why didn’t youread in bed?(提问/建议)
b.Why not read in bed?(建议)
a的直接意图是“提问”,其间接意图是“建议”,但b虽然也是问句的形式却只表示“建议”。这是因为人们出于礼貌或委婉的考虑,在建议别人做某事之前最好先问一问对方没有这么做的原因,例如要建议别人躺着看书,最好先问问他没有躺着看书的原因,于是问句a就经常有了“建议”这一间接意图。这样的语用法普遍使用和反复使用的结果就逐渐固定下来,听者听到a这样的问话后,不再需要凭借语用原则经历一个推导过程,而是一下子就直接得出“建议”的理解。这种隐含义进一步固定下来就会对原来的语句形式产生反作用,于是就有了b这样的紧缩问句形式专门用来表达“建议”,“建议”成了b这种句法形式的固有意图。[10]二是用语用原则来解释某些语法结构的演变现象,例如“在……下”本来表示一种空间关系,一般指“在桌下”、“在树下”等情况,后来“在这种形式下”、“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等也逐步进入这种框架,这是由于“心理意象投射”语用原则使得具体空间关系逐渐扩展演变到抽象空间关系。
篇章的语法化指章法成分转化为句法成分和构词成分,或者松散的篇章结构演变成为稳固的语法手段。例如汉语动词拷贝结构“(V+O)+(V+C)“(写字写累了,喝水喝多了)的产生就是篇章结构演变成为稳固的语法手段。在“V(得)OC”消失以后,需要产生一种新的语法结构能同时引进宾语和补语,这就是动间拷贝结构。它来自于两个独立的单句,第一个单句的动词引进一个宾语,第二个单句的动词引进结果补语,此时两个动词并没有任何制约关系,是一种话语结构。可是一旦成为动词拷贝结构,只有第二个动词才能具体标记与时间信息等有关的语法形式。[11]简言之,动词拷贝结构是篇章结构语法化的结果。
3. 语法化的机制
语法化的机制较多,但最主要的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重新分析是指表层形式相同的结构,其内部构造因语用或其他原因被重新分析,从而从底层上改变了音位、词法或句法的结合方式,对原来的形式或意义作出新的解释。例如英语连词since由表示时间到表示原因,其过程就是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这个虚化的过程如下:
(4)a. Ihave read a lot since we last met.(时间)
b.Since Susan left him, John has been verymiserable.(时间/原因)
c.Since you are not coming with me, I’llhave to go alone.(原因)
a里的since表示时间;b里的since既可以分析为表示时间,也可以分析为表示原因;c里的since一般分析为表示原因,这样原因义取代了原来的时间义,于是since实现了重新分析。[12]又如“被”字句的产生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被”字后面可以跟名词,也可以跟动词,而汉语中名词和动词是没有形态区别的。在“亮子被苏峻害”(《世说新语·方正》)这样的句子中,“害”可以理解为名词,这时“苏峻”作“害”的定语,“被”就是“遭受”义动词,全句为主动句,即“亮子遭受到苏峻的迫害”。如果把“被”理解为介词,“害”理解为动词,则“苏峻”就成了施事者,全句就变成了被动句。句子仍旧是原来的句子,但由于人们理解的变化,对这个句子进行重新分析,赋予了一种新的含意,被字句也就由此产生了。[13]
(三)隐喻和转喻
传统语言学把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看作语言层面上的修辞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隐喻和转喻被认知语言学看作思维和认知方式,是人们对抽象概念认识和表达的工具。
1. 隐喻
认知语言学的隐喻是一种认知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一个认知域被部分地映现(mapped)于另一认知域上,后者由前者而得到部分地理解。前者叫来源域(source domain),后者叫目标域(targetdomain)。在“Life is a journey”隐喻中,源域是“旅行”,目标域是“人生”,从“旅行”域映现到“人生”域上。源域包括以下显著属性:①旅行者;②旅途的起、止点,旅程,方向等;③旅程中的各种经历。在这一概念隐喻的理解过程中,旅行的各种属性被系统地映射到了“人生”这一目标域。因此,人生与旅途一样,是一个有起点、终点的过程;同时,在人生旅途中,并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会经历一些坎坷。因此,英语中有这样的表达法,如“I am at a crossroads in my life”;汉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法,如“现在我正处于人生交叉口”。在隐喻理解过程中,源域的结构特征被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中,并成为目标域结构特征的一部分,因此,源域决定了目标域的意义。
作为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系统方式的隐喻主要有三类: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14]“结构隐喻”是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描述一种概念的词语用于描述另一种概念。以“时间就是金钱”为例,用于谈论“金钱”的词语都可以用于“时间”,时间被当作金钱一样宝贵的东西,如“花时间”、“浪 费时间”、“节约时间”等。在“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隐喻中,时间概念是通过金钱概念来组织和理解的,构成金钱概念的许多“次概念”被映射在时间概念上。方位隐喻是参照空间方位而建立的一系列隐喻概念。空间方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上-下,前-后,深-浅,远-近等。方位概念是人们较早产生和理解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人们将其他抽象的概念,如情感、精神、身体状况、社会地位、数量等投射到这些具体的方位概念上,形成了用方位词语表达抽象概念的方位隐喻。以“HIGH STATUS IS UP;LOW STATUS IS DOWN”为例,“上级-下级”、“上台-下台”、“上岗-下岗”、“上场-下场”、“上士-下士”、“上层-下层”等等,这些概念反映的社会地位、权利等与空间上下结构相匹配,社会地位高、权利大为上,相反为下。实体隐喻指人类把对物体和物质经验的词语用于谈论抽象的、模糊的思想、感情、事件、心理活动等无形的概念,把这些抽象的概念视为实体而变得有形。在实体隐喻中最典型的是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通过呼吸、饮食等经验,我们把自身看作一个有范围、有表面、能量化的容器,由此引出将其他物体以及一些更为抽象的活动、行为、状态等看作是容器,这样就把容器概念投射到其他抽象概念,诸如事件、行为、活动、状态、视野等。例如“He is in good mood today”、“Out of sight, out of mind”中的“mood”、“sight”、“mind”都被看作容器。
2. 转喻
认知语言学的转喻是一种认知机制,指在两个相关认知域之间用一个突显的事物代替另一事物,转喻的来源称为转喻源(metonymy source),转喻所指向的概念称为转喻目标(metonymy target)。事物、事件和概念有多方面的属性,人的认知往往更多地注意到那些最突出、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性,即突显属性。船上的船员,英语用“hand”表达,汉语用“水手”表达,因为船员在船上最忙碌的就是一双手,这里用转喻源“手”转喻“水手”(人)。又如“壶开了”是用转喻源“壶”转喻目标“水”,“壶”与“水”同在“容器-内容”认知框架内,两者关系密切,“壶”在认知上比“水”突显,概念“壶”的激活自然会激活概念“水”。事物突显度的差异有一些基本规律,如整体比部分突显(刀-刀柄),容器比内容突显(壶-水),当然,突显度有一定的主观性,当人把注意力有意识地集中到某事物时,一般不突显的事物也成了突显事物。[15]
转喻主要发生在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转喻,有些是用“部分”转喻“整体”,有些是用“整体”转喻“部分”。前者如用“心肝”转喻“宝贝”,用“国脚”转喻“著名足球运动员”,用“新面孔”转喻“不熟悉的人”,等等。后者如“手里拿着刀”,拿的只是刀柄,这里用“刀”转喻“刀柄”;“她戴着帽子”只是头戴着帽子,这里用“她”转喻“她的头”;“自行车没气了”只是自行车的轮胎没气了,这里用“自行车”转喻“自行车的轮胎”,等等。
[1]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Lakoff, G. &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80.
[5]沈家煊《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中国语文》2001年第6期。
[6]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7]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王灿龙《词汇化二例——兼谈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当代语言学》2005年3期。
[10]沈家煊《语用法的语法化》,《福建外语》1998年第2期。
[11]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沈家煊《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载刘丹青主编《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3]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5]沈家煊《“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1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