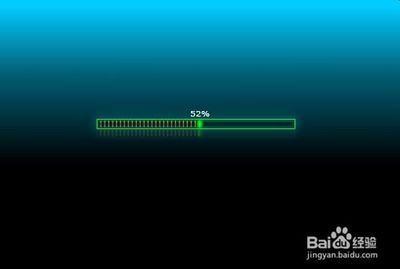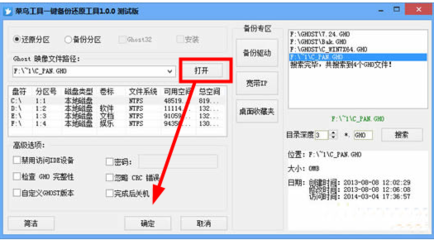自从我从台湾带回了几盒名叫“一条根”的草药膏,我就开始了神医生涯,有人晕车了,“快用一条根”,有人感冒头痛了,“快用一条根”,有人被蚊虫叮咬了,仍旧是“快用一条根”,甚至有人蹭破了皮,我也颠颠地奉上“一条根”,那清凉的药膏涂在出血的伤口上想必感觉十分给力,伤者往往一边龇牙咧嘴地说谢谢谢谢劳驾劳驾不用了不用了一边飞快地逃之夭夭……
反正,有了一条根,不管什么毛病到了我手里都成了小菜一碟,连东东都会说:“伤了病了不用怕,快找我妈妈,她有一条根!”
平时我用“一条根”给他治一些小毛病他倒也很配合,不过今天他坐车有点恶心,蔫蔫得只想睡觉,我建议他用开水冲一点“一条根”药膏喝下去,那味道一定很有特色,所以他被吓得立刻好了。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话说,这次我们的家庭旅游团又浩浩荡荡出发了,在冰箱一样的卧铺车里冻了一个晚上之后,三妹夫俞刚囊着鼻子直嚷嚷头痛,到处找感冒药,虽然我的包包里不缺“白加黑”、“散利痛”之类的应急药,可是我的原则是能用外敷的就不用内服的,因为是药三分毒,所以我一张嘴还是“试试一条根吧!”出于对大姐的尊重,三妹夫没有像三妹她们那样翻个白眼说“no”,而是很爽快地答应试试,于是东东自告奋勇,学着我平时的样子,往他三姨夫的太阳穴上鼻子下到处面涂药膏,边涂边说:
“有一点点刺痛吧?不要紧,忍一忍就好了。”
腔调很正点,好像他自己从来没有一听说抹药就撒丫子跑似的。
过了不大一会儿,俞刚笑嘻嘻地说“好了”,三妹不相信,一个劲地向他求证,他晃晃脑袋说“真的好了嘛,头也不痛了,鼻子也通了。”(于是三妹这个“坚定不移怀疑一条根”的家伙终于被收服了,后来的几天里她经常因为中暑啦晕车啦神马的被我和东东抹得满脸花。)
午睡醒来,大家都很有精神地凑在一起打牌,这时广播响了,说是十一号车厢里有个小孩突然头痛,如果哪位乘客有药请巴拉巴拉……我立马抓起一条根冲了出去,东东紧随其后,这种救苦救难的事向来都少不了他。到了十一号车厢,我们从这头问到哪头:“请问是谁生病了?”这个车厢里大多是小孩子,大概是参加什么夏令营活动的小学生,嘻嘻哈哈地上蹿下跳,貌似没有人注意自己身边有谁生病了。然后我们俩又问回来,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个抱着头蜷在铺位上的小孩子,我摸摸他的头,好像没有发烧,就对他妈妈说可以在太阳穴那里抹一点药试试,如果过一会儿感觉好一些,再到十三号车厢来找我。
当了一回天使大姐心情很好,回来接着打牌,不久孩子妈真的跑来找我,说娃儿感觉好多了,可不可以再给一点药抹一抹……我问这孩子不是感冒吧?他晕车吗?孩子妈很不好意思地说是因为他一路都在看电脑打游戏所以头痛,又跟自己解释说孩子这不放假了吗也该放松放松@#¥%……
东东在一边总结道:“我发现妈妈的一条根又可以治一种新毛病——电脑游戏病!”
呵呵。
反正这一路我一直在充当着治病救人的角色,不但各种旅行病都被我吓跑,连美女们脸上因为吃太多辣又加上太阳暴晒冒出来的火疙瘩都能被我治好。
不过,在某次试验之后,我发现用牙膏治火疙瘩更管用,于是在西安将近四十度的那几天,牙膏成了我的专用洗面奶。
——嘘,千万别说出去,这是俺的独家秘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