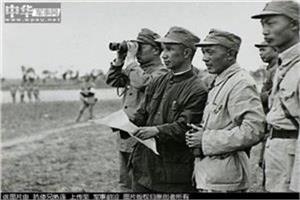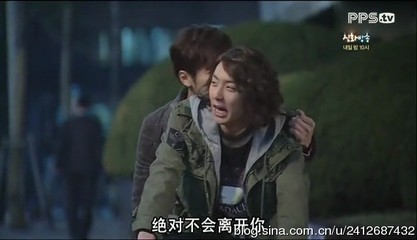醴、酒、玄酒
——周公制作管窺
張子閔
內容提要商紂酗酒喪德以至亡國,周人睹此前車之鑒,乃頒佈《酒誥》,厲行酒戒。既行酒戒,須明確區分何者為酒、何者非酒。因之,周人於酒、飲予以嚴格界定。周公制禮,以醴屬飲,使其通用於一般性主賓之禮(醴賓)。而《儀禮》一書用酒與《酒誥》規定幾於契合無間,處處表現出謹慎:不僅對使用場合有限定,且制定“獻、酢、酬”之儀節來限制飲酒量,更設置司正監察失儀行為,甚至於酒器製作上也極盡限節之能事。周公如此制作,正是本其理性精神,欲以維持周人德性於不墜。
漢魏之後,醴漸失傳,且學者久昧於酒、飲之辨,於周公制作之意有所未達,以致酿成酒祸。本文重在釐清酒醴(飲)之分,由此以窺周公制作之心,并冀藉此以揭示周公制作之核心為主賓禮。
關鍵詞 周公制禮作樂 主賓 醴酒
一、《酒誥》:周公制作之背景
文王之教
殷之末造,文王目睹商紂酗酒喪德,即對酒之流禍抱持戒懼之心,認為喪德喪邦惟酒之辜,因此在西土厲行酒戒,力求保持理性清明。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1]
文王明確教誥官吏子民無常飲酒,惟祭祀時方可飲酒,且不宜至醉。這與商紂酒池肉林適成鮮明對比。更關鍵的是,文王告誡其子孫要“聰聽祖考之彝訓”,而其後繼者,也頗能奉行勿失,且自承周之所以能“受殷之命”,乃在於“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2]。
文王教命所被,止於西土。殆武王克紂,奄有天下,即面臨殷民化紂俗,沉湎於酒之难題。若處理不善,難免殷人怨憤,致使東方沸騰;甚或周人亦漸染此俗,而不免蹈紂覆轍。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以大公至正之心,當國攝政。不意管蔡流言,武庚作亂,周公乃東征。這些動盪無疑會促使周公进一步探求致郅治之道。故戡亂之後,周公即出臺一系列措施,如建侯衛、營成周、制禮作樂,皆是經天緯地大手筆,遂奠定有周八百載基業,也確立了華夏文化的基本形態(禮樂文化)。
周公酒戒
鑒於商紂淫酒亡國,周公徙封[3]母弟於衛,乃秉文王遺教,參以當時政治局勢,復制以酒戒。此攝政四年事也。周公酒戒如次:
針對妹土之庶民: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
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4]
只要殷民孝敬父母,而父母欣慶歡樂,就允許用酒奉養父母。“父母慶”的標準實在是模糊。這酒戒是相當寬鬆的[5],一定程度是對東方舊俗的妥協,然而未嘗不是政治智慧的運用與表現。
而針對妹土司民的酒戒,則相對嚴厲: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6]
這顯然是恪遵文王遺教,但也做了調整,在“祀茲酒”之外,增加了可以飲酒的條件,即“克羞耇惟君”[7]。養老與君時,可以飲酒。從對文王遺教的這一調整可以窺見周公此時已在醞釀制作之事了。
既有教命,若觸犯酒戒,乃有嚴厲之懲罰。但周公仍將庶民與殷之故臣區別對待。對待庶民,嚴格禁止羣飲。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8]
羣飲者直接予以捕拏,送至周處死,用刑之重可見。而對殷之故臣,則不憚其煩,三令五申以教之,若仍不悛改,乃殺之。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蠲,乃事時同於殺。[9]
雖稍寬假,然而也相當嚴厲。刑罰如此峻烈,誠可謂“剛制于酒”[10]。或以為此有損於聖王形象,然當大亂之後,嚴刑罰以殺惡俗、收民心,雖聖王之不得已,又有何不可?何況是教而後誅,誅而無怨?
二、酒飲界分
酒與飲
既然周人對飲酒如此謹慎,一再發佈酒戒,那麼,自然就會引出如下問題:究竟何者為酒?何者非酒?若不加界定,酒戒便無從執行。禮,名為重。若名實淆亂,而欲其施用無礙,不知其可也。夫子汲汲於正名,用意正在此。其實,聖王於酒、飲有嚴格區分。惜乎學者未能予以充分重視,遂致昧于制作之意。現揭之如次。《天官·酒正職》:
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
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
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11]
《天官·酒人職》:
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
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12]
《天官·漿人職》:
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
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13]
酒正為酒官之長,統酒人、漿人等,因此酒、飲並辨之。五齊不是五酒,乃是雜酒、飲而言。鄭氏言:“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14]不當,因為除醴齊外,餘四齊非臨時所能備辦者。[15]孫詒讓謂:“五齊,有滓未泲之酒也。”[16]以酒代齊之名不確,然謂有滓未泲則誠為得之。蓋凡有滓未泲之酒、飲[17]皆可謂之齊。
酒人掌為三酒與酒正三酒相合;而漿人六飲則較酒正四飲多出水、涼,且有清、醴之異。其相同者,不復論;而其歧出者,則不得不予以辨明。酒正之清與漿人之醴本是一物,而涼亦別無所釀,但冰鑒諸飲而已。水乃常備易得之物,且無厚薄之齊,故酒正不辨,而漿人則不能不共也。
清、醴乃一物。鄭康成《酒正職》注謂:“清謂醴之泲者。”[18]《漿人職》注:“醴,醴清也。”[19]醴清亦即清醴。醴有清、糟之分。《內則》:
饮,重醴【,清、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20]
故知凡醴皆有清、糟之異,糟者又可名為齊。共王者則清醴也,一般賓主之禮所用則糟醴而已,故有角柶之設,為滑也。鄭氏云:“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21]
涼,冰鑒之飲。鄭氏注:“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22]鄭司農之說淆酒、飲,康成說亦未為得。若別有一種飲曰涼,則酒正當辨之。其實,非在四飲之外,別有一飲謂之涼也,涼乃四飲之冰涼者,如今之冰鎮飲料耳。孫詒讓引《呂氏春秋》高誘注、《楚辭》王逸注論之甚詳。[23]而《凌人職》云:
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24]
酒漿,即酒飲(以其漿人所掌,故可稱漿)。上酒屬下酒字,上漿屬下醴字。故知涼乃冰鑒之飲也。而酒人、漿人與凌人之職於此相聯。
這裡需注意:酒正言“辨”,酒人言“為”,漿人言“共”,措辭極為謹嚴。可知,五齊三酒,酒人釀為之,酒正但辨之而已。《酒正職》但言“以式灋授酒材”[25],不及飲材、式、灋。醴為酒人所釀,涼與凌人聯,水易備,然則其餘三飲究何人造為之?曰:女漿為之而與食官相聯。《天官·序官》載漿人有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鄭注云:
女漿,女奴曉漿者。[26]
則女漿當造三飲。又《膳夫職》云:
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
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27]
鄭注:“飲,酒、漿也。……六清,水、漿、醴、涼、醫、酏。”[28]鄭以飲囊括酒、漿(即漿人所共之飲),不妥。蓋鄭以《膳夫職》下有“王燕飲酒,則為獻主”[29]之文,故為此說。然雖為獻主,酒自酒官掌之,非膳夫職,故其文但言“飲用六清”,不及三酒。則食官於此乃與酒官相聯為用。
禮酒、飲酒/禮飲、漿飲
食禮酳而安食之酒,無獻酬之儀,謂之飲酒,以別於禮酒。食禮所飲之飲,無啐奠之儀,謂之漿飲,以別於禮飲。《公食大夫禮》云: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注:飲酒,清酒也。漿飲,酨漿也。其俟奠于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
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30]
飲酒,《酒人職》鄭注謂“食之酒”,與此合。禮酒,鄭彼注謂“饗燕之酒”。[31]以酒人所述為王者禮,故注如此,實則有獻酬之儀者皆可謂之禮酒。又《酒正職》鄭注亦謂:“漿,今之酨漿也。”[32]則以此為六飲中之漿,不妥(詳下)。而賈氏《儀禮疏》以漿飲為酳口之飲[33],胡氏進一步以為“非食時”所共之飲[34]。胡說不可從,因後文明言“賓坐祭,遂飲”[35],此即食時所飲也。非食時所飲,啐而不卒觶為禮飲[36](《儀禮》中所飲為醴)。禮飲重在禮,不在飲,即所謂不主飲食。可由《鄉飲酒義》論禮酒比擬而得之。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
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37]
《儀禮》中禮飲,醴也;所薦,脯醢也。醴賓時,脯祭而不嚌,醴啐而不卒觶。以酒禮賓時,則嚌肺而卒爵、觶,此其不同。而無論醴或酒,經此種儀節,皆旨在行禮,非為飲食,此其相通處。由此反觀《公食》所謂漿飲,則可知漿飲實為與禮飲相對之概念(猶如飲酒之於禮酒)。禮酒/飲非為飲食而設,飲酒/漿飲則為飲食而設。而《公食》所載賓於漿飲直祭而飲之,與禮飲法不同,故知漿飲為與禮飲相對之概念,則所謂漿必非六飲之一,實如漿人之漿,蓋與飲內涵相當,因不可名為飲飲,故易名為漿飲。
七十子後學不辨酒飲
酒飲之界分與《酒誥》有絕大關係。後儒於此未嘗深思,遂致注釋疏解錯謬百出,不勝枚舉[38],即七十子之後學,乃至鄭康成,亦或不免。《玉藻》云:
五飲:上水,漿、酒、醴、酏。[39]
又《喪大記》云: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40]
《玉藻》側酒於五飲之中,《喪大記》不能恪守醴之名而綴以酒稱(或當時流俗語如此),是七十子之徒昧於酒飲之辨也。而鄭康成《喪大記》注亦未能予以辨正,終至後世以酒視醴,淆酒醴(飲)之分,而周公制作寓禮於醴之微言大義遂因以暗昧不明,惜哉!
酒醴之别
四飲(水、涼除外)之中,唯有醴於禮經中足與酒相埒。而醴與禮之精神相貫通,乃越在酒之上。然魏晉以降,醴漸失傳,後儒不達酒醴之別,遂致聖王於醴所寄之理性精神堙沒千載。今略考醴酒之異如次。
媒糵不同:釀酒以麴,為醴以糵。由此致酒精、糖分含量不同:酒厚於醴,而醴恬於酒。《尚書·說命下》云: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41]
又《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
醴,以糵與黍相體,不以鞠也。
又《山海經·中山經》:
其祠糵釀。郭注:以糵作醴。[42]
又《天工開物·麴糵》云:
古来麴造酒,糵造醴,後世厭醴味薄,遂至失傳,則并蘗法亦亡。[43]
麴即酒麴,用來釀酒(黃酒);而“糵,芽米也”[44],經過一定加工,用來釀醴。釀酒、醴所用媒糵不同,遂至其酒精濃度、糖分含量不同。故鄭氏云:“醴恬,與酒味異。”[45]蓋酒之酒精濃度較高,醴之酒精濃度低,而糖分含量則稍高。[46]
釀造工藝繁簡不同:酒繁而醴簡。前已言醴一宿而熟。而造酒則繁雜地多。《酒正職》鄭注:
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47]
酒之釀造工藝複雜易於理解,不繁引。從工藝之繁簡,耗費人力、物力之多寡來看,酒實重於醴。然而由於聖王賦予醴以禮儀的意義,在某些場合,醴反重於酒。酒、醴畸輕畸重,若不善察之,不免迷亂不知所出(詳後醴酒之輕重節)。
三、醴與禮:醴賓/禮賓
醴得名之由,歷來儒者多以為汁滓相體。如上節所引高誘“糵与黍相体”說,鄭康成亦謂“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48]。此說為當時學者共識,實昧於聖王名醴之意。竊以為:醴也者,禮也,以其通用於一般性主賓之禮也。聖王名此飲曰醴,蓋欲醴禮一體,以化紂俗也。
醴賓:禮經中醴之運用
“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及事成,“謝其自勤勞”[49],宜有禮以致意,此為人際交往之一般原則,而此套禮儀即可名為一般性主賓之禮(或曰主賓常禮)。周公制禮,以醴飲賓(而非酒)為主賓常禮之核心,因謂之醴賓。以他物謝賓者,謂之禮賓[50],不可謂之醴賓。而醴賓固可謂之禮賓也。實則今文常作醴賓,古文常作禮賓,亦間有同作醴或禮者。而鄭康成於醴賓處必破醴為禮,參諸其出異文之字例,似乎康成實明瞭醴禮之關係。
今文作醴,古文作禮者。如《士冠禮》孤子冠節: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注:今文禮作醴。[51]
又如《聘禮》夫人歸禮賓介節:
明日,賓拜禮於朝。注:今文禮為醴。[52]
又還玉及賄禮節:
禮玉束帛乘皮,(注:今文禮皆作醴。按:以下有禮故曰皆)皆如還玉禮。[53]
《聘禮·記》公禮賓儀物節:
禮,不拜至。注:今文禮為醴。[54]
今文作禮,古文作醴者。《聘禮·記》君不親受之節:
不禮。注:辟正主也。古文禮為醴。[55]
此上皆今古異文,而古文作禮今文作醴者僅一例,不能不令人疑為傳寫之誤,然亦不敢遽下結論。
今古文皆作醴者。如《士冠禮》:
請醴賓,賓禮辭,許。注:此醴當作禮。[56]
若不醴,則醮用酒。注:醴亦當為禮。[57]
又如《士昏禮》納采節:
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注:此醴亦當作禮。[58]
又贊醴婦節
贊醴婦。注:醴當作禮。[59]
又舅姑沒婦庿見節: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60]
此上鄭氏破醴為禮,獨老醴婦未破(《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亦未破。然已於請醴賓處破之),疑注文有脫誤。而以上除“若不醴”用“為”字外,皆用“作”字,與上論“作”“為”字例亦相合。康成出異文或用“作”,或用“為”,蓋有深意。竊嘗考之,以為:用“作”者,康成意中二者於此處可相通;用“為”字,康成意中二者於此處不能相通。[61]出醴禮異文,“作”“為”似乎淆亂不能劃一,然細細推之,又似康成意中《士冠禮》、《士昏禮》中二者相通,而《聘禮》中二者不能相通(唯禮玉條用“作”,與例不合)。正可印證上所論:以醴飲賓曰醴賓,亦可曰禮賓;而以他物致意曰禮賓,不可曰醴賓。
今古文皆作禮者。如《聘禮》主君禮賓節:
請禮賓,賓禮辭,聽命。[62]
此處禮賓嚴格說來宜為醴賓,而今古文無異詞。與本不可作醴,而今古文皆作禮者自不同,不復引證。
除鄉飲、鄉射(鄉黨禮)、燕、大射(邦國禮)、祭禮用酒外,其他一般性主賓之禮所用皆醴也,乃至《聘禮》禮賓亦以醴飲賓。故醴賓不必破為禮賓,乃更能顯示醴之象徵意義。
禮賓:論主賓禮統攝《禮經》諸篇,為周公制作之核心
鄉黨禮、邦國禮、祭禮用酒,雖不可謂之醴賓,固可謂之為禮賓也。而主賓之禮實統攝《儀禮》諸篇,為諸禮之核心環節。《大宰職》云:
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八曰禮賓。注: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63]
鄭注不愜人意。經言馭萬民,而鄭乃解以禮諸侯,不得已而綴以示民耳。且後經文言“凡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注又謂“禮,賓禮也”。如是,經文豈不重複?以禮待賓客之治為賓禮諸侯無疑,則馭萬民之禮賓必非賓客諸侯,斷可知矣。竊以為此處禮賓,實涵括《儀禮》之醴賓、禮賓。以禮賓馭萬民者,乃制為主賓之禮,使萬民奉行勿失也。此說與《王制》七教之賓客實可相通。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64]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65]
《禮記正義》謂“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66]不可從。觀六禮之目,皆涵括於周禮中。六禮七教之說,須從“民”字著眼乃能得其解。《周禮》言治官、民、待諸侯等分疏尤詳,不容相攙。而六禮固民(主要指士)為主體所可行之禮,過此以往若朝、聘、燕、食、大射等,皆非以民為主體。冠昏喪祭四禮,後世為士庶之常禮。而鄉、相見乃與之並而為六者,相見固人際交接之常,而鄉禮尤為聖王深心之寄。七教為五倫益以長幼、賓客。長幼固可涵括於朋友之中。如是則七教乃五倫與賓客耳。賓客何以如此重要?竊嘗思之: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者,人倫之定名;主賓者,人際之虛位。故聖王制冠昏喪祭之禮以攸敘人倫,制鄉禮(相見涵在內)以燮理人際。聖王實以主賓為禮之陰陽,參(齒德爵)五(五倫)錯綜,以盡制盡倫。唯有充分理解了主賓禮之重要性,才能充分把握鄉禮之功用,才能真正契入“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67]之說。
主賓禮統攝諸禮,實深微難言。若冠禮之醴賓、昏禮親迎前之醴賓,為一般性主賓之禮,人莫不知。鄉飲、鄉射為主賓常禮之升級,亦易了解。《士冠禮》醴冠者、《士昏禮》醴新婦亦為主賓禮,則達者寥寥矣。至於《士喪禮》中喪主與亡者間、祭禮中配祀與主祀間,亦為主賓禮,人乍聞之,或不免駭然。請先論賓主之義,然後逐一論之。
凡人自外至曰賓[68],即與原在內者構成主賓關係;而自內出而不反者與居內不遷者,又何嘗不構成一主賓關係?《公羊傳》云:
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
止。[69]
此處論祭祀之禮為主賓禮之模擬,極精到。《孝經注疏》引此傳,釋之云:“言祭天,則天神為客,是外至也。須人為主,天神乃至。”[70]此說得之,而其主則配祀者也。所祭父祖相對於祭主來說亦是自外至者,然人子事亡如事存,不以賓禮待之,而饋養如生時。此祭禮之統攝於主賓禮也。
喪禮可統於主賓禮,非特喪主、吊賓間,更在喪主與亡者間乃構成主賓關係。此早經前賢指出。《說文解字》云:
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71]
賓遇之,已點破喪禮中亡者與喪主間為賓主關係。又《既夕》“徹巾,苞牲,取下體”鄭注:
苞者,象既饗而饋賓俎者也。……《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72]
鄭所引乃《雜記下》文:
或問于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
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73]
一般性主賓之禮,賓需得主人之俎以為復命之用。喪禮苞取牲體,正是對主賓禮這一環節的模擬。而喪禮的整個儀程,正是圍繞亡者漸由主人變而為賓來設計,其標誌一則在醴之使用,一則在空間之變化。空間,漸由室內(小斂),而於阼(大斂),遷於客位(殯)。《既夕·記》“小斂,辟奠,不出室”鄭注云:
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畢事而去之。[74]
又“大斂于阼”鄭注云:
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西階上賓之。[75]
《檀弓上》曰: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76]
故《坊記》統而言之,曰:
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
遠也。[77]
每加以遠,亡者漸由主人變為賓客。空間變化所昭示如此。
《士喪禮》之始死奠、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朔月奠、遷祖奠、祖奠、大遣奠皆醴、酒並陳,且以醴為上。以至日中而虞,以喪祭代奠,猶以醴為上。過此以往遂轉而用酒,進入吉禮。聖王之所以如此制作,竊以為:用酒者,合乎《酒誥》“父母慶”之意,是事死如事生,仁也。用醴者,實則包含對主賓禮模擬在內,蓋父母已喪亡自內而出矣,是智也。醴酒并陳所昭示如此。以上論喪禮之統攝於主賓禮。
學者往往以為《士冠禮》核心環節為三加,而於醴冠者之意義則未能充分闡明。醴冠者實為冠者成人後,主賓禮之初肄習。《士冠禮·記》:
醮于客位,加有成也。注:所以尊敬之,成其為人也。[78]
其實,醴冠者亦於客位(堂上戶牖之間南面之位)。成人前,作為童子,冠者無以與成人分庭抗禮、敘賓主之禮。既經三加,而成人,則已具備此種資格。故聖王制禮時,因之而制醴冠者之儀節。女子十五笄而醴之,與之類。此冠、笄禮之統攝于主賓禮也。
婦,古稱嬪。嬪,豈非女子來而為賓乎?《尚書·堯典》云: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傳:嬪,婦也。[79]
《詩·大雅·大明》云: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嬪,婦也。[80]
堯降二女時,舜為布衣,可見古者婦實稱為嬪。女子自外而來猶賓自外至,然賓則來而猶去,婦則來而不去。周公即基於主賓禮,加以變化而制昏禮。其核心之變化乃在於親迎與共食。
賓,主人迎于大門外而已。而婦,則壻親往女家迎之,故謂之親迎[81]。此其一。賓,所食非牢體(如《鄉飲酒禮》、《燕禮》牲為狗),且分食而不共食,而新昏夫婦則同牢共食、合巹以成禮。此其二。由此二變以推賓客飲醴而新婚夫婦飲酒,可見聖王重昏禮之意。此昏禮之統攝於主賓禮也。
四、《禮經》用酒與《酒誥》規定卯榫相合
《儀禮》用酒,與《酒誥》規定幾乎契合無間。略述如下。
祀茲酒:醴、酒、玄酒於喪祭禮之運用
《士虞禮》為凶禮鄉吉禮過渡的禮儀,其過渡性,從醴、酒在《士虞禮》的兼陳並用,可以看出。《士虞禮》陳虞祭酒醴:
尊於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注:酒在東,上醴也。[82]
上,尚也。吉祭,玄酒在酒上,而喪祭則醴在酒上。饗尸時,所用為醴[83],其後三獻則酌酒酳尸矣。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注: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
酢,變吉也。[84]
三獻畢,餞尸。則徹醴不用,而陳酒與玄酒矣。從此,乃轉為吉祭。《士虞禮·記》:
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注: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
也。言水者,喪質,無冪,不久陳。[85]
雖已即吉,尚未徹底轉為吉祭,因此玄酒稱水,且在酒西。其後,袝祭稱孝子,用溲酒,以至期而小祥(祥,吉也),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乃漸完成向吉祭之轉變。中月而禫之後,《記》云: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86]
是月,即禫月。當四時之祭月則祭,從此便開始了四時吉祭。《特牲饋食禮》載祭前陳設:
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注:玄酒在西,尚之。[87]
特牲三獻用酒,不待言。則四時之祭,全不用醴,而用酒。乃至奉君命出使而還,奠告於禰,亦用酒,而不用醴。《聘禮》云:
乃至於禰,筵几於室,薦脯醢。觴酒陳。席於阼,薦脯醢,三獻。[88]
如此严格奉行祭祀用酒礼制,无疑是恪遵文王遗训以及《酒诰》規定的。[89]
克羞耇惟君:鄉禮、朝廷用酒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中所用為酒,不待言。然而鮮有學者將其與《酒誥》“克羞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聯類而思之。
“羞耇惟君”(羞,饈也,養也;惟猶與也,及也)即養老與君。此時,乃可飲酒(與國君歡燕飲酒,乃自然之事)。《公食大夫禮》乃食禮,主飲食,故酒、飲並用。此為周公對文王遺教之調整。這一調整顯然是出於鄉禮構建之需要,也可見周公在頒佈《酒誥》時,即已醞釀制作之事了。
五、醴酒轻重考
酒、醴在禮經中的應用存在參差(畸輕畸重)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士冠禮》、《士昏禮》中。略述如下。
冠禮中之參差
《士冠禮》云:
若不醴,則醮用酒。注: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90]
賈氏因謂之為夏殷之禮,不為無據。結合《酒誥》對殷之故臣不憚三令五申以教之,不悛改,然後予以懲罰,則可知冠禮中,醮、醴並行的禮制,正是對東方舊俗的妥協,也是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精神的反映。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91]
賈氏謂:“三代庶子冠禮,皆于房外,同用醮矣,但不知三代庶子各用幾醮耳。”[92]言下之意,不徒東方庶子用醮,而周人庶子冠禮亦用醮。這樣顯然醴重而酒輕。因此《曾子問》載: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93]
因為成人後,即有資格參加一般社交禮儀,而一般社交禮儀所用為醴而不是酒,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醴重而酒輕。實際上,從物性上來考慮,酒無疑是重於醴的。
昏禮中之參差
昏禮親迎前,“父醮子命之”親迎,“父醴女而俟迎者”。親迎當日酒與玄酒並陳,而同牢共食時,所飲者,即酒也。婦明日拜見舅姑,舅姑醴婦;而“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其參差如是。
親迎飲酒上已論之,此略。婦亦自外來,而舅姑醴嫡婦,主賓禮也。醴之前,有婦饋舅姑之禮,則所以養舅姑也。饋與醴不可分,必饋而後醴,乃能真正見出其中意味。饋養舅姑,乃嫡婦所主,因此庶婦雖新來,而不饋舅姑,故舅姑亦不親醴庶婦,使人用酒醮之而已。嫡婦、庶婦此種等差,與嫡子、庶子冠禮時之等差正可比例而觀。嫡子將紹家事,故冠於阼而醴之客位。庶子無以紹家事,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而已。
至於“父醮子命之”親迎與“父醴女而俟迎者”之間參差,賈疏云:
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在寢。不同者?父禮女者,以先祖遺體許人以適他族,婦人外
成,故重之而用醴,復在廟,告先祖也。男子直取婦入室,無不反之,故輕之而用酒,在寢。知醮子亦不在
廟者,若在廟,以禮筵於戶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故在寢可知也。[94]
賈氏之說,不可通。禮經雖未言布筵設神席,然不可遂斷為在寢。其實,父醮子亦當在廟。關鍵是此時酒重醴輕,不似在冠禮中醴重而酒輕。若酒輕,何以昏禮承事宗廟之重而同牢共食時不飲醴而飲酒?賈氏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致誤。一般社交場合,酒輕醴重,此周公所制,以行酒戒也。故醴之重完全是儀式上的賦予。從物性來看,酒重於醴,因其製作工藝與所耗皆繁於醴。故酒多用於一些重要場合,如祭祀、鄉黨、邦國禮。若如賈氏說,酒輕而祀用酒,何以謂之國之大事?因此酒醴輕重,不可執一而觀。
六、寓戒於禮:周公制禮對飲酒之限節
為化淫酒之俗,周公曾嚴刑以剛制于酒。然此終非致太平之道,故天下底定之後,周公即制禮作樂,寓戒於禮,主要表現在飲器製作、儀節設置、人物設置、玄酒之尚諸方面。
飲器製作
《考工記·梓人》云: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
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95]
鄭康成破觚為觶[96]。此種飲器容量的規定,當是周公制作後才出現的,夏商飲器容量是否有等差,文獻不足徵[97],出土實物亦因爵等非重器,不甚為考古者所注意,故難以稽考。然《稽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云:
考商爵大於周爵,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較此觥,觥容兩爵大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98]
則似乎周爵容一升已是在酒器上所做的限節了。酒器類名、容量,不必一一細考,要須把握周制此種規定實與對飲酒的限制相關:飲醴時用觶,而一般飲酒時用爵,唯酬酒、罰酒時用觶。醴酒精度低,因此直接用觶。飲酒經過一獻而三酬的儀節,所飲恰為一斗(一獻用爵容一升,酬用觶容三升,故曰三酬,總計四升,是為一斗),為中人之食,其制作之謹嚴一至於此。
又名承酒尊之器為禁,所以為酒戒也。欲其酌酒、飲酒時,睹此器而心有所怵惕,以保持飲酒不過量。《特牲·記》作“棜禁”,鄭謂:“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99]此學者所熟知,不贅言。
儀節設置
周公酒禮有獻、酢、酬之儀節設置,且其間進退升降揖拜頗繁。獻、酢、酬之設置只有從對飲酒的限制上才能真正理解其意義。《樂記》云: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生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
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100]
此說尤得周公酒禮之精義。經過此等禮儀的浸潤,自生出一種優有所節的君子之態。故《玉藻》云:
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101]
這種君子之風實在是先王之禮浹洽侵潤出來的。
人物設置
《鄉飲酒》、《鄉射禮》《燕禮》《大射》皆立司正,鄭康成謂:“立司正為蒞酒爾”[102],又謂:“當監旅酬”[103]。則司正在旅酬、無算爵的環節實負有監察儀法之責。《鄉射禮》“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鄭注云:
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為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104]
然而在燕、射時立司正本為盡君臣之歡。《燕禮》云: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105]
乍觀之,此豈非勸飲耶?殊不知司正既負責監察儀法,若醉,必然失儀,是勸中寓戒。故無算爵以醉而不失儀為止。《大射儀》“無筭爵”鄭注:
筭,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106]
而後世忽視戒勿失儀之意,不免以司正純為督之使醉了。因此《賓之初筵》云: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107]
末世之弊以至於“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108],可見殷俗之難化而易漸。
玄酒之尚
《禮經》中除喪禮酒醴並設、食禮(《公食大夫禮》)飲酒、漿飲並設外,酒必與玄酒並設[109];而醴則獨設,所謂側尊,無玄酒。而玄酒之用,鄭康成以為“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110]。說本《禮器》: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
貴;莞簟之安,而稿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111]
又《郊特牲》: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112]
《禮運》謂:“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113] 汙尊而抔飲,所飲者水,是所謂玄酒為反本、修古之意。
王靜安先生《說盉》一文,指出浭陽端氏所藏殷時斯禁,上列有盉。經禮雖無是器,王氏考諸文獻,以盉為調酒之器。
然則盉之為用,在受尊中之酒,與玄酒而和之,而注之於爵。[114]
其論玄酒之用,反對反本修古之說,認為非虛設無用之物,曰:
蓋古者賓主酬酢,無不卒爵,又爵之大者恒至數升。其必飲者,禮也。其能飲或不能飲者,量也。先王
不欲禮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禮為苦,故為之玄酒以節之。其用玄酒奈何?曰:和之於酒而已。[115]
此說洵為得聖王制作之本,然而其謂殷時斯禁,恐當時未必有此名。如此,則醴側尊無玄酒,亦自然可解。蓋以“醴質”[116],酒精度本低,故不須酌玄酒以和之。而七十子之徒,發明反本修古之說誠為高妙,然恐亦昧于先王酒禮之一端也。
七、康樂毋荒:周公之理性精神
清華簡有《耆夜》一篇,記武王八年勘耆(黎)飲至之事。文中所記飲至儀節,容為後人追述。蓋武王時,未必即有如此完備的禮制。而其所敘立賓、立介,立主[117]之事,正可作為主賓之禮統攝諸禮的一大驗證。周公正是把握了主賓禮這一人際交往基本模式,而加以制作:或肄之使成(冠禮)、或合之使親(昏禮)、或申之使遠(喪禮)、或擬之使虛(祭禮)、或廓之使大(鄉禮)。故主賓禮統攝諸禮。周公睿聖之心,探人際之本,虛實變化以制為禮,其智蔑以加矣。在飲至禮上,周公作《蟋蟀》之詩。
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趯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
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藥(樂)。夫日□□,□□□忘(荒)。毋已大樂,則終以
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 (方)。
蟋蟀在席,歲聿云暮。今夫君子,不喜不樂. 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祚。康樂而毋
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蟋蟀在舒,歲聿雲□。□□□□,□□□□。□□□□,□□□□。毋已大康,則終以懼。康樂而毋
荒,是惟良士之懼懼。[118]
方君臣燕樂之際,周公睹蟋蟀在堂,感日月之邁,乃再三發“康樂而毋荒”之警戒,可謂理性清明。康樂毋荒,豈非酒禮之根本原則?此武王八年事也。故知周公制作之心,蘊蓄久矣。
八、醴失禮衰
《莊子·山木》庚桑楚答孔子問:
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119]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已成為人所常言之習語,然鮮有學者究其背後意味。水(即禮所謂玄酒)乃道家學說之象徵(絕棄仁義、清淨無為),而醴[120]則儒家禮儀之象徵。此種寓言為攻擊儒家學說而發,後儒不察,亦津津然樂道之,何蔽之甚!
漢時,醴猶存,而儒者已不能達其寓意。《漢書·楚元王傳》載: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121]
因穆生不嗜酒,楚元王為之設醴,而并不是因為意識到醴之象徵意義。漢儒以(甜)酒釋醴為通說,後儒襲之。降及魏晉,酗酒之風大熾,士人往往寄情藥、酒,曠棄禮法,此必然之勢也。陵夷至今,禮樂崩壞、綱常解紐,而酗酒之甚幾於人皆商受,可謂前古未有。昔我夫子於宗周禮樂,讚歎折服,為之夢寐不置,轍環天下欲為東周,不果,遂懸契於百世之後,其言曰:
殷所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所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122]
噫!百世,今其時也。陰陽消息,亦已極矣,繼周者其誰耶?
(本文發表於首屆中國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并收入論文集《禮樂中國》)http://www.zxhsd.com/kgsm/ts/2013/09/13/2640687.shtml[1]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6頁。
[2] 《尚書正義》,第206頁。
[3]關於分封康叔年代,古來以為周公攝政時。後學者疑何以武王時不封母弟,有以康叔年幼為解者,遂大起疑竇:武王耄耋之年何以有幼弟?於是或以為《酒誥》乃武王時作。如此漸推漸遠,歧論迭出。以致有學者認為《酒誥》乃成王涖政之後作者。(孔廣森《經學卮言》卷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45。)竊以為此解經而不達世務所蔽也。武王時封康叔,不礙周公時徙封于妹土。蓋勘定武庚之亂後,東方形成政治真空地帶,分封格局勢必調整,而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即是一有力證據。
[4] 《尚書正義》,第206頁。
[5]《玉藻》云:“唯飨野人皆酒。”兩相對比,可窺由酒戒到酒禮的轉化,聖人之用心。《禮記鄭注》,學海出版社,1992年,第391頁。
[6] 《尚書正義》,第206頁。
[7]孔傳云:”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是以進釋羞,不當。《尚書正義》,第206頁。蔡氏云:“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蔡沈《書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1頁。皮錫瑞引《尚書大傳》亦以羞耇為養老,未釋惟君。《今文尚書疏證》,中華書局,1989年,第324頁。按:惟,猶與也,及也。參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三,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8]《尚書正義》,第207頁。這種政策在《周禮》中亦有表現。《秋官·萍氏職》云:“幾酒,謹酒。”然已由以刑禁轉變為以禮節。《周禮鄭氏注》,孔子文化大全,山東友誼書社,1992年,第685頁。
[9] 《尚書正義》,第208頁。
[10] 《尚書正義》,第207頁。
[11] 《周禮鄭氏注》,第87-88頁。
[12] 《周禮鄭氏注》,第92頁。
[13] 《周禮鄭氏注》,第93頁。
[14] 《周禮鄭氏注》,第88頁。
[15]《說文解字》:“醴,酒一宿孰也。”許慎《說文解字》,天津出版社,2005年,第312頁。以醴為酒,不合聖王之意,然謂一宿孰,當為漢時釀醴之實。而餘四齊,康成均以漢時酒為況,則非朝夕能備也。
[16] 《周禮正義》,中華書局,第342頁。
[17] 聖王何以獨將四飲之醴入齊中,蓋醴之釀造法與酒類,故酒人亦掌為醴齊。
[18] 《周禮鄭氏注》,第88頁。
[19] 《周禮鄭氏注》,第93頁。
[20]重醴後清、糟二字,據《士冠禮》鄭注所引《內則》補。《周禮·酒正職》辨四飲之物注中先鄭所引《內則》無此二字。盧文弨以鄭《士冠禮》注所引為衍文。然《內則》鄭注:“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細味鄭注,糟清注之後,乃釋陪字之意,則清糟二字當即在重醴下也。又據文意觀之,清糟正為釋重醴,且為下稻、黍、梁之重為目也。又《儀禮疏》云:“云重醴清糟者。”(《十三經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第953頁。)則賈所見鄭《儀禮注》重醴後有清糟二字也。又《周禮疏》云:“按《內則》上言飲,下云重醴清糟。”(《十三經注疏》,第669頁中。)則賈所見《禮記》重醴後有清糟二字也。凡此,足可證今本《禮記·內則》有脫文。盧文弨貿然謂鄭《士冠禮》注所引為衍文,失之輕率。
[21] 《周禮鄭氏注》,第93頁。
[22] 《周禮鄭氏注》,第93頁。
[23] 《周禮正義》,第369-370頁。
[24] 《周禮鄭氏注》,第94頁。
[25] 《周禮鄭氏注》,第87頁。
[26] 《周禮鄭氏注》,第18頁。
[27] 《周禮鄭氏注》,第63-64頁。
[28] 《周禮鄭氏注》,第64頁。
[29] 《周禮鄭氏注》,第66頁。
[30]《儀禮鄭氏注》,楊家駱主編,國學名著珍本叢刊,羣經古注單疏彙刊之一,鼎文書局,第149頁。
[31] 《儀禮鄭氏注》,第92頁。
[32]賈氏乃云“此漿亦是酒類”,誤矣。《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69頁。
[33]《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80頁。酳口之說不切當,易誤為潔口,實兼安食之意。《公食》“賓坐祭遂飲”注:飲,漱。(《儀禮注疏》,第1082頁。)當與《士昏》鄭注酳相參。彼處云:“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食。”《儀禮鄭氏注》,第15頁。
[34]胡培翬《儀禮正義》十九,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六。
[35] 《儀禮注疏》,第1082頁。
[36]《酒正職》:“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周禮正義》,第90頁。)《漿人職》: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周禮正義》,第93頁。)禮醫、酏糟,禮清醴、醫、酏糟,即相當於禮酒,可名為禮飲。
[37] 《禮記鄭注》,第817-818頁。
[38]即賈公彥、江慎修、黃以周、孫詒讓諸禮學大家亦所不免。參《周禮正義》漿人職疏所引諸家說法,第351-369頁。
[39] 《禮記鄭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2年,第385頁。
[40] 《禮記鄭注》,第570頁。
[41]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上,第175頁。
[42]上二條皆《周禮正義》所引。孫氏云:“《韓詩》、《漢書》顏氏注則謂醴少鞠多米,與高說不同,未知孰是。”孫氏猶有一間未達,未能窺破周公用醴之意。參《周禮正義》,第344頁。
[43]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十七,明崇禎刻本。
[44] 《說文解字》,第147頁。
[45] 《周禮鄭氏注》,第89頁。
[46] 洪光柱編著《中國釀酒科技發展史》,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70-71頁。
[47] 《周禮鄭氏注》,第88頁。
[48] 《周禮鄭氏注》,第87頁。
[49] 並《士冠禮》鄭注語。《儀禮鄭氏注》第2頁、第6頁。
[50] 《聘禮》中多見之。
[51] 《儀禮鄭氏注》,第8頁。
[52] 《儀禮鄭氏注》,第136頁。
[53] 《儀禮鄭氏注》,第137頁。
[54] 《儀禮鄭氏注》,第144頁。
[55] 《儀禮鄭氏注》,第145頁。
[56] 《儀禮鄭氏注》,第6頁。
[57] 《儀禮鄭氏注》,第6頁。
[58] 《儀禮鄭氏注》,第11頁。
[59] 《儀禮鄭氏注》,第16頁。
[60] 《儀禮鄭氏注》,第18頁。
[61] 擬撰《鄭康成校刊體例發微》詳論之。
[62] 《儀禮鄭氏注》,第127頁。
[63] 《周禮鄭氏注》,第34頁。
[64] 《禮記鄭注》,第163頁。
[65] 《禮記鄭注》,第179頁。
[66]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42頁。
[67]鄉禮是主賓禮之升級。而《喪服》之儀節在喪禮,故仍統於主賓禮。《喪服》強化宗法,其發用以塑造宗族社會。鄉禮則突破宗法範疇,處理更開放場域之人際關係,其發用足以形成鄉黨社會。宗族社會偏於封閉,鄉黨社會更顯開放,且注重公德。《喪服》作用獨彰,《鄉飲酒》等鄉禮功能不顯。這就形成我國社會基本形態為宗族社會,而鄉黨社會則弱化或被含攝於宗族之內。學者多批評國人缺乏公德,至今公民社會構建困難云云。於此或可得到一定啟示,也令人不能不讚歎周公之遠見卓識。
[68]王夫之:“自外至曰客”。《張子正蒙注》,天地人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7頁。
[69]《春秋公羊傳注疏》宣公三年,十三經注疏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78頁。
[70] 《孝經注疏》,十三經注疏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53頁。
[71] 《說文解字》,第85頁。
[72] 《儀禮鄭氏注》,第208頁。
[73] 《禮記鄭注》,第540頁。
[74] 《儀禮鄭氏注》,第113頁。
[75] 《儀禮鄭氏注》,第113頁。
[76] 《禮記鄭注》,第81頁。
[77] 《禮記鄭注》,第672頁。
[78] 《儀禮鄭氏注》,第10頁。
[79] 《尚書正義》,第123頁。
[80] 朱熹《詩經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20頁。
[81]《詩·大明》言文王“親迎於渭”,則親迎或於周公制作前即已存在,然周公貞定於禮制之中。《詩經集傳》,第121頁。
[82] 《儀禮鄭氏注》,第217頁。
[83] 《儀禮鄭氏注》,第219頁。
[84] 《儀禮鄭氏注》,第220頁。
[85] 《儀禮鄭氏注》,第224頁。
[86] 《儀禮鄭氏注》,第227頁。
[87] 《儀禮鄭氏注》,第231頁。
[88] 《儀禮鄭氏注》,第140頁。
[89]《周頌·豐年》:“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恐制作前之詩,或詩人但連類及醴而已。《詩經集傳》,第156頁。
[90] 《儀禮鄭氏注》,第6頁。
[91] 《儀禮鄭氏注》,第8頁。
[92] 《儀禮注疏》,第957頁。
[93] 《禮記鄭注》,第240-241頁。
[94] 《儀禮注疏》,第972頁。
[95] 鄭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為斗。《周禮鄭氏注》,第814頁。
[96]《特牲·記》注引舊說同。《儀禮鄭氏注》,第243頁。
[97]《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盞,殷以斝,周以爵。”徒記三代爵名,不指明其容量,甚無謂。《禮記鄭注》,第415頁。
[98] 阮元《稽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二子燮兕觥條。皇清經解本(卷一千五十八)。
[99] 《儀禮鄭氏注》,第243頁。
[100] 《禮記鄭注》,第486頁。
[101] 《禮記鄭注》,第391頁。
[102] 《鄉射禮》“司正為司馬”注語。《儀禮鄭氏注》,第50頁。
[103] 《鄉射禮》“司馬反為司正”注語。《儀禮鄭氏注》,第63頁。
[104] 《儀禮鄭氏注》,第49頁。
[105]《儀禮鄭氏注》,第83頁。又《大射儀》: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眾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儀禮鄭氏注》,第115頁。
[106] 《儀禮鄭氏注》,第117頁。
[107] 《詩經集傳》,第111頁。
[108] 《賓之初筵》鄭箋語。《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上,第487頁。
[109]《士虞禮》由酒醴並設轉而為酒玄酒並設。《有司徹》“納一尊于室中”鄭注:陽厭殺,無玄酒。《儀禮鄭氏注》,第279頁。
[110] 《士冠禮》注語。《儀禮鄭氏注》,第7頁。
[111] 《禮記鄭注》,第315頁。
[112] 《禮記鄭注》,第338頁。
[113] 《禮記鄭注》,第284-285頁。
[114] 《觀堂集林》第一冊,中華書局,1961年,第153頁。
[115] 《觀堂集林》,第152頁。
[116] 《聘禮》主君禮賓節“公拜送醴”鄭注語。《儀禮鄭氏注》,第128頁。
[117]《周語上》:“王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魯語下》:“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與此立賓、立主之說同。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第28頁、第192頁。
[118]《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中西書局,2010年,第150頁。
[119]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七上山木第二十,中華書局,1978年,第685頁。
[120]《齊民要術》卷九醴酪“煮醴法”條云:“與煮黑餳同。然須調其色澤,令汁味淳濃,赤色足者良。尤宜緩火,急則燋臭。傳曰:“小人之交甘若醴”,疑謂此,非醴酒也。”既曰如黑餳,則此醴實為麥芽糖,故賈說非醴酒。賈思勰《齊民要術》(下冊),萬有文庫,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5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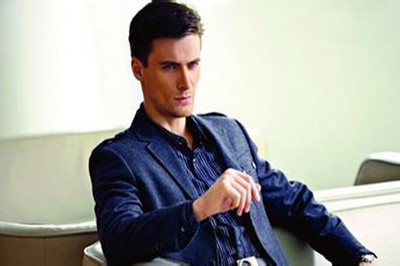
[121]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4年,第1923頁。
[122] 《論語集注·為政第二》,《四書章句集注》本,上海書店,1998,第12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