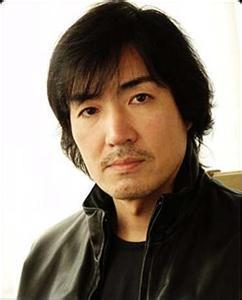陆林的《金圣叹全集》的出版,是金圣叹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在书前突出位置标明此书已经获得6项桂冠;出版后又获第7、8项桂冠: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著作一等奖
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一部个人完成的古籍整理著作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荣誉,5个国家级的,3个省部级的,可谓是无与伦比的。
作为研究金圣叹的学者,和首部《金圣叹全集》的编校者,我当然应该认真阅读此书。我在2009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买到了此书,看后却发觉大有问题!
首先,凤凰出版社(即江苏古籍出版社)从未与我联系、未经我的同意,背着我将我在该社的《金圣叹全集》(简称周本)的选题和出版成果转送给陆林。陆林的《金圣叹全集·后记》明确表示袭用在本社出版的周锡山“整理之作”,不再“重起炉灶”,将周本作为底本,剽窃抄袭了我的汇编成果和校勘、标点(部分标点,当年由合作者承担)成果。
其次,陆林《金圣叹全集》于2008年12月出版后,由陆林的朋友、学生和责任编辑共3人,撰写了3篇赞扬文章,发表在报刊上。2013年12月15日“江苏社科联网站”因此书“入选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又根据这些文章的内容(并点明出处,见下文),再次赞扬此书,并梳理和归纳全部赞扬文章中提出的优点。此文开始即说:
本书最大特色是:以坚实充分的文献史实研究为基础,将古籍整理与深度研究紧密
结合,强化了整理性学术著作的研究内涵。
这个总体评论,完全是违背事实的。评论说“以坚实充分的文献史实研究为基础”,笔者已有《金圣叹著作述略》下编的陆林专节(已在中国《水浒》学会的“水浒国际网站”·“周锡山说水浒”专栏发表),经过仔细的分析和论证,批评:“陆林对金圣叹现存的全部著作的版本全部搞错,还漏收《推背图》金批本。对于金圣叹著作不仅没有‘对其作品版本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而且因不懂版本而出现了众多的错误。”因此根本谈不上“以坚实充分的文献史实研究为基础”。
这个总体评论接着又说:“将古籍整理与深度研究紧密结合,强化了整理性学术著作的研究内涵”。事实是陆林从事的是金圣叹的外围研究,他从未涉猎过“深度研究”。陆林发表的文章都是关于金圣叹的生平事迹和交游的探索。这都是外围研究。金圣叹作为评点文学的最高峰、美学大师,研讨他的美学思想,给以宏观和微观的、具体和深入的、全面和新颖的研究、评论和总结,具体指出他在中国和世界文学批评和美学领域内在那些方面取得了领先的伟大成就,并将金圣叹的这些伟大成果提供当今作家参考,这才是深度研究。陆林于此阙如。陆林的“全集·后记”明确声明:“从事著述的全面整理,无疑会促进深入了解作者本人,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他读了金圣叹全部著作,自认为只不过“促进深入了解作者本人”,于金圣叹美学的研究毫无收获。
2012年陆林跟在自己的学生的名字之后,以两人联名的方式,出版了《话说金圣叹》(约10万字篇幅),列入《人文社会科学通识文丛·文学江苏读本》这个通俗读物丛书中,是一本从书名到内容都明确显示是介绍性质的通俗书,其中说及金圣叹文艺思想的部分文字,当然毫无新颖观点和深刻见解。陆林没有能力撰写金圣叹美学的研究著作,是铁定的事实。
总论说:“与以往出版的金圣叹著述相比,此书整理追求前沿性、学理性和原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按共4个方面)。”根据本文以上的批评,这个赞誉性的论点已经不能成立,再看此文所列举的4个方面,更可论证这个赞誉不能成立,而且这4个列举还正确梳理了陆本的四大学术错误:
一、首次为整理性著作注入个人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彰显整理之作的研究特色。如前言所论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与形成其文学批评特点的内在关系,是作者学术独创,《总集》首次考述有关经历(第6册“年谱”p20-31),介绍了扶乩降神对金圣叹的影响(前言p16-17)。被评为“走在金圣叹研究前沿的前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书评p111)。
所谓“首次为整理性著作注入个人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彰显整理之作的研究特色”,这句话是违背事实的。前已言及,陆林研究的内容是金圣叹的生平(并无突破性的新见解)和交游状况,与《金圣叹全集》的整理没有关系,无所谓特色。接着举出唯一的例子,是金圣叹扶乩活动对金圣叹的影响。并标明发表于陆本前言第16-17页。其内容为:
金圣叹青年时期所从事的扶乩降神活动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其深刻性是无可置疑的。至少因此长期被人以妖魔对待,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鲁迅《读金圣叹》,甚至牵连为其写《天台泐法师灵异记》的钱谦益也“颇受儒者谣咏諑”(《列朝诗集小传•叶小鸾》)。如此境遇,自然要在其心理上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我为法门,故作狗子。狗子则为人所贱恶”,此种令其无法撞头的精神压抑,势必要孕育或强化其证明自己的人生追求,以致于认为即便是“单词居要,一字利人,口口相授,称道不歇”(《第六才子书》四之四总评)亦不失为“立言”,因此而选择文学批评为“盖代无双”(《春感》之七)之业;也势必要孕育或强化其反抗传统的思想意识,一旦从事文学批评後,在选题、心态和方法上,自然会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甚至他对《西厢记》爱情主题的赞美,也是可以在其降神经历中寻踪摄迹的:泐大师在降神过程中遭遇了许多早逝的女性。“凡女人生具灵慧,夙有根因,即度脱其魂,……俱称弟子,有三十余人气均收于虚设之“无叶堂”中;他对叶小鸾豆蔻早凋的“记荆”解释,也颇有同情爱情悲剧、反对包办婚姻的意味(《续窈闻》)。这就难怪其对《西厢记》中莺莺“小儿女又稚小、又苦恼、又聪明、又憨痴,一片的的微细心地”(四之三【滚绣球】),有如此洞幽烛隐的透视了。这或许就是常熟王应奎为何说“圣叹自为卟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柳南随笔》卷三)的原因吧。
![[转载]陆林《金圣叹全集》及其评论的四大学术错误 金圣叹全集txt下载](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100645t01bb05108a5ca634da.jpg)
这段论述,逻辑混乱,内容零碎,结论荒谬。
众所周知,金圣叹将六部经典著作称为“六才子书”,发愿予以精心评点,是出于宏扬优秀民族文化的时代责任感;目的是将经典著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用宏观和精细相结合的分析和评论的方式,帮助读者欣赏,启发和指导作家提高创作水平,推动中国伟大文化的发展。其恢弘的抱负和远大的目标,在其《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诸序(包括《恸哭古人》和《留赠后人》)与两书的《读法》中,做了充分表达,并对读者和后世作家作了殷切期望和具体指导。
而陆林却舍本而求末,不着边际地将金圣叹贬低为因抗拒贬视自己的对立面造成的“精神压抑”,从而“势必要孕育或强化其证明自己的人生追求”,即为了抗拒“精神压抑”和一己私利的“人生追求”,而批书评书。这完全是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论点。他无视清初至民初众多的精当评价,独独采信“圣叹自为卟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一语,不确当地作为自己错误论点的支撑,是无力又无理的。
金圣叹是一位有宏大气魄的思想家、理论家,他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明确宣布:不能让大君出头,要让百姓出头,藐视皇帝,为民请命。他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和宏大的气魄,因此根本就藐视这些贬低自己的各类凡夫俗子,对他们的任何污蔑和攻击,在自己的著作中置之不理,不置一词,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名山事业——文学评点。陆林有什么根据可以这样随意贬低金圣叹?
金圣叹对自己评批《水浒传》艺术成就的重大意义抱有非常明确和正确的自觉,他说: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今
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
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
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呜呼!《史记》称五帝之文
尚不雅驯,而为荐绅之所难言,奈何乎今忽取绿林豪猾之事,而为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
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楔子总批)
他明确指出自己因为古人著书之艰难,今人无力领会精彩处,故而有此书之批,以指导读者阅读和作家写作。
另外,金圣叹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读法》中说的非常明白:他对崔张爱情的赞赏是对原作高明、准确、有力的描写的肯定。而且他在《读法》中强调:“《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圣叹便说,此一个人即是天地现身。”“想来姓王字实父此一人,亦安能造《西厢记》?他亦只是平心敛气,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总之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
陆林违背金圣叹《读法》的主旨和精神,毫无根据地将叶氏女子的一个非典型的“自由爱情”的例子,作为《金批西厢》的评点的根据,岂非荒谬。
金批与反对包办婚姻无关。金批《水浒》中,金圣叹对反对包办婚姻而红杏出墙的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皆抱批判态度;对宋江包办矮脚虎王英和一丈青扈三娘、花荣妹子与霹雳火秦明的婚姻则持赞同态度。
可见陆林对金圣叹评点的原文很不熟悉,他只能做一些金圣叹的生平事迹和交游一类低层次的考证,无力记住、更未能理解金圣叹美学的重要观点和精义,故有此不着边际、水平失准的评论。这样的“最新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特色”,只有那些对金圣叹缺乏研究和不懂学术规范的人,才会给以违背事实的高度肯定。
周作人《谈金圣叹》说,金圣叹少年时期的扶乩行为,“不知为何在他各才子书批评里却看不出一点痕迹”。笔者在《周作人的金圣叹评论述评》一文中指出:由于周作人是信奉科学、反对迷信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因此“周作人没有注意到金圣叹在《金批西厢》的批语中还是谈到过读书要‘通鬼神’,这便是痕迹。”
陆林不懂:中国古代文论、美学家认为极少数作家、学者在化出巨大努力、从事艰巨创作和研究的基础上,又因有了这个基础而“通鬼神”,从而取得极大的成就。因此陆林也看不出扶金圣叹的扶乩经历对他的评批著作的真正影响。至于古代经典名家的类似论说,举例来说——
在金圣叹之前,例如同处晚明而时间稍早的大书画家董其昌说:
作文要得解悟……妙悟只在题目腔子里,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
文》)。
与金圣叹同时的戏曲家、戏曲理论大家李渔在评论金圣叹时说:
圣叹之评《西厢》,……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期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之,神所附者耳(李渔《闲情偶寄》卷三词曲部,格局第六《填词余论》)。
金圣叹之后的史学大家章学诚认为自己思维活跃,读古人文字,“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原因在于“若天授神指”“(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
古人所谓“通鬼神”,指的就是灵感来临。古人认为,灵感就是通鬼神的结果:“灵感的灵,繁体字靈,从巫。《说文》:‘巫以玉事神’,曰靈。照许慎的解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型。’所以灵感这个词的翻译,可谓与柏拉图时代的含义相近”,“一是有通神的意思”。“二是与巫有关。”(朱狄《灵感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他》,彭放编《灵感之谜》第23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金圣叹还说:“《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西厢记·读法》六十二)”
古今修炼者认为,人与鬼神相通,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巫,或道行高深的修炼者;二是火。点香,即通过香火与鬼神相通。
金圣叹绝不会贬低自己为“装神弄鬼”,更不会自认为借此愚弄别人,骗取声名和利益。他自认为通过修炼或某种机遇,掌握了某种能力或通道,与鬼神相通。这得到钱谦益、叶绍袁全家和众多高层人士的认可,并受到高度评价。一般人可以通过火、香烛之火与鬼神相通。这在古代是一件非常严肃、尊严和高尚的事情,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教导,我们对研究的对象,对古人,要有理解之同情,而不能轻薄为文,随意否定和贬低。金圣叹、董其昌、钱谦益、李渔都是一代大家,他们的这种认识有其宏大的神秘文化背景和探索创作途径的高深用意。叶绍袁与其沈夫人、叶小纨等,亦皆一代才子和才女,不是随便可以欺骗、亵渎的。今日名家杨绛、王安忆、刘彦文等皆有名著和文章(杨绛在2007年于九六高龄出版《走到人生的边上》,商务印书馆2007;并获文津图书奖。王安忆在《中国西部文学》刊载与名教授张旭东的对话、年过九十的华东师大教授刘彦文于2012-2013年在上海《东方早报》发表多篇长篇系列文章。)发表了他们对鬼神真实性的见闻和见解。2013年2月4日光明网转载人民网刊登的国外报道《英国最后的女巫:因预测太准二战中被处“叛国罪”》说:在现实世界中,女巫是真实存在而充满神秘的“职业”。据说,她们拥有神奇的本领,能够与灵魂进行对话。英国著名女巫海伦·邓肯有着响亮的名声。至今,英国人提起她时,脸上仍然会表现出一种好奇而又神秘的表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通灵,使海伦·邓肯名噪一时,同时也为她多舛的命运埋下了祸根。1941年底,她为不幸的母亲招来其作为海军士兵的儿子的灵魂,详述他牺牲的过程和英军损失的舰艇、兵员的精确数字,英国政府以泄露军事机密的叛国罪将该女巫逮捕并判刑。近期,苏格兰议会向英国内政部提出为“英国最后的女巫”海伦·邓肯平反的请求,邓肯和其他大约4000名女巫可能被宽恕。这在英国引起了广泛关注。
对于此类灵异事件,在当今如此宽容的学术环境中,我们即使不相信,也应尊重前人和今人的探索,予以客观记叙,而非未经反证就随意否定,甚或暗寓讽刺嘲笑。
金圣叹的扶乩活动和读书、创作“通鬼神”,在我国更有着宏大文化背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古代学问精深的知识分子都能掌握,因此当时知识精英都相信和尊敬。当今也有不少学养精深的知识分子也能理解。为陈述方便,我借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1月版,北京中华书局将出简体字版)的论述来做简要说明。余英时先生在此书中指出:
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是礼乐传统,而礼乐来源于祭祀,祭祀则从巫觋信仰中发展而来。“礼乐是巫的表象,巫则是礼乐的内在动力。”“天人合一”和“绝地天通”是互相冲突的,但由于“巫”有特别技能,彼此隔绝的“天”与“人”之间就有了联系。《国语·楚语》指出,“巫”是古代社会中具有智(能上下比义)、圣(能光远宣朗)、明(能光照之)、聪(能聪彻之)的特征的人,只有他们可以“降神”。“巫”是一批超越寻常,有特别知识、道德和能力,可以沟通神与人、天与地之间的精英,这些天赋异禀的巫,不仅成为中国古代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也逐渐在后世转变为负担着精神世界的知识阶层“士”。(锡山按:所以古代医是巫医,史是巫史,即医生和史家都是由巫担任的。司马迁的祖先就是巫史。)沟通天地人鬼之间的“巫”,需要“受命于天”,得到“天命”,托庇“鬼神”。
在此书第五章《孔子与巫传统》中,余英时先生引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的《要篇》中孔子所说的“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并进而指出,后世儒家之君子,把“天命”、“鬼神”这些外在于人心的神秘力量,转换为超越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责任(道、仁、弘毅)。
陆林不懂这些高深的知识——不懂金圣叹、董其昌、李渔谈读书创作的“通鬼神”的来龙去脉和深意,不懂金圣叹扶乩经历对其评批著作的真正影响在于“通鬼神”与灵感理论,才会作他的这番错误而粗浅的分析和评判;更严重的是在写作动机、人生追求和胸襟情怀甚至人格道德上贬低了金圣叹,还自认为是“个人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彰显整理之作的研究特色”。
二、首次依照现代学理,科学分类编排各体著作,以适应研究需要。金圣叹现存近20种著作,内容繁富纷乱。新编全集,将现存已知著述250万字归结为三大卷,是以学理为依据、以方便研究为目的的富有创意之举。“全书编排允当,层次明晰,从中可见辑校整理者的良苦用心……对中国古代其他作家作品的搜集整理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书品》书评p35)。
这是根据陆林《金圣叹全集》的责编吴迪的书评写的吹捧文字。1985版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的《后记》说:“为方便阅读,全书以形式分类,第一、二册为小说评,收入金批《水浒》;第三册为戏曲评和古文评,收入金批《西厢》、《天下才子必读书》和《才子书汇稿》中的古文评批和哲学论著;第四册为诗歌评和圣叹自己的著作,收入《唐才子诗》、《杜诗解》、《才子书汇稿》中的诗歌评批和《沉吟楼诗选》(《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88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陆林的“全集”袭用其本社1985年出版的《金圣叹全集》的这个创意,将全书分为“白话小说卷”(即“小说评”)、“诗词曲卷”(即“戏曲评”和“诗歌评”)、“散文杂著卷”(即“古文评”、“时文评”和金圣叹自己的著作)。同样的分卷思路和方法,却自称为“首次”。因怕落到“抄袭”的罪名,就大局不变,略作个别归并,却反显凌乱。尤其是“散文杂著卷”,“时文”不能说是散文,而金圣叹的精彩哲学文章和一些诗文创作,用“杂著”来统称,也失去郑重和规范的意味。吴迪的文章对陆林乱作吹捧,抹杀其本社的前辈编辑的成果,很不应该。
三、首次对金圣叹所有著述,均以现存最早版本为底本,参校后出的主要版本,加以校勘。因金圣叹著述曾遭禁毁,原刻本甚为稀见。本书以充分的文献调查为基础,网罗其著述的现存最早版本,其中大多数是原刻本,解决了一些向来悬疑的问题。有关校理已非单纯的文献比勘所能做到,“而是整理者同时又是研究专家的身份,在古籍整理过程中特有的优势呈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书评p111)。
陆林《金圣叹全集》中,有多部著作不是现存的最早的底本,例如《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和《天下才子必读书》,拙文《金圣叹著作述略》(已于中国水浒学会“国际水浒网络”发布),皆已提示和指出:陆林根本不知其现存的最早底本藏在何处,其所收的根本不是现存的最早的底本。
四、首次收集整理了20万字的《小题才子文》、搜录散佚诗文35篇,首次在正文后编著了近19万字的《附录》,分为《年谱简编》、《著作序跋》、《传记资料》、《“哭庙案”史料》四个系列。分类得当,方便研究。其中《年谱简编》约4万字,“对金圣叹生平、交游、创作等各个方面的事迹搜罗完备、考订翔实,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中国新闻出版报》书评),为金圣叹研究提供了许多新史料。
首次“收集”《小题才子书》的是黑龙江学者梅庆吉,首次整理《小题才子书》也是梅庆吉。梅庆吉先生最早发现、收集此书,并在报刊上宣布了他的这个发现贡献的报道。他将首次收集、整理的《小题才子书》,在1990年代初期即向凤凰出版社申报了选题。陆林和凤凰社掩盖事实,吹捧自己,是令人吃惊的。
至于陆林“全集”书后附录的都是常见的资料,学者专家都已拥有,完全是旧资料,因此对他们无用,却吹捧为“新史料”;而对于一般读者也无用,他们需要的是用简洁的语言作一番精当的介绍,而非冗长乏味的文言文详尽记载,他们更需要的是对金圣叹评批的精当评价和提示,陆林却没有能力做。
至于陆林《金圣叹全集》的其他错误,拙文《金圣叹著作述略》下编已有论述,兹不重复。这里需要再次指出的是:陆林在其“全集”的《后记》中说:
从事著述的全面整理,无疑会促进深入了解作者本人,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只是如果案头已有前贤的整理之作,很少有人会另起炉竈重开张,我也不例外。庆幸的是,正是通过三年来围绕金圣叹著述的系统整理、反复校读,对其作品版本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
陆林承认其“全集”没有“另起炉灶”,即全部袭用了“前贤的整理之作”——1985年版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凤凰出版社)周锡山《金圣叹全集》的成果(这个承认,已经推翻了3篇吹嘘文章和江苏省社联对陆林“全集”的全部吹捧文字)。至于陆林说:只对作品的版本“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前已指出,陆林对金圣叹作品的版本的认识全错。
检阅此书,单以《金批西厢》为例,其标点错误也很多,《中国知识产权报》调查后也在其第一篇报道中特作指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