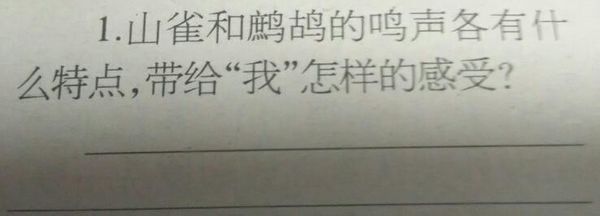瞿元立,名汝稷,苏州常熟人。学通内外,尤尽心于佛法。时径山刻大藏,元立为文导诸众信,破除异论,其言曰:
世之诞佛者,皆比于范缜之神灭也,而神灭非圣人所立教也。夫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即心也,即道也。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圣人所以参赞化育者也。是岂形之所及也?唯圣人为能穷神,而庸愚固未尝亡,特不知其即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则一狥于形,于是遗范围天地之广大而自局,弃曲成万物之微妙而自秽,终日役役,不过耳目口腹。圣人愍焉,故喻之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谓之道,复虑人之自画而高远之,谓非己所及也,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尧之所以尧,穷此神也;桀之所以桀,昧此神也。是神者,溯之无始,推之无终,岂形生而始生、形灭而随灭哉?形有尽而神无穷,故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而缜之言曰:“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生而神生,形灭而神灭。”藉如缜言,操则存者存形与,舍则亡者形亡,与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百髓九窍六脏,谁为然与?心不在焉,视而不见;梦说筑岩,岂目所瞩?处今而忆昔,在吴而知越,何形之能然?缜亦不思甚矣。缜之言,使人重形而遗神,沦胥以溺者也。谓形即神,则舍形无我,舍形无我则凡形之所欲皆我之所欲,而以礼义维之,是强也,是外铄也。神不灭而谓灭,则尧桀均尽,颜跖均生,均生则纵逸者自适,均尽则好修者徒劳。于是示之以余庆,戒之以百殃,则见以为茫昧而难征也;揭之以仁义,则以为仁义撄人心;揭之以性善,则以为性恶,则以为善恶混,几何其能信之?于是聿皇得丧,徽缠贪毒,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沉瀹昏衢,莫能自出,旋复流浪,为苦无已。
如来智入三世,圆应众机,五时说法,海墨不可胜纪。其流入震旦者,才海墨之一滴,是为今一大藏。其语报则征之三世,其语性则尽之妙觉。知三世之报,则尧桀不均尽;知性觉之妙,则性善无所疑。故下焉者得其说,必惕于三世之报,恶不俟惩而革,善不俟劝而行矣;上焉者得其说,则妙契性善之真,居仁由义,若耳听目视,何有撄我心哉?是以圣贤之教得如来而大畅。惜哉!缜之不讲,谓神灭形灭而诞佛也。惟如来之教,能穷此神之广大微妙。语其大,则天地者,无尽大海之一沤耳,元会运世者,无尽时劫之一瞬耳。语其妙,则无声无臭,此之空谛也;精一执中,此之尸波罗密也。一言演为无量义,竟古今而推之,莫能竟也。儒佛之是非,黄老之秘密,与夫百家之雄辨,一言蔽之而有余也。佐尧而尧,佐舜而舜,父以之而慈,子以之而孝,护法以之而护诸众生,帝释以之而离爱,梵天以之而胜慧,二乘以之而回向真乘,菩萨以之而证入妙觉,四圣六凡,无根不被。故其言必至于海墨也,河沙妙德罔越穷神,故其要必归于一乘也,世出世法莫不竭尽无余矣。
南朝时范缜曾著《神灭论》,曰:“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生而神生,形灭而神灭。”
《易经》曾 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瞿汝稷认为,所谓神,就是心,就是道。形而下者,能生能灭,形而上者,不可说生灭。并以此非难范缜之说。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范缜所谓的“神”究竟何所指?如果范缜所说的神,就是指形而上之道,则范缜所说自然是错误的,而瞿汝稷所说是对的。如果范缜所说的神是指心,而心又有真妄,真心自然无生灭可说,妄心则有生灭,则范缜所说未必全错,而瞿汝稷所责也未必全有理。何以故?凡夫众生不识真心,皆以妄心为神,此神固有生灭,人生而有见闻觉知,人死则无见闻觉知,此亦普遍经验所共知者,范缜谓形灭而神灭未尝不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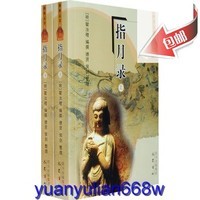
这里的关键,就是对“神”这一名的定义如何。自古以来,很多不必要的争论,皆由所论之名的不同所指而导致。如果两人说的不是同一回事,又何争论之有?只有两人所说同为一事时,谈论才能相应,否则尽成戏论。
范缜所谓的“形”与“神”究竟何所指呢?
形,即指人的肉体;神,即指人的识心。
从佛法来看,此肉体本是四大假合,终将坏灭;此识心也念念生灭不住,不可把捉。识心与此色身诸根,如同交芦,相依而存,一亡俱亡。从这个角度来看,范缜说形坏而神灭,未尝不对,未尝不符合佛法。
只是范缜毕竟是教外之人,其说只代表了世俗人对此身心的一种普遍认识,不能识得不生不灭之真如佛性,故以此虚妄识心为神而论生灭,故其为学终归于断灭而无所归宿凭依处。如佛所说,只得半偈,不亦可惜乎?!
佛所说半偈者,即雪山童子曾从古仙人处得到半偈,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无疑非常正确,而有重大价值,但单凭此半偈,是无法了脱生死的,故雪山童子乃至愿舍此身来交换其另外半偈。范缜所得者,正是雪山童子所得的上半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