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派纪录片人系列访谈之二十 《红跑道》:谁人的起点谁人的梦
——纪录片编导干超访谈
刘 洁 片 名:《红跑道》 (The Red Race)
片 长:70分钟
类 型:人文类纪录片
导 演:干超(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
摄 影:龚卫、朱骞(使用机型:HDCAM750)
剪 辑:巴斯•洛特林克(【荷兰】Bas Roeterink)
副导演:黄瀛灏
完成时间:2008年
获奖情况:2009年获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The George Foster PeabodyAward),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白金奖;2008年获得美国电影学会银泉纪录片节(AFISILVERDOCS)评委会特别奖,巴塞罗纳国际纪录片节大奖,萨格勒布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上海电视节最佳社会类纪录片奖等12项国际奖。
梗 概:在上海某所少体校,一群6-8岁的练体操的孩子,如邓彤、王露凝、大双和小双、阿南、吴畏等,他们背负着亲人们太多的希望,承受着超出同龄孩子的苦痛,每天在他们的教练俞指导和黄指导的严格甚至是严酷的训练中跌跌撞撞地或挣扎、或无奈、或不知所措地成长着……然而,慢慢地一种自主的责任感悄然萌生。影片的结尾处,在黄浦江的轮渡上,外滩的霓虹灯远远地映照着,邓彤说想变成美人鱼游到北京,可转念一想“我的体操怎么办?”
纪录片《红跑道》编导干超
【访谈背景】
《红跑道》就似一个寓言。
它并不是一部地域性很强的纪录片,而是一部能够刺疼观者的最共通的脆弱之处——茫然挣扎的今日与不知何往的未来。臆想着种种生命的出口,为他人,也为自己。
2004年,通过纪录片《房东蒋先生》,我熟悉了干超。那时,26岁的干超刚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Bristol)戏剧系硕士毕业不久,便在他供职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与自由摄影师梁子合作完成了这部好看的纪录片。2007年,他又完成了纪录片《刚开始的旅程》。
《红跑道》是在画外俞指导的呵斥声中展开的,画中是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翻落在红地毯上,不知所措。这正如《房东蒋先生》的开场,在画外的梁子一声紧似一声地追问下,蒋先生的不知所措。
似乎干超更在乎被话语追责下的人的状态。其实,无论蒋先生,还是这些少体校的孩子们,甚至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常常被命运的轮转追责着……干超在导演阐述里这样说:“表面上,《红跑道》讲的是练体操的孩子和他们家庭的故事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但把孩子作为观察的主体而不是沉默的客体,观察孩子们如何在大的环境和体制下形成自己的人格。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值得记忆的起点,但我们最终成为今天的我们,是因为我们都走在一条没有尽头、也没有退路的跑道上。那么,这条跑道是由什么铺成的?”
追问,正是一种方向。在《红跑道》的展开中,面对孩子们强忍着的巨大痛苦与一次次挫败后的空洞茫然,面对教练们近乎无情的严酷,以及家长们深切期待的沉重……这一切似乎都命中了那句话——每个人都构成了他人的生存环境。
这是一个宿命,又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谶语。 受访者:干超纪录片编导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副总监
访问者:刘 洁 中国传媒大学
时 间:2009年2月25日
地 点: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办公室 充满期待的命运出口 刘我第一次看到《红跑道》是在2008年12月的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当时没看到全片,只是片花儿。
干 是个德国人放的吧?他们有些投资。她放的那个版本跟你现在看的不太一样。
刘刚开始,觉得《红跑道》可能表现的是这些孩子们正在经受着的一种比较残酷的童年,但是现在看了两遍之后我反而没词了,我觉得特复杂,不是简单地用一个词能概括得了的,有点像一种命运的寓言——我们劳神费力地拼了半天命,前途是什么?明天是什么?谁都不知道。
干在国外展映的时候,有人问我对这种培养人的体制怎么看。我说我肯定是不喜欢的,但问题是荒诞就在于此,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有点像这样,你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它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当代社会的生存方式。
刘就好像你没办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每个人都脱离不了他的生存环境和时代环境。
干这和蒋先生有些像,整个世界都在变,他一个人守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到最后还是逃不了,还是给揪出来,这是一样的。
纪录片《红跑道》剧照
刘 当初怎么想着要去拍少体校的这些孩子?跟奥运主题有关吗?
干这个倒没想到,只是后来才觉得无意当中扣合了这个主题,同时还和市场需求契合了。德国人为什么投给我钱,就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市场因素。
刘是啊。湖北电视台的张以庆早期拍了一部纪录片《红地毯上的日记》,也是纪录体校的这些孩子的。黑龙江电视台的王冬冬曾经也拍过杂技团里的一些孩子《化蛹为蝶》。虽然大家的拍摄角度,表现方法都不同,但共通的是:关注孩子们的命运,映照观者的命运。你的初衷呢?
干当时,我就想拍一个小孩的东西,想回顾一下自己小时候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写一篇文章,说一两句话就可以表达清楚的。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卢湾区少体校打羽毛球,有一次没场子,无意中走到一间体操房里,一看就蛮震撼的!这里全都是红的,红地毯,四周挂满国旗,标语也是红的。这里有好多好多小孩在叫闹着,还翻着跟头,最小的孩子还光着屁股。其中,就有邓彤他们这些6、7岁的孩子,看得出来他们已经训练了一些年头了。当我看见,有几个孩子边练边哭,心里就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就这么决定,拍一拍这些孩子。
刘 面对一个群体,总会有一些人和事慢慢冒出来吧?
干一上来,我们就拍了一个镜头,很漂亮!邓彤,就是片子里那个老爱哭的小女孩,她边哭边在平衡木上做动作,因为体操房里有镜子,我们就从镜子里的邓彤摇下去,正好摇到两个特别小的小姑娘在镜子前正摆弄着自己的小辫子。这让我觉得有一个历程的东西在里边。
刘是啊。就像我们也有这么个“历程”,转瞬就包含了成长。邓彤后来成了《红跑道》的“主角”了。
干后来,我们到邓彤家里去了一次,那个地方特别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她爸爸也不上班,妈妈在超市里做点事。这小孩子特别懂事,说长大以后要给爸爸妈妈买大房子住。
刘 这种反差就使题材本身有了意味。
干那时我还看见有两个小姑娘在哭,我就问其中一个为什么哭?她说手很疼,我一看手全部都破了,我说那么疼,还练体操干嘛?她说我喜欢体操。这时教练并不在旁边,我觉得她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这让我蛮受震动的。后来,我了解了这些小孩的身世,他们特别纯真,但是背后心酸的东西特别多。有的父母离异,有的家境贫困。有个小姑娘的爸爸是发广告小传单的,他们住在地下室,妈妈在新疆,她已经有四年没见到妈妈了,教练说她父母早离异了。
纪录片《红跑道》剧照
刘 那个漂亮的王露凝也是这样的,看了让人心里不太舒服。
干这个小姑娘从小实际上是被邻居领养的,领养她的那个“外公”一直在培养她,还叫她去考什么演艺班,可王露凝说自己喜欢做体操运动员。
刘大小双、阿南,还有那个横劈着叉,同时又被俞指导坐压在身上的吴畏,这几个孩子也是慢慢“浮”的?
干其实第一眼能看到的就是双胞胎兄弟,俩都拖着个小辫子,长得不像,性格也不像。小的非常精明,是队里成绩最好的,大的大大咧咧,敢和教练顶嘴,有点幽默感,是队里成绩最差的。那个吴畏我特别喜欢,很聪明,眼睛特别小,一笑还三角眼,教练觉得他将来是可以进国家队的,但是他的故事我挖不出太多。
刘 我倒是因为阿南的妈妈记住了阿南。
干阿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正好在拉单杠,我就跟俞指导说,这小孩练得肌肉很发达的,教练就把他叫过来说,你把衣服拉起来,给两个叔叔看看你的肌肉,他莫名其妙地就哭了,大概两个小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哭。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后来教练跟我说,他家是从广东潮州过来的,在门口开了个小超市,日子过得蛮清苦。他有两个哥哥,都在俞指导这儿练过体操,而且都还拿过市里的金牌,可是送到市队去不久就突然给退下来了,原因很复杂。让我觉得惊讶的是,他母亲竟然不顾一个、两个都没有培养成,还要送来第三个,这倒是有些戏剧性。阿南这么哭个没完,是不是因为压力全在他身上,是最后的唯一希望了。
刘 这种希望,真是有些悲凉。
干但是,平常你在他们脸上不一定能读到这些,反而看到的是一种阳光、坚强、成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去了两次就喜欢上这些小孩,两个教练也比较有性格。
刘就是那个俞指导和黄指导吧。那两位教练好像并不避你们的镜头,孩子们都被他们“吼”呆了,还要被体罚,好多人看了都说教练太厉害了。
干我觉得他们真不装,特别是那个黄指导一点都不避讳,说她们原来训练的时候比这狠多了。开始,我们也觉得她特别凶,拍了一个月以后,就觉得他们的训练就是这样,她人倒不坏。那个男教练俞指导,虽然也“吼”人,但也是蛮可爱的,他心情好的时候会跟孩子们搞笑。他从来没练过体操,有的教练看不起他,说他是学院派的,可是他教出来的学生,成绩又是最好的。
刘 他们看了《红跑道》以后有什么反应?
干 之前,少体校领导要来审片子,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剪了一个“阳光版”——孩子没什么压力,很快乐的样子,题目也改成叫《希望》。片子看完,那个女教练跟我说,我平时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东西,不真实。她说我不可能为了拍片子就改变什么。 凝视人物的表情状态 刘 选题确定后,在具体操作上有些什么不一样?
干创作《房东蒋先生》那会儿我和梁子都是专业地在做这件事,可是现在我没有这个时间了,每天都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不可能完全被动地去跟拍。再加上我看过一些国外的纪录片,他们的拍摄方式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值得我们借鉴。开拍前,我们去观察了一个月,准备工作做得蛮充分的,所以并不想盲目地跟拍。
刘拍摄中要有很强的计划性,这是由拍摄经费、制作周期,以及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允许时间等等因素构成。我们不少纪录片人,特别是独立导演容易忽视这一点,大多是随着被拍摄者的进退而进退,有时拉得时间和战线都特别长。呵呵,比如我,拍长春观就拍了一年。
干呵呵,每人的做法不同。换个角度说,拍体育类的这种片子有两个特点:一是,体操有行动、有动作,从视觉上很好看。二是,它是封闭性的东西,从训练到最后比赛、出结果,在固定时间里就可以完成。如果我不知道三年、五年还是七年到底会怎么样,我就没法拍了。
纪录片《红跑道》剧照
刘 你拍了多长时间?
干这个片子,我们基本上是利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拍出来的,六月份开始,十月份结束的。
刘 是2007年吧?
干07年初就想拍了,但从有这个想法,到真正开始拍摄,其中涉及到体育局、少体校等各方面的关节,有些事情还需要去申办。
刘《红跑道》的片头很有意思,墙是红的、地上是红的,画面很好看,那些小男孩一个接一个翻进画面,那位俞指导在画外呵斥着每一个孩子,孩子们茫然的表情……那是你们搭的景?
干不是的。地上是红地毯,墙边立的海棉垫也是红的,大概怕小孩子撞到墙壁。那时我们无意识拍了这个场面,后来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拿它做了片头。
刘那个红跑道让人感觉就是一个功利的跑道,同时又让孩子充满着希望。是多种东西掺和在一起的。
干 对,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多义性。
刘你和摄像有没有一个磨合期?整个片子画面拍得特别冷静。比如说,教练在画外大声说:“膝盖打弯了!”镜头绝不会摇到膝盖上,也不分切其他画面,而是非常肯定地依然对准孩子的表情。还有好多处,无论画外音怎样说,镜头都特别肯定落在人的表情上。这一点是开拍前就设计好的吗?
干这本来就是我们想好的。龚卫是我们频道首席摄像,以前合作过,彼此都还蛮熟的,朱骞也拍了一部分。目前,体育类的很多片子大都是动感很强的,被拍的人在动,镜头也是晃的。只是,我和龚卫的性格相对都比较沉静一些,这些年我也看了不少国内外的片子,感觉单镜头可以有很多内涵。于是,我们想在一个镜头内,看看到底可以传递出多少东西。这样的拍法可能比较冷峻,但它会让你逼视某样东西。就像北京有个画家,他画了很多文革时期的一些人的头像,比如矿工,都是画得和毛主席的头像一样大。当这些画全堆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种意识,有一种气场的感觉,你或许就会把心态放下来,有机会平视地去看他们。
刘看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就有这种感觉。天安门广场,多嘈杂!对一个老外来讲,满是新鲜,但是他不拍别的,就盯着人的面孔。这种“凝视”人的表情状态,在《红跑道》里特别明显。
干嗯。另一个原因,这个片子是用高清大机器拍摄的,通常就只有我和摄像两个人,我要举话筒,另外还要拎着一个监视器,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话筒都弄坏了好几只,老挨他们骂。而且大机器很难弄,你要我们跟着跑,还真没这个本事,如果跟不好的话,还不如安静下来。
刘 呵,这无意中倒形成了一种风格。
干对。龚卫自己也想实验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用这种方式去拍片子。我们想好不加解说词,要尽可能让这些镜头不是完全被动地跟着被拍摄者跑,其中要有一个主动的姿态在里面,只是呈现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没法控制。
刘在《红跑道》里,很难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好几处都听到家长或老师的画外音:“笑一笑,笑一点好看,高兴点”,但是从头到尾很少看到孩子发自内心的一种灿烂,没有。这是你拍摄或者剪辑的过程中有所选择,还是别的什么?
纪录片《红跑道》剧照
干我并没有刻意去做这样的选择,还是希望中性一点。因为我一直觉得,即使再苦的地方也应该有幸福的东西,哪怕是早上有一缕阳光照进来。如果有一点小小的温暖,这些孩子都会反馈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拍摄邓彤他们上画画课时,我调整了一下。邓彤的画不是画得最好的,我就请老师把金奖的奖牌发给她。因为观众总看到她被骂,或者被打,在家里她也老是哭。奖牌给了她以后,她特别高兴,就独自跑到隔壁的体操房去照镜子,还鞠躬什么的,我们开始没发现,是后来才跟过去拍下了这一幕。
刘她挂着金牌,面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整理着头发,这时有音乐衬着,挺温暖的感觉。邓彤的表情里有一种满足感。
干这个小孩你看她表面上木讷,其实内心特别丰富。我一个朋友看了后说,他很喜欢邓彤的那种表情,有一种倔强。
刘你让老师把金牌给邓彤,这么做,不怕被人说成是“不真实”的?虽然我认同这是一种催化作用,因为此刻你纪录的重点并不是谁的画真正画得好,而是要纪录这种“催化”下的反应。
干给她奖牌是我“导”的,我始终都承认。导演也是有人性的,否则我拍这样一个东西干嘛!训练要排名次,连画画也要搞个比赛,如果单纯这么拍,其实是重复的。因为我不是拍单纯的教育问题,我是以孩子为主体的,想让孩子有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
刘或许这更符合一种观众的心理真实。当然,任何一个创作都是创作者和被反映者共同来完成的。这还看出来了你内心的温暖和某一方面的脆弱——不忍心看到那个孩子面对这么残酷的现实。
干 呵呵,实际上《红跑道》反映出来的东西已经比现实要温和多了。
刘 你们总共拍了多少个小时的素材?
干 大概60个小时。
建构故事的推进阶梯
刘《红跑道》没有那种严丝合缝的故事情节,没有表面化地去“讲述老百姓的故事”,都是生活碎片。但是,片子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饱满,非常有质感,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你在剪辑的时候,一定不容易吧?
干很难剪的,因为当中人物太多了。如果仅仅是一些过程性的东西,如比赛、训练什么的,这倒不难,难的是这里面包含着许多社会问题。你说这个片子像个寓言,是因为每个场景都有一些意思在里面,这不是我强加的,观众看到这儿也会想到一些东西的。这种情节不容易建构,而人物的建构就更难了。
刘 对,特别是一个群体。
干我不像有些导演可以天天守在拍摄现场,一个事情发生以后就可以从头到尾地惦记着,我们就不行,所以拍之前就要想清楚。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教练对双胞胎的小辫子很不满意。他说了很多次,双胞胎和他们的爷爷一直都没有动静。但是到了比赛前夕,爷爷突然有一天电话我,说要帮两个小孩子把辫子剪掉,让我过来拍一下,留个纪念。有了一头一尾,当中正好还有一些过渡性的情节,这样大小双的性格就很自然地表露出来了。比如说大双和国旗拍照的事。
刘就是男队在训练小测试中,按排名每个人可以得一份小礼物,大双最末,没有礼物,只能和国旗照张相。后来我们看见照片上的他,一脸的落寞。
干前面你必须要有一个引子,然后大双和教练犟嘴,以及大小双和爷爷生存的状况,包括小双念爷爷的“劳动模范”证书的磕巴状态,这些东西本身都是一个一个的推进的阶梯。
刘 对,说得好!在结构这类片子时,建构推进的阶梯特别重要。
干包括邓彤也是这样的。一开始在船上,她让你感觉到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孩子,她在船上做体操,感觉很美。结尾也在船上,她和爸爸的背影衬托在外滩的霓虹灯下。邓彤说:“爸爸我要到海里游泳”,她爸爸没理睬她。我觉得这话挺有意思,就让她爸爸接着问。她说她想变成美人鱼,要爸爸变成大海龙,游到北京去。她爸爸问到北京干什么?邓彤说,想去逛街买东西吃。爸爸说,应该去北京看奥运会。这时,邓彤一脸心事地说:“那我的体操怎么办?”
刘这句话挺感人的。忽然你就会发现这孩子哭了半天,实际上这些让她痛苦的东西早已经在她的心里扎根了,这个最让人难受。
干她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和体操都有关系了。其中变化的东西有吗?有的。开始是希望,到最后是一个被锁住的希望。这当中,是什么东西在束缚着她?训练受挫,家境的逼迫,画画得了金牌。这就有一些起伏,你从中就能开始理解这个小孩,她为什么会说出最后的那句话。
刘 每个小孩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样?
干 是的,包括阿南也是这样的。
刘除了建构故事的推进阶梯外,《红跑道》还将各种生活碎片归置成一个个团块,比如训练场、场外生活、家庭场景,而且团块与团块之间相互勾连,层层递进,这样有利于观众在观看时不至于掉到一堆生活碎片里,不知其衷,难解其妙。
干 是的,如果现在再去拍,我就会更加强化这种勾连感。
纪录片《红跑道》剧照
刘比如说,一开始,俞教练就说大小双的“小辫子”是什么玩意!让他们回去跟爷爷说把小辫子剪了。同期声里说到爷爷,紧接着镜头就切到大小双家里,爷爷和奶奶的场景出现。再比如,王露凝的外公说她小时候身体不好,想让她练体操。后面,小朋友们在观看奥运会一周年倒计时的晚会时,王露凝悄悄地对邓彤说:“我的小乌龟生病了,我想让它练体操。”紧接着就切到“急诊室”的画面,阿南的妈妈在打吊针,妈妈跟阿南说你要努力,不要让妈妈失望之类的话。
干看到这里,你就会突然明白了阿南,他身上原来有那么多的责任!之前他一次又一次地哭,俞教练说他妈妈30多岁却见老,而此刻我们便自然感受着他内心的沉重。
刘 这种递进式的推进与勾连,便很好地结构了这部纪录片。
干也正是因为这样,双胞胎和小辫子、阿南和妈妈、王露凝与小乌龟就自然联系在了一起,这有利于观众对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进行辨识。好多老外就分不清楚邓彤和王露凝。我看到一本国外的综艺杂志评论《红跑道》,作者写得很有意思。他说,虽然有的时候一些人在辨认上比较困难,他们好像是一个群像,但是反过来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孩子是被剥夺掉个性的。作者把这种难以辨识,理解成了一种剪辑技巧。
刘 呵呵。也就是说个人背景在这里都不重要了,一个群像更具有冲击力。
干当然,要做到情节的推进与勾连,我们就必须设想好,这些情景该怎么建构,怎么推进,这一点,我们必须向很多外国导演学习。
刘 我也看过一些片子,他们的推进感和预先的设计感是比较强的。
干有一个得了很多大奖的纪录片,叫《英国医生》,澳大利亚人拍的。开拍前,他就很清楚情节的走向,所以3台机器只拍了就拍了16天,40盘带子。一个医生有什么好拍的!而且是一个英国医生跑到乌克兰去行医,这有点像一个好人好事,可他没有这么拍。一条主线非常清楚:某天早上,一个病人从乌克兰乡村出发,要到乌克兰的基辅去找这个英国医生给他开脑瘤,结果可想而知,开刀后病人好了。这没什么,有意思的是有两条副线。他先设了一个悬念,这个医生反复在说当年有一个漂亮的十几岁的小姑娘,得了脑瘤,她妈妈推着她来看病,当时他很有信心给她看好,说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死去。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手术后小女孩全身都瘫痪了。这时,你就会想,现在这个手术能成功吗?
刘 这就首先打破了一个顺拐的故事。
干这时,影片将这个医生手术成功后的落点放在了医生去这个小姑娘家里访问。那个时候小姑娘已经去世了,她母亲斟了一杯酒敬这个医生,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地珍惜生命,而且要很好地活下去。医生在女孩儿墓碑前说:“如果我们不去帮别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又何必活着呢?”这当中又穿插着很多生命感的东西。
刘 这三条线索,其实并不复杂。
干关键是导演事先都想清楚了,是带着本子去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是这么在做的。我总是在想:这个故事应该怎么建构?只是我们做得还不是很成熟。
刘 而且,你片子里的人物多,头绪多。
干是呀。虽然说这几个人物线索都是有递进的,但怎么穿插呢?如果一开始三个人都出现,然后再分头叙述,观众可能会记不住,搞不清谁是谁;而如果你一条线一条线地讲,这又很拖沓。之前我们找了一个剪辑师,工作了很长时间,剪出来一个四个小时的本子,大家看了以后觉得有些拖,观众也无法接受这么长的片子。 营造画面的自然语境 刘 那后来怎么办?
干 后来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荷兰剪辑师。
刘 巴斯•洛特林克。
干我们叫他巴斯。他以前是读数学和建筑的,给荷兰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导演剪过片子,我看过那个片子,曾经获得阿姆斯特丹的大奖。他那会正好跟女朋友在上海生活。
刘 他听不懂中文吧?
干能听得懂一点点,我给他找了一个实习生做翻译。他有一个特点,记性特别好,一分钟场记都没记过,但什么镜头在哪儿都知道。之前的剪辑师从60个小时里挑出了30个小时的东西,巴斯就快进着看,有兴趣的才停下来看看。第二天开始剪,就剪了十分钟。他基本上是早上9、10点钟来,下午5点钟走,要什么镜头,我尽量帮他找,帮他补拍,晚上我再看一下他剪的东西,然后第二天讨论一下。整个过程里,我干涉不多。现在这个片子,他只用了两个礼拜就剪出来了。
刘巴斯真是厉害!剪辑的节奏、构架,片段与片段之间的勾连,真是好。这种做法真是太职业化了,专业人做专业事。前几天我在武汉采访陈为军,他说他最近的一个片子《世界最大的中餐馆——长沙西湖楼》就是曾经给《藏龙卧虎》做过剪辑的老外给剪的。现在我们很多独立导演大都还是在“自己动手”,一可能是创作的习惯,觉得这样才是“自己”的,二跟财力也有关系。
干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自己的片子要自己剪。有一部分人现在一直这样做,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这往往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没有团队的支持,偶尔运气好碰上一个选题,获了奖就没有下文了。我们要用一种职业的方式去思考,大家在技术上的进步也是要靠职业去做的,因为你必须要相信别人。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职业圈,要有一个好的创意,好的摄影师,好的剪辑师。他们是职业的,可以为你加分。
刘片子一开场,就是一段交叉剪辑。女教练黄指导正在大声呵斥着女队难的邓彤,声音线没断,画面插入小男孩们正在带护腕、做准备,来回交叉剪辑了几次,你就会马上产生一种立体的感觉,同一场景下,不同的人物的状态一一再现,简洁、明晰而且节奏很快。
干一开始这场戏其实蛮难的。两个队在一起,有一个互联关联的气氛,但是状态又不同,怎么交代?之前的剪辑师,他迷恋于一种状态性的东西,也是这些男孩子在戴护腕,一个说我的牙齿松了,另外一个孩子说我把牙齿拔掉了,妈妈说不拔掉会长不出来的——这对话持续了一分半钟,讲了一个成长的主题。可是入题太慢了,因为观众此刻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有必要听他们讲牙齿的问题。所以巴斯这么剪,用很短的时间就把环境、人物都交代清楚了。
刘 这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只有想明白了才变得简单。
干他剪得很干脆,有些东西点到就走。比如说大双测评最差,没有得到礼物,你看他就用到那个全景镜头——每个人手里都有礼物,大家还互相说着什么,只有大双两手空空站在队伍里,尴尬而落寞。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镜头,有的小孩子嘲笑他,有的同情他,要把东西分给他一点,小双在他后面拿着一包东西低着头,一直陪着他。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但是巴斯就此打住了。
刘全片没有采访,没有解说词,没有解释性的字幕,甚至没有人名的交代。在这种前提下,没有一处黑场、叠画,刀刀全是硬切,但片子看起来自然流畅,不生硬。
干这点我也蛮佩服他的。当中有一处,领养王露凝的外公,原先是坐在沙发上拿着照片讲的王露凝的身世的。后来巴斯就跟我商量,如果不是采访风格,无论如何不要用这个画面。我赞同他,于是他就想办法把外公说的话贴到了外公带王露凝乘坐大巴去外地看望王露凝的爸爸那一段里。巴斯的这种意识是很强的,他希望整个片子风格要一致。
刘 片子的空镜似乎也用得很收敛,呵,我用“收敛”这个词,主要是说他不滥用空镜。
干我拍过很多空镜头,但是巴斯都用得非常少,他没有莫名其妙地插入树叶、马路、楼房等等空镜,和故事没有关系的镜头几乎没有。除非要交代这个孩子家里的环境,才偶尔用一个交代环境的空镜。片子里,那些从船上拍到的外滩空镜,其实是有含义的,这和孩子们普通破旧的家形成对比——中国发展的代价,含义就在里面。
纪录片《红跑道》剧照
刘有很多编导特别爱用空镜。呵呵,在《房东蒋先生》里你也用了不少空镜,比如雨夜的街景、蒋先生的影子、树叶等等。
干现在想来,这都是一种无能的表现。空镜、渐黑、叠画、谈出淡入等等都是一些艺术的表现手段,但是如果用得没有道理,那只能说明你没招儿了,只能这么做,真正有办法的人是不靠这些的。
刘片子中间有一个俯拍的大全景镜头,红跑道上,两队孩子们迎面穿插着翻跟斗,很好看,紧接着就切到俞指导和阿南的妈妈在二楼走廊上交谈,说的是孩子,是阿南妈妈的希望。这使得俯拍的大全景就像是他们的视角,那么自然、合理。他们的交谈并不是你们有意调到二楼去拍的吧?
干对,当然。这种组接看上去很简单,其实是很难的。这两个场景根本没有关系,剪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呼应关系,否则单看两人的交谈,或者单看小孩子们的训练,都很莫名其妙。
刘这就真正构成了一种让画面自己去说话的自然语境。有不少人不自知,他们往往越过了画面的自然语境,忽视了叙事或描述性的话语,特别自作多情地硬贴上一些判断性的字句,比如说:“老张幸福地走在大路上”、“她一个人待着,真可怜!”
干是的。我们在做片子时,很容易陷入到自我的主观判断里面,而且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你就有这个立场,这样就会限制了观众的想象空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呈现一些能够感动人或者能够刺痛观众的东西,没想过要表达什么理念,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想去表达什么。
刘 但至少它是一种人生经历。
干对,后来我跟教练说,其实我也在做一件好事情。这些小孩子的童年或许你认为蛮苦,或许他们自己觉得蛮快乐,这个我不能瞎说,但至少等他们长大了以后,这是一份记忆。这一点我感触特别多。我出生在上海,很小就随我爸妈的军工厂去了四川广元,后来在南通住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上海。我曾经想过很多次再回去看看,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成行,可能是记忆中某些东西你不愿意去触及吧,直到这次四川地震,突然看到广元全都变成一片废墟,我就知道这个记忆完蛋了,再也回不去了。
刘是啊,即使回到广元,也不是曾经记忆里的了。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在他们的记忆里,有没有也不愿碰触的东西呢?有一个2分50秒的长镜头,就让我有一种深深的刺痛感。邓彤和王露凝在为训练耐力而持续吊杠,在这里,个体的辨识已经不重要了,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超越极限的抗衡,两个小姑娘边哭边痛苦地坚持着。音乐响起,像撕心裂肺地哭喊,也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
干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高潮,放在了片子的1/2处。当前面逐渐交代清楚各种人物关系后,在进入比赛之前,这里作为一个转折点,紧张的气氛越来越逼近,人物的交织也从这里展开。
刘更绝的是“高潮”之后的承接!坚持到最后的王露凝已经是浑身颤抖,表情痛苦之极,最后跌落杠下……音乐戛然而止。这时,一个特写镜头:敞开的书包里慢慢爬出一只小乌龟,爬着爬着突然跌落……。小乌龟的跌落和王露凝的跌落形成一种同构效应。情绪一起一伏,紧张与舒缓,节奏感特别强。同时也自然呼应了后来王露凝说的:“小乌龟生病了”。这时音乐起到的宣泄作用特别强。
干对,但有些人说这样用音乐太主观了,应该客观一些,不要配音乐。但问题是,我们试过不配音乐,将近三分钟的长镜头,看不下去。而且这个镜头我们是长焦调的,当时担心教练不让我们拍,环境也很嘈杂,她们的喘息声我们根本录不到。在片子里,前后用了两段音乐。这些音乐都是巴斯搜集的,Google都查不到,最后是从一个音乐通那里得知这是一个地下乐队创作的曲子,而且乐队早已经解散了,经纪公司还在。于是我们签下了使用权。
刘 对于声音的处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种导演意识吧?
干片子完成以后,我就跟我们的创作人员说,我们还可以有方向去进步,就是声音的录制与处理。在电影院放映时,声音就是片子的一半,我们先不要讲立体声什么的,现在有很多纪录片连清晰都做不到,乱七八糟的,有很多干扰的音源在里面。声音录得好,前期的准备很重要,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准备,还有你对这个情节的了解与把握,如果下一刻你都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你怎么录声音?如果你是一个很成熟的导演,你完全判断得出来。 【访谈结语】
尽管,《红跑道》混杂着希望与想象、无奈与挣扎,但它都无可质疑地塑型着一种生命,这生命如同我们每一个个体。在我们的人生起点,以及随后的生长过程里,从来都交织着自我意志、他人的期待甚至强扭的压制。然而,当一次又一次的超越经历过,我们分明看见了生命的成长,这时一种精神品质也悄然聚成。正如干超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体制里形成自己人格的过程,恐怕不能仅用快乐和悲伤去概括。但孩子们有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贯穿于他们的生活和训练。”
这是《红跑道》给予我们的映照。生命的起点是纯粹的,然而过程却累积了太多的附加与羁绊。
此时,我想起一位早逝的电视人陈虻先生的一句话:“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出发!” 作者:刘洁 中国传媒大学 副教授 博士 [ 注:原文始发于《南方电视学刊》(双月刊)2009年第3期 ]
中国纪录片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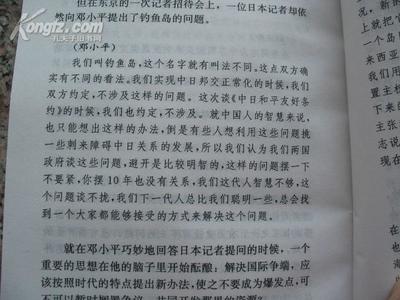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