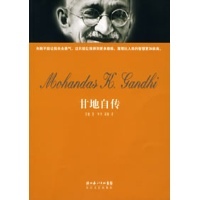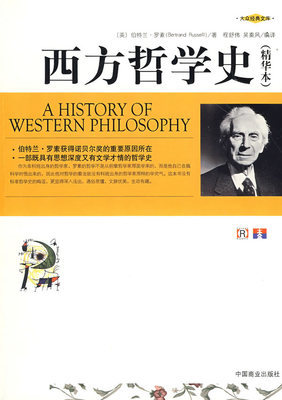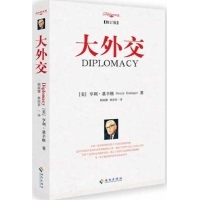1.《公众舆论》内容回顾整理
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是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对公众舆论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卓有成效地梳理了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如:“公众舆论从何而来,它是如何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对于其他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公民个人是否是理性的(是否具有理性的做出判断的能力)?精英治国所掌握的制造同意和共同情感的技艺是如何掌握的?同处于虚拟环境中,领导者是遵循着何种途径脱颖而出成为意见领袖的?等等问题”,李普曼仍然处于一种怀疑和思考的态度,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和描述。因此,本篇读书笔记就要在对于《公众舆论》这本书的内容整理的基础上,找出一些书中并未给出答案的问题,并且做下一步讨论。
1.1《公众舆论》的写作背景
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时时出现的有关时政和时局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府宣传机器为了战争胜利在国内国际大造舆论的种种做法给李普曼思考的“虚拟环境”问题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虚假的、偏见的战争报道,以及战前战后参战和分赃中出现的一系列有悖于传统道德约束的很多问题,被媒体和当局巧妙的遮蔽了。在整个媒体参与营造虚拟环境的过程中,普通公众在资源和信息匮乏的情况下表现出的认识事实真相的“无力”和精英阶层对于整个局势的控制,在这个历史阶段突出的表现了出来。
1.2《公众舆论》的章节安排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主要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本书的前四部分分别就影响公众不能作出理性判断的三个因素分别加以阐释:
第二部分 对外部世界的研究
由于信息流通的不通常、不完全,信息资源的有限,由于人类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的不确定性和不统一性(相似于皮特斯在《交流的无奈》中提出的观点),还有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把关和筛选信息的制度之存在,公众处于一个虚拟环境之中,无法直接、真切的得知与自己所处环境相隔甚远(时间上、空间上)的事情的真实情景,因此,通常会作出非理性的判断。
第三部分 成见
由于固有的成见、偏见、固有的价值观念的存在,公众对一件事物的认识很难达到准确。
第四部分 兴趣
由于兴趣、自我利益等因素的不同,公众作出的判断往往是主观的、非理性的。
在第五、第六部分,李普曼详细的阐述了公众舆论是如何被左右的。
在公众意见庞杂、非理性的情况下,作为领导者的人通过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寻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将公众的情绪和意见整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公众舆论,因此公众舆论是可以被操纵、可以被疏导、可以被利用的。而在公众之中走出来的领导者,并非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执行者。很多看似民主的、顺应民意的决定和决策,很多时候是通过暗地操纵、疏导公众舆论造成的。
2.读书线索一:公众舆论和公众是非理性的吗?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肯定了公众舆论的非理性,认为公众是否能够真的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内容一致的舆论还是未知数。但是李普曼似乎没有涉及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即:公众的非理性并不代表个人的非理性(群体动力学的影响),个人的非理性是否是由于缺乏理性能力,抑或是因为被群体的力量所左右(沉默的螺旋),作为公民的个人是否具有足够作出理性判断的能力?
2.1 文献综述
在美国20世纪初期,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非理性的见解与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的思想似乎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其实两者之间也并非绝对的对立。德国的批判学派社会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也涉及到了公众领域形成的问题。
2.1.1杜威《The Public and ItsProblem》
杜威认为,民主的基础是对人性之能量(能力)的信赖,是对人的理智、对集中的合作性经验之力量的信赖。这并不是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完美的,而是相信,只要给他们机会,它们就能够成长,并不断创造用以指导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知识与智慧。
对于公民是否具备理性的智慧,杜威则认为,公民虽然不具有为政的技艺,但是“鞋子在什么地方挤脚,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的”。智慧的分布虽然并不平均,但是只要相信个人的能力,组合起来形成集中智慧,就能作出贡献。
对于李普曼的“技术精英治理国家”的思想,杜威坚决反对。他认为所谓技术精英,他们的智慧其实与普通的大众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两者还是可以沟通的。
2.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对于社会结构有自己一套独立完整的体系。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他总结归纳了欧洲多个国家公共领域形成的历史脉络,并且强调了:公民财产私有、公民真正可以以一个“私人”的身份独立于旧有的国王封建辖制之外,是形成公与私对立、随之产生一个沟通两者的公共领域的基本条件。公权和私权、公利和私利之间存在冲突,公共领域开始的存在是作为一个抒发、宣泄,最终能够实质性的影响到国家决策和法律制定过程的这样一种力量。公众舆论在其中有两种不同的作用:作为批判的作用和作为交流的作用。作为批判的公众舆论是建立在保护私人领域的基础上的,而作为交流的公众舆论是建立在诸如道德的基础上的。
2.2 公众舆论的非理性、公众的非理性
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李普曼从公众本身的认识局限和意见领袖的强势两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公众认识的局限源于虚拟环境,而意见领袖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和操纵则源于其能够在不同的意见中制造同意。公众在虚拟环境中受到刺激,却在现实环境中作出反应;意见领袖通过对于不同意见的整合,让公众认为最终作出的决定确实是延续了自己原有的想法和意见,自己的利益最终得到了实现和保留。
因此,在以上这样一个“弱势”一个“强势”,一个“有能力”一个“无能力”的对比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无形中占据了上风,所谓技术精英通过自己所具有的技术和智慧,能做出比普通公众更加理性和科学的决策,因此将公众的地位踩在了脚下,建构出了一幅“精英引导群氓”的图景。从这种程度上说,公众的确不能独立思考、思辨,其着眼点的局限性也就决定了其落脚点不可能顾全整个局面,最终必然被一种统一的、影响力巨大、包容性极强的公众舆论所吸收。而少数人一旦具有了够操纵公众舆论的技艺(甚至构成了事实),就更加不能说公众舆论是理性的了。
2.3个人的非理性:能力问题还是环境问题?公众舆论的非理性:主动还是被动?
信息的不畅通、不完备,虚拟环境的产生,对公众做出理性的判断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因为身处于这个环境之中而无法做出判断,那么是否能以此断定作为个人的公民就不具备独立理性判断的能力呢?显然不能。视野的局限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虚拟环境可以由主观因此产生,也可以由外部力量建构,如一战二战期间的宣传工具。因此,身处于其中的个人是由于个人智慧能力的缺乏还是被虚拟环境所蒙蔽、被限制其看到事实,是 有待考察的。个人会做出非理性的决策,是因为其本身能力的缺乏还是环境造成的障碍?李普曼似乎没有特别提及到这个问题。即时个人真的具有这种理性和智慧,而始终无法看到现实环境中发生的事件,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仅仅是操纵舆论这么简单了。作为精英的阶层是站在“普渡众生”的高尚角度来引导“群氓”还是通过“焚书坑儒”的愚民洗脑以维护自己作为精英的地位和统治呢?公众舆论是否可以“理性起来”?是它自身不可以做到“理性起来”还是社会精英不希望它有能力“理性起来”呢?公众舆论的非理性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个问题,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似乎没有展开讨论。
3.读书线索二:精英治国
作为技术专家的精英治理国家,李普曼认为,具有统治和领导技艺、具有制造同意的技艺的精英群体,可以整合公众庞杂多样的舆论,使之最终合为一股。通过这种技艺,能够掌控舆论,稳定形势,取得优势地位。明为民主,实为寡头。
3.1 文献综述
西方文化中的精英主义理论是怎样一种思想呢?笔者一斑窥豹,通过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简单了解一下。
3.1.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当中提出了一套整体的模型,按照统治人数的多寡,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这三种政体又有三种变体,分别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暴民政体。第一类政体类似主人与奴仆,第二类政体类似家长于子女,第三类整体类似于老师与学生。
技术精英治理国家,在李普曼看来,应该就是属于贵族政体的类型;而在杜威看来,就应该属于共和政体的类型。亦即:精英对于公众应该是家长还是老师?他们进行统治和决策还是提供知识和意见?
3.1.2柏拉图《理想国》、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用“哲人王”这种精英人士来担任国家的主人,但是却没有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他希望由精英运用其精英的方法和思想来治理国家,但是最终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能够有开明的政体能够启用哲人,用他的智慧来领导国家,类似于舵手为航行指引方向。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当中则开始公开讨论作为统治者所需要具备的压服众议的技艺,他强调统治者所要具备的种种技艺,也使一种间接涉及到精英治政的想法。
3.1.3 精英主义
系统而有影响的精英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其发展的顶峰。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大众民主兴起的保守态度,人们试图以精英主义来对抗大众民主的潮流。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批判和挑战,精英主义在当代日趋衰落。
3.1.4柏拉图的“洞寓”,放映假人假兽虚像的精英
能够从洞中的束缚中挣脱出手脚,柏拉图认为那个囚徒是偶然做到的。挣脱出之后能够完成第一次的灵魂转向,走出洞穴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真,就仿佛从虚拟环境中成功地突围,最终看到了现实世界的太阳。
柏拉图的“洞寓”始终还是一个比较简陋的故事。我很好奇的是这个囚徒在两次灵魂转向(出洞和进洞)的过程中,是否看到了那个一直在土墙后面负责放映假人假兽的投影的那个人?如果说一定要把柏拉图的“洞寓”中的情节拖进现实世界中一一对号入座的话,那么我想这个负责抬着假人假兽放映虚像、往洞中的火堆里不断添加木柴的人,就是精英。
而那个最终命丧于“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先知囚徒则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从虚拟环境中遁形了的个人。他没有受到主流的公众舆论的影响,强行脱出,而后又强行突入试图劝服公众、妄图改变公众舆论的主流方向,最终不会被精英亲手抹杀,只会被精英培养出来的公众所抹杀。
3.2 精英能够完全控制公众舆论?
在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技术精英治理国家的思想其实也是精英主义在现当代的一种延续,即:不相信公众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具有治理国家的智慧,实际上也不能自发的形成对于一个公众问题的共同认识。这种精英主义的思想,配合以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似乎是更加如虎添翼:运用大众传媒的宣传手段能够更加顺利的建构出社会事实,或掩盖社会事实,从而人为的建构起一片虚拟环境。而公众舆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就更加缺乏独立判断的信息和技术支持,随着虚拟环境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凌乱的步伐。
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更类似于传播效果论里的魔弹论:经历了世界大战宣传机器的狂轰滥炸,很多学者倾向于相信公众就是应声而倒的子弹靶子,公众舆论其本身的公共性和合理性也愈加的岌岌可危。
这种强效果论的观点,可以说是李普曼在考虑公众舆论问题时的一个突破点(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世界),但是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公众是否真的会“那么顺利”的沦落为虚拟环境任意可以摆布的奴隶呢?公民作为个人的智慧和理性是否会因为环境的强势而彻底泯灭呢?李普曼其实在《公众舆论》中并没有回答公民作为个人是否具有智慧和理性,只是认为即使他们具有理性,面对这样一个普遍非理性的环境,个人或者多个人的理性也是无济于事的,“以理性的方式对付非理性思维的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李普曼,《公众舆论》,P292]。并且,“当理性与政治的第一次大邂逅中,理性的策略是愤然退场”[李普曼,《公众舆论》,P292]。
因此,公民作为个人是否具有理性根本就不在李普曼的考虑问题之列,他如此的相信,当理性的个体面对非理性的群体、非理性的政治(规则)甚至是整个非理性的公众舆论时,被影响、被同化、被划归到一个大的群体中消去棱角和特殊性,最后形成一种共性的模糊,是必然的结果。只要具有这种模糊界限和利益,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恢复“共同意识”的尝试也未尝不会取得成功。
3.3 精英是如何从虚拟环境的边缘产生的?
那么,问题是,在基本上涵盖了全部人口的公众(偏离世界的舆论而孤独的囚禁在诸如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士兵之类的人除外)当中,是哪些人能够超然置身于混浊的世外,透过亦真亦幻的虚拟环境俯瞰到整个现实世界的全貌并且从中斡旋、制造同意从而操纵引导公众舆论的呢?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技术精英,是如何从公众中产生的呢?是原本就世袭着精英身份的人始终站在整个现实世界的观景台上、站在洞穴中负责放映投影的虚像,还是真的有一些智慧超乎寻常的平民能够从假人假兽的交替渐变中看透了世界的本真、从而爬出了洞穴呢?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提及的作为君主所必需要具备的一些技艺,似乎是在说,作为精英也需要从头学起、从最本真的社会运行规律学起。这点在《理想国》里就比较虚无缥缈,因为哲人王的智慧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柏拉图认为是“天赋”的,是上天用金子把他们做出来的。现代的观点认为,精英产生于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超前的深度的学校教育和进入上流主流社会的社会交往中所得到的教育和熏陶对培养一个精英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能够让人成为精英的教育始终与出身的高贵相挂钩。但是,这种“精英是教育出来”的说法其实和柏拉图的“天赋”观点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出生在高贵的家庭才能享受到精英的教育,那么作为一个新生命,他能否生在富人家呢?这完全又是一个“命定”的东西。
李普曼在这点上,也没有对旧有的精英主义的观点有任何突破,用“个人的理性敌不过世界的非理性”来回避了个人理性的产生问题。
4.结论:“以理性的方式对付非理性思维的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
在李普曼先生《公众舆论》一书的最后,我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解答了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李普曼先生认为,去探讨公民做为个体本身是否具有能够理性的做出判断的能力,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徒劳的。即使个人是理性的,但是面对着价值观、偏见和虚拟环境的影响,用理性的方式来对付这样一个非理性思维德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
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还有勒庞在《乌合之众》之众对于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的阐述。勒庞认为,群体心理是一种低劣的、无理性的、极具破坏性的力量。来自于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来自于强大的同盟的力量、来自于瞬间爆发出来的炽烈的情感,即使是理性的个人也无法逃脱这一轮非理性的巨大漩涡之中,一同做出完全违背日常行为规范和情感标准的暴力事件来。
那么由此看来,不论是李普曼还是勒庞,在面对所谓的“公众的声音”这个问题上,都是有些悲观的。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和在这样一个时间中随波逐流的民众以及他们发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声音。这与他们生活的时代、生活的国家的历史有着紧密地关系——法国大革命的暴民政治、雅各宾派的血腥屠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机器、凡尔登绞肉机的猛烈冲击……所有的无论是事实还是意见的诸多画面都融合在了一起,而在这样的发生巨大变动的社会中的人们,无不以一个弱势的、无力的同时又容易被人操纵的形象出现。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现实”的如李普曼和勒庞这样的社会学者,自然会萌生出群体的非理性、公众舆论的非理性这样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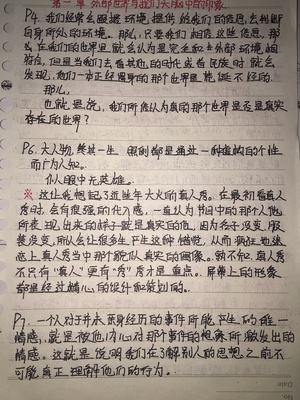
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使他们能够用如此细腻、思辨的笔触把这样的一个宏大的社会场景和人们的心理动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也不能够忽视的是——这仅仅是社会的一个层面、一个角度。如果真的如同李普曼所讲述的虚拟环境发挥着作用那样,他们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没有看到,这些方面就是我相信的:仍然有理性的人能够抗拒虚拟环境的影响,发出理性的、思辨的、高亢的声音——不论这些人是精英还是草莽。(完)
5.参考文献
《公众舆论》,沃尔特·李普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交流的无奈》,皮特斯,华夏出版社;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学林出版社;
《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孙有中,上海人民出版社;
《君主论》,马基雅维利,商务印书馆;
《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商务印书馆;
《理想国》,柏拉图,商务印书馆;
《乌合之众》,勒庞,中央编译出版社。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