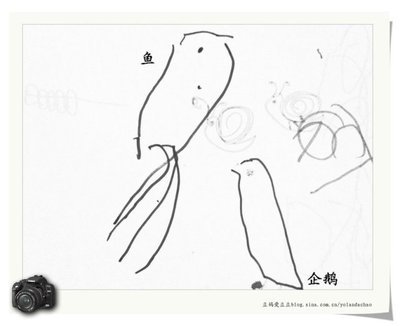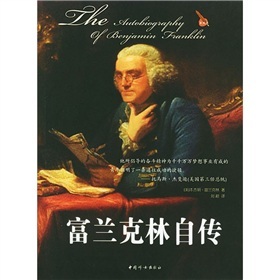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引言
初识马克思·韦伯是在研习民族学的本科,成打的人类学理论人类学大家和人类学书籍如三座大山般压着我,我如同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般迷恋着这个学科。马克思·韦伯便是这些众多社会学人类学家大拿中的一个。每每泡在图书馆沉浸在人类学大家的哲理名言和睿智思维的海洋中,总是会偶遇马克思·韦伯和他的众多著作:《经济与社会》、 《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学术与政治》还有这本最为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后来,适逢毕业和实习,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点就选在了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当地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隆务寺成为了我与其他几位同学的调查点,寺庙经济成为我们这次调查的主题。怀着对藏传佛教的好奇和对隆务寺的崇敬,我们每日穿行于隆务寺各大学院之间,和僧人攀谈,观摩辩经和大型盛会现场,收获颇丰。调查过程中会根据当天调查的资料在脑海中搜罗读过的书目或者研习过的理论中是否有可以支撑调查之结果的相关理论。最后在撰写实习调查报告时,就大量运用了马克思·韦伯的卡里斯马权威的相关理论。
后来有幸读到了韦伯夫人玛丽安妮为丈夫所做的传记,其中记载了在德国民主革命爆发后,韦伯在海德堡一个学生会上的演讲,演讲中的一段话深深的碰触到了我的神经:
“当你们看到第一位勇敢的走进但泽的波兰官员被子弹射杀的时候,你们决心噤声不语的时候——当你们已经认定,这样的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时候,那时,我任凭你们处置,那时,你们先把我收拾掉得了!”
这两句话,韦伯是“挥舞着双手充满激情的说出的”,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和者寥寥,整个世界以冰冷的沉默答复他的野火般的激扬,着实令人心酸。
一、内容概述
马克斯·韦伯的主要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作为一名社会学者,韦伯受到了几种思想体系的影响,如苏国勋先生认为“韦伯从实证主义中汲取了客观性,从德国浪漫主义中学到了敏锐关注个体性的意志自由的原则,从形而上学中借鉴了它的历史性。”但作为一名深受李凯尔特影响的新康德主义信徒,韦伯关注个体性的意志自由的原则和拒斥任何脱离经验的研究方法都可以从新康德主义哲学中找到解释。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著述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书中韦伯主要论述了两方面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本质;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韦伯阐明了新教中加尔文教派的理性化程度和理性化过程,回答了为何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伦理何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很强的亲和性,指出加尔文教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真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初步建立起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在韦伯看来,个人应该如何行动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最终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意义上,韦伯是个人主义唯名论。
“因为,圣徒的永恒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尘世生活里,人为了确保他蒙承神恩的殊遇,他必得‘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昼隐退’主的意志明确昭示,唯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123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部分和《经济与社会》中支配社会学的部分,韦伯用“铁笼”来隐喻资本主义现代生活的图景。在韦伯眼中,世界从新教徒暂时居住的异乡变成难以逃离的“铁的牢笼”是西方理性化的一个悖论性的后果。西方理性主义发展到新教阶段,把信徒变成上帝的忠实奴仆,他们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而刻苦工作,用经济上的成功作为恩宠确定的标志,过着简朴的生活,结果便很自然地导致了财富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使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遭遇到了和中世纪修道院类似的下场:宗教理想受到严重侵蚀,“增加上帝荣耀”这一新教徒唯一的人生目标和激情的来源被他们的后代子孙渐渐淡忘,唯剩下“为赚钱而赚钱”的现实心态,物质产品对人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蓬。’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蓬变成一只铁的牢笼。”
二、本书的理论方法
韦伯的方法论中还有一个亮点是提出了关键性的概念工具——“理想类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种理想类想,目的在便于探讨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宗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并且韦伯还用类似于“类型比较法”的方法考察了世界各大宗教和经济伦理之间相关性。
说到马克思·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者们总是会不自觉的将另一位马克思——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进行比较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书于1904~1905年,这个时期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已经盛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可是,韦伯在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为何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作出了全新的诠释。关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法的分歧和相似之处的多角度分析也是社会学中的热门话题。
研究角度而言,韦伯是一位宗教社会学家,而马克思的主要研究领域则是哲学与经济学。因此,韦伯更注重从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来解释社会现象。另外,马克思与韦伯进入经济学的路径不同:一为“历史哲学”,一为“史学”。马克思的理论的基本构架是黑格尔式的整体主义历史哲学,而韦伯所受的却是具体的史学训练。所以韦伯更重视个案与个体(这一点从他所举的例子便可看出)。而马克思则强调集团、阶级。
需要强调的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错误阐述可能会导致我们认为韦伯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其实不然,他所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单纯从经济改革中推出宗教改革。在书中的结尾他也提到,只是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整个社会条件的影响,但是,“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
三、关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的比较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有两位德国思想家以他们天才般的独特智慧和思想体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雷蒙·阿隆将马克思作为第一代古典社会学家,而将韦伯作为第二代古典社会学家。吉登斯则将马克思、杜尔干和韦伯三位作为最杰出的经典社会学家,他们代表了社会学中三种重要的传统(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批判社会学)。
说到马克思与韦伯的不同:一位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预言家或先知,一位是“价值中立”的倡导者;一位宣布其理论本质上的阶级性与政治性,一位宣称学术与政治分离;一位是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发起人,一位是社会主义运动最严厉的批判者;一位被认为开创了唯物主义,一位则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这些区别显而易见,但是如果因此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韦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始终站在与马克思对立的立场,那么我们将严重忽略一点,那就是韦伯的理论不单单是出于寻求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它同样也有对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诊断与批判,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韦伯决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相反,倒是大大发展、扩展并补充了马克思的理论。尽管他们对现代社会研究的视角并不完全一致,但这种不一致与其说构成了简单的对立关系,不如说是形成了一种互补。
卡尔·洛维特在其名著《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与韦伯的终极关怀都是“人的解放”。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他们分别提出了“自我异化”与“合理性”概念,在洛维特看来,这里的差异只是表明了他们所生活的历史阶段的差异,“合理性”是对“自我异化”的发展。这一点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劳动者“异化”观念已经在生活中淡化,无产阶级的劳动被归结为一种自由劳动,并且我们习惯的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是一种理性组织,因此才会动摇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信念。
四、个人愚见
关于卡里斯马,韦伯有这样一段话:
卡里斯玛支配无论在哪一方面——当然也包括经济的基础这方面——都与官僚制支配正好相反。官僚制支配要靠恒常性的收入,特别是货币经济与货币租税来维持,而卡里斯玛则虽生存于此世,但却不赖此世之粮为生。关键性的要点在于:卡里斯玛对于有计划的、理性的赢取钱财——事实上,一切理性的经济——总觉得有损品格而加以拒斥。
——马克思·韦伯《支配社会学》P.265
在经过对隆务寺的寺庙经济课题的调查之后,我意识到,以宗教与经济的视角而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在于他从宗教的角度提供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学解释。韦伯对世界诸文明的比较和历史研究也正是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推进。然而韦伯在分析中国何以缺乏发展理性资本主义因素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于佛教这一维度,而仅仅将佛教划入救赎的大众宗教,却忽略了佛教所营建的经济与公益事业及其社会影响。尤其是长城之外的藏区,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国家、家族力量之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在社会经济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过去藏区寺院的经济,由于占有大量赐封的土地,围绕着寺院进行的政教合一的生产是寺院获得经济的主要来源。而这样的获得,其实有着自身的一套布施、供养的宗教逻辑在内,其所得不是用来继续发展扩大再生产,而是对于神佛的馈赠,围绕寺院展开的经济活动,也是在一种非理性的支配之下。佛教的意旨是个人、众生的灵魂救赎,是一种拒绝与世俗妥协的修道生活。然而,作为经济体的寺院,其僧侣的日常生活又需要金钱与物质的供养。修道生活在其发展的卡里斯玛阶段,是一种反经济现象。韦伯在为这种修道生活作出解释的同时,也指出:“想要靠着反经济的手段来维持生计,长久而言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一种政教合一的阶层制组织,藏区特殊的宗教环境和政治、经济条件正好孕育了这样一种维系寺院作为经济体和宗教正当性的体制。佛教并非在印度,而是在藏区发展出喇嘛教(藏传佛教)的阶层组织,甚至在仪式的细节上都达到可与西方罗马教廷相对应。
在人类精神的谱系中,马克思.韦伯自始至终都是同样杰出,不可缺席,尽管在其生前并未获得相应的荣誉。在文明盘根在高效率机械的基础上、文化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下,用宗教伦理的而非经济科技的手段去解读资本主义,其行为本身便具有一种不可泯灭的精神,是一种强调,为文化复兴竖起的一面招魂幡。另外,在唯物论日炽的形势下,马克思.韦伯坚持认为,宗教思想不可能从经济的物事演绎出来,有自己固有法则性和不可抗的力量。譬如路德派和卡尔文派之间的差异,“如事关非宗教因素的影响,那么主要也是来自政治的作用(而非经济)。”韦伯学术的传承者帕森斯则公然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所写。书中固然多处出现与唯物论者商榷的语句与例证,尤其在其著作最重要的特色之大篇幅的注脚里,韦伯的主张更加鲜明。但不可以以偏概全,掩盖或无视两个马克思观念的相同处,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特征,对资本主义的忧虑,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性关怀,不少地方二人的观念都如出一辙,虽然在对社会未来的展望上,两人是完全相逆的,马克思.韦伯持悲观态度,卡尔.马克思则抱乐观态度。某种程度上来讲,帕森斯响亮的论调毋宁是对韦伯精神的背离,“对于历史真实的解明,两者同样是可能的,”这是学者应该具备的客观而谦和的态度。现代的人阅读韦伯的著作,内心依然时时被那些日久弥新的思想所激荡,丝毫不见故纸堆里的腐旧落后,一方面是由于韦伯的远瞻性和坦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和韦伯的时代仍存在不胜枚举的共通性。无论从文化精神、学术研究、和对当下的指导意义来说,韦伯及其著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五、结语
马克思.韦伯是一个“不写诗,不幻想”的人,但不能因此认定他古板无趣,毫无诗性的特质,相反,人们只需稍加留意,便可以在其严谨的学术著作里找到诗歌阴郁的基调。本质上讲,这是一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和理性主义来架构诗章的人。换言之,诗性是韦伯著述的基础,也是韦伯从同时代的思想者群体中脱颖而出的诸要素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1904年的美国之旅后,当马克思.韦伯决计用宗教伦理去诠释自己的时代,我们就应该得出上述的结论。“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在他的名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束处的这一句,更让他的诗意的特征无可逃遁,又有谁能够冷静的把它视作隔靴搔痒的学术语言。对国内的韦伯爱好者来说,最为耳熟能详的是于晓、陈维纲的译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日前亲见新浪微博上有人针对某佛寺面临的驱逐僧团、强占庙产的相关微博作出这句评论时,更加想到了韦伯和他的这本书。“幻想”这个词,用来形容韦伯,韦伯夫人用的难免透出几分无奈,但是从而让我打心底里更加确知韦伯笔下所反对的“幻想”跟诗意完全是两码事,因一种妄自尊大的成分在内而被鄙弃。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卷第一章“入世禁欲的宗教基础”最末一段所写:“此种禁欲则封起修道院的大门,转身步入市井红尘,着手将自己的方法论灌注到俗世的日常生活中,企图将之改造成一种在现世里却不属于俗世也不是为了此世的理性生活”,走出斗室“入世”的还有韦伯本人,他意图将自己的学识全数“灌注入俗世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他从政理想以至竞选德国民主党地方领袖的驱动力,不同的是,前者全面获胜,后者迎来的却是冷淡沉默的会场,还有不愿意去理解接纳他的民众。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彭强译[M].四川人民出版,1986
2、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张钰.解读韦伯的三大隐喻探测韦伯对现代性的洞察[J].社会,2005年06期
5、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思.韦伯传,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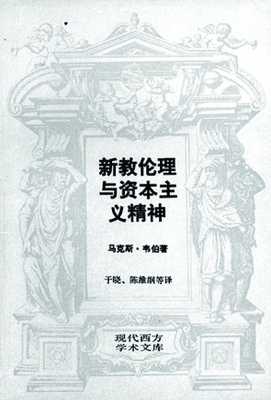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