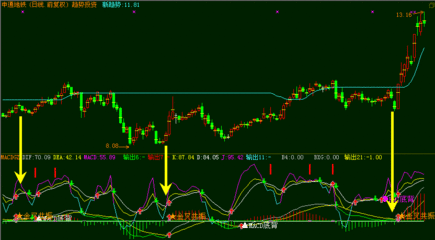为文之前先炼“心德”,在我看来,把自己说不清楚说不明白的道理硬说出来,便是“失德”了,因为它不但不能开启童蒙很可能对世人的思想造成新的蒙蔽,遗憾的是不求甚解已成为一种中国理论界一大特色。比如,“意象”问题,这些年我读了所谓名家们几千篇关于“什么是意象”的文章,至今没见一篇能说明白的,我也跟很多所谓名诗人交流过,至今没遇到一个能分清意象和物象的。有的引用了很多西方理论夸夸其谈,但是在举例过程中举的例子反而是“非意象”,如,针对庞德说过的一句话,“写一百本书,不如创造一个意象”,很多中国知名砖家便摇头晃脑地说人家代表作《地铁车站》一下子创造了四个意象:面孔(faces)、人群(crowd)、花瓣(petals)和树枝(bough),纯粹一派胡言!“面孔”“人群”“花瓣”“树枝”这些随处可见之物如何成庞德创造的?其实,老庞德所做的只是激活了“人群”与“树枝”“面孔”与“花瓣”两组“被遮蔽”的物像关系而已。还有些自称理论家的人说出“意象多了就是说教”这样的比外行还外行的笑话(尽管明明在胡说,你还不能说他胡说,人家还挺要面子),因为这和把用意象说话的唐诗宋词全盘否定差不多。玉上烟有句诗“我是个用尽力气的人”,作为一个行文者可谓最好的行为提醒,如果每一个评论家也把它用作为文之道就好了。
什么是意象
何谓“意象”,约定俗成的解释是“寓意之物”,但仅仅这样定义还是不易区分,因为在诗歌中所有的物象都是有用的都是诗人有意为之的,否则诗人不会写它,若这样认定等于和把诗歌中所有物象皆认定为意象差不多。比如,“床前明月光”、“锄禾日当午”,诗人选择“床”和“明月光”、“禾”和“日”时,肯定也是有意的,那它是否就是“寓意之物”?如果是,在诗句中它又只能代表这个物象的基本义本身,是不产生引申义歧义的,如果认定它为“意象”代表另外的意思,这将造成语言逻辑的混乱,失去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共时性沟通的可能。因为,若一首诗中有的物只代表其自身,有的物象则是“指桑骂槐”,不把它们的“身份”厘清区分开来,就会令读者陷入顾此失彼的五里雾中,因此,对意象概念的界定需建立在和物象相区分的前提之下。
从意象在诗歌中行使的职能来看,所谓“意象”其实就是“诗人对物象的角色化处理”,类似把一些寻常之物弄到一个“戏台”上共同演一出戏,让它(他)们扮演不是它(他)但和它(他)有内在联系的另个它(他),首要一点就是它(他)是个“扮演者”,即“物非物本身”,至于“戏台”以及“戏台”周边的非角色的布景物,可视为物象。若由此给意象定义:所谓意象,其实就是“物的修辞物”,当物象以单个出现,后个“物(意象)”又系前个被修辞物寓意的放大与延伸时,我们称其为“独立意象”,还有些意象表面是看不出修辞关系的,而是通过诗力场场化出来的,它(他)们系以一个群体来影射另一个群体,我们称其为“复合意象”。
独立意象,“物的修辞物”
独立意象鉴别起来很简单,只需诗句中“像”字“是”字“宛如”等等后面的物找出来,大部分便是意象(也有的属于隐喻,这些词语可省略),如,张三是王八蛋,“王八蛋”就是张三的意象,但张三不是意象,又如李四像只乌鸦,“乌鸦”就是意象,但李四也不是意象,因为张三李四只具有词的基本义,只代表其自身。只不过这些“意象”属于缺少诗性的低级“意象”罢了。
如庞德的代表作《地铁车站》
人潮中涌现着一张张脸;
如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花瓣点点
只有两个意象“黑色枝条”、“ 花瓣”, “黑色枝条”是人潮的意象,“花瓣”是脸孔的意象(人潮有的译作人群在此暂不作意象)
又如,伊沙的《名片》
你是别人的女婿
我是自个儿的爹
“女婿”“ 爹”是“你”和“我”的意象,但“你”和“我”不是,但伊莎管这叫口语诗,不叫意象诗,不过他自己说了不算。
又如艾青的《冬天的池沼》
给W。I。
冬天的池沼,
寂寞得像老人的心——
饱历了人世的辛酸的心;
冬天的池沼,
枯干得像老人的眼——
被劳苦磨失了光辉的眼;
冬天的池沼,
荒芜得像老人的发——
像霜草般稀疏而又灰白的发
冬天的池沼,
阴郁得像一个悲哀的老人——
佝偻在阴郁的天幕下的老人。
像字后面的物象都是前面物象的意象。
又如:李白的《静夜思》
床 前 明 月 光,
疑 是 地 上 霜。
举 头 望 明 月,
低 头 思 故 乡。
只有一个意象,“霜”,其余皆为物象。
又如杜牧《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只有一个意象“二月花”。
又如苏轼《饮湖上初晴雨后》
水光潋艳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只有一个意象“西子”。
有时,像字是字等词语和修辞物可省略,但有隐蔽的修辞关系也是意象,如孟浩然《春晓》
春 眠 不 觉 晓,
处 处 闻 啼 鸟。
夜 来 风 雨 声,
花 落 知 多 少。
此处只有一个意象“春”,在此处“春”字是被比作了一个睡醒的人。当然了,若按教科书的惯常解读办法也可解释成叙述,(我)一场香甜的春睡不知不觉醒来,那么这首诗便无意象。
又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颖是银河落九天。
尽管无像字和是字,但“香炉”和“紫烟”仍是庐山的意象,“银河” “九天” 是瀑布的意象。
有时候意象和物象也会混淆,无明确界限(多数为复合意象,下文讲)全看读者怎么读,如杜甫的《绝句》 :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若非要从中找出一个独立意象,只有一个“窗”,因为后面的“含” 字令“窗”字具备了“口”字的修辞性,但这又造成了和下句“门”字的撞车,所以从下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来看,这个“窗”也不是意象,这个“含”字还只能当“涵盖”“包含”讲,否则杜甫就会把下句改成“门吐东吴万里船”了,岂不更加对仗。
复合意象
所谓“复合意象”就是被诗力场“场化”的物像,多数凭借相近之物的组合以达到“同气相求”“互生互动”的影射效果,它不能离开那个“场”而存在,一旦离开便被打回原形由意象成为物象,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一旦提出一句这些物都是物象,但两句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场”,这些物都被“场化”(诗化)了,成为了“美”或“道”“禅”字的分体意象。
在古诗中有很大一部分诗歌属于复合意象,也有的是物象和意象兼有,不能单独提出一个物象说,这个物象代表什么什么,那样会断章取义破坏诗歌的整体寓意,针对某些专家教授考古似地研究古诗(比如,有人查了几万卷书考证床前明月光的“床”,到底是个啥东西),实际都是把“诗”当成“尸”了。
如前面提到的如杜甫的《绝句》 :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西岭“雪”“门”“船”等等物单独提出皆为物象,单独提出一句也是物象排列,但他们合在一起却组成了一副绝妙的山水画,皆可视为复合意象。
再如杜甫《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相对于上一首的双句成诗,这首是以单句为单位的复合意象,因为“风急”“天高”“猿啸哀”,这三个物象就可构成“悲秋”(在古代,秋字含有肃杀之气)图,而在“无边”“萧萧下”的修饰下“落木”也成了意象。但即便如此,也不可随便提出一个物象单指什么,这些物象还是代表其自身。
又如:马致远 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些物象随便单独提出哪一组或哪一个都是物象,合在一起成为了悲凉之秋“秋”字的意象,只不过“小桥流水人家”是中性的,有些勉强。
现代诗中,多数为复合意象和简单意象相融合的,复合意象并不一定非得出现在复杂的诗中,简单之诗和复杂之诗均可存在,如现代诗中顾城的《感觉》
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中
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
一个淡绿
“天”、“路”、“楼”、“雨”、“孩子”单独提出皆为物象,组合一处成了一幅“意境画”的复合意象。
又如于坚的《零档案》(原文略)
虽然看起来很庞大,实际结构也很简单清晰,若把《零档案》设定为一个中心意象,那总标题下的《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日常生活》《表格》这五个小标题便可视作它的五个分体意象,而每个小标题下的物象群也可视作它们的分体意象。实际上就是个《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日常生活》+《表格》(为什么)=《零档案》的算式。
咏物诗的物像大部分属于复合物象。如郑板桥的《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又如,于谦《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些诗只有一个中心意象——标题,每一句都可理解为是所省略这个中心意象的复合意象,单独拿出某个物皆为物象,否则就得解释成一锅粥。现代咏物诗也是,例子略。
事像
所谓事像,顾名思义就是能产生象征、隐喻效果的叙事情节,它也应算作复合意象的一种,在诗中一般由多个有内在联系的短情节组成。但不是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事像,也有很多叙事诗即为叙事本身,此处所言“事像”是指那些具备彰显普遍意义的典型情节,是把那些故事性的叙事诗和那些吃喝玩乐的有趣段子排除在外的。
在古诗中“事像”可理解成“用典”。如李商隐《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庄子梦蝶的典故,杜宇化杜鹃的典故,南海鲛人哭泣时眼泪化为珍珠的典故,在这好比是个“同心圆”,被一个“思”字穿成了“连通器”,这些典故在这已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而是都具有了影射性和互生性。
又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词中孙仲谋抗曹、刘义隆北伐、佛狸反宋、廉颇被弃用的典故皆为事像,都是来反衬自己壮志未酬的心境。
由于白话新诗不像格律诗要求那么严格,因此对事像运用要随意得多,大多是随意拟造穿插任何情节,而不必像格律诗那样仅仅是把人所共知典故的标签贴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金斯堡的《嚎叫》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
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天使般圣洁的西卜斯特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星光闪烁的发电机沟通古朴的美妙关系,
他们贫穷衣衫破旧双眼深陷昏昏然在冷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着烟飘浮过城市上空
冥思爵士乐章彻夜不眠,
他们在高架铁轨下对上苍袒露真情,发现默罕默德的天使们灯火通明的住宅屋顶上摇摇欲
坠,
他们睁着闪亮的冷眼进出大学,在研究战争的学者群中幻遇阿肯色和布莱克启示的悲剧,
他们被逐出学校因为疯狂因为在骷髅般的窗玻璃上发表猥亵的颂诗,
他们套着短裤蜷缩在没有剃须的房间,焚烧纸币于废纸篓中隔墙倾听恐怖之声,
他们返回纽约带着成捆的大麻穿越拉雷多裸着耻毛被逮住,
他们在涂抹香粉的旅馆吞火要么去”乐园幽径“饮松油,或死,或夜复一夜地作贱自己的
躯体,
用梦幻,用毒品,用清醒的恶梦,用酒精和阳具和数不清的睾丸,
颤抖的乌云筑起无与伦比的死巷而脑海中的闪电冲往加拿大和培特森,照亮这两极之间死
寂的时光世界,
摩根一般可信的大厅,后院绿树墓地上的黎明,屋顶上的醉态, 兜风驶过市镇上嗜茶的
小店时那霓虹一般耀眼的车灯,太阳和月亮和布鲁克林呼啸黄昏里树木的摇撼, 垃圾箱
的怒吼和最温和的思维之光,
他们将自己拴在地铁就着安非他命从巴特里到布隆克斯基地作没有穷尽的旅行直到车轮和
孩子的响声唤醒他们, 浑身发抖嘴唇破裂,在灯光凄惨的动物园磨去了光辉的大脑憔悴
而凄凉,
他们整夜沉浸于比克福德自助餐馆海底的灯光,漂游而出然后坐在寥落的福加基酒吧喝一
下午马尿啤酒, 倾听命运在氢气点唱机上吱呀作响,
他们一连交谈七十个小时从公园到床上到酒吧到贝尔维医院到博物馆到布鲁克林大桥,
一群迷惘的柏拉图式空谈家就着月光跳下防火梯跳下窗台跳下帝国大厦,
絮絮叨叨着尖叫着呕吐着窃窃私语着事实和回想和轶闻趣事和怒目而视的对抗和医院的休
克和牢房和战争,
一代睿智之士两眼发光沉入七天七夜深沉的回忆,祭祀会堂的羔羊肉扔在砖石路上,
他们隐入新泽西禅宗子虚乌有乡留下一张张意义含糊的明信片,上面引着亚特兰大市政厅…….
诗人随意截取了生活中的若干个侧面,就像上帝造人一样,“一根头发”、“一个指甲”、一个关节样把它们粘结起来,组成一张时代的立体画,这些情节单独提取可能没什么诗性,但组合一起却具有了整体的映照性。
“意象诗”与“口语诗”
不知道“意象诗”与“口语诗”的概念是不是伊沙命名的,因为这两个概念实在模糊,是指意象多了叫“意象诗”还是有意象的诗就是“意象诗”?抑或无意象的诗就是“口语诗”?据说“口语诗”的概念是作为“意象诗”的对立面(当年盘峰论战之后,诗江湖论坛经常见到辱骂“意象诗”的所谓口语诗人)而出现的,但“口语诗”并不和意象有冲突呀,它俩是两门子构不成矛盾关系,假定把“独立意象”的概念设定为打比方用的物,“口语诗”比书面语更兼容意象才对,又如何和“意象诗”对立呢?我们不妨把当年盘峰论战双方代表作品拿来参照一下:先看伊沙的《饿死诗人》
那样轻松的 你们
开始复述农业
耕作的事宜以及
春来秋去
挥汗如雨 收获麦子
你们以为麦粒就是你们
为女人迸溅的泪滴吗
麦芒就像你们贴在腮帮上的
猪鬃般柔软吗
你们拥挤在流浪之路的那一年
北方的麦子自个儿长大了
它们挥舞着一弯弯
阳光之镰
割断麦杆 自己的脖子
割断与土地最后的联系
成全了你们
诗人们已经吃饱了
一望无边的麦田
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
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
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
麦子 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
我呼吁:饿死他们
狗日的诗人
首先饿死我
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
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
若意象多了就算意象诗,那么这是一首典型的“意象诗”, 诸如“泪滴” “猪鬃” “麦子”(以及“麦子”的复合意象“ 阳光之镰”“脖子”), “农夫” “帮凶” “杂种”等意象比比皆是。
再看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然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正如你,要忍受更剧烈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你的
拉丽萨,那美丽的、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就在眼前!
还有烛光照亮的列维坦的秋天
普希金诗韵中的死亡、赞美、罪孽
春天到来,广阔大地裸现的黑色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苦难,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
而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 月的冬天
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寻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
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
虽然(破碎的)节日、(笔下的)刻痕、(高贵的)名字、风雪、钟声等可视作意象,因为修辞性不强,或因取自大众日常用语失去了修辞性,除了“钟声”外视作物象来解读也未尝不可。
由此可见,所谓“口语诗”的概念和“意象”其实关联不大,只是多了几句粗鄙俚语而已,甚至伊沙诗歌中的意象密度远大于王家新,如同余怒写“口语诗”骂“口语诗”一样,很可能伊沙们骂了多年的“意象诗”弄不好是在骂自己,王家新们只不过李代桃僵的替罪羊罢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