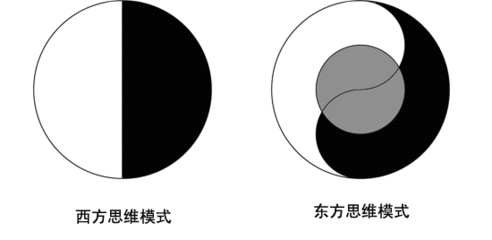月亮与中国文化
严行
月亮是中国文化的密码。
月亮在世界各国各族中都没有在中国文化中的显赫地位。在中国古诗词中,咏月可谓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有陈风的《月出》、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中有《明月何皎皎》,最早的文人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有“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之语,此后到数不胜数的唐宋诗词,写满了对于月亮的吟诵,月亮在中国人的心底投下不可磨灭的光影。几千年的古老农业文化中,月亮留给这个民族以至为深远的影响,世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对月亮存有如此情深意长的感情了!
一、农耕与月亮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长期存在的历史悠久的小农经济之国,晚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上,中国始终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农社会。农耕生活是这片气候温和的广大区域中人民最典型的存在方式。农田、农业、农家、农事……,人们在“举头望月”与低头务农之间,俯仰一世。这是绝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漫长岁月中的基本活动,也是他们祖祖辈辈都过着的相同的日子,或者说,是他们的命运。
当然,也曾有人厌倦了这种“土里刨食”的活法,想通过举孝廉或中科举改变命运,在他们春风得意进入仕途之后,远在农村的故乡,依然是他生命的最后依托,一旦宦海翻船,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归耕”,“辞官归故里”。那个农耕的家园,是他永远不能放弃的生命之根,也是他有朝一日一败涂地之时唯一的安慰。当然,若是他飞黄腾达,甚至称雄天下,家乡也是他炫扬富贵的所在。一世英雄项羽不就说“富贵不归乡里,犹衣锦夜行吗?”汉皇刘邦坐了龙庭之后,不也带着浩浩仪仗回故乡耀武扬威一回吗?
“农耕·故乡·月亮”是中国文化三位一体的核心。
如果说农耕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故乡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月亮则是这种生活精神的代表。三者是紧密相联的。
农耕生活让人与土地牢牢地拴在一起,彼此不可分离。根据“条件”必将向“目的”转化的规律,土地最终成为农民的依赖。于是,农民,唯有农民,对土地才会有最深切强烈的感情。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人的故乡情结。在全世界各族中,唯有中国人对故乡故土的怀恋之深,万难磨灭。中海外,到处都有中国人的同乡会,也只有汉语才有“乡亲”这样的名词。翻遍《圣经》会发现,神几乎从来不拣选农业民族也不拣选农民,大概原因就在于农耕文化之下,人对土地、对世界恋得太深吧?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祂所指示的地去,亚伯拉罕应命而行,从此一百年再也没回过他的故乡——当时世界最繁荣的大城吾珥。从《创世记》中,我们从来看不到亚伯拉罕的“思乡”之情。他放弃了他原来定居的生活,以及荣华富贵的家业,甘愿“百年孤独”,支搭帐棚,游牧一生。这是中国人很难认可的决定,也是中国人很难接受的选择。许多华人曾问“当初耶和华为什么不选择中国人?”言下,若是选了中国人,岂不是今天会有十几亿的基督徒,何等大的人口优势?但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上帝深知人心,祂知道人的一切心怀意念,知道中国人迈出家门的一步是如何艰难!
《圣经》从“新约”到“旧约”,在上帝所拣选的先知、使徒之中,罕有农民。《圣经》中第一个农民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杀人犯该隐,他杀死了弟弟亚伯;从方舟走出的挪亚后来似乎是做了农民时,而做了农民的挪亚也犯下了他饮酒过度赤身露体的过错。农耕文化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对民族自身文化的保持充分警醒,其实是华人基督徒应该注意的。
农耕生活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种植年复一年明确的周期性,要求对历法、气候、天象、季节有明确的了解,这导致了中国有着世界上最详尽清晰的历史纪年。中国人从远古就发明了天干地支纪年方法,以六十甲子轮回的方式循环不断。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共和元年开始,一直完整记录到今天,令西方史学惊异。西方世界以前从未有过这样完整的历史纪录,公元六世纪僧侣狄奥尼西将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公元元年的建议,为教会接受,才有了统一的纪年法,而直到一千年后罗马教皇制定的格里高利历法,才成为今天国际通用的“公历”。因此,对比中国史书,圣经旧约历史几乎很难确定发生的时间。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左传》,准确记载了历次大战的时间地点,准确到某一日,甚至到某一时辰。而圣经中出埃及记、士师记、撒母耳记都不存在准确的日期。究其原因,那时并不存在可以广泛承认的历法,因此无法确定年份。
中国的历法为一种阴阳合历的特殊形式,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为月,以地球绕太阳的周期为年。以大约十九年七闰的方式调整年与月的差值。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了以日、月为基本单位的习惯。在印刷并不广泛的古代,百姓家中虽然没有历书,他们抬头望月,便知道这一天是几月几日了。
此外,需要掌握晴雨规律的农民,也在观察月亮的过程中,了解未来的气象情况。月亮不仅告诉人们现在的农时,月亮也告诉他们未来的日子可能是阴还是雨,所谓“月晕而风,日晕而雨”、“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不怕初一雨,就怕初二阴”……都与月亮有直接的关系。
农民早出晚归,与日月相伴,月亮在他们的生活中结成了不解之缘。仅以田园诗人陶渊明为例,就有“清晨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等关于月的诗句,可见在他劳作或休息之时,在他下田与收工之际,头顶的月亮,陪伴他,“月亮走,我也走”,给他莫大的心理慰藉。
作为这一文化的遗留,中秋节到今天一直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为温馨幸福的庆典,是集丰收、团圆、欢聚为一体的节日,而这美好的日子,又是与头顶的明月一同欢度的。五谷丰登,繁衍多多,人丁兴旺,生生不息,花好月圆……,所有农耕生活所盼望的美好,都最大程度地体现在这个节日中,而天上,那轮又大又亮的中秋月,代表着圆满,代表着光明,代表着祝福,让人心头充满快乐——世俗生活的快乐。
这是属于农耕文化的快乐,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快乐。
月亮,作为农耕生活的象征符号,就这样在中国农耕文化的每一页都打上了它的印迹。月亮在中国人心中是如此重要,因此在中国,民间有“拜月亭”,皇家有秋天祭月的“月坛”,由此可见,月亮是多神崇拜之中国人的祭拜对象之一。
《圣经》提到月亮的次数是十分稀少的。在《圣经》前五卷的“摩西五经”中,唯有最后一卷《申命记》先后提到两次月亮。这两次,上帝耶和华都清楚无误地教训世人,唯有祂是神,人不可拜别神,不可拜日月星辰。耶和华说:“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事奉它”、“(不可)去事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申命记4:19;17:3)。上帝知道人心里所想的,因此上帝在三千五百多年前就藉摩西写下祂的诫命,警诫人不可以月亮为祭拜对象。
月亮作为上帝的造物之一,在宇宙中本没有特别的位置,中国文化向月亮移情,甚至祭拜,这是其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二、审美与月亮
从形而下的具体生活中升华出来的形而上审美文化,既是存在的一种抽象反映,也从另一方面揭示存在的本质。
儒道杂合的中国文化,虽然老子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说法,但他更强调“知其雄,守其雌”,强调“以柔克刚”;虽然孔子也说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刚强进取之辞,但更多的时候他表现的是温柔敦厚的一面,推崇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内向性格,以及含而不露、温文尔雅的理想人格。他排斥的是伉直好勇、率性急鲁的子路,爱重的是谨行慎言的颜回。《说文解字》中,许慎以“柔”释“儒”,所见颇深。
农耕文化的固定与不变,导致了中国文化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侧重于静止的、不变的、稳定的、秩序的特点。农民守着家园,自然是“深固难徙”,直到王朝末期,兼并剧烈,农民失地,才会被迫成为“流民”。当不流动的农民开始流动时,社会秩序就走向混乱了。“流氓”成为中国文化特有的贬义词,原就本是指这种“流动人口”。直到今天,“流动人口”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西方社会,人的迁徙移民是正常的,但在中国,除了朝廷下令进行的移民活动,人口大规模移动往往都是政治的祸因。因此,中国文化语境中,“安定”是可喜的现象;“动乱”是可怕的问题。老子提倡“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高扬“仁”道的孔子也说“仁者静”(《论语·雍也》)。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儒、道两家,在“静”这一问题上却殊途同归,这一点十分清晰地表现,二者虽在主张上各执一词,但毕竟都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土产”。
与“静”相应的,是中国文化的“柔”。老子认为柔能胜刚,他说“弱者道之用”,并以水作喻:“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子的“仁”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礼”则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次序。在君为“阳”,臣为“阴”的礼法格局中,除了天子一人为阳(“天子”面对天时则为“阴”),几乎所有人都为“阴”。这样一种将天下之人尽划入属“阴”一族的情形,必然构成了普遍的“阴柔”文化。这样,中国文化整体就呈现一种“阴柔”风格。就算是权臣武将,在君王面前,也只能行“臣妾之道”。由此,也可以解释中国文化的女性化倾向。
“月者,阴之宗也”(《淮南子》),“月者,太阴之精”(《大戴礼》),都将月亮推为阴的极至,就这样,月亮责无旁贷地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人化自然”。以中国人的眼睛看来,宇宙间唯有月亮,最能表现中国文化所追求的静态的、阴柔的特色。这样,这轮离地球最近的月亮,与农耕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月亮,同时也是他们审美意识最直接的投射对象。月亮的宁静感,月亮圆缺规律稳定的秩序感,月光的柔和、婉约、含蓄感,月光之下万物的朦胧、蕴藉、淡远感,都与中国人的审美意趣相合,因此,在世界上,唯有中国人对月亮有最浓郁的深情。
以诗歌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关于月亮的诗词歌赋,关于太阳的却少得可怜。农耕文化与太阳的关系本应是更为密切的,为什么中国的诗人却绝少以太阳为抒情对象?究其原因,审美感受的巨大差距是这其中的主要因素。对于静态的阴柔的中国文化来说,太阳过于强烈了。在古典诗歌中的太阳,最多也不过是“夕阳、残阳、斜阳”之类近似月亮效果的落日。这一情形直到五四以后,新文化大举进入,工商业发展导致传统的农耕文化受到巨大冲击,文学景观方为之一变,歌颂月亮的作品大为减少,礼赞太阳的作品蓬勃出现,这可以视为中国文化转型带来的文学效应之一。
在《圣经》中关于月亮的记载很少,以总数150篇诗篇为例,只有7篇提到月亮。在这些诗中,或以月亮为喻显示上帝的大能,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诗8:3)、“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诗104:19)、“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诗121:6)、“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136:9);或用月亮表达时间的恒久,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诗72:5、7)、“他(大卫)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诗89:36-37);或用表达整个宇宙自然对上帝的赞美,如“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诗148:3)。《圣经·旧约·诗篇》中这种有关月亮写法,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绝不存在的。农耕文化的实用主义和世俗精神最缺乏的就是《圣经》所展现的这种超越性、终极性,当然也更不会有认识上帝掌管宇宙万物的恢宏意识。中国文化中对月亮的态度是,把上帝所造的高悬夜空的月亮拉下来,让它成为自己生命的点缀或安慰,让它与自己一起悲欢,让月光照耀下的人生多一点温柔平静。这种浓郁的世俗倾向是与《圣经》完全不同的。
如果说上帝用《圣经·旧约·诗篇》中的月亮向人启示祂的创造、祂的永远、祂的慈爱、祂应受的赞美;那么,在《圣经·新约》中共有三处关于月亮的经文则全是警示。其中出现在福音书中的,都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对门徒的告诫:“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马太福音24:29),“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马可福音13:24)。中国人心中最温柔的月亮,在这里是可怕的征兆,是灾难的预示,警告世人末世的必然临到。这一点,大概也是中国诗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三、抒情与月亮
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牵动无数中国人的感情。中国文化里的各种情感都可以藉月亮传达。比较而言,古文中关于太阳的别名十分有限,而关于月亮的别称则多而又多。“嫦娥”、“婵娟”、“素娥”、“素魄”、“金蟾”、“玉兔”、“广寒”、“玉盘”、“桂宫”、“天镜”、“玉轮”……,这些不同的充满诗意的名称,充分显示了中国人对月亮的热爱。望月怀远,观月有感,对月抒怀,月下悲秋,瞩月思乡……,成为人在不同境遇下抒发心绪的方式。在中国人的感受里,月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月亮是有生命的,是与人相系相通的。
李白《静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照进古来无数异乡游子不眠之夜;杜甫《月夜》中的“今夜鄜州月”,更将乱世思亲之情展露无遗;苏轼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安慰了彼此思念的亲友之心。“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秦时明月汉时关”,跨越时空,寄托着历代思妇遥念征夫的苦情;“晓风残月”与“月上柳梢头”,道尽恋人的悲欢;而失意文人更是藉月亮抒发其满怀惆怅——“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吟风啸月”也往往是他们苦中作乐,放浪形骸的方式;即使是苏轼力图从“入仕”与“下野”的狭隘圈子中脱出,也仍然是藉月亮表达他的挣扎与旷达“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云散月出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可以说,若是将月亮从中国古典诗文中删除的话,那么中国文学会损失很大比例的佳作,中国文学的蘊藉婉约、绮丽缠绵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以南唐李煜而言,在他存留世间有限的词章中,绝大多数都与月亮有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笛在月明楼”(《望江南》)“花月正春风”(词牌同上)“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乌夜啼》)“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中国人对生命哲理的表达,对宇宙永恒、人生短暂的追问与慨叹,不用说,更是与月亮紧紧相联。《春江花月夜》最深沉的疑问是向月亮发出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李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叹也是向月发出的。月亮竟是如此地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纠缠不休,以至参禅谈玄,喻理论道,都不免拿月亮说事,寒山禅师就以“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更与何人说。”来表达他宁静淡远的心境。一轮明月,在中国文化中处处闪光,无疑地,“此中有真意”。
以阴柔、宁静、安稳为基调的中国文化,追求的是朦胧、空灵、妙悟的诗性思维方式,即一种典型的非理性思维方式,月亮可以说是这一文化的代表符号,月亮的柔和,月光的朦胧,月夜的幽渺,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一切,显然与阳光下的明晰性、确定性构成相反的对比。确定性与逻辑性是相关的,朦胧性与诗性相关。因此,中国文化缺乏逻辑性就不足为奇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作为诗,是能唤起人强烈感情的句子,但作为一种观念来说,则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在中国的六大传统节日中,“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重阳节”,其中两个节日都与月亮相关,占了三分之一,月亮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了。《圣经》中,以色列民的节日也很多,但全与月亮太阳无关,他们的节日只是纪念上帝耶和华对他们的拯救,此外就是谨守每七天一次的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些节日带他们追想耶和华对他们的慈爱与怜悯,也让他们谨守自己的心。欧洲也有很多节日,同样全无类似中国中秋节的节日。关于月亮的节日,只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景观。
当今天中国人绵软摇曳地唱道“月亮代表我的心”时,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也曾准备为他所爱慕的朱丽叶“对月发誓”,然而,他的誓词未及说完就被朱丽叶急切地拒绝了。朱丽叶说:“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幼无常的,每个月都有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
看来,月亮只能代表中国人的心,不能代表他人的心啊。
被月亮所代表的中国人,在欢度月亮的节日“中秋节”之季,该驻足深思一番我们的月亮文化了。世人应当记住的,是《圣经·诗篇》中的话:“你(上帝)安置月亮为定节令”(诗104:19)。因此,月亮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美好的恩典。故此,面对月亮人最正确的表达,是应该赞美爱我们的上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