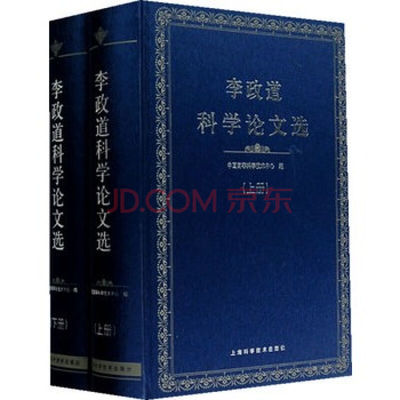马良死了快一年了,但他死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我还记得。最近,我发觉自己的记忆有衰退的迹象,所以我想了想,还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好。
一
马良和我念的是医科大学,当初我俩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大学毕业后马良回老家当了医生,而我则完全抛弃了原专业,考进了省城电视台做记者。马良说话喜欢用排比句,当时他形容我的举措是“关公战秦琼,牛头不对马嘴,屁股决定脑袋,”白念了五年大学。我说自己的悟性实在很低——看个病人没半小时下不来,开药专挑便宜的,动手术绝不会把纱布落在病人肚子里,这样的医生怎么能称得上合格?马良摇摇头,说我总是太偏激。我拍拍他肩膀,说他和神笔马良是同个祖宗,手上的活儿都挺出类拔萃的,以后一定要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没想到这最后一句话却一语成谶,而马良竟是以异常悲壮的方式完成的。
毕业后我和马良就断了联系。有时想起也觉得不可思议,昨天还在一起勾着肩膀喝酒,今天却连话都说不上了。偶尔,我会突然想起他温良的脸庞,但转瞬间又消失了。我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没想到有一天他竟然主动找到了我。在某个异常闷热的夏日傍晚,距离大学毕业已经六年的时候。
马良先是给我打了电话。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得知我的手机号码,所以刚听到他的声音,我很惊奇。他一上来就说想上省城来找我,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他没和我寒暄,直接就奔了主题。这又让我觉得惊奇。因为印象中,他这个人说话做事总是带点温吞的感觉,没想到六年后的这通电话里,他说话竟然如此干净利落。
我嘿嘿笑出了声。职业的敏感让我觉得马良打电话给我,多半是有事想我帮忙的。虽然我们曾是一起逃过课、给女生打过分、看过A片的上下铺关系,但多年来的记者经历却让我长了个心眼,我习惯了用复杂代替简单,用绕弯代替笔直。我笑着说他几年没见,变性了,从前是喜羊羊,现在是灰太狼了,看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是经不起时代考验的。
听了我的话,马良在电话那头竟然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才叹了口气,对我说:小飞,我没变,恐怕是你变了吧。我是真有事,有急事找你,我没时间和你打哈哈了。
马良最后一句话我不爱听了。我不欠他的,没有道理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但我没将这种不快表现出来,只是收起了笑脸,淡淡的回答他:看把你急得,天塌下来了不成,可找我什么事呢?我个子小,撑不起天。
马良用很坚定的口吻说:是正经事,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很多人,这件事无论如何你要帮忙的。
这句话存在很多疑点,比如为了很多人的“正经事”,应该去找领导,而不应该来找我,我只不过是个小记者。再比如难道为了很多人的“正经事”,我就非得帮忙吗?个人能力很渺小,我越老越明白这个道理,我本想先和马良解释清楚,但容不得我多说,他就把电话挂了。
他和我约好明天傍晚见面,他坐明天一早的火车过来。我终于要见到马良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有着一丝的忐忑。这很怪异。
二
我差点认不出马良了。他消瘦和苍老了很多。一幅黑框眼睛耷拉在他的鼻梁上,头发掉得很厉害,稀稀疏疏随风摆。念书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他是有谦谦君子风度的,混在一堆邋遢男生里他是出众的,因为只有他和大家一起欣赏真人版“动物世界”的时候,不脸红脖子粗。而且他还带着淡定的微笑。现在的他,眉头拧在一起,衣裳不整,彷佛全世界都欠他的,一脸的苦相。
我站在电视台门口,看着六年后的马良,心里有说不出的恨。周围熟悉的同事来来往往,我甚至愿意当做从来不认识他。
马良见到我很是高兴,脸上挤出了笑容,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刘小飞,刘大记者,终于见到你了!
马良说这话显得有些夸张了,他哪里是把我当同学看了,简直就当成亲人解放军了。我赶忙推着他往路边走,嘴里说:找个地方先吃饭,这里人多眼杂,小心敌特破坏。我这句话本来是玩笑的,没想到马良却当真了,停下脚步,警惕的看了四周,然后贴着我的耳朵说:有人跟梢,但被我甩了,放心。
我哭笑不得。那个时候我以为马良在说笑话,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真的。
我选了个偏僻的川菜饭馆。店里没几个客人,服务员是个胖姑娘,没事的时候就盯着苍蝇看。刚一落座,马良就急着打开随身携带的黑包,掏出一个文件夹,要打开给我看。我按住他的手,对他说:先吃饭后革命。
马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但我故意装作没看见,和他东拉西扯。等到菜终于上来了,他没吃上几口就放下了筷子,然后对我说:小飞,为了这件事,我找了很多人,可是都没人理我,现在只求你们媒体能帮我呼吁一下了,这事关系我们家乡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
我笑着说:朗朗乾坤,太平盛世,你又妖言惑众了。
马良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大声说:我不是在和你说笑,你认真听我说嘛。我轻轻脱开他的手,示意他慢慢讲。他说自己的家乡自从发现金矿之后,大肆挖掘,挖矿后的工业废水乱排放,环境一年比一年差,护城河见不到鱼了,城里人都喝买来的山泉水,凡是金矿周边的农田都不长稻子了,因为地下水都坏了。而更糟糕的是,这几年得癌症的越来越多,很多婴儿生下来就是畸形,甚至夭折。老百姓的健康,越来越差,我是做医生的,这些我都清楚。
他说话的语速很快,我不动声色的听着,偶尔吃几口“水煮肉片”,麻辣的味道直呛鼻梁。
马良见我没有动静,以为我不信,于是又打开他的文件夹,指着最上面的A4纸对我说:这是近三年来我家乡统计的癌症发病率,以及和全市其它区县的对比情况。特别是和周边县比较,我那儿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每千人致癌率甚至是其它地区的好几倍。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啤酒花汹涌而出。我深深喝了一大口,然后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冤有头债有主,水污染了,要找金矿主;生病了,要找金矿主索赔,不给的话就找法院;环境破坏,要向环保部门投诉;实在不行,还可以写举报信,找信访部门。有困难找市长,要充分相信政府嘛。
马良听了我的话,愣了片刻,接着一仰脖子灌下一杯啤酒。放下杯子,他狠狠的拍了下桌子,然后怒发冲冠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操你妈的刘小飞!我大老远来省城找你,不是来听你放屁的。我说的都是事实,是活生生的人。你作为记者要有良心,要替老百姓说话,要披露真相。你不要满嘴喷粪,和我打官腔。
马良又用上了排比句,这让我想起似曾相识的他。旁桌的客人投来异样的眼光,胖姑娘翻了翻白眼,见怪不怪的样子。我等马良不那么激动了,才开口说:你骂我有什么用?我只是个小记者,我的上面有责任编辑,有中心主任,还有编委会。我采访的新闻,不是所有的都能播出,新闻必须要经由他们同意才播出。先不说采访了,就是这样类型的新闻,披露社会阴暗面的,能不能通过选题都还不一定……
我能理解马良的心情,但很多事情不是我个人能为之。我尽量用简洁的道理向他说明这点:再说了,我们媒体的作用能有多大呢?你看的也许只是污染环境了,死人了,可是这背后的黑洞有多深,你能知道吗?难道仅仅是破坏环境那么简单吗?你动得了他们么?
他们!马良眼神有些发呆,嘴里轻轻说了这两个字。他咧嘴苦笑,然后就不再出声。他的智力不差,应该知我说的是什么。这曾经让我很是无奈,但后来我也就麻木。这或许也可以当作马良认为我之变的注脚。
从川菜馆出来,天空已经换做一块巨大的黑幕。我仰头望,看不见尽头。马良也抬起头,忽然他问我已经有多久没看见星星了。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留马良在家过夜,他婉拒了。他说已经订好夜班的火车,摇晃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回老家了。他说话的时候,是失望的眼神。我无法对他做出任何承诺,他一无所获。我只好安慰他,让他将相关情况发电子邮件给我,然后等我的消息,我回去后再想想要怎么弄。
说完这句话我从马良的眼睛里捕捉到一丝跳跃的火花,但一闪即逝,他的眼神又黯淡下来。他小声的说,怕是来不及了。我一时没搞清楚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想追问下去。可他没回答我,只是转过身向我告别了。他慢慢远去,留给我个艰难的背影。我忽然想,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操蛋的生活,竟然让马良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三
回到家,老婆问我见到老同学了吗?我窝在沙发里,看着电视上重播的“新闻联播”,有些疲惫的点点头说有。她本来还想问我些什么,但见我似乎不想说话,于是也就作罢。转而给我泡了杯热茶,陪我一起看电视。
老婆知道我和马良是大学同学,而且是睡上下铺的。六年没见,总有些说不完的话,但我在面对马良时,却常常失语。我甚至没来得及问他这几年来的情况。我们见过面,说过话,可怎么感觉却是那么虚无。
正想着出神,门口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我们家一向很少人拜访的,晚上有人敲门,这让我和老婆都觉得很奇怪。我起身开门,站在门外的是杜九,满脸是暧昧的笑容。这一幕发生在夜里,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杜九也是我大学同学,他是省城当地人,念书的时候是走读,平时总是很神秘的样子,和我们这班住宿的同学没什么来往。毕业后他靠家里的关系留在了省第一医院,要知道那是所三甲医院,那时我们这种地方医科学校毕业后能进去的,少之又少。毕业后我见过他几次,似乎在某个会议的现场,他脸上总带着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有些让我敬而远之。但总的来说,我和他之间是没有交集的。所以他今晚的到访,让我心生疑虑。

我呆在门口好一会儿,还是杜九先开了口:刘大记者,你就是这么对待老同学,把我晾在门外的吗?
我回过神,拉开门让他进来:咳,这不是夜黑风高,最近社会恶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嘛,我这是紧张过头了。对不起了,老同学。
杜九轻轻笑了一声:你少来了,不把我当阶级敌人对待,我就要感谢你了。
我关上门,然后深深看了他一眼:杜九你可是个稀客,这么晚找我,不是要找我做思想工作的吧?杜九念大学的时候,做过一段时期的团委书记,以勤做女生思想工作而闻名。我们医学院女生寥寥无几,据说都接受过他的谆谆教诲。
杜九没接过我的话,看到我的老婆,用很热络的声音说:哟,这是弟媳吧,刘小飞好大的福气,娶了个这么好的老婆。杜九张嘴就说胡话,看样子似乎比我还更了解我老婆。老婆微笑谢过了杜九,给他倒了杯茶,然后就回了卧室。杜九看着卧室的灯灭了,然后将脸上暧昧的微笑抹去,突然严肃起来。他问我:小飞,晚上见了马良了吧?
我的心里打了个愣,他问得很唐突,我猜不透他是什么用意。我和他开玩笑,问他难道对我有兴趣,跟踪我了?杜九倒是不隐瞒,他说自己跟踪的是马良,但没想到却见到了我。杜九说得如此不慌不忙,我的后背却一阵冰凉:没想到马良说自己被人跟梢这件事是真的,而且更加没料到的是,跟梢的居然是杜九。
杜九发现了我脸上的异色,然后不自觉又露出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他笑着说:你不用怕,我们要相信群众嘛。我和你坦白说了吧,马良为了矿山排污的事,写过举报信、贴过大字报、甚至好几次上访,他的行踪早就被掌握了。不过现在强调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嘛,地方政府不好限制他的自由。可是,他为了这件事,穷尽一切办法,这些情况我们都是了解的。
我不解,问他: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杜九神秘的笑了笑,然后靠在沙发背上谦虚的说:我早就离开了医院,现在信访局工作,负责一小片业务。我点点头说:嗯,负责跟梢。杜九看着我,意味深长的说:你别用话来刺我。我们是同学,今天我是好心来告诉你情况的——要和马良保持距离!马良在省里也是挂号的,我们和地方时刻保持联系,就怕他发神经要进京告状。
严防死堵,稳定压倒一切。我问杜九,是这个意思吗?杜九没回答我,接着说:马良反映的事情,很多地方是不客观、不负责任的,他的做法完全是给地方政府正常的经济工作添乱。脚下有金山不采,那是傻子。安于贫穷不求致富,那是落后。你是记者,不能偏听一面,你自己也知道,这种事牵涉各方,不是你一个人能左右的。
杜九说话的样子,纯粹把我当幼儿园小朋友了,就差没用他厚厚的手掌抚摸我的脑袋。我是受过党多年教育的记者,稻和麦我还是分得清的。但我不喜欢他说话的语气,甚至是心生厌恶。于是我站起身,作送客的意思:谢谢你的好意!杜九似乎并不介意,往门口走的时候还对我露出了宽宏大度的笑容。临走的时候,他丢给我一句话:有时间先做个调查,看看马良做这件事有没有个人恩怨在里头,他是不是别有用心的!
杜九给我留下了个悬念,他要我自己去解开。我发现自己正慢慢陷入到一场诡异的关系当中。我无法止步或后退,只能任由某种神秘的力量推着我向前。
四
接下来的几天,我时常心神不宁。马良说的事,如果纯粹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看,是值得报道的。但说实话,我对这一“猛料”毫无头绪,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我尝试着从电视台带库中去找资料,看看以前是否有过类似的报道。很巧的是,竟然被我发现了。
这则新闻报道的时间是在2003年6月,在评论节目《特别关注》里播出,一个月内做了两次连续报道。新闻报道的内容,竟然说的也是马良家乡环境污染的情况。那时候,马良家乡刚组建的最大的矿业公司——吴山矿业有限公司,不慎将工业废水氯化氢排放到了护城河,造成水质严重受污染,上下游大量河鱼死亡。由于护城河沿岸有不少渔业养殖户,所以也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节目报道了污染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受灾渔民的愤怒,矛头直指吴山矿业。但是很奇怪的是,节目做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不见下文:吴山矿业是否受罚,渔民是否得到赔偿等等后续事宜,都不见报道。节目有始无终,总是有原因的。我看完片子,抱着头,长出了一口气。
马良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里面有文字资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天他要给我看的“癌症发病率统计表”,是市卫生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的一次秘密调查。想来马良是以自己做医生的便利偷偷复印的。表格上的对比数据触目惊心,某些人在造孽。还有些照片,是护城河今昔对比照片。矿山在河上游,沿河而下,绿水不见,鱼草不生。
我不断的在文档和图片中点击查看。我的心中忽然有了些冲动。当初做氯化氢污染事件报道的记者,正是我现在的中心主任。我没想到主任当时的报道是如此犀利,这和他多次“枪毙”我批评报道稿的形象截然不同。我简单做了个报道选题,附加马良给我的一些文字和图片资料,申报上评论节目。做的时候我心中全然没底,但咬咬牙,硬着头皮交了上去。
主任看过我的申报选题,轻轻放在一旁,摘下宽边眼镜,抬头看我。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了,他才问我是谁给我报的“料”?我有些发憷,但还是笑了笑说,根据保密原则,线人是不宜曝光的。他也跟着笑了,然后站起身,双手叉在有些发福的腰上。他问我知道当年吴山矿业的氯化氢事件吗?我说知道,而且当年那起事件就是您披露报道的。他又问我那是否知道为什么后面没了下文吗?我摇了摇头。主任下意识的往门外看了一眼,彷佛忌惮着有人偷听,可实际上门是关着的。他对我说:当初吴山矿业是明显的工作疏忽,玩忽职守。但那时这家企业刚组建,地方上盼着它能下金蛋,上面也有意进行扶持,所以这起污染事件最后仍然是点到为止,没再追究下去。现在,吴山矿业已经是上市公司了,鸟枪换炮,它还怕小小几篇报道吗?再说了,你现在打击的目标是一大片,大小金矿一起揭批,难度太大了。它们完全可以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死不认账,说你这些数据来路不明,毫无根据,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我急了:这不是有图片么?我还可以到矿区周围去采访,采访受污染群众,调查实际情况,取得第一手资料。主任重新回到了办公桌旁,戴起眼镜,手指敲着桌子:做了那么多年记者,你怎么还如此幼稚?我即使批准你去采访,但可能播出吗?现在正闹金融危机,舆论导向是强调保增长,你去披露这件事,让矿企停产,工人下岗,你说领导会同意吗?动动脑子,讲讲政治!
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我这样的典型。我默默叹了口气,为什么同一个人换了时间换了位置,却完全变了样。我仿佛是自言自语:那么,当年……主任听到我的话稍微愣了下,但很快又风卷残云,表情平静。
离开主任办公室的时候,身后传来一句话:你可以去看看,但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转过身本想追问主任几句,但却看见他埋首在文件当中,以致我看不清他的脸。
五
我决定去马良的家乡。去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查阅了些资料,了解了些情况。夜晚,我闭上眼,却整宿无眠。
我走之前谁也没告诉,甚至连老婆都不知道。就要上火车前,我几乎是同时收到了两条短信。一条是马良发来的,他问我情况如何,能过来采访报道吗?他说自己没时间了。另一条则是杜九发来的,他问我,是否搞清楚了马良在这件事中的个人恩怨?如果清楚了,会不会让我的意见有所改观——我改观他大爷!杜九一直在冒充思想引路人的角色,这很滑稽可笑并让我愤怒。
一进马良家乡的地界,满眼看到的就是“吴山矿业”的广告牌,还有当地政府立的一些宣传标语,特别是其中一条——“青山绿水,————黄金之乡,致富之路”,让我印象深刻。下了火车,我就给马良打了电话,他有些吃惊,问我怎么没提前告诉他一声。我说这还不是和他学的,趁其不备直捣黄龙。马良说让我稍等,过了片刻就看见他骑了辆摩托车“突突突”的赶来。
他比我上次看到更显得消瘦了,脸色愈发白了。头上戴顶帽子,从帽檐下可以看到他刮得干净的头皮。我坐上摩托车,和他打趣,说梅兰芳蓄须明志是为了抗日,你剃度做和尚是上演的哪出戏?马良不知道回了句什么,我只大约听到“以后会明白”这句话。
火车站离县城很近,马良载我先进了城。他问我这次来是采访的吗?我含糊的回答他先看看再说。他提议先去城东的护城河畔看看,那里离金矿不远,可以看到河水污染的情况;然后再去城西,那里是下游,住着一些以前的渔民。
马良自顾着说,完全没注意我的反应,也没问我是否同意。眼看着他重新启动摩托车想要离开,我拍了下他的肩膀,示意他先等一下,我有话和他说。
这个时候是午后两点,太阳热情有余,让人有些眩晕。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几只丧家的犬垂着大舌头喘着粗气。这里是县城,和所有中国进行旧城改造的小城镇一样,新与旧交替出现,不时有断壁残垣映入眼帘。小广告、“办证”等字眼如狗皮藓东一块西一块。街道上还有散落的红色塑料袋、冰激凌包装纸、西瓜皮等等。这些东西很眼熟,让我不会有陌生感。
马良不明白我的用意,呆呆的看着我。豆大的汗珠顺着他脸上的沟壑落下,嘴唇没有血色,太阳帽将他的脸衬托得更小。我心中忽的有了一丝的悲酸,六年前的他不是这样的,人怎么说变就变了。我问他:马良,我们是朋友,你老实告诉我,你做这件事还有没有其它目的?
马良先是一愣,但接着似乎想到了些什么,于是他反问我: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是不是听到了些风言风语?
我不打算隐瞒他。我说:杜九,你还记得他吧?他来找过我,就是你来找我的那个晚上。他说他现在信访局工作,说他们早就注意到你了,说你上访、举报污染的事,有个人目的……
马良一声长叹,充满了悲哀。他的眼睛朝向天,我看到了浅浅的一湾水。他忽然冷笑:哼,河水都他妈烂成那样了,是个人都看不下去。说个真话为什么这么不容易?我都家破人亡了,我还能有什么“个人目的”?
家破人亡?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马良靠着摩托车,这个时候他显得很虚弱。他对我说,声音有些抖:我三年前结的婚,老婆挺漂亮的,但跟人跑了。
怎么会这样?我皱起眉头,不知道这时安慰他是否合适。
操,怎么不会?马良嗓子一动,吐了口浓痰在地上,然后用脚踩净:潘金莲都能杀夫,我没被杀已经是幸运的了。结婚后我一直很忙,经常不在家,我只是个普通医师,不努力不行。但赚得却很少。那女人结婚后就像变了个人,虚荣,说我赚钱少,最后是彻底的嫌弃。她跟了我们这儿的副县长,他正好死了老婆。
不过是没了老婆,至于家破人亡吗?我插了一句。如果跑了老婆也叫“家破人亡”的话,那我觉得马良也太不像个男人了。
马良索性坐到了车座上,并且不时的按着腹部,似乎很不舒服。他说话变得很辛苦:那女人是其中一个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我到处反映环境污染的问题。别人都说我是傻子,是疯子。那女人跟的副县长,刚好分管县里的矿山和企业,于是都说我是因为老婆跟别人跑了,心生不满,打击报复,不仅报复副县长个人,而且是报复整个社会。为了这个,医院停了我的职,父母也不理解我,都当我在发神经。我看他们才是有问题,为了这么个烂货,我至于吗?
这我就不解了,那马良你做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无名无利,自己捞不到一丝好处,难道真是活雷锋么?马良没有马上回答我,他让我坐上车,然后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摩托车穿街走巷,两轮卷起的沙尘,彷佛弥漫了天空。
马良把我带到了城西,紧挨着护城河的地方。那是一座红色砖瓦的两层楼,但明显是未完工,墙面没有粉刷,二楼甚至连窗户也没有装,看来只有一楼在正常使用。
马良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个十一、二岁左右的小女孩,瘦瘦小小的,病恹恹的样子。小女孩的眼睛倒是挺大的,多少还有些神采,她看到马良,叫了声“马叔叔好”,并把我们迎了进去。
因为朝北的缘故,客厅光线不好,厅里摆着几件不成样的家具和电器,都显得老旧了。有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走出来,眼袋很重,看见我们,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然后又折回房间去了。房间里传来沉闷的咳嗽声,声音不大但感觉却是用尽全力。马良拉着我走到了房间门口,屋里光线更暗,我的眼睛一时没适应,瞬间失明。几秒过后,我才看清有个枯瘦的男人半躺在床上,面部浮肿并泛着黄色,不时的咳嗽,近了听倒更像是声嘶。刚才见到的中年妇女捧着碗,正用汤匙给那个男子喂流质的食物。男子看见我们站在门口,有些困难的挤出了一个笑,并说“马医生好”,声音虽小,但却足够让我们听清楚。
我们又折回客厅,这里很安静,静得让我有些不自在。马良似乎经常来这里,进出都显得很随意。我看了马良一眼,示意他说点什么。但他故作不知,拉过小女孩,问她书都看完了吗?小女孩点点头,说都看完了,《活着》那本书最好看了。我吃了一惊,《活着》这本书是她这个年纪的女娃娃看的吗?马良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给她看这书。马良接着说他家里还有些书,回头他再带些过来。小姑娘说好。
马良让我在这里拍些照片,包括人和物。我不解,但他没解释,看他坚持,我只好拿起相机拍了起来。拍完照,我们就准备走了。临走前马良趁小女孩不注意,压了几张“老人头”在桌子上。出门的时候,小女孩站在门口小声的说,谢谢叔叔!小女孩仰着脖子,阳光在她的脸上打出分际线,明暗相间。马良这时笑得很灿烂,回答她说不用谢,下次再来。才转过身,我忽然发现马良的身体有些发抖,但他一直强忍着。等走到巷子的转角,离小女孩远了,马良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喘着气说:没有下次了,等不到了。
一个大男人,顶着烈日,在斑驳的小巷里,泪如雨下。
傍晚,我和马良站在护城河畔,夕阳把我们裹得严实。河水徐徐,和我们相对无言的流过。我已经傻站着快两个小时了。马良哭后就把我带到了这里,可是他愣是再没开口。这个驴日的,任凭我在一旁软硬兼施,上跳下窜,问他究竟怎么了,他就是不解释。最后我被逼急了,踹起地上的黄土,对他大骂:马良,我操你个傻逼蛋子,你他妈就是死了,也得死给我个说法!
马良不怒反笑了,在雨水充沛的夏日他的嘴唇却起了皲裂。他看着眼前的河,一字一句的说:快了,阎王爷在催我了。小飞,我得了肝癌,现在已经到第三期了,我没时间了。
我大吃一惊,粗暴的打断他的话,骂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得了肝癌不好好治疗,到处折腾是为了什么?这样做,是想死得更快吗?
马良说: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期了,你也是学医的,治疗多半也是自我安慰罢了。得知自己患癌的时候我很沮丧,觉得上天对我很不公,老婆跟人跑了,身上又没钱,现在又得了重病,真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那天我经过血液科,听到有小女孩的哭声,我走过去看,看到一位瘦小的女孩抱着大夫的手,哭着说自己不治了,要把钱留给爸爸治病。我向一旁的护士打听,原来这个小女孩得了白血病,但却不愿意接受治疗,说要把钱留给她爸爸治疗。她爸爸得了肺癌,晚期。这个小女孩,你刚见过了。
是,我是见过了。病恹恹的她,她垂死的爸爸,还有破败的家。我都见到了,亲眼所见。可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马良忽然看着我,摇了摇头:小飞,也许你是真的变了。怎么没关系呢?医者父母心啊,这是最基本的吧。我找到了这个小女孩,想多少帮助他们一些。到了他们家,我才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其实算不得什么。小女孩爸爸原来是渔民,挨着护城河的地方租塘养鱼,眼看着就要发家了,却没想到吴山矿业排放氯化氢,导致鱼全死光。吴山公司推卸责任,没有赔偿,这就害惨了这家人,让他们欠下一屁股债。为了还债,小女孩爸爸什么活都干,可没想到家里一个接一个的得了癌症。
我忽然想到了小女孩的大眼睛,心里猛地一阵揪心。
你说,这是上天的错,还是谁的错?马良问我,我没有答案。他有些自说自话起来:因为家里穷,买不起山泉水,他们只能喝井里打来的水,而这井水早就不能喝了,都被污染了。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我问他到处奔波,反映环境污染的情况,就是为了替小女孩一家要个说法吗?
马良说:是,但又不全是,我是要为所有乡亲百姓要说法!真正促使我站出来的,还是“癌症发病率”的调查结果。市卫生局秘密进行了“癌症发病率”调查,结果显示这几年家乡发病率明显偏高。当时的意见就倾向认为是因为金矿挖掘,乱排污造成的。可是,这么个严重的情况,市里竟然压着,外面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好几次在医务会议上提出要公开,要解决,要赔偿,但别的医生都视我为异类,院长甚至斥责我,说我这是煽动情绪,唯恐天下不乱。但我是这么想的,总要有人做牺牲者的。我了无牵挂,又将死了,所以就如你所说,到处折腾了。
这不是折腾,不是折腾。我喃喃自语。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
小飞,我也没时间折腾了。如果你能帮我把这里发生的事,报道出去,告诉外面的人知道,这就好了。如果办不到,也就算了。我还是太天真了,一个人左右不了什么的。马良对我说。
吴山矿业上市前发行过原始股,当时很多官员都买了。股票上市后,原始股翻了好几十倍。这是我调查到的一些情况。换个角度理解,现在要去动包括吴山在内的大小金矿,已经很难很难。但我不能把这个告诉马良。他死的时候,至少应该还是带着希望的。
我很想哭,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为了马良。
六
马良“头七”过完我才回台里。主任问我去了解情况,要这么久吗?我说我的“线人”死了,他没什么朋友,我帮他料理些后事。主任又问我有什么“收获”吗?我说有,然后将自己在马良家乡拍的照片和视频都拷在他的电脑里,还给了他一份文字报道稿,做成了专题形式。
主任看完我的稿子,然后再看照片。看到一半,他自言自语,说自己以前采访过这家人的。我凑过去看,是小女孩家的照片,有她爸爸,还有她自己。主任说,当年她才六岁,今年也该十二岁了吧。我告诉他,她爸爸得了肺癌,和我的“线人”同一天死的,小女孩得了白血病。主任听完,默然。良久,我似乎看见他眼睛有些湿润。我还想看清楚些,他却摘下了眼镜,揉着双眼。我又一次看不清他的脸了。
主任最终没用我的稿子。不过他通过关系,悄悄将我的稿子给了中央的某个媒体。后来有一天,我在家里看电视。电视新闻里男主播用声色俱厉的口吻,报道了一则新闻:由吴山矿业公司上市一案牵连出一批贪污受贿官员,发现一起严重的“窝案”事件。男主播还念出了犯罪的主要领导名单,其中就包括那个“抢”了马良老婆的副县长。
我一边看新闻一边流泪。老婆在一旁,不明就里,手足无措。
责任编辑泓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