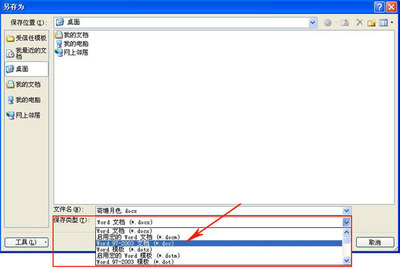谭畅:关于对女诗人及其诗歌评价的一个回答
关注“写作”比关注“女性”更重要,这点穗穗说得很有道理。当然,诗人和评论家们咬住一个议题,深入持久地碰撞和讨论,可以相互挖掘出更多潜在的智慧,在某个方面启发创作的自觉,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但回顾关于“新红颜”诗歌的争论,发现呈现的有些问题相当严重,无法一笑而过地忽视,还是在这里尝试回答吧。
一、我也是女人,觉得女人足够好,女诗人也各有各的风采和特质,她们的诗文本和人一样可以成为审美的关照。一朵玫瑰不需要通过否决牡丹才证明自己的美。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只有恶女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诗歌,而不是江湖。女人们可以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自信美好的形象,对男人不那么学术的赞扬报以宽容的微笑。
二、决不支持某些男人对女诗人不怀好意地贬损!如评论中自命为“诗圣”的某猥琐男,对女诗人们不负责任地指名点评,说西娃“语言上还没入门”,施施然“闷骚,成都锦瑟的“王呀妃的虚假想象”,李承恩的“三从四德”,翩然落梅的“古诗词白话翻版”,横行胭脂的“爱情空泛意想”等。他的评论,语言放肆侮辱,立场有相当大问题,值得所有人警惕!引以为戒!
“诗圣”这个自命不凡的网名就暗示了其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敬畏,更不可能知道性别之间的尊重和友好。这个人在现实中很可能是女人懒得侧目的路人甲!男人们宁愿忽视的人格最短板,道德残缺物!这种人只会以淫邪的目光投向女人的背影,决不敢直面她们姐妹般清澈的眼眸和真诚的质疑。
三、“诗圣”这样的人并不只一个。这种苍蝇连征服有缝的蛋的能力和耐力都没有,却无时不在等待着天鹅蛋们自己因精致而细碎的差异互相碰撞,流出奶白的蛋清和金子般的蛋黄,多少贪婪的唇齿在深渊里饥渴地等待......高贵的公主在鄙俗者眼里仅是一堆美味的肉......
无法言尽对这种现象的忧虑和愤怒......今天把“诗圣”拉出来示众,剥去他的皮,看看文人的这种阴暗心理!仅仅是提个醒,希望女诗人们更清楚自己的处境,自觉屏蔽那些相互攻讦的言论和做法,清静爽利地追求真正的艺术和美好人生。
附1.
诗圣原文:
新红颜的最大问题是思想陈腐,沦为旧红颜,只是初学者在模仿古典意像,如施施然的闷骚:渴望被草莽掳上马背,带上你的名字下辈子约会。如成都锦瑟的穿越到古代的王呀妃的虚假想象,如李承恩的要现代人向虞姬学习忠男人的三从四德的折射,如翩然落梅的古诗词意想的白话文翻版。
新红颜的第二大问题是缺乏艺术表现力,诗意浅薄。如横行胭脂的诗歌要不是爱情的空泛意想(没有娜夜的真实细腻)要不是生活表像的描写,没有深入现实的力量。如西娃的诗歌多为佛学心得,并没有与世俗生活有机融合,没有人性符号,显得空泛与虚悬,文字拖沓散乱,语言上还没入门。
新红颜的第三大问题是与当下隔膜,绝大多数女诗人在现实中消失,丧失了自己的位置,也缺失了对未来的希望与追求。这才是可怕的倒退,不是作者说在求新就是求新了,她们中有些人毕竟没写几年,不懂历史,思想幼稚,把吸取传统文化与古诗歌糟粕也当作了诗艺提高,这是可笑的。
我很奇怪,在改革开放30年后,在西方普世价值明显上升的今天,新红颜还在老调重谈?与现代文明隔山隔水,这到底是编辑者的思想出了问题,还是女作者们出了问题?我们的编辑与诗人不但落后于社会上网络上那些前卫青年与中年愤青,也落后于独立的文化知识人,值得深思。新红颜如果写出了折射当下生存状态与文化思考的有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的诗歌,新红颜的命题才成立,可惜编辑者,把初写者的无病呻吟,把美女照片赢的意淫粉丝的博客重点推出,其用意就让天下读者与诗人怀疑
附2.
谭畅原文:
李少君在当前提出的“新红颜”写作,在中国竟意外得到了女诗人们明确的支持和自觉的维护,不少女诗人似乎很喜欢,也不忌讳自己被进行这种命名。这种反常的现象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的女性写作者缺乏和男性并驾齐驱的野心,也不能认为是太渴望成功的女诗人对自身成名所作出的妥协。相反,这可能更证明了中国女性的自主性和独特性。中国的妇女运动在戊戌维新(1898年)时代就已拉开了序幕,比中国新诗的历史早了18年,维新派将形体解放与思想解放视为争取女权的基础,并强调妇女解放与国家强盛密切相关,即“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家所存者幸矣”。而国际上三八妇女节也直到1910年才确立,比中国妇女运动的发起整整晚了12年。
中国当前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无可回避的现实潮流。这种觉醒并不一定体现为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与另一个性别的激烈对抗。相反,中国的女性们更多地以一种静水深流的方式,依靠岁月里长期坚忍不拔的努力悄悄获得了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既体现在家庭权力分配和家庭资金流向上,也体现在学校里男女学生的成绩排名,更体现在科研和教学机构(尤其是文科专业)里日益具有压倒性数量优势的女学者、女博士们,当然,在政坛和政府单位里,女领导也日渐增多,公司和企业里的女上司更成了一片葱葱茏茏的好风景。《时尚女魔头》、《欲望都市》、《杜拉拉升职记》等反映女性职场生活的作品的流行,亦从需求层面上证明了女性在职业发展方面的大量诉求。
与以往掩饰自己性别特征、追求与男性趋同化的女性相比,当今的女性们似乎更坦然于自身的性别特征,而且以此为荣。当“性感”一词成为对女性魅力和外表最高级别的赞美时,女性在赢得事业竞争的同时也赢回了自己对身体的主宰权。体现在诗歌创作里,女诗人们不再忌讳谈论自己和她人的身体,但绝非以等待者和接受者的卑微姿态,更不是男权社会消费品的商品特征来言说。对她们而言,身体是一种自在物,使其成为不同于男性的值得自豪的前提和基础,这身体如此美丽和神秘,如此敏锐和精巧,在对世界的感知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对女性写作者来说是一种得天独厚的馈赠。这种对身体普遍的信任使当前女性的创作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独立自主走向真正的自由。
正如哲人所预言,21世纪是女性的世纪,“永恒的女性带着你走”(歌德),女性将再次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的建设性、对待世界的包容性、人际关系的融合性”等特征和智慧,迎接上天的托付,福佑人类和文学的未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