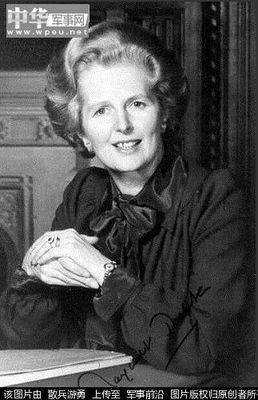(一)
王铭铭(1962年3月——)福建泉州人。曾就读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1——1987年,附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于1984年10月正式设立,首任系主任陈国强先生,厦门大学人类学的同学许多是从历史系转过来的),1992年获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1993、1994、1995年在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伦敦城市大学中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员。
话说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笔者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正好有机缘见到王铭铭先生,听王先生趣说人类学,真是一桩赏心乐事。
二〇〇三年九月八日,回圆明园校区午饭,休息。下午二点四十分在三教201教室听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此公头顶运动帽,身高1.65米左右,眼看教室前三排学生,就此门课程的性质进行解说。声音极小,但有大家风度,态度甚闲逸,颇有魏晋风度。休息时间,用打火机迅速点上烟斗,真是好玩。
第二节课则坐在椅子上,快下课时又迅速点上烟斗。有趣。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当代中国,人类学界是否形成较为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若有,请举出几位学人;若没有形成,请说一说哪几位具有如此气象?第二,当代中国人类学界和西方人类学界有很大的落差,处于弱势话语;就当代中国人类学界而言,大陆人类学界又比台湾的人类学家李亦园、乔健先生有很大的落差;大陆学术界若追赶西方一流学术,是否首先追赶台湾的人类学。不知王先生以为然否?
王先生闻听此言,表情非常丰富,极其兴奋:“你是社会学的吗?”“否”。“你研究什么?”“我在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绘制工作,先生已被我绘入学术地图。”“啊,谢谢。”
王先生接着说道:你的问题是关键之所在。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人类学界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因为利益的争夺,有很多基本问题还在讨论,大家都有很大的分歧。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确是这样。台湾有位学者曾写文:大陆人类学比台湾人类学起码还差十五年的时间,不过看过王铭铭的书后,感觉离得不是太长了。
下课后,我走到讲台,与王先生握手致意,王先生问我从哪里来,我做了简短的回答。我接着问如何看待郑也夫先生,王先生脱口赞曰:“那是一条汉子”。我提出郑也夫和王铭铭都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前沿人物,并且认为郑也夫先生的社会学有很大的原创性,并且具有深厚的思想穿透力,王先生表示认可。我提出可否每年由杰出学人推选本年度杰出著作和论文,或许有助于形成学术共同体。王先生亦点头。
王先生问我还否听课,我说会的。王先生表示下次课拿过来一个表,注上自己的电话。话别而去。
时间接近五点,前往北大学五食堂吃饭。
九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三、四节,三教201,听王铭铭先生的《社会人类学》。今天王先生讲人类学的方法。王先生讲课中风趣地说:新闻界非常有趣,原来的新闻寻找好人,寻找一种叫雷锋的人种;现在寻找坏人,比如刘晓庆、王铭铭啦!王氏此言,非常有趣味。只有具备了足够的学术自信,才能够进行自嘲。王先生接着指出,人类学要研究“异文化”,采取观察的方法并且实行主位法。“中南海”能不能称为一种异文化,王先生此言有很深的意蕴,极其有趣。第二节课王先生主要以提问为主。我问了两个问题:人类学适应殖民地的拓展应运而生,所以人类学家最初是殖民主义者,后来才变成人道主义者?第二个问题:人类学最本质的东西是不是平等。有一种“齐物论”,当代中国还有一些人代表官方,似乎是民政部新闻司发言人,去到一个偏僻贫困的地方,好像是访贫问苦。
关于当代中国人类学的现状,王先生谈到:中山大学的人类学侧重于考古和海外华人华侨的研究,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好像统战部的对台工作,北京大学的人类学也是各唱各调,没有共同的理念,只是“众声喧哗”而已。考古人类学的一些学人似乎特别喜欢“大历史”,挖出一个墓葬,总想把中国历史 往前推好多年,有人甚至要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动不动就往前推几百年,上千年。王铭铭坦言喜欢搞小历史,研究民族村落地区,原住民的个人生活史。王氏对中国人类学有一个期望,中国人类学家反过来研究欧洲和美国。第二节课接近下课时,王铭铭先生指出费孝通先生有句话叫“志在富民”,费先生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的追求。西方人类学界却在批判欧洲的消费文化主义,对现代化持有一种“省思”的态度。王铭铭本人不太赞成“志在富民”这一理念,并认为应持有韦伯的“志业观”,保持一点学术的独立精神。对王先生的这一理念,我是赞成的。学术研究应对“功利”持有谨慎的态度,但学术也不可能丧失任何的价值判断,你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不代表官方,你恐怕对研究的对象持有一种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但你不可能把自己混同于原住民。在这种时候,学人的态度是非常有趣的。李亦园先生曾说过,文化人类学家的工作,在政府看来,是非常讨厌的,因为他们总是站在少数族群的立场上,说政府没有平等地对待少数族群;文化人类学家到少数族群地区,又受到白眼,因为这些人认为人类学家打扰了他们的工作,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李亦园先生总结人类学的工作时曾说:寂寞的人类学生涯。
人类学的视野是很好玩的,它有助于人类族群的自我认知,他人是自己的影子,自己是他人的影子。由此发挥开去,进行当代中国大学史研究、学术史研究,知识分子研究,可以借鉴人类学的视角,从“异文化”中去体会“同文化”,从同文化中去体会“异文化”。
下课与王铭铭先生匆匆告别,前往北大农园吃饭。
以上材料来源于笔者在北京大学访学时的学术日记。近距离观察王铭铭,感到此人的确有真性情,真的不像有些教授,架子十足,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所谓的北京大学的边缘人。
(二)
近日我从河北省图书馆借来王铭铭先生的几套书:《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6月第1版,23.6万字,18.6元)、《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32.3万字,24元)、《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30万字,28元)、《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社区的历程》、《逝去的繁荣》、《王铭铭自选集》、《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15.7万字,18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走在乡土上》,我在北大访学时曾经在风入松书店看到过。王铭铭还有翻译著作《甜蜜的悲哀》(萨林斯著王铭铭、胡宗泽合作翻译,三联书店出版)。
王铭铭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的引言中说:“我接触社会人类学,是从阅读厦门大学已故林惠祥教授对文化人类学的论述以及北京大学费孝通教授对社区研究、乡土中国结构与文化变迁的论述开始的。不过,本书所包含的知识更多地直接来自于社会人类学的大本营英国。1987年,我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社会学人类学系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在该系有机会、有条件阅读各种社会人类学原著,并参加社会人类学当代潮流、社会人类学原理、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与象征研究、家族制度、汉学人类学等研讨课的讨论。经过大量文献与理论方法准备,我于1990年至1991年在家乡福建泉州从事田野调查一年,获得大量资料,并依此写成博士论文。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还在闽台农村从事广泛的田野调查,力求通过地方性的深入探讨,以详实的人类学描述,回答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社会的组织特点何在?如果中国社会具有其独特性,规范社会科学论述是否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相匹配?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否对一般人类学有潜在的贡献?本土概念是否可以发展出社会科学概念?等等。”〔1〕
王铭铭先生回国即将十年,我们可以把他十年来的工作简单概括为:“述、评、作”。当然,“述”、“评”结合,“述”中有“作”。应该说,这样的作业方式,对王铭铭好处极大。王铭铭立志深入了解社会人类学科的历史,应该说,学科史的了解往往是对学科产生文化自觉的前提条件。王铭铭著作大部分是学科史方面的,反映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自觉,花费的辛苦是可以有丰厚的回报的。王先生社会人类学的逻辑开展是:反思——对话——田野——自觉。「反思」就是了解社会人类学的历史,「对话」主要通过书评,田野就是自己熟悉的闽台社区的田野作业。「自觉」是进行理论创设。《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两书主要是「反思」;《漂泊的洞察》主要是书评,书评是对话的一种有趣的方式;《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逝去的繁荣》主要是田野工作;《人类学是什么》里面有许多深刻的洞见。反思——对话——田野——自觉,其实贯穿着王铭铭先生所有的著作,只不过某一方面的色彩重一些。「反思」是王铭铭最先进行的一个工作,由于多年没有用汉语进行著述,所以,《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两书中,王铭铭的语言运用,没有脱离娴熟的英文,以至于可能对于王铭铭来说,用汉语进行学术著述可以说进行了一次“跨文化的沟通”,我们读王铭铭的著作,这时候肯定感觉语言晦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可以指责王铭铭中国文化的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不负责任地说“王铭铭对西方社会人类学的掌握是否有些差劲?”我在想,《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这两部书,是否王铭铭英文学术札记的汉语硬译?在我看来,一部中文学术著作晦涩难懂,可以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作者没有真正把问题搞懂,第二,著作中的词汇,中文目前没有与之对应的;第三,著作的学术思想的确深邃,一般人难以理解。王铭铭会是哪一种情况呢?我看,可能是第二种情况。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判断,不同意见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逝去的繁荣》两种著作是王铭铭进行田野调查的总结,但因为存在提升中国人类学理论品质的宏大抱负,所以书中的理论和小地方的实践之间结合的并不是那么水乳交融,有一点用理论来编织实践的倾向。但是,《人类学是什么》、《漂泊的洞察》这两本书,给我的感觉并不是晦涩难懂,而是清新活泼,有时甚至趣味盎然。为什么同一个王铭铭,有的书晦涩难懂,有的书就清新活泼?据我分析,王铭铭通过和国内学术界的沟通对话,他的文化人类学的汉语语感建立起来了,这里面,邓正来、朱苏力、梁治平对恢复王铭铭的汉语语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王铭铭在和几位学者的互动中,文化人类学的汉语语感被激活了;另一方面,王铭铭先生讲课,我是见识过的,那是非常有趣的。王铭铭先生曾经讲过:“一个好的人类学科系,能提供三个方面的课程:研讨班、讲座、民族志电影。……讲座一般是由成名的人类学教授主讲,老师上了讲台,只带着几片卡片,就能讲两个小时,内容很丰富,注重启发。”〔2〕这一段话,似乎是夫子自道。在我的印象中,王铭铭先生似乎从没拿过讲稿,讲起课来,津津有味,真是别具一种魔力。讲课生动活泼的人,写成文章就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令人难以卒读;第三个方面,王铭铭进行的学术工作是社会人类学,这门学问有自己的职业特点,要懂得人的心思。但是就是懂得了别人的心思,能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还有一个人生境界、学术境界的问题。王铭铭写作《人类学是什么?》时,恰好是四十而立。我感觉的确有人生境界的问题。我并不是说,四十岁以前人生境界就很低,可不是这样,雷锋死的时候很年轻,但已经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了。我是说,四十岁,很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新的层面,这时候,对人生的理解,似乎比以前加深了,捎带着学术境界也能够往上升。学问这样做得就会比以前更加滋润,更加鲜活。这一点,在王铭铭的《人类学是什么》中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不管王铭铭本人怎样看,我以为代表着他的思想境界,体现着某种程度的文化自觉。
(三)
我非常喜爱《人类学是什么》和《漂泊的洞察》两部著作。当然,按照当代中国的学术思维,《人类学是什么》只能被认为是科普式的书,《漂泊的洞察》是一本读书随笔,有些学人当然会怀疑它的学术含量。
《漂泊的洞察》一书分为五部分:一、飘泊的洞察,收入八篇文章;二、历史与现实,收入四篇文章;三、叙说于乡间,收入十篇文章;四、半步进历史,收入两篇文章;五、青黄不接,收入十篇文章。全书总共收入三十四篇文章。主要是读书札记、随笔、学术讲座。
其中第五部分的标题“青黄不接”看上去就会有一种感伤。王铭铭其实是很有一些学科的忧思的,这一辑有五篇文章写到了人类学学科的先贤和当代名家。分别谈到了潘光旦、费孝通、张光直、钟敬文、宋蜀华先生。文章的题目是《“人文史观”——潘光旦与我们这代人的问题》、《费孝通与我们所要承担的》、《由张光直想起的》、《坚韧的钟敬文先生》、《宋蜀华先生二三事》。这五篇文章,可以见出王铭铭的真诚。述往事,思来者。这一辑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逝者如斯”》。潘光旦先生、钟敬文先生、张光直先生、宋蜀华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费孝通先生也垂垂老矣。中国人类学的新一代学者,却还没有健康地成长起来。
五位先生当中,王铭铭最早见到的是一流的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历史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铭铭还没有到英国开始自己的「海龟」生涯。当时王铭铭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却对人类学产生极大兴趣,组织“学生人类学社”,邀请张光直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张先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后来,张先生应邀来到厦门大学为“学生人类学社”的成员作了一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报告,王铭铭正是学术报告的主持人。张先生的严谨和敬业给王铭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所以,王铭铭说:“我永远忘记不了张先生。他那场关于考古学的讲演,我这个当了这么些年‘考古学的叛徒’的人,至今仍念念不忘。”〔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铭铭从考古学转学人类学,是有着深刻的机缘的。王铭铭翻看文革时期的考古老期刊,杂志的扉页总要写着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让王铭铭产生错误的感觉:以为考古学是为一个过时的意识形态服务的。而张先生考古学,为中国考古学界带了人类学的新空气,这确是王铭铭转向人类学的背景之一。王铭铭感谢张光直先生,因为“他为我们离开那门值得痛恨的学问铺了路,接着感谢我们的老师,以为他们为我们的离去,找到了不需回归的理由。”〔4〕从那时算起,王铭铭已经花了20年时间读人类学了,按照王铭铭的说法:这20年的大部分时间,被我花在与考古学划清界线的“努力”中。张光直先生曾经写文章,阐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中,考古学当有自己的贡献。王铭铭看到,文化人类学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学者,由于失去历史学的滋养,僵化地坚持固有的民族志传统,不仅无助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将使这门学科失去洞察社会事实的能力,而落入“坐井观天”的境地。
《由张光直想起的》一文,有两个特别有趣的例子,给人很大的启迪。一个是云南大理喜洲的部族被确定为“白族”。王铭铭随博士研究生梁永佳前往大理喜洲,进行田野调查。问及当地人的来历,一位农民竟说:“来自南京应天府”。到底“来自南京应天府”的人怎样成为“白族”?或者倒过来说,白族怎样成为“来自南京应天府”的人?王铭铭觉得这个现象真正有趣。这些白族,我也觉得有趣。如果确是他们接受过汉族文明,如何由“化外之民”成为“化内之民”?如果这些人就是来自南京应天府,那么,汉民如何化成白族?包括中国境内的民族,我们进行田野工作,如果没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大格局,那么就不会历史地、发展地、整体地来看待汉族族群与少数民族族群。就会落入王铭铭所说的“坐井观天”的境界。中国从政治上强调“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大家是清楚的,但是为什么,进行历史研究,就忘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道理?所以,要想对汉族进行深入地研究,就得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要想研究少数民族,恐怕还要深入研究汉族。不在大的文化格局进行思考,恐怕就会陷入僵化的民族志的“死结”,怎么也挣脱不出来。我觉得,这些话还是符合王铭铭先生的心思的。
《由张光直先生想起的》一文,记载了王铭铭在与法学社会学家朱苏力的闲聊中,朱苏力的一个有趣的见解,真是亏他想得出来,令人喷饭。朱苏力说:“西方(社会)人类学原来是研究殖民地民族的,与殖民主义有密切关系。中国引进这门学问,又没有什么殖民地,只好研究少数民族和农民了。”〔5〕
王铭铭进一步发挥,有精彩的思想火花:“朱先生的这个说法,恐怕有人类学同事会反对,但在我看来,他切实‘不幸言中’了我们学科的要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确实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和边缘社会群体。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我对这一点没有什么异议(我认为研究什么一般不是问题,怎样研究才是问题)。可是,我以为有必要注意到,我们在研究一个‘少数民族’或一个‘农民社区’时,为了‘方法的便利’,通常将自己的视野固定在那个民族和那个社区本身,将它‘隔离出来’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存在。这样一来,通过民族志的论述,我们便‘话语上造就了’这样或那样的‘民族’或‘社区’”。〔6〕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就是没有懂得人的心思,这样,研究的品位和品质当然就会大大地降低。但是这种被大大降低品位的“话语”往往量大,占据了“话语霸权”的位置。对这种“话语霸权”的颠覆,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1993年,还在英国从事研究的王铭铭,乘田野调查之便,拜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先生。当时,钟先生已经九十岁高龄,但对民俗学依然钟情不减,整整一个下午,与来访者王铭铭小友娓娓而谈。这一个下午,不要小看了,这一席谈话,在小友王铭铭看来,无疑是民俗学精神的极好阐释,因为钟先生可以说是中国民俗学的活化石。钟先生的长寿不是偶然的,是对民俗的挚爱,使钟先生产生了与民俗相似的品格。风狂雨骤,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令人难忘的1957年,钟先生和夫人,双双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右派,一举成为中国反右历史上著名的“夫妻店”,但是具有草根品格的钟敬文先生,平静地面对这一切。坚韧地活下来。可以设想,若是钟先生去世于1978年以前,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就会产生空前的灾难。有钟先生在,民俗学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所以,钟先生不仅是民俗学的活化石,还是中国民俗学的保护神。一身而系学科之重,环顾神州,岂非钟先生之喻?
钟先生于2002年1月10日零时1分,平静地离我们远去。王铭铭听到这一噩耗,深深地陷入思念与回忆之中,写出《坚韧的钟敬文先生》。王铭铭当时好像有到北京师范大学钟先生身边的意思,在与钟先生的谈话中,提议创设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在王铭铭看来,民俗学是人类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钟先生非常理性和清醒,回应王铭铭说,现在有个教研室已经非常不易,不想再不知深浅,扩大地盘。钟先生这里恐怕有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心思,民俗学在北京师范大学尽管是一个小小的教研室,但却是钟先生可以掌握的空间。当然,大度的钟先生鼓励王铭铭向大学的负责人倡议。后来钟先生真的创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据说,九十高龄的钟先生还爬上楼梯,催促自己的博士生早起,博士生没有一个不感动的。百年的传奇人生,那是对钟先生的回报,钟先生贡献给中国社会的便是民俗学这一民间文化在大学的扎根。说起来,天道酬劳。民俗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轫,是与新文化运动相联系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新文化不仅是西方的发现,它是一个整体化的运动,同时还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发现,对庙堂文化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新文化的健将发现了中国的民间传统。民俗学就是中国学者对小传统的关照,歌谣、谚语、故事、传说、民间信仰,都吸引了一流的学者,但是能够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恐怕当属钟敬文先生。
斗转星移,雾走云飞,你的头回也不回。
没有一点对学科的热爱,没有一点人格的力量,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恐怕是做不到的。这位中国民俗学存亡续绝的伟大学者,化为泥土,回归到民俗学的大地。钟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只要我们提起民俗学,那么,钟敬文先生的名字,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所以,钟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民俗学者心中的一种信念,坚韧的钟先生,就是中国民俗学界的一大风俗,感召着无数的后生。
潘光旦先(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是近代中国卓越的人类学家,大学教育思想家。1934——1952年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图书馆馆长。潘先生融合中西,形成了独到的人文史观。由于潘先生思想的深邃,直到现在,还没见有深度和穿透力的研究成果,也许,注定潘光旦先生会是寂寞的。对潘先生的思想的接续,可以见出中国人类学家的超越自我的努力。潘先生的这份思想遗产,在苦苦等待着继承人。
每当我看到河北省图书馆十四卷本的《潘光旦文集》寂寞地躺在那里,一种深深的烦恼便会向我袭来。所以,我发愿购置《潘光旦文集》,以便在我所开设的《百年中国人物》通选课上向学生传播潘光旦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治学路径,至少让他们知道,百年中国有这样一个纯粹的伟大学者。学生们似乎记住了我所讲的故事,知道了历史上有潘光旦这个人。但是,河北省图书馆的《潘光旦文集》依然是寂寞的,尘土依然围困着《潘光旦文集》。选《百年中国人物》的学生,对于一个省级大学来说够多的了,我统计一下,总共有1500位同学,可见学生对这门课,还是喜欢的;可是,我的魅力并不足够大,说句不恭的话,几乎没有一位学生懂得我的心思,别看他们课前占座、上课鼓掌、课后围着我问寒问暖。他们表面上好像和我有共同语言,所以对我的《百年中国人物》特别捧场,但是他们好像是听热闹,听完之后,觉得特过瘾、有意思、好玩,下课之后,兴奋地到学校饭厅,打一份红烧肉,快乐地吃起来。我的课,确实增进了学生的食欲,但是他们的精神食欲,好像还是不见长。他们还是非常爱听“我不要昨天,我只要今天”这种后现代、新人类的流行歌曲。这些学生,对于我这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来说,这些八十年代的新人类,好像真的是一种“异文化”。在他们中间,我有一种当“少数民族”代表的尴尬。
潘先生认为人具有三性:性别、通性、个性。「性别」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通性」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具有「通性」,所以才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个性」是人类的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怎样保持性别、通性、个性的综合平衡?潘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位育」这个词汇,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洞见的。我们现在来理解这个词汇的意思,好像还没有足够的人格和学术的储备,更不要说体会这个位育的深邃内涵了。潘先生的“人文史观”建立在人的「三性」基础之上。潘先生申说“人文史观”的时候,曾说过人才形成的因素实际复杂的,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属于生物遗传的,二是属于文化背景的,三是属于平生遭际的。我们看,可以和性别、通性、个性相互发明。性别属于生物遗传,通性往往来与文化背景,个性的造就是否属于平生遭际?在先生的“人文史观”中,似乎并没有说出王铭铭所总结的潘先生的“人文史观”的意思,王铭铭在文中说:“让我们充满希望的是,潘先生提出一种‘人文史观’,他的意思,潘先生说得明白:文化的发轫,要靠知识分子的思考,而文化要继续维持或代有积累,也要靠知识分子的努力”。〔7〕这里,也许是王铭铭先生误解了潘先生的意思。我读了一下潘先生的那篇经典性的文章,联系潘先生所作《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先生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得明白的承认优伶是一种人才”。〔8〕既然优伶在潘先生眼中是一种人才,那么,也就不存在王铭铭先生所说的“非人民历史观”,恰恰相反,潘先生论证优伶也是一种人才,完全可以符合后来的毛泽东所提倡的人民史观。潘先生在《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人文史观不是伟人史观。潘先生的人文史观,在我理解,是“人才史观”。人文史观的宏论,正好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之后,是否潘先生通过伶人的研究,升华为比较自觉的人文史观?
潘先生这么好的学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死得好惨。1967年6月10日,潘先生死在费孝通的怀里。那时,我还是冀中平原上刚刚一岁半的婴儿,爸爸被游斗,妈妈和哥哥、姐姐都要参加大批判会。听大人说,幼小无助的我,当时整天和我们家那头异常肥大的老母猪为伴。
王铭铭先生那时整整五岁,要比我大三岁。王铭铭1994年从英国回到中国,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正好在潘先生的小女儿潘乃谷所长的领导之下。这样,王铭铭对潘先生的做人和治学,就有了一个接近的机缘。特别是潘乃谷的两位姐姐潘乃穆、潘乃和全力编辑完成十四卷本的《潘光旦文集》后,正好是潘先生的百岁诞辰,这样民盟中央、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举办潘光旦先生百周年诞辰座谈会,时间是1999年9月15日,同年的12月8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纪念潘光旦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这对一向力行“推己及人”的潘先生来说,似乎也是一个迟到的慰藉。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之上,出版了《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对潘先生进行学术纪念的文集,并没有在出版《潘光旦文集》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也没有在举行学术纪念的潘先生晚岁工作的地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否遇到了经济上的障碍?我还没有潘先生那样的涵养可以做到“推己及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王铭铭先生《“人文史观”——潘光旦与我们这代人的问题》,尽管对人文史观有所误解,但是不影响对先生的敬仰和追怀。王铭铭对学术先贤相当的谦恭,字里行间看出,是很真实的。这种真实,还有一种真诚,令我感动。王铭铭有一个感觉:“我们中国学术的前辈与我们之间的‘代沟’,很难被我们这些后生来跨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缩短,还有拉宽的可能。”〔9〕这样,王铭铭前面对潘先生的误解,就具有了很强的象征意味,王铭铭这样如此喜欢向前辈学者学习的人类学家,对代沟都很难跨越,更何况其他“二把刀”呢?恐怕连了解前辈的兴趣都不一定有。
费孝通先生二十五年前受命恢复社会学,老先生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人才。这一段时间,社会学也算重建起来了。人才从表面上看,似乎也不少。但是费孝通对迅速成长的社会学人才,是非常失望的,所以才有茫然四顾的孤寂感。迫不得已,费先生辞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所长职务,来到北京大学,担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名誉所长。费先生这个名誉所长,绝对不是挂名的,费先生是要做事情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没有很好的心境做事情,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费先生似乎焕发了学术青春,回到了「魁阁」时代,在老师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潘乃谷的倾心协助之下,创办一个新的「魁阁」。费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新魁阁」的灵魂,通过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先生想造就一个进行学术对话的地方——席明纳。看起来,这种方式对王铭铭很受用,“青黄不接”就是因为“逝者如斯”所引起。王铭铭在《漂泊的洞察》一书中,言说方式越来越从容,一方面是人生境界的问题,另一方面,费孝通先生的熏陶,不可能不起作用。王铭铭开始接着费孝通先生讲了,费孝通和王铭铭之间的气场慢慢接通了。所以,当王铭铭感到困惑的时候,可以向高龄的费先生请教人生哲学,费先生告诫王铭铭,对某些事情“不要忘记,但也不要老记住”。不要忘记什么呢?不要忘记“我们所要承担的”。
费孝通先生能够看到王铭铭的成长,其实是欣慰的。
但是相差五十二岁的两人,并不是师生,而是同学。两人都毕业于伦敦大学,还是系友,相差五十一年,费先生1936年入学,王1987年入学。费先生当然是学长,只不过王铭铭这位学弟有点太小。
《费孝通与我们所要承担的》披露费先生向王铭铭送书,那时一点都不奇怪的。这是一本小册子——《师承、补课、治学》,但费先生的心思并不是轻松的。
王铭铭打开书本,看到扉页上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铭铭同学”,落款是“费孝通”,注明时年“九十二岁”。王铭铭猜想,“费先生以‘同学’相称,包含一种特殊的谦逊。‘同学’,令我看到了悲情的谦逊带着的那份郑重的期待——我们(对他来说的‘你们’)如何才能使我们赖以表达自身及社会关怀的学科免遭断送与我们自己手中的命运?对此,我们这代人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和特殊的风险。”〔10〕
宋蜀华先生生于1923年,五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界的小伙子,现在竟然也早早地走了。宋先生194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当时的系主任是林耀华先生。1949年获得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成都华西大学考古及民族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队,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宋蜀华先生可以说是百年中国人类学历史上的第四代学者的代表。宋先生具有开明的学术理念,这种理念表现在待人接物,都有一种谦逊、和善的气度。王铭铭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京城的学术会议或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经常可以看到宋先生沉稳的身影。宋先生的谦和与诚恳,让王铭铭时刻体会到一位开明的中国人类学家的无限期待。宋先生在高级研讨班上的发言,往往言而有物,意味深厚,清新旷远。无论什么时候,宋先生也不愿意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总是留有余地,量入为出。但是宋先生的沉潜和雍容,包含着激烈和英锐。王铭铭说宋先生“既注重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传统的继承,又特别注重吸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优秀成果,表现出这位学科的继往开来者的特殊魅力”,〔11〕真正做到了「守先待后」。
王铭铭体会到学科的继往开来这是最值得我辈珍惜的,可惜像宋先生这样的继往开来者已经为数不多,而且多已退居二线。所以王铭铭经常会“想象到宋先生的微笑,知道它的意义与价值,坚信能继续在这样的微笑中面对学科存在的诸多问题。”〔12〕
(四)
回望百年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峥嵘岁月稠。
蔡元培先生、严复先生是百年中国人类学的第一代代表,李济先生、潘光旦先生、吴文藻先生代表中国第二代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瞿同祖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第三代人类学的代表,宋蜀华先生、俞伟超先生、李亦园先生、张光直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界的第四代,王铭铭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界第五代的代表,第五代中的出活学者萧兵、周星、高丙中、纳日碧力戈等先生。其实,法学学者梁治平先生、朱苏力先生都是杰出的人类学家,只不过,除了王铭铭先生这样称呼他们外,好像还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们。对于当代中国人类学界,王铭铭是非常失望的。所以,他总是想体会老一代学者的心思,新老学者之间,似乎存在一个巨大的代沟,给人的一个感觉是“青黄不接”。王铭铭心中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本书第五辑的题目就叫做“青黄不接”。体会老一代学者的心思,就是为了接续中国人类学的传统。王铭铭在接续人类学的学术传统方面,还是有着相当的文化自觉的。
学科史的自觉意识,可以说体现一个学人的成熟程度。只有一个学科的“二把刀”才会总是给人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是横空出世。这些横空出世的“二把刀”,绝对不会崇敬学科的祖师爷,也不会善待自己的师傅和师兄。学术界的“二把刀”们总是太多,所以,中国的许多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总是不见长进。笔者以为,在学术上,存在一个守先待后、文化自觉的问题。所有学科的推进者,其实都是学科的守护者,守护什么呢?守护学术的传统,传承学术的精神。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们发现,对学科有强烈自觉意识的学人,都会对先贤的学术成果存在相当的敬意。对体现学术传统的学人,保持一种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并不单单是对一代学人的尊敬,往往有薪火相传的学术理念在。我们看,从事学科史的学人并不一定是一流的学者,但是一流的学者往往是对学术传统有着自觉的学人。比方说,经济学名家厉以宁先生,本身就是出色的经济思想史权威;法学名家梁治平先生出身于西方法制思想史专业,对中国传统法文化有深刻的自觉;文学史大家杨义先生曾专门下功夫研究近代中国学术名家的治学路径和学术理念;中国哲学史名家陈来先生更是对近代学术先贤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有专深的研究,并写有学术专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思想史名家葛兆光先生对近代学术史、大学史有着温情的敬意,曾经在清华图书馆藏书楼发思古之幽情,编辑《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历史地理学名家葛剑雄先生对百年历史地理学先贤,报持着极大的同情,撰写先师的传记《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
在《漂泊的洞察》中,“青黄不接”一辑中,王铭铭有两篇文章谈到邓正来。邓正来是当代中国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的学术品格已经深深地嵌入二十五年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史,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平民色彩的知识英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正来就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有着文化自觉。当时我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一位喜爱读书的读书种子,导师萧延中先生曾经一度介绍我到《北京青年报》帮助打杂,我的志向非小,愿意进行类似《光明日报》“学者访谈录”的工作,为此,拜访过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杨念群先生,遗憾的是,由于学养的不足,我的工作并没有深入进行下去。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小插曲。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1988年,邓正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己任所长,夫人任总干事。《北京青年报》把邓正来的做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改革中出现的东西,那时是很能鼓舞人的,因此该报记者对邓正来进行采访,发表访谈文章。我到北京青年报打杂,正好刊出对邓正来采访的报纸。萧先生在报社的朋友委托我把这期报纸,送给邓正来本人。事情就那么凑巧,原来邓正来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简易的苏式房子。好像在挨近楼梯的二层一间很狭窄的房子里,我找到了这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邓正来与人交往,并不注重风度,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就问我来自哪个系。当他听说我来自中共党史系,露出一脸的不屑,我带着满腹的委屈离开了邓正来的家。后来,当我见到谢选骏先生时,把我的遭遇告诉了谢先生,谢先生倒是非常通达,说过“何不告诉邓正来你是研究国民党党史的”。
邓正来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正来的能量充分地显露出来,香港出资,由邓正来主编两本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邓先生主持两本刊物,注重学术规范,主旨在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邓正来的生活方式,值得一说。在我的感觉中,他很早就是学术自由人,独立于当代中国的大学或社科院系统之外。这一点,确实是相当不简单的。当代中国学术史中,邓正来的确是特立独行的一位。躲过北京的学术界的喧嚣,在海淀区的家中,寂寞地读书,寂寞地译书,按照王铭铭的说法,从事于知识增量的工作。大约1998年,开始看到邓正来的著作。邓正来著述有三个特点:第一,喜欢小册子,不喜欢大部头。所以邓正来的著作,篇幅都不大。第二,邓正来喜欢进行长篇学术文章的撰写,别看著作的篇幅不大,但是每一篇文章都特别长。第三,邓正来的文章非常不好懂。也许的确是思想深邃。邓先生的学术工作,得到香港学术界的赞许,被香港学人认为是大陆关于市民社会研究的重量级人物。我曾对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发现邓正到上海过年时,拜访王元化先生,得到王先生的款待。顺便说一下,邓正来的弟弟在石家庄就业,开设一家书店,名叫嘟嘟知识书店,书店的学术品位在石家庄算得上最高的。
王铭铭本人是邓正来主持的「六郎庄读书小组」的核心成员。可见,王铭铭在人类学的建设中,学术视野是开放的,依托相关学科,寻找人类学的精神资源。这样王铭铭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界,站得的确够边缘的,在正统的人类学学者看来,说得好听是自我放逐,说得不好听是不务正业。王铭铭由人类学的中心自我放逐到学科的边缘,在我看来,是有着学科的自觉的。王铭铭总想对人类学进行彻底的改革,但谈何容易。传统的强大力量,包括民族学院的“民族学”学者对学科的固守,社会学学科的丧失学科特质和品位,考古学科的自然科学化,都让王铭铭非常头疼。别看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资源非常可怜,但是却特别愿意故步自封和坐井观天。自从1994年回国后,王铭铭就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担任教职,可以说是人类学学术中心的人物了,但是王铭铭有一种自觉,人类学既然是一门边缘学科,那么,完全可以从邻近的学科,为人类学灌注新的源头活水。王铭铭的确是这样做的。王铭铭和哲学家赵汀阳、法学者朱苏力、政治学者邓正来进行密切的学术对话,所以人类学界根本无法束缚王铭铭的手脚。王铭铭在对话之中获得了什么?
(五)
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正好是2004年12月21日,农历冬至。今年的石家庄很有冬至的景象,雪花飞舞,寒气逼人。今天下午我在学校讲述《百年中国人物》选修课,这种天气讲我喜欢课,我特别愉悦。讲完课程,天色已晚,校园笼罩在一片银白的雪花中。与两位小友,踏着柔软的积雪,聊着我课上所讲的“席明纳”,一位小友特别赞同我的意见,告诉我她就好喜欢进行学术对话,读书读到有趣处,特想向别的同学诉说,每当听到同学懂得了自己的心思,非常快慰。顺便说一下,这位同学就特别喜欢看邓正来的著作,热情地向我推荐。我对两位小友说,对话就要推己及人,有句歌词“你是否懂得我的心?”是啊!懂的人的心思,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人世间,由于不懂得别人的心思,把多少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如果对话的基础是平等,对话的方式是民主,对话的目的是自由,那么,我们就可以建构一个自由的学术空间,精神的自留地。
王铭铭通过对话,获得了更大的人类学的空间。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人类学?世间的事情恐怕都是如此。王铭铭对人类学所保持的态度是我所赞赏的,这也许未必是人类学发展的唯一路径,但是通过学术对话却开辟了人类学的无限可能的路径,这难道不是一桩好事?
窗外的雪花还在不知疲倦地飘舞,一扫往日的喧嚣与骚动。这座小城的夜色在雪花的映衬下,是那样的美好。
人生到处知何似?
雪泥鸿爪记踪迹。
注释:
〔1〕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6月第1版,第7页。
〔2〕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2004年6月第7次印刷,第190页。
〔3〕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50页。
〔4〕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51页。
〔5〕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59页。
〔6〕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59页。
〔7〕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35页。
〔8〕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2000年12月第2次印刷,第83页。
〔9〕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34页。
〔10〕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49页。
〔11〕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69页。
〔12〕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69页。
(《王铭铭与当代中国人类学》完成于2004年12月22日凌晨,雪花飞舞。2005年4月10日校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