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以文言取代白话,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字载体。自从1918年元月,《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1期发表胡适等人9首白话诗开始,就宣布了新诗的诞生;从此,传统诗词作为文学革命的对立面被打入冷宫,成为文学的弃儿,被排斥在诗的主流之外,几近无家可归。1920年秋,由于校方的提倡,清华大学校园里又出现了学习古诗的一股小小的潮流,当时还是学生的闻一多立即在《清华周刊》上撰文《敬告落伍的诗家》予以猛烈抨击,非常肯定地宣称:“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路走。”“若要知道旧诗怎样做不得,要做诗,定要做新诗。”旧诗的处境简直是到了“老鼠过街”的地步。
从1918-1937这20年间,在中国的诗歌舞台上,各种流派的新诗纷纷登台亮相,各领风骚,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是不是就没有旧体诗的位置了呢?也不尽然。在这20年间,新诗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诗词。不但继续写作诗词的仍然大有人在,甚至若干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也借此抒发感情(例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王统照等都擅长此道),而且还有若干诗社组织及其活动的存在(如著名的南社),还有发表诗词的刊物(如《甲寅》、《学衡》)。可以说,虽然处于不利的环境,其研习、创作却不曾断绝。甚至南北各都会以至中小城鎮,文人经常組织雅集,诗酒風流,唱酬切磋,留下作品。诗词还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呢。
这是因为,历来诗歌形式的发展方式就不是取代、更替,而是不断丰富,多样化;人为地要“打倒”一种形式如同推翻一个朝代那样取而代之是没有先例,不符合规律的,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传统诗词这一整套形式体系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其生命力之旺健使其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内容表达之需要。
抗战时期,为什么已经被放逐了的这样一种古老的诗体,会突然间重新获得旺盛的生命力,繁荣起来了呢?这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必然原因与深厚根基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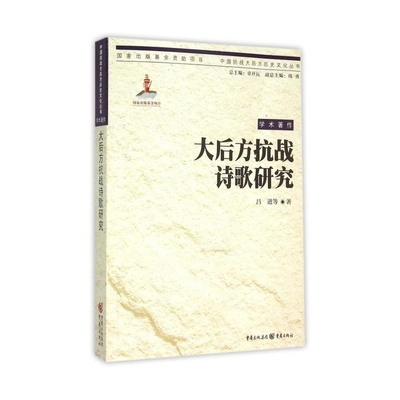
首先,这是时代赐予的机遇。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浩劫,同时也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大团结,大奋起,大抗争。江山不幸诗家幸。正是如杜甫所处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代。家仇国恨,同仇敌忾,怎能不诉诸笔墨,讴歌吟唱?长歌可以当哭,这时候,诗歌自然成为形式的最佳选择。
中国历史上,以诗歌反映抵御外侮的战争,反映战乱中人民的疾苦,有着悠久而优秀的传统。早在《诗经》中就有《无衣》、《黍离》、《君子于役》、《扬之水》等名篇;后世的民歌中也有《木兰诗》、《十五从军征》这样的不朽篇章。至于中国诗歌的高峰盛唐时代,更有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留下多少辉煌的绝唱!下至宋词的苏辛豪放派,陆游的爱国诗篇,又有多少无价之宝!如此丰富优良的传统,当然不能不对当时的诗坛产生巨大的影响。
诗自然要出自诗人的笔下。当时离辛亥革命不过二三十年,一些活跃在各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大多正当壮年,其青少年时代都受过古典文学熏陶,有很好的诗词根底。所以一旦情积于怀,不吐不快,便很自然地选择了诗词形式来倾吐。于是,祝捷,感时,纪事,抒愤,悼亡,怀人,种种过去习用的题材通通在诗词中有所反映,而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容。一些文学界中人,更是本色当行,纷纷大显身手。吴组光1942年在重庆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及此:“近来复古之风甚盛,许多埋没已久的古书古人古迹都得到机会在伟大的抗战年代里重新出头露面了。只以诗来说吧,甚至二十余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抱着凌厉无前以创造中国的新诗为职志的大师们,也兴高彩烈地大做起旧体诗来。事实甚多,不烦枚举。”这样的人物可以毫不费力地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郭沫若、沈尹默、田汉、张恨水、郁达夫、叶圣陶、老舍、罗家伦、阿英、王统照等等,至于本来就是著名诗词家或古典文学专家的,如柳亚子、赵熙、唐圭章、潘伯鹰、谬钺、胡小石、向楚、汪东、成善楷、易君左、霍松林等等,经常活跃诗坛,为抗战诗词多所奉献,就更加顺理成章了。由此可见,从事抗战诗词创作的诗人队伍是相当庞大而精锐的。
这样,整个中国诗坛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新诗人们奋发踔厉,以诗为枪,投入这场殊死的搏斗的同时,传统诗词也焕发青春,重登大雅之堂,发出正义的怒吼,“兵气每于文字见”(卢前句)!一些原本不理解、不认同、不喜爱新诗,却受过传统诗词熏陶、懂得其格律规范的各行各业的人士,因为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就纷纷拿起笔来,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新文学中许多骁将早年都受过传统诗歌熏陶,这时也不禁技痒,重操吟事,佳作迭出。队伍之壮,作品之丰,使诗词创作走出低谷,形成高潮。于是一些优秀之作不胫而走,传诵一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五四”以后传统诗词的复兴。这些抗战期间的诗词创作,我们称之为“抗战诗词”。
第二节不容忽视的民族文化遗产
实际上,局部抗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已开始,相关诗词也因势而生。前文所称抗战诗词,则是指写于1937年7月-1945年9月的以抗战为题材或与抗战相关连的诗词作品;而囿于本书的研究范围,又主要涉及以战时陪都为主的大后方产生、发表、流传的诗词作品。
抗战诗词的内容主要是正面歌颂民族抗战图存,揭露日寇滔天罪行,以鼓舞士气,坚定信心;与此相呼应的则是反映中国百姓的苦难生活,艰苦历程,战争带来的深巨创伤: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抗战诗词的佳作精品,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足以传世的很多。只是囿于长期存在的偏见导致歧视甚至抹杀,这部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亟待加强。比起抗战时期新诗所享受的“待遇”,实在是差得太远,令人遗憾。
最新的例证是,2012年结题的,在国内10余位著名学者的共同参与下,经过近8年的精心撰写,通过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仍然沿袭所谓“新文学”观念,无视中国诗词创作在1911年之后的客观存在,将其顽固地拒之于诗歌的门外!即便是跨越清代和民国的诗歌团体南社,该书只承认她在清代的历史,而蛮横地处以腰斩酷刑,强行扼杀了她1911年之后的鲜活生命!当然其中的抗战诗词也被蛮横地开除了诗籍!
既然如此,我们编写此书,就更应该对这部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给予充分的重视,以纠正那种显而易见的偏见,有意无意的误导,以期对当代诗词创作和新诗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节恢宏翔实的抗战诗史
抗战诗词有一个方面是新诗无法比肩的。那就是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日开始,几乎每一场重要的战役、每一个重要事件都留下了相应的诗词作品。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壮烈牺牲,后方百姓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字字血,声声泪,贯注浸淫于字里行间。当此“四海惊波围古国,域中烽火念苍生”(王统照《忆老舍与闻一多》)之际,诗人们“蓄将心力补危艰”(田汉句)。这些海量之作品,如果按照时间先后排序,就成为一部辉煌的抗战诗史。
全面抗战的第一枪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打响,举世皆惊。敏感的诗人们纷纷发出愤怒的吼声,歌颂抗战的英雄。其中最可贵的是由50首七绝构成的大型组诗《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作者王冷斋时任宛平县县长,是参与了整个事件的亲历者,这组诗从“七七”一直写到7月28日佟麟阁、赵登禹二位将军英勇殉国,还结合了当时全国大势,不仅具有很高艺术价值,而且每首诗后皆附“本事”,堪称信史。王冷斋后来到大后方参加抗战,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王冷斋赴东京出庭作证。解放后,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1960年在北京逝世。这是后话。
7月8日深夜,我军大刀队冒雨突袭敌营,与寇肉搏,一度夺回卢沟桥,王蘧常用班超率三十六骑攻杀匈奴之典,以《大刀勇士》颂之,豪气干云。按王蘧常为著名书法家,其抗战诗文,编为《抗兵集》,诗如《八百孤军》、《闻平型关捷报歌》、《大刀勇士》、《胡烈士歌》,文如《论倭不足畏》、《胡阿毛烈士传》,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抒发了民族正气。抗战胜利后,王蘧常在暨南大学任教。1949年开始,在无锡中国文学院任副院长。1951年起,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后调哲学系为教授,直至1989年去世。
常值得一提的是,就连当年的“第三种人”杜衡也有《卢沟桥衅起》七律,抒写“关河百战终摧虏”的必胜信心呢。
郭沫若是新诗的开创者之一,同时又擅长诗词。1937年7月25日从日本回国投身抗战,写下一首步韵鲁迅的七律《归国杂吟(之二)》,其结句为“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唱出了时代最强音,立即不胫而走,广为传诵。紧接着,是年10月,上海闵行仓库八百壮士英勇抗敌的事迹传遍中华,又掀起一个吟唱热潮。郭沫若的七绝《弹八百壮士大鼓书付潜修》:“枯肠搜索费沉吟,响遏行云弹雨音。词与健儿同壮烈,自拟身亦在枪林。”既歌颂了壮士抗敌的壮烈,又赞赏了表演的精彩,堪称酣畅淋漓。
此前的上海“八一三”战事,八路军平型关大捷(9月),以及稍后的南京陷落、日寇屠城,无不有诗词反映。
抗日战争虽然开始战局不利,但是也打了不少胜仗,所以祝捷之作很多。庆祝台儿庄大捷的诗作当时不知几多,不少是气壮山河,令人斗志倍增的大气之作,如胡厥文的《台儿庄大捷》、欧阳翥的《闻台儿庄大捷喜赋》就是。为武汉空战胜利,涂康作七言长歌相庆,并且讴歌了飞将陈怀民的英雄事迹:“猛撞敌机愿同尽,足动天地泣鬼神!”
这还只是抗战前期的一些反映“战史”之作。随着战事的进展,几乎所有重大战役、事件,直至抗战胜利,全民狂欢,莫不留下诗之记录,可以彪炳史册。甚至那些易为时间淘洗而为后人所难知的史实也在诗词中得以存留。如1938年2月23日,中国空军出征台北,炸毁日机40架,全部安返。冯玉祥、杨沧白皆有诗咏飞将之奇功。另如1938年秋,空军烈士孙景灏于汉口驾机撞毁敌舰,陈禅心即集唐人诗句以歌之,将其誉为博浪沙锥击秦始皇之壮举。对于敌军暴行,大如重庆大轰炸自是得到充分反映(代表作有杨沧白《哀巴渝歌》),就连奉节这样的小城挨炸也有所记载(重庆诗人李重人《闻奉节被炸简问亲友》1938)。
抗战诗词所涉猎者,还及于境外战场。如李根源(近代名士、国民党元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的《滇缅战场纪事诗》共九题十一首,起自1944年3月4日,迄于12月15日,历述中国赴缅远征军之战功,其小序曰:“贼胆已寒,国威远张。欣慨之余,随口吟唱。”
一些诗人的眼光还关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这方面的作品以姚伯麟、李竹侯二人为多,由一些诗的标题就可知其内容。如《日关东西遍遭轰炸》(姚伯麟)、《美军在菲律宾中部登录》(李竹侯)等等。沈祖棻《减字木兰花·闻巴黎光复》如下:
花都梦歇,枝上年年啼宇血。还我山河,故国重闻马赛歌。
秦淮旧月,十载空城流水咽。何日东归,父老中原望羽旗。
由巴黎念及南京,殷切盼望胜利之情感人肺腑。
抗日战争是空前惨烈的,许多将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所以也不乏悼亡之作。陶铸的《悼左权将军》写出了同仇敌忾的气势:“此日三军同痛哭,河山誓死逐强梁。”而“生前气已吞胡虏,死去魂犹作鬼雄。”(濮智诠悼念赵登禹、佟麟阁将军)和“拼死留得真面目,图存不惜好头颅。”(汪巨伯悼念王铭章师长)皆为绝妙对句。
正面描写战争生活,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女诗人李蕙苏填有《减字木兰花.从军乐》三阕,其一为:
和衣卧雪,笑拔霜刀映冷月。一响冲锋,跃马声嘶战雾浓。
枕戈待旦,斩敌男儿终不倦。奏凯回军,手弄弦声欲上云。
金戈铁马,豪气干云,巾帼不让须眉。
四战时生活的生动写照
日寇的入侵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对此,许多作品有沉痛的描述,将作为罪证,作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永远的控诉。像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无不铁证如山,记录在案。而山河破碎,兵荒马乱;流离失所,背乡离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血雨腥风卷落花”(丰子恺《七绝》,1939),“家仇国恨两悠悠”(柯尧放《送内之湄潭》),“抚时伤事心如焚”(何鲁《黑龙潭》,1937),“睇笑中原泪未收”(汪辟疆句),中国人民无穷的灾难尽都入木三分,有诗为证。这样的诗例太多了。著名词家唐圭璋的《雨霖铃·流亡图》如下:
风狂雨急。向前途去,不辨南北。乡关极目何处?但迷雾里,千山遥隔。负老怀婴,浑不管衣履都湿。只念念谁收?庐舍成灰火犹炽。
茫茫四野天如漆,问无村一饭何能觅?荒庐败苇深处,凝泪眼几星磷匿。忍死须臾,伫望三军,扫荡腥迹。会有日万众腾欢,相伴还京邑。
离乡背井,饥寒交迫,还念在期盼胜利之日。
1938年1月,叶圣陶举家入川避难,行至宜昌,有诗纪实:“下游到客日盈千,逆旅麇居待入川。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纯用白描手法,流民惨状如在目前。1942年,他在重庆思乡心切,夜不能寐:“终日驰车不见津,滔滔江水未归人。渝州万籁一时寂,夜雨啼鹃听到晨。”宛敏灏的《新春偶成》:“一从西走避胡沙,道路流离到处家。底事新春动乡思,他乡胡豆又开花。”柳诒徵的《霞坳》:“荷叶街头早稻肥,霞坳雨后翠成围。频年客路飘零惯,但听乡音即当归。”与此异曲同工,都是难以排遣的离人愁绪啊。
抗战期间,齐白石陷身北平。徐悲鸿时常念其安危:“烽烟满地动干戈,缥缈湘灵意若何?最是系情回首望,秋风袅袅洞庭波。”一往情深,却山遥路远,不通音讯,无可奈何。
田汉是新文化运动骁将,亦以诗词名世,被屠岸称为“巨擘”。1944年他到了贵阳,一首七绝道尽物价飞涨的艰难时世:“爷有新诗不济贫,贵阳珠米桂如薪。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赠人》)。
诗人们的悲愤之情无时不有。成都诗人闵虚谷有两句诗: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形象写照:“惊心故国事全非,剩水残山夕照微。”“南天魂已断,故国恨难平!”(刘大杰《哭郁达夫》,1945)。则更加突出了悲愤之感。“戴花村女歌牛背,不似中原战六年。”(屈义林《渝蓉道中杂咏之六》,1943)就是面对美景,亦不忘国难。刘孟伉《答友》第三联云:“身边妻女从何托,眼底流亡大可哀。”不止于一己之苦,更瞩目同胞之哀。
老舍是文学全才,亦擅诗词,抗战期间寓居重庆。作于1941年的《述怀》是一首于沉痛中不失信心,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辛酸步步向西来,不到河清眉不开。身后声名留气节,眼前风物愧诗才。论人莫逊春秋笔,入世方知圣哲哀。四海飘零余一死,青天尚在敢心灰!”
再摘取一些精彩的片段:陈禅心听逃难者说日寇暴行后,集杜诗记之:“焚烧何太频,谈笑行杀戮。……积尸草木深,天地日流血。”唐圭璋这样写成都遭受空袭的惨境:“悲恻。弹雨密。料血染游魂,楼化瓦砾。城堙火炬连天赤。”优秀女词人沈祖棻以《声声慢》一曲记述了“闻倭寇败降”的复杂心情,喜余还忧,十分沉痛:“肠断吴天东望,早珠灰罗烬,乔木荒寒。故鬼新茔,无家何用生还!”
毋庸讳言,抗战期间百姓所受灾难痛苦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日寇,当时社会也存在着种种腐败行径、丑恶现象。对此,诗人们满怀义愤,不吝笔墨,给予有力的揭露、鞭挞。试举诗词大家向楚《感时之三》以见其犀利:“铜臭摸金手,重重刮地层。人为窃食鼠,官似撞钟僧。民贱妻孥贵,天通鬼蜮能。终南开此径,捷足让先登。”卢前的《内江行》写了“乞儿满街走”,“一人哀号数人和”的惨状后,结尾直指当局:“邑有流亡责在谁?寄语内江贤父母。”
第五节几位有特色的诗人
如前所述,抗战诗词数量之多难以统计,而诗人队伍亦及其庞大,名家辈出,众星争辉。本书已经选出号称“当代李清照”的女词人沈祖棻作为个例详说,为了更周到一点,这里再举出几位有特色的诗人予以介绍,仅可略见一斑耳。
卢前,是抗战期间名头很响的学者、诗人。他原名正绅,字冀野,自号饮虹、小疏。江苏南京[]人。1905年3月2日生,1951年4月17日因肾脏病逝于南京大学医院。卢前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先后受聘在金陵等多所大学讲授文学、戏剧。主编过《中央日报·泱泱》副刊。卢前自小聪颖,1921年16岁,投考南京东南大学,虽中文成绩优异,因数学0分,未被录取。一年之后再考东南大学,以“特别生”名义被录取入国文系。当时吴梅应东南大学聘,举家南归,成为卢前的老师,对卢前一生学术上的影响甚大。卢前后来成为元曲、戏曲专家。在抗战诗坛上,他以大量的曲作见重于时。兹举其《商调梧叶儿·募寒衣慰问信》为例:“单绵袄,一封书,寄到战场无?争执殳,作前驱。可忘了他们痛苦?”语言浅近,而情长意深。再如《仙侣游四门·劫后成都》:“停车夜宿锦官城,重向御街行。暗中空想楼台景,荒芜独心惊。腥!血债记分明。”记述成都遭到空袭后的一片惨象,声讨日寇罪行。
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卢前立即写就《水调歌头》一词,加入了抗战诗词的“合唱团”,并成为其中的优秀歌者。此词写情势之危急有云:“火焰已燃眉睫,如箭在弦头!”而以“何以消吾恨,不共戴天仇”诉说对日寇的仇恨,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卢前除了自己创作,对抗战诗词的重大贡献还在于,他从1938年5月出到1945年12月,主编了《民族诗坛》,共出版五卷二十九册,为诗词提供了发表园地,对诗词创作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禅心,1912年9月生,1936年9月加入中国抗日空军第四大队,参加保卫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的大小战斗。在其戎马生涯中著有爱国抗日诗篇《抗倭集》(全系集句)、《沧桑集》两卷,计2000多首,部分在《中国空军》、武汉《民族诗坛》等报刊发表,鼓舞同胞们抗日斗志,因而被郭沫若、柳亚子、于右任、董必武等称誉为"抗日空军诗人"、"爱国诗人”。他对中国古典诗词非常熟悉,名家名作烂熟于心,所以常常以集句方式叙事抒怀,得心应手地把本来毫不相干内的诗句集中起来,做到恰到好处,天衣无缝,因而又被时人成为“集句圣手”。
1937年冬,陈禅心在南京光华门送飞行员晓战,集唐诗得二绝曰:“重叠遥山隔雾看(李白),山川龙战血漫漫(胡曾)。更催飞将追骄虏(严武),千里追风也不难(曹唐)。”“越岫吴峰尽接连(李中),男儿酬志在当年(伍乔)。我军气雄贼心死(朱湾),来保江南一片天(沈彬)!”如果隐去原作者姓名,实在很难容易视为新创之诗;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除李白外,其他诗人都不算知名。
1944年,有一位抗日战士、诗人陈国柱将其手稿《沧州吟集》请陈禅心保管,陈禅心竟以陈国柱诗集成200首新作,再集李贺句得此:“帐前轻絮鹅毛起,七星贯断姮娥死。真是荆轲一片心,半卷红旗临易水。收取关山五十州,地无惊烟海千里。明星灿烂东方陲,人之得意且如此!”抗战胜利后,陈禅心分别集王建、常建、李贺句得诗三首:《日妇哭夫》、《哀战地日寇遗骸》和《吊中华抗日无名英雄》,简直是无所不能!其腹笥之丰,运用之巧,叫人叹为观止。
所幸陈禅心是一位长寿诗人,解放后是福建省文史馆馆员,出版诗词集、文史著作14本,各大图书馆广为收藏。1995年他已83岁,还曾来渝参加纪念抗战40周年学术研讨会呢。
前文提到,中国新文学营垒中人,亦不乏擅长诗词者。其中田汉毕生不弃诗词,量丰质高,且于抗战诗词着力最多,成就斐然。他的抗战诗词中有许多感时纪事之作,亦具有诗史之价值。
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田汉即自南京奔赴前线,沿途写有《京沪征尘》七绝一组,其中有“无数人家归不得,泪痕应比弹痕多”这样惨烈的诗句。其《过大世界》也是惨不忍睹:“宛如霹雳下晴空,舞断歌残一击中。凄绝铁门纤手落,指尖犹有蔻丹红。”
紧接着,田汉又在沪松前线写下组诗《访闸北前线》,直击战场烽烟,讴歌抗敌勇士,其中不乏佳作。
11月上海沦陷后,他踏上了流亡之路,所写组诗《从上海到长沙》,计有七绝30首,在历经战乱劫波之后,犹自发出了“长沙岂止三千户,众志犹堪御暴秦”的铮铮之声。其中《晤某将军》则表现了必胜的信念:“国事原来尚可为,无边英气郁浓眉。河山尽使成军垒,直到倭奴屈膝时!”
1938年11月,田汉率国民政府军委会三厅抗战演剧队由长沙赴衡阳,又写下《衡阳道中纪行》组诗,共七绝11首,记录了文化人在抗战中的艰苦生活和精神风貌。其一为:“猎猎秋风卷柳丝,将军慷慨誓雄狮。画囊在背琴悬肘,齐向山村出发时。”英姿飒爽,意气风发,历历在目。
除了这几组抗战早期的力作,田汉一直保留了以诗纪实的习惯,写下许多单篇,成为抗战期间方方面面的生活实录。他是著名的捷才,往往“援笔立就”,堪比“温八叉”。多产的快手,而能保证艺术质量,在抗战诗词中独树一帜,实在难能可贵。
他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叶圣陶、张恨水等新文学作家抗战期间均在四川大后方坚持诗词创作,成就斐然,就不一一介绍了。
五抗战诗词的生态环境
之所以抗战诗词能够兴旺发达,取得重大成就,成为值得珍惜的诗文化遗产,是与其走出了“被边缘化”的困境,生态环境大大改善分不开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报刊:园地的提供
抗战期间,许多报刊都为诗词开绿灯,提供发表园地,促进了诗词创作的繁荣。重庆战时首都的地位使其冠盖云集,人文荟萃,成为当时的全国文化和舆论中心。其报业兴盛,《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扫荡报》、《时事新报》、《新华日报》、《益世报》等报在此出版,其中不少报纸办有文艺副刊,发表诗词新作。其中来自战区、沦陷区的作品,也就自然包含在“大后方”范围之中了。
这些作品由于年代较久,零星分散,收集整理难度很大。根据《新华日报旧体诗选注》编者谷莺所撰前言,《新华日报》之《新华》副刊从1938年1月11日在重庆创刊到1947年停刊,共刊载诗词300多首。而该书共编选截至抗战胜利的诗词150余首。在这里显山露水的,不妨称为“《新华日报》诗人群”。他们的作品,引人注目者有朱德的名作《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1940年7月24日见报)神采飞扬,气势不凡。沈钧儒的七律《经年》也出手不凡:“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山城夜正寒。”忧国伤时,难以释怀。尾联“痛哭狂歌俱未足,河山杂沓试凭栏。”则远望家山,忧心如焚。当时虽然大局是国共合作,但是矛盾、摩擦不可避免。毫无疑义,作为国统区唯一的中共党报,就是发表文艺作品,也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这些诗词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是必然的。不过抗日大局绝对不会违背,就是抒写个人感兴,也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
有一家名曰《民族诗坛》的杂志,1938年5月创刊于武汉,10月起迁址重庆。主编卢冀野,发行人项学儒,独立出版社印行。总经销处是正中书局,1941年5月开始变成正中书局服务部和中国文化服务社。每月一册,到10月第六册为第一卷,此后仍然是六册为一卷,到1945年12月为止,共出版五卷二十九册停刊。这是一处专门发表诗词、传播诗词知识的阵地,对于抗战诗词的发展自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族诗坛》杂志的宗旨是“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之情绪”。作品多以控诉日本侵略,表达国土遭受蹂躏的愤怒、憎恨、厌恶、悲哀之情为题目。每期都将有关诗词的论文或者随笔放在卷头,然后按诗(绝句,律诗等旧体诗)、词、散曲、新体诗(现代诗)的顺序刊登作品。
其作品略举二例,其倾向可知一斑:
村东蓝缕妇,云是战士妻。冰天雪地中,母哭儿饥啼。
夫婿少也壮,从军赴晋西。血肉当驳火,横飞山之径。
遗此小儿女,龙钟况母慈。饥寒胡足论,所望在此儿。
血债终须偿,九世犹非迟。
——贾景德《冬日杂咏》3卷1期
这首诗描写了丈夫战死,独自抚养幼儿和老母的痛苦的妻子,嘱托孩子要报仇雪恨。下面的诗刻画了日军空袭的惨状,表达对“倭奴”即日军的仇恨和诅咒。
再看:
笛悲鸣,断续时,空袭发警报、奔避不迟疑。
母唤儿,夫寻妻,东市尸枕籍,西市血成泥,不见所爱唯悲啼。
不用啼,不用哭,谁使人间成地狱,
齐心复大仇,杀尽倭奴恨雪足。
——许崇怡《空袭词》4卷2期
这是对日寇暴行的血泪控诉,和深仇大恨的表述。
《民族诗坛》的主要撰稿人有:曾琦、曾小鲁、陈家庆、贾景德、江絜生、李元鼎、李仙根、林庚白、卢前、钱少华、王陆一、许崇灏、于右任、易君左、张庚由。从上稿频率看,于右任、卢冀野、易君左、王陆一、江絜生、张庚由可视为核心成员。
于右任,陕西人,国民党元老。据于右任年谱作者刘延涛和刘凤翰记载,于右任1937年聚集学者、诗人成立“民族诗坛”。另外卢冀野的学生霍松林(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也在陈述中提到《民族诗坛》是在于右任的指导下出版的。1938年于右任已年近六十,又值担任监察院院长公务极其繁忙的时期,但他却与主编卢冀野同样成为最热心的撰稿人,除第三辑五卷外每期都有作品发表。
卢冀野即卢前,作为主编是支撑杂志的关键人物。1938年7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一期参政员。国民参政会是为集结全国的力量参与抗战而设立的,卢冀野当选参政员据说是因为学术上的声望,他与于右任、陈立夫等国民党要人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易君左,湖南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记者、学者和作家。抗战爆发后任湖南《国民日报》主笔。1938年秋开始任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员等职。与于右任关系密切,跟卢冀野也十分亲近。
王陆一因为同乡关系颇受于右任信任。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书记长,1930年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从1935年开始任国民党中央委员。
张庚由,也是于右任的同乡,因为有才而深得王陆一喜爱,娶王陆一之妹为妻。1937年受于右任之聘,进入监察院担任于的秘书。
由以上情况可知,《民族诗坛》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这对其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也是过去对此刊较少关注的缘由吧。今天,我们对其以诗词为武器参与抗战的历史事实,在抗战文学史中给予应有的位置,是完全必要的。
二、诗社:组织的保证
大后方各地都有一些规模不一的诗词组织。
“饮河诗社”是抗战期间在重庆研究和创作诗词的文学团体,1940年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等人发起,创办。社名取庄子“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之句。社员借此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抒写爱国情怀。即以当时的年轻诗人许伯建为例,从1937年“七七事变”起,就每年写一首同韵《满江红》,直到1944年的《卢沟国难七周年八叠韵》,始终表现了高昂的抗敌激情,必胜信念。
饮河诗社不但团结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包括俞平伯、朱自清、缪钺、叶圣陶、郭绍虞、陈铭枢、肖公权、吴宓、黄杰、谢稚柳、徐韬、黄稚荃(女)、黄苗子、蒋山青、钱问樵、王季思、沙孟海、程千帆、沈祖棻、萧涤非、成惕轩、施蛰存、曹聚仁、萧赞育、叶恭绰、屈义林、陈寅恪、王遽常、游国恩、谢无量、李思纯、夏承焘、浦江清、潘光旦、马一浮等。一时群贤齐聚、俊彦荟萃。
社址在重庆市中区大溪沟下罗家院张家花园三号,附近是中苏友谊文化交流会办公地。入社的重庆人士有田楚侨、柯尧放、许伯建、芶梦陶。柯、许二人还为诗社提供了一定的活动条件。社刊创办了《诗叶》、《饮河集》、《饮河》刊物,还在《中央日报》《扫荡报》《益世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上开辟专栏,潘伯鹰任主编,共刊出一百余期。
诗社活动得到重庆诗人柯尧放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活动方式是传统文人那种“吟集”,彼此唱和,自印刊物,也在报刊发表诗作,颇有影响。先后参加《饮河集》、《诗叶》和《饮河》渝版的作者共一百余人。通讯的诗友遍及全国各地。许伯建在《怀宁潘伯鹰先生家传》一文中写道:(潘伯鹰)“为饮河之社,以恢宏大义相鼓吹,声气所洎,应者万里。居恒诗简络绎,尽其晦明慷慨之思焉。”可见“饮河”影响之广。
顺便提及,在抗战胜利之后,“饮河”东迁上海,还继续活动到1049年底;而重庆还保留了“饮河渝社”至迟坚持到1947年(许伯建《饮河渝社丁亥小重阳社集柬》可证)。
三、活动:创作的推动
有了诗词组织,有了发表园地,必然就会开展以一些诗词活动,而活动则必然会促进诗词创作的繁荣。
诗人之间唱和赠答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产生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佳篇,而且往往不止于友情的表达,还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抗战期间同样如此,这样的交流也活跃了诗坛,促进了创作,产生了若干优秀作品。
即以“新华日报诗人群”为例,他们在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此类作品。其中有一些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意在配合某种形势的需要。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的话剧4月《屈原》在重庆公演,诗人们便围绕此剧纷纷唱和,一共在《新华日报》副刊“《屈原》唱和”专栏先后发表66首诗作,蔚为壮观。
另一种活动方式是诗人们的雅集、诗会。饮河诗社就经常举办这种活动。当时重庆青年诗人柯尧放在南岸老君洞的住所下临长江,可以由此俯瞰山城,便成为“饮河”诗人们经常品茶饮酒,高谈阔论之处,往往兴味高昂,触发灵感,即席吟诗,收获多多。
1940年重阳节前,缙云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和尚,倡议举行“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
这是一次激发抗日热情的聚会。应邀者28人,当天实际到会18人,聚集缙云寺,攀登狮子峰。与会者按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分韵,在狮子峰顶,每人拈得一字为韵作诗,当场朗诵。王维诗系28韵,缺席者由到会人员代拈,然后再函告本人,限期作好寄太虚汇集,共得诗31首,编辑成《庚辰重九缙云登高集》,发表于《海潮音》杂志上。
1945年8月15日夜,数十万重庆人民在街头彻夜狂欢,庆祝日寇投降,抗战胜利。柯尧放激情难抑,作长歌《快哉此夜行》,生动地描绘了空前盛况,巧遇诗友李春坪,“直欲买醉思新丰”。事后,此诗引起“饮河”诗友共鸣,纷纷跟进,辑成《陪都闻捷胜利唱和诗》,付梓印行,算是为永远彪炳史册的大后方抗战诗词留下一条刚劲有力的“豹尾”。
如此看来,抗战诗词从复兴到繁荣,是具备了充分的内在与外部条件的,这也是诗歌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结果。设想诗词真正被历史淘汰,整个的抗战诗歌只有自由诗,岂不少了半壁河山!
结语
抗战诗词的光辉成就,虽然迄今尚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取得应有的地位,但是,真正的珍珠决不会长久被历史的尘土淹没。当我们回顾抗战诗词辉煌成就的时候,不能不结合当前诗歌创作的现实,思考一些问题,从而获取一些启示。
首先,让我们惊叹的是中华诗词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如前文所述,古典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经遭到一次横扫式的几乎致命的打击,但是在抗战期间进又奇迹般地复苏了。
其次,我们不能不惊叹于诗词(曲)形式对于崭新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容受与适应能力。优秀的诗人运用这种古老的形式,完全可以得心应手,意到笔随。
这一事实,同样由新时期以来,20世纪传统诗词的第二次复兴所证明。抗战诗词创作高潮随着抗战的结束而消退。50年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诗词创作再次遭遇厄运。如今,诗词创作的复兴已见端倪,其高潮经过20余年的酝酿,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也许就参与者的广泛而言,如今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抗战时期。但是毋庸讳言,由于形成的知识断层、认识误区,人们的古典文学修养与六七十年前相比,那就大为愧色了。就连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不能做诗填词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无论怎么说,当今的诗词创作中之佼佼者,同样证明了诗词形式对于今天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证明了她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更令人鼓舞的事实是,2011年由国务院参事室和国家文史馆共同创建了中华诗词研究院,成为官方的研究机构,而诗词集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参评资格。这就为新世纪诗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让我们更加珍惜抗战诗词这笔无比丰厚的文化遗产,认真学习其精髓,汲取其精华,为有力地促进诗词创作在新世纪的繁荣兴旺而努力吧!
参考文献
《抗战诗史》,陈汉平编注,团结出版社,1995年。
《中国抗日战争诗词曲选》,重庆市文史馆编,重庆出版社,1997年.
《21世纪诗词注评》,钱理群、袁本良注评,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李遇春著,华中师大出版社,2010年。
《新华日报旧体诗选注》,谷莺选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巴蜀近代诗词选》,薛新力、蒲健夫主编,重庆出版社,2003年。
《重庆文史资料》第44辑,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师大出版社,1996年。
《民国旧体诗史稿》,胡迎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