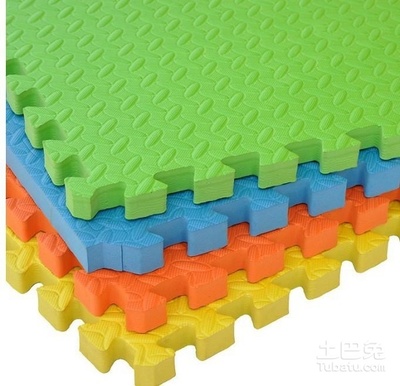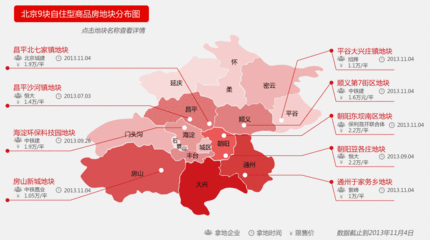(尧十三《雨霖铃》)
1
我去采访周云蓬的时候,要进绍兴一个公园拍点外景,公园管理处的人看见我们的摄像机,连票都不卖了。穿蓝制服的大姐头不抬,说:“公园今天维修。”
我们说:“拍鸟,不拍人。”
“那也不行。”
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么上火,要么低声下气求一下,老周站在边上,蔫蔫地问:“鸟也修吗?”
大姐被逼得只好说:“也修。”
我们手忙脚乱拿了介绍信,请示她的上级,当确认了我们只是拍摄“一个盲人歌手在绍兴的文化生活”后,放我们进去了,还有三五位在后面很客气地跟着。
进了公园,周云蓬说:“领导是怕鸟上访,一进门,孔雀跪一地。”
后边跟着的人也短促地笑了两声。
绿妖乐得眼睛弯弯,我问过她为什么跟云蓬在一起,她说:“王小波小说里写,一个母亲对女儿说,一辈子很长,要跟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就为了这个吗?”
“有趣多难啊。”她说。
2
绍兴小街光净,桥上的青石头被磨得锃亮水滑,他和绿妖夹着手臂,不用盲杖,走得比谁都快。走过木店,他闻着刨花香,停下脚,让我们买几个新鲜的木陀螺。绍兴雨多,开着电暖气,围着暗红的光搓手哈气,桌上几个橘子,剥皮后又凉又沉又香。雨真冷,我说:“你一个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觉得北京像汤,是水和火的结合体,老在加热,在锅里,咕噜噜,老汤,一百年,很浓,“能解饿,但就是不新鲜”。熬到后来,除了金刚一样的人,很多人都被煮成汤料了。
他爱在半生不熟的时候蹦出来溜达,说这是他的命,“人的一生往往围着一个动机转。音乐,也是第一句重要,有一个旋律动机的时候,这首歌的命运就注定了。”
动机从他幼年开始,他妈带着他看眼睛,坐绿皮火车到处跑。“绝望是没有出路,一望一堵墙。不安是不知道看见什么,还有百分之五十。”
去富阳的火车上,我们聊天,有人觉得盲人到这么多地方也看不到什么,他一笑:“现在过钱塘江了吧。”
边上的人都不知觉,“你怎么知道?”
“过桥的声音,比较空洞。”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人要被困住了,就想去新鲜的地方,每个地方的味儿都不一样,连鸡叫声都不一样,河南的鸡叫声就比西藏的暴躁些。”
这本书里大多是他到处乱跑的记录:翻跟头的手风琴者,大熊一样的胡德夫的手,一玻璃杯黄金一样的阳光,香港的两只牛蛙像老头一样咳嗽着聊天,海南每棵植物下各自“噼噼啪啪”的雨,一个人的春节——腊肉白米饭老熟的陈香。
就这么出出进进,停停走走,怕自己被砌在一种水泥模式里,他说“不管是自强不息式的意义,还是流浪在路上的意义,要是被绑架了,其实都是在表演,哪怕这个词多好听。”
“人嘛,害怕没拐杖。”我说。
“那也是一种绑架,我后来争取尽量不依赖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地方。关键要看是 不是诚实,如果内心的声音不是那样的,就别那样。”
3
我们在绍兴的小店里吃芋艿,二十五块钱要了四个菜、三碗黄酒,白米饭随便加,他说:“这要是在北京,饭店不是自己房子,租金贵,老板肯定说,这还了得,为什么不用地沟油?”
很多写诗唱歌的人不问俗事,老周关心世俗,他写崔健与罗大佑,也是写自己,“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地甩开。”
他书里写的都是这类的感受,没有以世界名著爱好者和业余思想家自居,面对公共性问题也是从个人出发,“有人伤害了你的朋友,或者伤害了你关心的人,你也觉得很疼痛,疼痛和幸福都扩大了。”
不过他一边写社会新闻,一边自我责问,觉得这种限时的紧张要求不从容,每周一期的专栏,有的时评写的时候看得出有点急,有锻字炼句的痕迹,一觉得勉强,他就把专栏又停了。他这种自我警觉性总是很强,说,“自由就是有权利不断地怀疑,或者有怀疑的可能性,怀疑就是自我更新。”
绍兴他家的房后,有条河,寒绿色,他坐在河边的石台上抱着吉他随手拨弄:“生活和弹琴一样,不能只紧,也不能只松,得这么松松紧紧地沤出来。”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他写父亲的那一篇,是一件事在心里沤了多少年,悲酸欢慨,滚热过,又放凉了,凝结在心,从心里顶出来的。
老周讲过一个故事,也许可以用来说一下文字的标准。他住圆明园时,一个艺术青年掉进了河里,一开始文质彬彬,冒出一个头,对岸上人招手:“能不能救一下?”
沉下去再浮上来的时候喊:“救一下。”
再浮上来的时候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救命啊!”
写文章,得写到这个份儿上——不吐不快,没有苦吟,也不用琢磨,连修辞都是一种烦琐,老实道出就是。
4
我看老周在书里写尧十三,就找来听,他用贵州织金话唱《雨霖铃》——“我要说走嘞,之千里嘞烟雾波浪嘞/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拉们讲,是之样子嘞,离别是最难在嘞/更球不要讲,现在是秋天嘞/我一哈酒醒来,我在哪点/杨柳嘞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嘞……”
听得我。想起高秉涵说“人总是要有个窝的,小狗也一样,这个窝是个烂棉花也行,有它从小闻的味儿。”
中国人现在不管在哪儿,总像老周说的,有那种“身在外地”的感觉,是一种焦虑。像地下河一样,日夜都不停,焦虑都不自知。
民谣里头有这个千百年来的味儿,张佺、玮玮、小河、李志、马木尔……唱的都是自己的窝,人要没有这几根沾土的草茎连着,活着活着就干枯了。
“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就这几个字,这么一个调,从古到今的苦乐哀愁在里头,但人听了能有一个宽解,就是老周说的“人不是完全活在当下,你有很多延伸在古代里面,也伸在未来,是一个纵深的、完整的人”。
人活着,情动于衷,嗟叹不足,歌之咏之,只要槐花还开,杨柳还摆,风还吹着小月亮,民谣就还在,它会自己长,带着腥味儿从硬土里拱出来,白天黑夜,种子被鸟带走,被风吹来,带着青湿之气,它自己要找出路,绳子捆不住,石头压不了,把水泥地淹了,钻过篱笆,在水边暗暗会合,蔓得千枝万枝。
它不与什么对抗,它就是要按它的一股子天性自在地长。在绍兴他写字的窗子底下,周云蓬指给我看过,小木窄门里头那个老太太用电子琴伴奏唱革命歌,气壮山河,日夜不息。他写:“我起初放雷鬼、死亡金属,加以对抗,都不管用。后来想起邓丽君,找了一张邓丽君全集。”
一腔自顾自的柔情,把火红焦亮的东西都渗透了,浇得没声了。
5
老周在这本书里写的多是别人,但从别人身上倒映出了自己。
当年老罗要给曾轶可录专辑,很多朋友都不赞成,老罗找了周云蓬他们来配乐,还租了最好的录音棚。大家觉得滑稽“把他俩拉在一起……”,老罗一路说,边上的人一路哈哈哈,等他说到最后曾轶可不肯来,他们摆了一张空椅子在中间,照了张缺了歌手的乐队大合影,听的人已经乐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有个哥们连喘带笑说“我早就告诉你……”
老罗把小杯子往桌上一推,拔腿走了,边上的人拽袖子没拽住,差点把碗筷都带到地上了。再怎么叫也不回来。
过了两年多,我才听老罗说:“那天我没回来,可不是因为生气。”
我看了他半天:“你……不会吧……”
“就是啊,眼睛通红,回来没法看。”他说,“跟好朋友说说委屈还不行吗?”
老周在这本书里写了这件事儿的过程,费了那么大劲,他一句埋怨讥诮没有,是老周建议大家照合影作为纪念的,“我们一起碰杯,感觉这个事没白做。在老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一腔血性,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
我一边看一边自惭,看人家老周。
之后不久,吃饭时席间谈起中医,老周挺中医,老罗反中医,两人越谈声音越大,老周扶案而起,气得有点哆嗦,一股子黑沉沉的摧城拔寨的气。老罗也站起来了,也是一团黑,两人两只大动物一样咻咻地对峙着,堵得满肚子话说不出来。我们一边笑一边往开拉。绿妖推着老周先走了,老罗发了半天牢骚才算。
到了春节,老罗见了我,按捺不住:“我想给他发个短信……”摸出手机给我看,“结果他先发了一个,‘可春节不好过,我们吵过架……’”——是老周自己唱过的歌词改的。
呵呵,男人这种动物,脸上能有这种扭捏的心潮澎湃,一个是刚跟姑娘说话的时候,一个是跟兄弟言归于好的时候。
几个月后两人见面,老罗正感着冒,带了一袋中药,对着老周装可爱:“为了你,我连中药都吃了。”老周说:“我先发那条短信,就是怕被你抢了先机。”
老周写“被老罗喜欢的人是比较有福的”,被老周喜欢的人也是。
6
有天我在《收获》上看了史铁生写的信,觉得写得实在好,非跟谁分享一下不可,就突兀地发给周云蓬让他看。
史铁生跟另一人谈的是信仰,这种事最难谈,人人各有经验,非要说天眼开了,谁也否认不了谁。旁人很难置喙。
史铁生说自己很多事没想明白,但有一条,人和人谈话,不是比高低,他反对绝对武断,“行嘞,听我的,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让人不明白的事儿最容易抓人,承诺一个真理、一个终点,挺容易让人入迷,跟着就走了,但这种事情却往往不让多问,“听我的不得了,老这么问东问西的,咱这事可就瞎了。”
他说:“这里头最容易孕育一种霸道,但凡全能的或者宣称全能的,我都听着邪乎”。
我把这文章发给老周看,是觉得他在这点上和史铁生挺像——在采访的时候,周云蓬对我说过:“要像划船一样,自己有个舵。不是要故意逆流而上,那也是一种做作。但是允许个人把舵左偏偏,右偏偏,船为什么要有这么个东西,因为个人要有一点方向,人要有一点调整。”
他俩的相近是诚实,诚实就是精神上的一贯性,不相信什么神迹和顿悟,对别人手拿把攥的东西,总要有一点疑问。
我们采访结束告别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吃饭,大家忍不住夸一下“老周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他比我们明眼人看得还清楚”。
周云蓬听了一会儿,朗诵了一句“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吧”。
众人哄笑而散。
(以下是《看见周云蓬》视频,老周书叫《绿皮火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