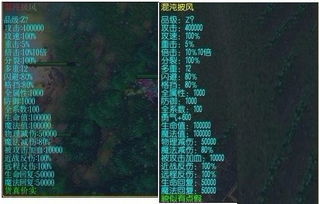“谁欠你地图……不要自说自话好吧?禳解的办法也不是没有,你不要往东边去就好了,你这命大利西方,在这里调头就是了。”项泓说。

“可月河湾在东边,我要去月河湾……”西越武说,“换个别的办法禳解一下?”
项泓想了想,点了点头,扭头就跑。
“喂!喂!你跑什么?我又不是老虎,我还一口吃了你啊?”西越武傻了一会儿,对着项泓的背影大喊。
“总之我不跟你走一路就可以驱邪避灾了。”项泓一边大声喊着一边跑进了白雾里。
“喂!喂!”西越武沉默了片刻,接着喊。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跟你一路走的了!”项泓的声音渐渐远去。
“项大兄,我其实是想跟你说,你去的不是西南……你在往北跑……”西越武低声说。
他站在一片茫茫白雾中,周围隐隐绰绰的是行商们收拾着各自的行囊,商队也即将开拔。西越武忽然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孤独,其实内心里他是很希望项泓,甚至姬云烈和他们一起走的。那两个家伙一个长得和兔儿相公似的、行为扯淡得很,另一个始终冷着一张脸看向无人处、好似世人都欠他了钱似的……不过不知为什么,西越武觉得跟他们有点亲近。
也许是因为陌路相逢吧?其实在这支商队里,他西越武何尝不是个外人?
“那个项公子总算走了么?”燕老师和龙搭桥并马而立,远远地看着西越武的背影。
“你不想他和我们一路?”龙搭桥问。
“我不喜欢和奇怪的人一路走。这么个世家公子一样的人来趟这片戈壁滩,是不是有点怪?”燕老师说。
“怎么?”龙搭桥挑了挑白眉。
“他画的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他的地图上不但包括了道路山川河流,还包括了河道的深浅、山峰的高度、甚至四季的风向,都用特殊的标记标明了。”燕老师幽幽地说,“这里虽然是片戈壁,可是距离帝都并不远,拿到他那份地图的人……”
龙搭桥沉默了很久,微微点头,“那是份行军地图,谁拿到,就能带着大队人马穿越戈壁去帝都。”
“掌柜的,我有句话说,”燕老师沉吟了片刻,“我们俩都是一把年纪了,也该收手了。这些年来,这条道上的钱掌柜的你赚得已经不少了,我们出来跑的人,不知道哪一次就把命跑没了,所以更要惜福。这一趟跑完,我想撤了,我在青石城外买了片小山,想种片果林做营生,我那个儿子聪明,我想他长大了混个一官半职,别被我拖累了。”
“我知道了,没问题,”龙搭桥低声说,“其实……去年那一遭后,我已经想洗手了。但这一次我不能不来。”
“怎么?”燕老师一愣。
“今年是多少年?”龙搭桥那双总是眼帘低垂的眼里忽然闪过一丝冷厉的光。
“德兴十年。”燕老师说。德兴是当今皇帝的年号。
“不,按照我们的纪年,今年是星流四千七百四十年,星流纪年的第四百七十五个十年的开始。”龙搭桥深深地吸了口气,“每隔十年,我们中都要有人去那座城,今年轮到我了。”
燕老师的瞳孔猛地放大,“掌柜的,今年你是轮转使?”
龙搭桥默默地点头,“谁是轮转使,在那一天才会揭开谜底,按理我什么都不该跟你说。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总之老伙计,麻烦你陪我跑这趟。最后一趟,这趟之后,我们就彻底离开。”
“掌柜的……”
龙搭桥笑着摆摆手,“其实轮转使虽然是个要命的活儿,可临着要洗手被选上当这个轮转使,我还是开心的。我已经老了,常常遗憾在我有生之年无所作为。好在我退出之前,终于能为大家做点事情!”
燕老师松开了紧握的刀柄的手,重重地拍在龙搭桥肩上。“掌柜的,我们出来跑的人,最忌讳说最后一趟,不过这最后一趟……我陪着你!”
龙搭桥没有来得及说话,燕老师已经策马前行,逆着扑面而来的雾气和风,高声吼,“开拔!”
戈壁滩的天,孩子的脸,接连几日都是能把皮肤晒爆的骄阳,居然一变天就下起了暴雨来。
“老天爷,我没看错吧?这戈壁滩上也能下那么大的雨?再下下去戈壁滩都得涝了!”西越武在头顶兜着一块油布挡雨,对着漆黑的天空抱怨,瓢泼而下的雨流像沾水的银色鞭子抽在他脸上。
他回头看去,大车头接尾,尾接头,用铁链扣死,连成一条长蛇,拉车的马在两侧牵引,力量合在一处,崎岖起伏又潮湿的砂石路面都不在话下,商人们披起蓑衣戴上斗笠,拉着备用的驮马躲在背风的一侧走,大车挡去了八九成的风雨。要不是这些特制的大车,在这么糟糕的天气里连夜赶路简直不可想象,西越武不得不佩服龙搭桥,确实是经验老道。
他们已经进入了唐兀山的地界,唐兀山是座连山,高虽然不高,但是绵延上百里,是这片戈壁里的天然屏障。淳国在山间最大的峡谷处筑城,起名唐兀关,号称“东陆第一雄关”,这座关隘的雄奇,在于它于荒漠中摩云而立,远看仿佛一座高塔,于荒漠中跋涉了数百里的旅人看见这座关陡然出现在地平线上,无不觉得自己是看见了海市蜃楼。此外,这座关也是扼守帝都的要害,北拒蛮族,除了天拓海峡的天堑之外,靠的就是这座关。
它与号称“东陆第二雄关”的殇阳关并称,唐兀关又称“帝都北锁”,殇阳关则是“帝都南锁”。
“到雨季了,这里每年就是雨、旱两季,雨季一个月,旱季十一个月,每年春天天拓海峡的暖气南下,在唐兀山转弯,就会下几场大暴雨。可这里都是沙地,留不住水,过了这个月,地面又干得冒烟儿了。”龙搭桥在旁边解说。
他也是在头顶张着一张油布,牵着马走路,却丝毫不显得狼狈,还有心情把烟锅好好地藏在雨水 淋不到的地方,滋滋地抽着。
“龙大掌柜,照这么走,我们可什么时候才能到月河湾啊?”西越武问。
“估摸着不远了,只是这雨下得太大,我有点辨不清方向。小兄弟你没去过月河湾吧?月河湾雨季的时候可是个好地方。”龙搭桥说。
“这戈壁滩里能有什么好地方?”西越武不信。
“有好看的女人!腰这么细!”燕老师双手一箍,“腿那么长!”燕老师又拉开双臂,有如怀中张开一张大弓。
“燕老师你逗我的吧?腰那么细……岂不是腰围只有一尺?腿那么长……比我们拉车的马腿还长了!这样的女人天下也会有?”西越武瞪大了眼睛,“要按你这么比,除非是一人高的蚊子!”
“年轻人没见过世面,不信就算了!”燕老师扭头对着赶车的商人们低声说,“传话下去,兄弟们加把劲儿!风大,过了这道峡谷再歇!”
“掌柜的,为什么非得过这片峡谷啊?”西越武抱怨,“出了峡谷就能找到遮风避雨的地儿?”
“小兄弟你是没有走路的经验,你看看两侧,这里的山是沙山,谷是沙谷,这些砂石在这里堆了也不知几千几万年了,按说根基很牢,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塌了。尤其是刮风天下雨天,砂石间容易滑动,一滑坡跟雪崩似的,我们这队人一个都活不下来。这种沙谷有个说法叫‘鬼咬舌’,说鬼过沙谷的时候都咬着舌头不敢出声,免得滑沙了。”龙搭桥叹了口气,“我的老大,那是个盖世英雄啊,骑一匹好马,那马叫‘追风骥’,说它跑得能追上风。可还是给滑沙埋了,滑沙下来的时候,我们远远看着老大骑马狂奔,可愣是没跑过流沙。唉!”
“那……那真滑沙了可怎么办?”西越武脸色“唰”地白了。
“就算是滑沙,等砂石滑下来把我们淹了,总片刻工夫。”燕老师凑过来说。
“这片刻工夫我们便当如何啊?燕老师您教我。”西越武满脸谄媚。要不是双手扯着油布挡雨,他非上去给燕老师捶两下背孝敬孝敬,这救命的本事,他是一定好好学的,行脚商西越家没有家训,要有也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十个字。
“给家里写封信,拿油纸裹了,揣在怀里。”燕老师认真地说。
“这……”
“滑沙淹了人,也就埋你几尺深,等到大风天风把砂石吹开了,你就露出来了,干瘪瘪硬挺挺的,用读书人的话说,面目还栩栩如生呐!要是遇到后来的好商客,把你怀里的家书带回去给你家里人,可不比被雪崩埋了开心?被雪崩埋了的都冻成冰坨子了,几千几万年都化不得冻嘞!”燕老师挤眉弄眼。
“呸呸呸呸!晦气!真看不出燕老师你这张木头开裂似的老脸上还能挤出那么多表情来!”西越武嘴里不软,脚下发软,踩着路面就觉得那砂石要往下陷。
龙搭桥扶了他一把,“叭叭”地抽着烟锅,“老伙计你逗孩子干什么?”又拍拍西越武的肩膀,“别听燕老师逗你玩,不是那样的。”
“掌柜的是好人,那掌柜的你教我?”西越武立刻转向龙搭桥,满脸表情仿佛跟亲爹撒娇。
“我们出来跑路的,早知道有风险不是?心安就好,真要死了也没办法。”龙搭桥慢悠悠地叹口气,“要是真的滑沙啦,就趁没被埋,抽口烟,跟老伙计们拍拍肩膀,说句要是真有来世再做兄弟,也就这样了。”
西越武脚下一软,不巧绊在一块石头上,平平地拍在砂石地上,摆出个“大”字形。
龙搭桥和燕老师相视而笑,这时旁边的车队慢了下来。
“怎么?”龙搭桥神色一变。
“听。”燕老师摆手。
风雨声里,有人奏琴,琴声在风雨声中若隐若现,像是有大群的野马正在雨中狂奔而来。
“果然该来的还是躲不过。”燕老师猫着腰,按住腰间刀柄,无声地奔行,越过几辆大车来到队伍的最前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