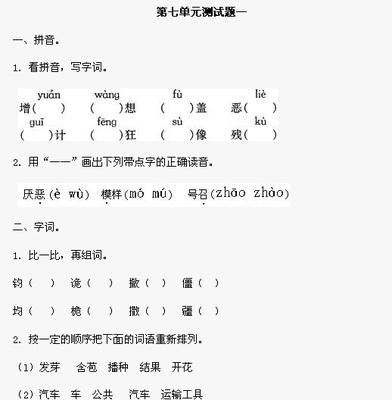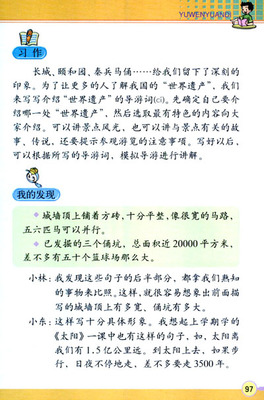【教学目标】
1.了解曹禺“诗化戏剧”的艺术特征。
2.认识戏剧人物性格的展示与戏剧主题思想的关系。
3.理解曹禺关于《北京人》是喜剧的说明,从而拓宽学生对于喜剧类型的认识。
教学设想
一、启发学生认识《北京人》的独特性。比如,与本教材所选的其他剧目相比,《北京人》的舞台指示对于物质环境的设计与描述是最详尽的。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对于戏剧行动发生的时间、地点的交代都非常简洁。到了易卜生、契诃夫的戏剧里,舞台指示对于环境的描写开始花较多的笔墨,但《北京人》的舞台指示不仅在篇幅上超过了它的戏剧先辈,而且对于音响效果的诗意营造,也是前无古人的。老师在指导学生诵读第三幕第一景愫方与曾瑞贞的那一大段精彩戏剧对白时,一定要提醒学生注意:这段戏一直是在一个特殊的音响背景下进行的──“由远远城墙上断续送来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在凄凉的空气中寂寞地荡漾”。从曹禺写出的富于情感色彩与诗意情调的舞台指示里,让同学们感受到曹禺的诗化戏剧的美质,同时也感受到《北京人》的独特戏剧风格。
二、曹禺的上演最多、也最为人知的剧作是《雷雨》,可以让同学把《北京人》与《雷雨》作一番比较。剧作者在《北京人》中已经不像在《雷雨》里那样刻意地追求戏剧场景的险峻与浓烈了;再联系曹禺在谈《北京人》时也暗示过的“契诃夫影响”,把《北京人》与契诃夫的《三姐妹》也作一番对照,理解为什么人们乐于把这两部剧作相提并论,而且认为曹禺的借鉴是创造性的借鉴,诚如曹禺自己所说:“不是照搬模仿,而是融入,结合。在这种融入结合之中,化出中国自己的风格,化出作家自己的风格,总之,是引出新的创造来。”
三、《北京人》的独特性还表现在愫方这一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上。研究者们都认为愫方是曹禺笔下最美的一个女性形象。然而,这个人物也有其明显的“弱点”──她性格上有逆来顺受的软弱性,不过曹禺把这种“软弱性”又表现为人性的至善。今天的人们会如何看待愫方的这种分明经受过封建家庭束缚的性格呢?这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又如,该如何评价愫方在第三幕第一景里对曾瑞贞的那段由衷的倾诉:“他(即曾文清)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但终归要让学生们相信:愫方最后的毅然与瑞贞一起出走是可信的,愫方这个近于理想主义的女性形象是可信、可亲、可敬的。
赏析举隅
一、《北京人》的喜剧底蕴
在戏剧评论界,曾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以为《北京人》是一出“凭吊往昔”的悲剧。曹禺却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他写的是一出礼赞青春的喜剧。他说:
“有人曾说《北京人》是作者唱出的一首低回婉转的挽歌,是缠绵悱恻的悲剧,是对封建社会唱的一首天鹅之歌。这些说法我都不同意。我觉得《北京人》是一个喜剧……我觉得喜剧是多种多样的……我说《北京人》是喜剧,因为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这难道不是喜剧吗?”
曹禺认为喜剧有多种样式。有莫里哀的喜剧样式,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样式。曹禺把《北京人》的喜剧性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喜剧性相提并论,他说:“我觉得《北京人》是一个喜剧,正如我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喜剧一样,《罗》剧中不少人死了,但却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所以是喜剧。”
因此,要理解《北京人》的喜剧性,主要并不是着眼于剧中的像江泰这样的曾有喜剧性性格特征的人物,而是应该着眼于全剧的“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的精神升华。
我们要认清貌似悲剧的喜剧底蕴。比如瑞贞与曾霆的协议离婚,表面看来是让人感伤的事件(曾霆毕竟也是个品性不错的男孩儿呀),但仔细一想,他们的离异给他们都带来了重新生活的可能。再如,曾文清的死,乍一看来也是件悲伤事,但实际上这正是曹禺所说的“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的喜剧性底蕴,因此曾文清的死也不啻是一个“人间喜剧”。
尽管《北京人》的调子有些忧郁,但曹禺说这种忧郁的调子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感觉”,并不影响整个剧本蕴含的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
曹禺对于《北京人》是个喜剧这一观点的坚持,有助于我们找准对这个剧本思想意蕴作整体把握的角度。与其说《北京人》是对旧的、沉沦中的昨日的“北京人”的一曲挽歌,毋宁说是对于新的、成长中的明日的“北京人”的一首赞歌。剧本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但更反衬出了勇敢地从这个封建泥潭中挣脱出来的新的青春生命的光焰。因此,《北京人》里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是淡淡的欣喜,是深蕴的乐观主义。
二、《北京人》中的新人形象
《北京人》的乐观主义的高潮是瑞贞与愫方的最终离家出走,这对应着全剧的最后一句舞台指示──“远远传来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她们乘火车上哪儿去了呢?曹禺后来说:“我清楚地懂得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没有点明。”这就是《北京人》中的新人的形象高度。
瑞贞是最早觉悟的。她受的是新式教育,容易接近革命思潮。在戏开幕之后,她已经下定了走出这个封建家庭的决心。她的戏剧行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劝说愫方与她一起出走。
愫方是曹禺笔下最美的一位女性形象,在这个形象里注入了他的极大的精力与情感(曹禺承认在愫方的形象里有他妻子方瑞的影子)。曹禺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愫方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恍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幽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着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与哀怨。……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仅仅用“善良”二字来形容愫方的好心肠还不够,至少要在“善良”前面加个“太”字。她太善良了,以至于会这样真情投入地去爱那个不成器的曾文清,会那样逆来顺受地去照拂那个虚伪而暴戾的曾皓,这些我们不一定能认同的愫方的行为,却又是她那真诚忘我与以德报怨的美德的一个反映,她的似乎是有局限性的地方反倒显示她的博大。因此,《北京人》一剧导演蔡骧当年在对愫方作形象分析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你不能不承认,即使你不同意她的生活态度,却不能不赞扬她的善良品质。”而曹禺说得更明确:“人都说愫方傻,她怎么能爱上文清这个‘废物’?她不是傻,是她心地晶莹如玉,是她忘记了自己。”
然而,美丽善良的心灵是最容易接近真理的阳光的。愫方终于也觉醒了,而愫方的觉醒,使这样生长在黑暗山谷中的幽兰吐露出沁人心肺的芳香。
三、关于诗化戏剧
如果把《北京人》与《雷雨》《日出》等剧相比较,评论者们都会指出,《北京人》有更高的文学性。
曹禺在谈论《北京人》的时候,说了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我的理解是曹禺在这里说到了戏剧的诗化的可能。
《北京人》第一幕里北京猿人黑影的出现就是一个曹禺自己提及的实例 :
“曹禺同志谈到古人论诗,说诗有‘赋、比、兴’。就《北京人》里猿人的黑影出现的情节论,这种安排就好比是起了诗中的‘兴’的作用。”
《北京人》中有不少具体的、具象的东西是可以为抽象提供可能的,从剧本开头的“鸽哨声”到剧本结尾的“火车汽笛声”,这里蕴含着接近于诗的象征意味。
而《北京人》中最令人难忘的音响效果当是第三幕第一景的“号声”。请看曹禺是如何在舞台指示里对它形容的:“在苍茫的尘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这来自遥远,孤独的角声,打在人的心坎上说不出的熨帖而又凄凉,像一个多情的幽灵独自追念着那不可唤回的渺若烟云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伤,那样充满了怨望和依恋,在薄塞的空气中不住地振抖。”
就是在这“像一个多情的幽灵”般的“号声”的声响背景下,曾瑞贞和愫方进行了心贴心的交谈──
愫方……(忽然扬头,望着外面)你听,这远远吹的是什么?
曾瑞贞(看出她不肯再谈下去)城墙边上吹的号。
……
愫方(眼里涌出了泪光)是啊,听着是凄凉啊!(猛然热烈地抓着瑞贞的手,低声)可瑞贞,我现在突然觉得真快乐呀!(抚摸自己的胸)这心好暖哪!真好像春天来了一样。(兴奋地)活着不就是这个调子吗?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感动地流下泪)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
这一场戏是《北京人》里的华彩乐章。和《雷雨》不同,《北京人》里最动人的戏剧场景,不是剑拔弩张的激烈冲突性场景,而是表现经过心灵碰撞之后心灵得到进一步升华的抒情性场景。
而决定着《北京人》的诗情基调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曹禺塑造的愫方这个永远向往着美的女性形象。所以蔡骧导演有理由说:“如果《北京人》是诗,那么这首诗的灵魂是愫方。”
《北京人》是一出有点儿“契诃夫味道”的戏。契诃夫戏剧给予曹禺的启发是,戏不必写得那样“张牙舞爪”,戏可以在平易中见深邃;戏不必写得那么“像戏”,戏可以散文化。而曹禺的《北京人》,在做戏剧“散文化”的尝试中,达到了诗的境界。
探究与实践参考答案
一、曹禺是怎样刻画“北京人”形象的?剧作者为什么要把几十万年前的“要爱就爱,要恨就恨”的“北京人”与像曾文清那样怯弱、无能的“北京人”对立起来?曹禺心目中的新的“北京人”是谁?
曹禺在《北京人》第二幕中,通过人类学家袁任敢的一段台词,刻画了“北京人”的形象:“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曹禺用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形象与曾文清那样的现代“北京人”对立起来,是要强调一个题旨:再也不能像曾文清似地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了!于是曹禺在剧中着力塑造了两个新的“北京人”──愫方和曾瑞贞──的形象,把全剧结尾在她们奔向光明的离家出走上。
二、对《北京人》的舞台指示中的音响效果作一番梳理,探寻一下它们的含义,比如,指出哪一些是属于生活气氛的烘托,哪一些是属于诗意的象征,哪一些是人物精神状态的外化等等。
第二幕开头那段舞台指示里“漫长的叫卖声”当属生活气氛的烘托,曾霆诵读“秋声赋”的声音和深巷传来的“木梆打更的声音”颇具诗意,而“水在壶里呻吟,像里面羁困着一个小人儿在哀哭”,便分明是人物精神状态的外化了。但《北京人》里最有名的一个音响效果出现在第三幕第一景里──“室内一切渐渐隐入在昏暗的暮色里,乌鸦在窗外屋檐上叫两声又飞走了。在瑞贞说话的当儿,由远远城墙上断续送来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在凄凉的空气中寂寞地荡漾,一直到闭幕”,这个一直延伸到闭幕的号声,既是生活气氛的烘托,又是人物精神状态的外化,而且不失为一种诗意的象征。

三、《北京人》公认是曹禺一出颇有点契诃夫戏剧味道的戏。试着对照契诃夫《三姐妹》第四幕和曹禺《北京人》第三幕的相关段落,体会曹禺所追求的“寓深邃于平淡之中”的诗化戏剧的妙处。
曹禺在契诃夫的《三姐妹》里,体悟到了“秋天的忧郁”。《北京人》里的时令也在秋天,其中也有“秋天的忧郁”。特别是从第三幕“由远远城墙上断续送来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的舞台指示开始,到愫方与曾瑞贞的最后出走,剧情的悲喜剧因素的交织,达到了诗意盎然的程度。──就如愫方说的:“听着是凄凉啊!可瑞贞,我现在突然觉得真快乐呀!……活着不就是这个调子吗?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愫方对于曾文清的幻灭(所谓“天塌了”),从绝望中生发出新的希望。戏里没有什么特别张扬的情绪表达,但读者与观众分别感受到了剧中人物的精神升华。
四、有戏剧表演兴趣的同学可以在《北京人》里选一些可供诵读的台词,有感情地进行朗读。比如,男同学不妨带感情地诵读一下人类学家袁任敢的那一段关于“要爱就爱,要恨就恨”的“北京人”的台词;女同学则可以尝试着两人一组诵读第三幕中愫方和瑞贞的那段在“号声”伴奏下的抒情对白。
学生可自主进行。
参考资料
一、曹禺谈《北京人》
创作总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但是,它又不是简单地按照现实那个样子去写。创作也是复杂的,这其中有着许多似乎说不清楚的因素在起作用。当你写作的时候,真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那些生活的印象,人物、场景、细节等等都汇入你的脑海之中,在化合,在融铸,在变化,是在创造新的形象、新的场景、新的意境。
我写《北京人》时,记忆不仅把我带到我的青年时代,而且带回到我的孩提时代。那是非常奇怪的,不知怎么回事,那些童年的记忆就闯入我的构思之中。譬如第三幕,愫方和瑞贞谈着知心话,在瑞贞说话的时候由远远城墙上断续传来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在凄凉的空气中寂寞地荡漾,一直到闭幕。我为什么这么写,这个印象是有生活根据的。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到宣化任镇守使。我一个人非常寂寞,就常常走到城墙上坐着,经常听到那种单调的却又是非常凄凉的号声。偌大的宣化城,我一个小孩子,知道自己没有了亲生的母亲,心情是十分悲凉的。听到那号声似乎是在呜咽,在哭泣。号声引起的是伤痛,是心灵的寂寞和孤独。我写这一幕时,这种生活的印象和感受便进入形象思维之中,化入这场戏的意境和氛围之中。它当然和我童年的生活有联系,但又不是我那时生活印象和感受的简单重现。
人们总爱问我,你剧中的人物是写的某某人吧?碰到这种发问,我总是不以为然。我常说,我十分熟悉我剧中的人物,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写的就是生活中熟悉的某个人。《北京人》中的曾皓这个人物,就有我父亲的影子,但曾皓毕竟不是我父亲的再现。我对我的父亲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我爱他,也恨他,又怜悯他。他是很疼爱我的,他盼着我出国留学。那时,家境逐渐欠佳,他就对我说:“为了你留学,我再出去奔一奔,赚点钱!”曾皓的台词也有类似的话,就是从我父亲那里借来的。还有,曾皓发现文清还偷着抽大烟,于是便跪在文清面前,求他不要再抽了。这个细节也取自我的父亲。我父亲这个人总是望子成龙,他看我的大哥不争气,便恨他。我大哥也抽鸦片烟。有一次,我父亲对我说,“你哥哥又抽大烟了,我就给他跪下,求他!”像这些,我就说曾皓有我父亲的影子。但是,我的家和曾家不大一样,我的父亲也和曾皓不一样。曾家这个封建官宦的世家,曾经是炫耀几代、气象轩豁的望族,而如今却是家道衰微,内里蛀空,徒有其表了。这个家庭,我是有生活依据的。我认识这样一个家庭,它的老主人就颇有曾皓的遗老之风,原先在北平也是颇有名气的官宦人家,现在败下来了,手中还有点钱,便还摆着阔绰的架势,每天去中山公园吃茶聊天。他家少爷、姑娘不少,外表看上去,都是知书明礼的,一到夜晚,少爷们就把家里的东西偷出去卖。曾家的往宅,小花厅的格局,诸如装饰摆设,都和我认识的这一家有点关联,但是,又不全是这一家的。《北京人》中的北平的秋天景象和生活习俗,我是根据剧情费了些思索的。像白鸽的哨响,还有奶妈送给文清的鸽子,北京胡同里的水车的“吱妞妞”的声音,剃头师傅打着“唤头”的声响,我有的用来作为渲染刻画典型环境,有的就融入人物的创造。
至于思懿、愫方、文彩、瑞贞这些妇女形象,我记得曾经同你谈过,我很熟悉她们。特别是像愫方这样秉性高洁的女性,她们不仅引起我的同情,而且使我打内心里尊敬她们。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界太美了。说到这里,还可以插入一段故事。大概是1957年,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演《北京人》,周总理去看戏了。散场后,他请剧团把第三场“天塌了”那场戏重演一遍。总理看完后就问导演说,台词中“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句,是不是新给愫方加的?导演说,原来的本子上就有。总理说,那就好。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我就是这样理解愫方这些妇女的,我没有夸张。人都说愫方傻,她怎么能爱上文清这个“废物”?她不是傻,是她心地晶莹如玉,是她忘记了自己。只有“天塌了”,她才能改变她的看法。她跟着瑞贞走了,毅然决然地走了,的确是“天塌了”。她总是向往着美好的未来的,离开这个家,也说明她对美好的前途的憧憬和追求。思懿这个人是招人恨的;她的性格虽然奸险,她也有她的难处。她为人惹人嫌恶,但这个“家”是她支撑着。
生活的感受终于化为舞台形象,或者写到剧本里,是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过滤、透视,经过蒸腾,或是说是发酵才能实现的。这里,既有思想的,也有感情的、心理的因素。在《北京人》中,我不只一次提到耗子。我为什么会写耗子?曾皓老是把儿孙比作耗子:“活着要儿孙干什么哟,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干什么哟!”我在北方生活,也看到过耗子,印象不深。抗战期间到了四川江安,江安的耗子好大哟,耗子成了灾。我准备写历史剧《三人行》,把搜集来的资料放到抽屉里,想不到资料与一部分稿子被耗子啃啮成了碎片,那是费了不少心思得来的。有一次,耗子竟然钻到我的棉袍子里,吓了我一跳。因之,我就对耗子格外憎恶。吴祖光同志为此曾写过一篇《鼠祟》,他说的是实情。但是,一旦我把耗子写入《北京人》里,就不是我那时对耗子的憎恶所能概括的了,可以说,是那时对耗子的认识,对耗子的厌恶的一种延伸、升华。它含蓄着更多的东西,但又不是直接说出来的。你说耗子是象征什么隐喻什么,说什么都可以,那就任凭群众去联想了,也任凭评论家去分析了。我写的时候,倒没有想得那么多。
我总觉得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在这个戏里,瑞贞觉悟了,愫方也觉醒了,我清楚地懂得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没有点明。她们由袁任敢带到了天津,检查很严,又是在日本占领的地区。这样写,不但要写到日本侵略军,当然把抗战也要连上了。这么一个写法,戏就走了“神”,古老的感觉出不来,非抽掉不可。这个戏的时代背景是抗战时期,但不能那样写,一写出那些具体的东西,这个戏的味道就不同了。这点,我和有些人的主张是不大一样的。现实主义当然要写时代,但不一定把那个时代的事都写进去。写对时代的感觉,我很佩服我的师辈茅盾先生,时代感写得很准确,政治是个什么情况,经济是个什么情况,都写进去了。这个戏是在四川江安写的,写的是北平。要明写,袁任敢带瑞贞走,他是有路子的,他自己可能就是共产党人,或者是靠近党的人士,他装傻就是了。甚至连江泰也知道瑞贞是接近共产党或进步人士的。我不能这样写,我也不愿意这样写,更不能把这些都写个透底。如果这样,我就觉得这样的戏失去了神韵。说得明白些,戏就变了味,就丝毫没有个捉摸劲儿,也就没有“戏”了。说到底,我的体会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路子,并不是说都按现实的样子去画去抄。我还是那句话,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
《北京人》里的瑞贞去的是延安,我没有指明。但在我的剧本前面,我引了唐朝诗人王勃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隐喻共产党的朋友们的。那时,我已经见过周恩来同志了,他不单是作为一个长我一辈的南开学长,更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来关心一个年青作者的。从政治上指点着前进的方向,生活上也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国立剧专也有党的支部,当然是不公开的。我知道谁是共产党员,我不说,我心中明白。我的学生方琯德、梅朵等都是党员,他们每天都到我家里来。从他们身上我受到启示和鼓舞,他们同我讨论着我的作品,那么坦诚那么友爱。我总是怀念江安那些十分清苦但却充满令人温暖的师生情谊的生活。我家的房东,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是共产党人,都是我家里的常客。我就生活在这些共产党人身边。可以说,写《北京人》是党影响着我。
我曾说过,我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受过契诃夫的影响。《日出》还不能说有契诃夫的影响,《北京人》是否有点味道呢?不敢说。但我还是我。契诃夫那种寓深邃于平淡之中的戏剧艺术,确曾使我叹服。像他的《三姐妹》,每次读了都使我感动。在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我看过演出,更迷恋着他的艺术。但是,只能说是受点影响。我以为学某某艺术家,学是学不像的。契诃夫的戏剧,中国是演不出来的,就是演得出,也没有很多人看,学外国人的好的东西,是不知不觉的,是经过消化的。不是照搬模仿,而是融入,结合。在这种融入结合之中,化出中国自己的风格,化出作家自己的风格,总之,是引出新的创造来。我说《北京人》受点影响,但我还是那句老话,我写作时,也没想到我是在学习那位大师。
(选自《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二、《北京人》导演杂记(蔡骧)
一“诗”与“戏”
我极爱《北京人》,认定这出戏是剧作家曹禺最成熟的作品。1941年夏,当我终于得到排演机会,兴致勃勃地去向曹禺师请求同意时,他却劝我放弃这个打算。他说《北京人》是出“关门戏”。
《北京人》是出“关门戏”?!──我觉得不太有把握了。但我仍然坚持要排,老师扭不过我,只好同意。此后几天我不断思索如何避免这种可怕的后果,不由得想起多年前曹禺师的一席话。
1943年冬天,某个夜晚,在重庆。我从剧场后台陪曹禺师回家。当时我正热心于契诃夫,写了个带“契诃夫味儿”的剧本,话题便落在“契诃夫风格”上,曹禺师给我浇了点冷水,劝我“不要学契诃夫”。他说中国人看戏的习惯是“有头有尾”,他认为莎士比亚比契诃夫更易于被中国观众接受。当时我脑子正发热,那肯放弃我的爱好!15年后,面对《北京人》演出的成败,我不能不考虑一下中国观众的“习惯”了。“《北京人》有点契诃夫味儿”,这是我的看法。这出戏通篇笼罩在诗一样的意境中,剧本第一页对曾家花厅所做的那番描述,就是一幅意境深远的油画。戏未开始,那发自蓝天白云中的冷冷鸽哨声,已把读者带入20世纪30年代初的“北平曾家”。以后的戏更像抒情诗一样,沁人心脾。这气息,我在契诃夫的剧本中是闻到过的。
但是,仔细思索,《北京人》和《樱桃园》究竟不同。别的不说,那味道的浓淡便大有区别。我重读了《雷雨》和《日出》,回忆起那些令人窒息的戏剧场面,繁漪吃药、四凤发誓、周萍与四凤会面、周朴园令周萍认生母以及黄省三哀告、小东西自缢、李石清与潘月亭生死搏斗、陈白露自杀等。再读《北京人》,觉得其中也不乏如此浓烈的场面。如瑞贞哭诉、愫方说嫁、文清与愫方夜会、曾皓中风、愫方信念的破灭与出走、文清服毒等等。看来,《北京人》的味道不淡,只不过它的表达方式比较含蓄。尖锐的矛盾冲突“埋藏”在不那么尖锐的日常生活中,再加上封建礼教掩盖了人物的真情实感,给表现带来了困难。
曹禺是戏剧大师。他的戏剧风格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即:交织谨严的生活逻辑,轮廓清晰的人物形象,紧张尖锐的戏剧冲突和真实生动、耐人寻味的台词。抒情也是曹禺风格的一部分。《雷雨》《日出》《家》都有许多抒情的场面,《北京人》则是作者的最高成就,整出戏像诗!“诗”“戏”交融、浑然一体。《北京人》是“诗”又是“戏”。在我写导演计划以前,有点偏向于“诗”,很想把它这种“诗味儿”排出来。后来,我在《导演计划》中这样提醒自己:
……不应该因为《北京人》一剧有新的特点,就放弃或忽视作者固有的风格。从第一幕起,就应该让它在正确的节奏上进行。作者在开幕时已拉满了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即没有把每个角色的内心处在拉满弓的状态),那么必将失去这出戏的内在力量。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忽略它的诗一样的调子。要在那些压得人透不过气的矛盾冲突中,突出作者有意安排的微笑的场面、大笑的场面、欢快的场面、充满幽默与讽刺的场面、以及沁人肺腑的抒情场面……使全剧在节奏上有多种变化。
这些想法对于后来的排演,确实起了作用。我时常警惕自己,不要偏向这边或那边。
二 诗魂──愫方
愫方是个复杂的艺术典型,是在封建束缚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式的善良妇女的化身。她温柔、纯洁、真诚、富于同情心,多才多艺、情操高尚、吃苦、耐劳、勇敢、肯于自我牺牲,优美。读完剧本,掩卷抒怀,这些潜台词便源源而出。也许可以这样说:愫方是曹禺历来创造的最成功、最优美的典型。没有愫方,《北京人》将失去光彩。如果说《北京人》是诗,那么这首诗的灵魂是愫方。
愫方在《北京人》中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作者在理性上,在《北京人》中提出并暗示了一组“新人”形象,其中包括反抗性很强的瑞贞,无拘无束的袁圆,脚踏实地的袁任敢,还有并未出场的瑞贞的同学们以及吸引瑞贞投奔光明的革命者。但从感情上说,作者捧出的理想人物是愫方。愫方在生活中的态度很难为现代中国人所苟同。她知恩报恩、守本分、不强取、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她还“以德报怨”“逆来顺受”。后来更在这种自我道德完成中悟出了要“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的人生哲学。所有这些,你都难以加以肯定或否定。你不能不承认,即使你不同意他的生活态度,却不能不赞扬她的善良品质。作者在第三幕第一景的戏中,含泪把愫方推到理想的峰巅,然后在“天塌了”的情节中使她的幻想破灭。她“出走”了。很显然,“破灭”了的是愫方对封建制度的错误认识,被否定的是愫方性格中的消极因素,而不是“理想”本身。愫方是带着她业已升华了的形象出走的!作者有意让瑞贞做愫方形象的补充。她拉了她一把,一道出走,上了火车。
《北京人》演出后,周总理风趣地说:“愫方到解放区是个很好的保育员。”(我们听到这句话都笑了)作者知道后补充说:“她可能穿上了军装。”是的,我要说的正是这句话。愫方在革命队伍中,不论干什么,都将发出热和光。她的情操与品质和革命的要求一致。她是金子!
我喜爱愫方的品质,把她说成是《北京人》的灵魂,不知道是不是“过”了?不过我不想回避这个问题,导演《北京人》时,我的目标之一,就是尽力把愫方的“美”显示出来。我相信这样做是对的:观众确实都爱愫方。
(选自《〈北京人〉导演计划》,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
三、《北京人》的演出(冯亦代)
曹禺先生写的剧本中,我最喜欢《北京人》。不仅由于剧本中的诗的语言和诗的情调,而且由于剧作者的写作技巧在这个剧本里已经到达圆熟的峰巅;但主要吸引我的,却是剧作者透过剧情,对于生活所表达的强烈鲜明的爱憎。在曾家那间曾经煊赫一时、如今已显灰颓的小花厅里,生活被幽囚着。一代人追忆昔日繁华,眼前只能等候死日的来临;另一代人痛心于少年时的错着,无可奈何地缅想那逝去的岁月和残破的梦境;再一代人则不甘心于死气沉沉的禁锢生活,抱着冲向新天地去的企望。可是生活的羁绊,却使这些可怜虫群集在这间小花厅里。难道人们就不想迈出一步去呼吸一下清新空气,享一下人间幸福?不过冲出这一生活的重重障碍却需要无畏的勇气,要明白这一点,却也不是件易事,正如曾霆所说的“这明白是多难哪”!剧作者真替他们感到气愤,他借学者袁任敢的话,对于这孱弱的一代人,痛加谴责。袁任敢告诉大家“北京人”曾经如何生活,他说:“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对比之下,像小耗子样生活着的人真该愧对祖先!但是剧作者却没有就此失望。让卑怯者烂在土里,霉在屋里,让勇敢者跑出这囚笼似的小花厅走向宽广的生活去。他对生活的信心也感染了我们,因此对曾皓、思懿、江泰、文彩之辈我们无所顾惜,而对文清、愫方、瑞贞、曾霆却寄以无限的同情。……
从演出里,我们看到了导演对于原作的潜心体会之处。在舞台上,他抓住了气氛的要求,加以适度的渲染。一面是陈腐衰亡所列下的严阵──垂死的挣扎,在无望中寻求希望;一面则是新的一代和新的生活对这座封建堡垒的进攻。他强调了老一代旧生活的执着的固守,也就显出了新的力量更为勇猛,更为犷野。
(选自195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四、登上峰巅(田本相)
一部杰作的诞生,决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更不是对现实进行即兴速写的结果。譬如地震的爆发,是漫长的地壳运动中产生着强大的地应力,而这种强大地应力的长期集中又造成巨大弹性应变能,在岩石中积聚着、蕴蓄着,直到岩石再也不能支撑自己,便爆发了地震。创作也是这样,也要经历这样一个积聚、贮蓄的过程。愈是优秀的作品,愈是经过长年的积累、观察、思考和孕育,《北京人》就是这样。
关于《北京人》的素材来源,曾有过种种猜测。曹禺就此也陆陆续续地回答过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
我写《北京人》主要取自我的老同学孙毓棠的外祖父徐家。1930年暑假,我和孙毓棠一起参加清华大学的考试,就住在他的外祖父家里。毓棠的外祖父也可以说是清朝的遗老,那时他做着中山公园的董事。每天,他都去中山公园喝茶、聊天,过着清闲的生活。徐家的少爷、小姐不少,但是,家都破败了,夜晚,经常有人把家里的东西偷出去卖。虽然,已经失去了徐家祖辈的荣华富贵和家运旺盛的繁荣,但是徐家的陈设,仍然是十分讲究的,处处都是古色古香,即使房屋的构造、格局,都能看出昔日的威严,栋梁上也留着过去金碧辉煌的痕迹,就像我在《北京人》中所写的。当然,也不都是取自徐家,像曾皓,就有我父亲的影子。曹禺同笔者谈话记录,1982年5月26日。
《北京人》的写作,也可以说是“杂取种种人”。不过,他一向最醉心的还是写出人物性格,特别是写出人物的灵魂。《北京人》就是要写“活人”,“有灵魂的活人”,能“抓牢”读者观众灵魂的活人。他是这样说的:
你问我《北京人》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是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的,甚至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时有一种想法,还是要写人。一切戏剧都离不开写人物,而我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心理、人的内心隐秘、内心世界的细微的感情写出来。这个戏中的人物,大都在生活中有着他们的原型,或者说影子吧。我说曾皓就有我父亲的影子,也有别的人的。我曾看到一位教授,他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剥夺别人的感情,这件事曾经使我感触很深。我就是由他的灵魂,引起联想,开掘了曾皓的卑鄙的灵魂,把他内心深处的卑鄙自私挖出来。这个教授并没有多少故事,也没有什么惊险热闹的东西。那时,我还碰到一个女孩子,年龄稍大些了,没有出嫁,住在姨夫家里。当然,这个姑娘不像愫方那样,但有些相似吧!就这样把曾皓和愫方连在一起了。
我曾对你说过徐家,那的确是一个大家庭,他家的宅院是一个套院连着一个套院,真是深宅大院。但的确败落了,不知怎么就又和耗子连起来了。这个家就是被耗子咬空了。徐家的少爷、小姐赌博,抽鸦片烟,把家中的东西、古董玩物拿出去变卖,这些少爷就有曾文清的影子,他懒得要死,成天无所事事。守着家,吃、偷、拿、玩,是废物,典型的废物,真像耗子。但是,这些少爷,没有曾文清那样的文雅。对这些人之所以印象深刻,这同我的大哥也多少有些关系,曾文清身上也有我那位大哥的影子。我那位大哥,是学法律的,抽鸦片烟,一辈子什么事也没做成。大概我的父亲也是恨铁不成钢,有一次,父子冲突起来,父亲把大哥的腿踢断了。结果,大哥出走了,从天津跑到东北哈尔滨,过了一冬天,又回到天津来了。他大概也是混不出什么名堂又回来的。但是他又不敢回家。后来,还是母亲把他找回家里。大哥依然故我,恶习未改,他有一次抽鸦片烟又被父亲看到了,父亲就跪倒在他面前说:“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父亲,我求你再也别抽了!”这些,我都写进去了。曹禺同笔者谈话记录,1982年5月28日。
还有一次曹禺带着很深沉的感情,谈到愫方的塑造:
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为什么起名叫愫方,“愫”是她取了她母亲的名字“方素悌”中的“愫”,方,是她母亲的姓,她母亲是方苞的后代。方瑞也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家庭里,她是安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先生的重孙女,能写一手好字,能画山水画,这都和她的家教有关。她是很文静的,这点已融入愫方的性格之中。她不像愫方那样的具有一种坚强的耐性,也没有愫方那么痛苦。但方瑞的个性,是我写愫方的依据,我是把我对她的感情、思恋都写进了愫方的形象里,我是想着方瑞而写愫方的。我把她放到曾家那样一个环境来写,这样,愫方就既像方瑞又不像方瑞了。方瑞的家庭和愫方的家庭不完全相同,她的妹妹邓宛生和她性格不一样,是很开朗的活泼的,当时是一个很进步的学生。袁圆的性格也有她妹妹的影子。没有方瑞,是写不出来愫方的。曹禺同笔者谈话记录,1982年5月24日。
曹禺的剧作,有他独到的艺术经验。但是,倾心于人物,也可以说是历来剧作家所关心的。特别是杰出的剧作家大都由于写了名垂千古的人物而留传后世。但是,这样的成功秘诀,并不见得都能为人得到,有人知道却不去做或者不能做到,这就是差别和距离。在中国的剧作家中,肯于为此而呕心沥血的剧作家并不多见。在生活中,他留心的是人,引起爱憎的也是人。他不是冷静地客观地去写人,他的爱憎,他的痛苦和苦闷都揉进他的人物里。他对方瑞的爱,写成他的愫方,但是,愫方中也有他自己的时代的苦痛。愫方的孤独,也凝聚着他的孤独感,那从小就有的孤独感。他说:
《北京人》中的号声,是我在宣化生活中得来的,那时天天听到号声。每听到这种号声,说是产生一种悲凉感,不是;感伤,也不是;是一种孤独感。我童年常有这种孤独感,这种印象是太深太深了,就写进愫方的感受之中,写到戏的情境之中。曹禺同笔者谈话记录,1983年9月14日。
不知是谁说的,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有着他自己,他写的每个人物,写的是别人,也是写着他自己,曹禺也是这样。他谈到江泰时说:
江泰是根据我在抗战时在四川的一个小城里,遇到的一个法国留学生作为原型而写出来的。这个法国留学生和他爱人住在他老丈人家里,是一个乐天派。每次见到我,都是东拉西扯,谈得兴高采烈,不像江泰那样满腹牢骚。我父亲还认识一个法国留学生,是研究科学的。在那个时代,搞科学的人是很不得志的,他不会做官,很失意,常常和我父亲在一起穷聊。江泰这个人物就是取材于这些生活中的人物,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的某些幻想。
思懿这个人物在生活中也有原型,这种人我见得很多。印象最深的是某个学校的校长夫人,嘴很刻薄,但不是那么凶残。剧中其他人物如瑞贞和曾霆也是我在生活中见到的人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哥哥三十六七岁,就有一对十七八岁的儿子和儿媳,他们叫我叔叔,这对小夫妻缺乏爱情,儿媳经常回娘家去,后来,我听说一个自杀了,一个病死了。我没有把瑞贞和曾霆写成这样,因为我不忍心这样写他们,那样写就太残忍了。我写瑞贞,让她从那个大家庭挣扎出来。曹禺同笔者谈话记录,1983年9月14日。
他说,他的人物都有原型,并不等于他全然按照这些原型去写。他很讲究人物的孕育,讲究人物的创造。
(选自《曹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