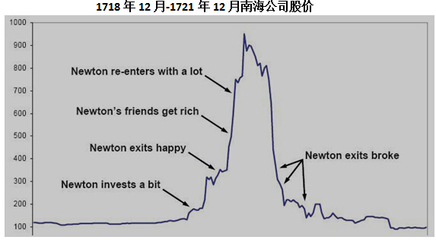博主按:说起来,笔者还是在八九岁的时候蹲在全家所下放农村的湖南省会同县长寨公社半界田间地头牧鹅时看完大哥不知从什么地方借来的红色经典小说《朝阳花》、《苦菜花》的;而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朝阳花》的作者之一(或曰直接关系人)谭士珍老师竟十分凑巧地又成为我的直接领导。必须说,在经历了太多的人生苦痛与不堪之后,谭士珍老师对下属、对我们年轻人、对文学新人是仁慈的,是充满包容心的;或许就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来东莞后还曾数次热情地接待过他和他的夫人沈姨……如今,谭老已年近八旬,但特殊历史背景导致的这宗文坛悬案却仍不能让他的暮年生活得到清净。究竟谁才是长篇小说《朝阳花》的真正作者?到底孰是孰非?无情的岁月都屏蔽了哪些事实的真相?
我只是一名无关紧要的旁观者。但我们有义务为历史存疑。尽管,作者的文章也许并不能代表本博主的观点——自然,这也是在转帖前需要特别说明的。
(转帖)文坛悬案:究竟谁才是长篇小说《朝阳花》的真正作者?!
谭士珍
(一)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幸事,也有各种各样的憾事,对我而言,最大的憾事,便是与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朝阳花》所发生的纠葛。
长篇小说《朝阳花》于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距今已有半个世纪。由该书引发的版权官司,到现在也有21个年头了。可以说,《朝阳花》版权案,乃当今中国文坛一大冤案,作为深谙其前因后果的当事人之一,21年来,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如今政治清明,法治建设长足进步,我个人也已两鬓苍苍,余年不多矣,是到了我应该把这桩由特权导致的中国当代文坛最大冤案的前前后后,向世人作一交代的时候了。这一方面是给自己的一种解脱,一方面也是一个作家不泯的良知使然,对时代,对社会的一种尽责。因为这,我顶住压力,愿意耗费晚年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在赶写出这篇短文后,另打算出版一本更为详尽揭示本案的书,力求正本清原,还历史以清白,还事实以本来面貌,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谐发展。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狄德罗说得何其好:“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我有理由相信,历史、时间、公道、人心总有一天会对《朝阳花》版权案的是与非,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公正判决。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朝阳花》,反映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二方面军医务人员生活的长篇小说,书中塑造了红军女护士、医生、医院院长、政委及医院的炊事人员、警卫人员等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形象。“文革”前曾先后出版134万册,打倒“四人帮”以后又重新出版4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日本翻译出版,在六十年代的我国,与著名长篇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并称为“三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有评论家称:“这是一部壮丽的史诗”。
1989年却是一个不同寻常之年,多事之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大事件。也就是在这年的年末,中国文坛一桩特大版权冤案也相继发生。原被拖着捂着的一桩版权案,突然被被告主动拽出,被告摇身一变,成了原告,原告则变成了被告。转换角色了的原告是谁?为当时享受军级待遇的老红军马某。作为一名老红军,她对革命的贡献,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当她忘记了革命的宗旨,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时候,这种蜕变,就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了。马某依托某复杂的社会背景,获取当地政要的支持,致使其仅凭口述部分创作素材,竟成为一部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的唯一作者。而为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绞尽脑汁的作者之一,时任湖南省怀化地区文联副主席的我,却惨遭败诉。尚幸人间自有公道,此后,我曾多次接受过新闻媒体的采访,也收到诸多文艺圈内外朋友的来信,他们都同情我支持我,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记得在湖南怀化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朝阳花》版权一案时,原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孙健忠就顾不得夫人右手摔伤,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作家的正当权益,在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之时赶往怀化参加庭审。著名诗人于沙闻讯,也主动与孙健忠同行。还有其他很多湖南文艺界朋友也落座旁听席。在庭审进行中,孙健忠正气凛然书写证词,为执笔者之一的我辩护:《朝阳花》一书初稿不是回忆录,而是小说。原《三湘都市报》资深记者古竹采访湘籍著名作家谭谈和谢璞,征求他们对《朝阳花》版权案看法。谭谈说:“《朝阳花》不署老红军马忆湘的名字是不行的,但不署执笔者的名字也是不行的,因为不是回忆录,而是长篇小说了。”谢璞说:“现在的问题是,只署了口述者的名,没有署执笔者的名,这就难以理解了。”原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朝阳花》一书责任编辑黄伊,对《朝阳花》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最为了解,他于上世纪80年代初,风尘仆仆跑到怀化与我会晤,将两人的谈话录音整理成《朝阳花二人谈》,这份珍贵的录音带我一直保存着。他不厌其烦前后给我写了40多封信,其中有一封信写道:“我反正不相信马(指口述者马忆湘)写了一本书就洗手不干的。我也不相信马除了有一本书就从来不写文章的。我更不相信连写一封简单的信也要靠秘书写的人能写出什么作品。如果有本事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写呢?”作家舒新宇,有次偶尔在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没有封皮的《朝阳花》,便买了下来,精心为它制作了一个封面,上书“谭士珍著”四个字,此举令我好感动。有这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尽管版权案败诉,但真理根植在人们的心里,宽慰着我。
(二)
关于创作《朝阳花》一书的初稿, 我己保存半个世纪之久, 它应该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之所以珍贵:一、长篇小说《朝阳花》是一本有影响的书,曾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人;二、《朝阳花》初稿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铁证,口述者可以享受署名权,为什么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执笔者、作家却没有署名权?三、《朝阳花》初稿是“四人帮”之流为打倒贺龙留下的罪证,文中凡是写到“贺龙”二字,就打“×”并编号。笔者有感于此,特将《朝阳花》初稿原件影印一些附于其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并照录原文,一字不加,一字不减,影印稿均为原稿扫描件。另外,把马忆湘的革命回忆录《在长征的路上》一文也附上,此文14600字,是原湖南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赵清学执笔的,1959年1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这本薄薄的书是很难找到了。1999年我供职于毛泽东文学院,到湖南省图书馆几经查找,终于找到。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如果打版权官司的时候有这本小册子作证据,我的理由就更充足了。口述者马忆湘不是口口声声说《朝阳花》 都是她口述的吗?《在长征的道路上》是他口述的,可是长篇小说《朝阳花》中诸多重要情节和人物并非出自她的口述(下面会具体提到),而是执笔者提炼素材丰富素材加工写成的。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一字不改编进书中,白纸黑字,两相对照,最清楚不过的了。另外,在正文后附版权案有关法律文书和社会反响,便可知此案的全貌。正如著名作家张扬说的:“一时成败在于力,千古成败在于理。我坚信,总有一天,《朝阳花》版权案会露出她真正的面貌。”
(三)
有关《朝阳花》的写作经过。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湖南省军区成立“文艺献礼办公室”。办公室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创作,二是收集革命历史文物。我热衷于文学,早在50年代中期便开始发表作品。于是在1958年12月,省军区献礼办把我从黔阳军分区(现为怀化军分区)借调上来工作。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叫赵清学,如前所述,他曾给老红军女战士马忆湘写过一篇万余字的革命回忆录《在长征的道路上》。该文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回忆录丛书《战斗的历程》中刊出后,编辑来信称:“马忆湘同志写的《在长征的道路上》生动感人,文字朴实利落,有思想性。我们觉得这篇回忆录尚未结束,似乎还有许多故事要写,希望能继续写下去,长点无妨。”
当时,赵清学系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献礼办主任,公务繁忙,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去,经过研究,认为我完成这个任务较合适。当赵清学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曾满口应承下来。
这里要详谈一下马忆湘了。 马忆湘,女,湘西永顺县人,土家族,家境贫寒,小时候当过童养媳,13岁那年参加红军,是红二方面军年龄最小的一个女兵,在医院当护理员。这么小的年纪居然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个奇迹,确实值得人尊敬。解放后,马忆湘任长沙市粮食局第一面粉厂厂长,身体不好,基本上没去上班。其丈夫叫晏福生,当年系湖南省军区政委(中将)。
我在开始写书时,几乎每天都到晏政委家找马忆湘了解情况,听她讲起自己,从小时讲起,一直讲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一连采访了十来天,作了大量笔记,然后,我又找来大量反映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当时盛行写革命回忆录)阅读。我在占有丰富素材的基础之上,写出了提纲,于1959年4月初开始动笔,写到7月底。此时,晏政委和马忆湘要去南岳避暑,我随即也跟了去。同年8月下旬,我在南岳写完第一稿,14万字。初稿写成后打印若干册送给有关作家和评论家征求意见,同时寄给贺龙的夫人薛明(因书中写到贺龙)。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黄伊看过初稿以后,认为写得很不错,但真真假假,已不是革命回忆录了,不如干脆当做小说来写。湖南省文联为此召开座谈会,大家认为中青社这个建议好,于是定了下来,干脆把《朝阳花》当做长篇小说来写。当年的《湖南文学》对这部初稿也情有独钟,在1960年和1961年的《湖南文学》上,选载了《三个女红军》、《水》、《走吧,同志们》、《粮食》等四个章节,都是以小说形式发表的。1960年第11期《中国青年》杂志选载《通过缺水地区》一章。署名马忆湘口述,谭士珍整理。
1960年2月,我和马忆湘赴京找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查核史料并继续收集材料。3月初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我和马忆湘同去上海参加《朝阳花》一书剧本提纲的讨论。剧本由上海著名作家艾明之执笔。之后,我和马忆湘赴杭州陆军疗养院创作《朝阳花》第二稿。这时中青社的责任编辑黄伊急不可待了,从北京赶来杭州,与我同居一室。我写一章,他看一章。他看后提出意见,我接过来再改。时值炎炎盛夏,不知雷峰夕照是什么光景,更不知苏堤柳浪是什么韵致。忙到7月中旬,第二稿总算写完了。我们这才长舒一口气,相视而笑,都“人比黄花瘦”了。
同年7月下旬,全军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和马忆湘又同赴京城。8月初,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召开,我应邀列席。在会议期间,我因故中断了《朝阳花》的创作(文革后才给我落实了政策),第三稿是由省军区献礼办林志义接手完成的,该书终得在1961年1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戚本禹曾胡说,《朝阳花》是一部为贺龙歌功颂德的“反党小说”(文革初期,贺龙被打倒),于是《朝阳花》一度被列为“禁书”,作者们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斗争,受尽了苦难。打倒“四人帮”以后,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该部多灾多难的长篇小说,后来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接连出版了4次。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朝阳花》作为红色经典之一,再次被隆重推出,2001年9月,该书改名为《女红军》,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予以出版。
(四)
这是一本没有序言没有后记没有责任编辑没有写作时间的书。

按说,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是有序有跋有责任编辑有写作时间的。唯独《朝阳花》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让人诧异!
序就是前言,分自序和他序两种,是正文前的文字,简要介绍作者情况和该书的内容或者写作得失等等。跋也称后记,附在文后,主要说明该书的写作经过和写作感受。每本书都有责任编辑,以示负责。一般来说,长篇作品后面都注明写作时间,一稿于哪里?二稿于哪里?等等。但《朝阳花》没有?如果写前言和后记,便不能不提到写作过程,提到由谁执笔的,马忆湘对此讳莫如深,因此前言后记干脆不写了。马忆湘不仅否定了执笔者,连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也予以否定。从开始组稿到该书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黄伊就一直担任责任编辑。《中国出版人名辞典》(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关于黄伊的条目是这样认定的:“曾组织编发了《创业史》、《烈火金刚》、《朝阳花》、《高玉宝》、《阿诗玛》等书稿。”1985年10月2日,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江晓天致我的信说:“黄伊同志一直是《朝阳花》的责任编辑,他为此书稿去过湖南、去过杭州。”但是,为何不署责任编辑呢?原来,在写作过程中,马忆湘与黄伊发生过分歧,马一怒之下便不承认他是责任编辑了。马是老红军,脾气大,把这事闹到出版社, 出版社不敢得罪,只得妥协,出书时便没署责任编辑的名字。至于写作时间,该书刚出版时,文后附有“三稿于从化”字样,一稿于哪里?二稿于哪里?马忆湘皆含糊其辞,不予注明,到后来出书,连“三稿于从化”的字样也没有了。
我国图书浩如烟海,没有前言、没有后记、没有责任编辑、没有写作时间的书,是绝对没有的,在这方面,《朝阳花》创下了新闻出版界的“奇迹”。
(五)
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这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以该书中“三个女红军”为例。1935年初冬,红二方面军从湘西桑植县出发,开始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马忆湘口述的《在长征的路上》只用了1500字,平铺直叙红军从湖南湘西到达贵州之事,非常简单;而长篇小说就不同了,居然写了13章共14600字。其中写了田小兰(小说主人公)当童养媳备受折磨的苦难,当上了女红军的喜悦以及在医院当护理员的生动生活。特别是三女找红军写了三个章节(即10至12章),这是《朝阳花》最精彩最感人的篇章,多家报刊选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1月15日至21日在权威的《人民日报》整版推出,这是《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仔细阅读了马忆湘回忆录《在长征的道路上》,根本就没有三个女红军在部队后面追赶主力的情节,倒是有四个女红军到达康藏高原过雪山受不了那种艰难困苦偷偷离开红军队伍,当了逃兵的事。这四个女逃兵分别叫伍玉莲、夏玉莲、朱国英、小老张,马忆湘的回忆录写得清清楚楚,这就是生活的真实。红军并非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出现个别的败类在所难免。然而文学作品是教育人,鼓舞人的,我读了这个情节后,经过构思,笔头一转,把“逃跑”变成了“追赶”,于是就有了三女找红军这一催人奋进的篇章。
马忆湘的叙事中有没有追赶红军的情节呢?也有。当时马才13岁,小小年纪怎么长征,岂不是成了部队的负担?组织上只好动员她留在后方,但是马不愿意回家当童养媳,也舍不得离开红军,坚持跟在部队后面走,从桑植跟到溆浦,时间3天。红二方面军医院政治处主任李贞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马的意志坚决,只好收下了,继续在医院当护理员(注:李贞系甘泗淇上将的夫人,1955年授少将军衔)。如果照实写下来,太简单。我在这一基础上也做了大量的加工改造,由一人变成三人,由三天变成三十天。我写这三个女红军战士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与部队失散,除了主人公田小兰外,还有一个性格温和但有病的女护理员温素琴,还有一个沉着老炼年龄比较大,还带着孩子的女护士陈真梅。三个人的年龄、性格、身世各不相同,我写了她们之间的战友情,写了她们与当地老百姓的军民情,写了追赶队伍途中的艰难困苦,写了她们与敌人相遇的英勇机智,写了她们追找红军的坚强意志……通过这些情节,把三个女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充分展示出来,同时人物性格也很好地凸显出来了。
这三个女红军的模特在马忆湘的回忆录中有没有呢?也是有的。回忆录中的马忆湘变成小说中的田小兰,秦真梅变成了陈真梅,文新妹变成了温素琴。但秦真梅和文新妹根本没有追赶过红军。文新妹这个人物在回忆录中并没有任何具体描写,只有个名字而已,红军路过云南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文新妹不幸被炸掉一只胳膊,不能跟随队伍继续长征了,寄养在附近一个老百姓家而已。至于秦真梅呢,也没有追赶过红军,当然也没有把自己心爱的孩子寄托给深山老林里的一个老婆婆的事,在小说里有关她们的情节都是杜撰的。
再以陈真梅过草地生孩子为例。
陈真梅和丈夫赵云胜都在红二方面军工作,过草地的时候,陈真梅生下孩子,在马忆湘的回忆录中只有一句话:“秦金美(即陈真梅)刚生下孩子。”就这样一句话,经过我的酝酿,以此为线索扩展开来,变成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章节《草地生孩子》(第21章)。陈真梅挺着大肚子行军,大家给予她诸多关怀,不能走路,就让她骑马,都盼望她生下红军的好后代。当孩子生下来后,战士们争着给孩子取名字,把自己一点救命粮分出来给陈真梅吃。贺龙司令员听到这个喜讯,派警卫员送来麦粉。任弼时政委听到这个喜讯,派人送来小孩穿的衣服。红红(小孩名字)一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笑声,给疲惫的战士们带来许多欢乐。回忆录里的一句话变成了一个章节,什么是创作,这就是简单的回忆与小说创作的根本区别。
马忆湘曾在《朝阳花》版权案的《答辩状》中大言不惭的说:“《朝阳花》一书的构思、故事、人物全出于我”,“文稿也最后由我修定”。这些话太不符合事实,不值一驳。如果马忆湘真有这么大的本事,自己写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他人执笔呢?我至今还未见到世界上有第二个只口述而不执笔的口述作家,马忆湘参军前没读过书,在部队才学习一些字,文化不高,写封信都需请人代笔,怎么会写长篇小说呢?
(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下决心平反冤假错案,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与另一执笔者,即第三稿作者林志义取得联系,两人观点一致,联名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妥善处理《朝阳花》出版权和稿酬分配问题。理由是,马忆湘只是口述者,并非执笔者,作为小说,其情节和人物都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化典型化而创作成的,口述者马忆湘仅是作者之一,执笔者同样是作者。关于稿酬,该书出版后,究竟有多少稿酬,执笔者全然不知,只是在1961年该书出版时,马忆湘分给林志义800元,而分给写过两稿的主要执笔者的我只有400元。一直到“文革”初期,广州军区三次派人来到黔阳(现为洪江市)勒令我写所谓“检举材料”时,我才知道该书当时的稿酬就有1.5万多元,当时算是一笔不菲的稿酬了。马忆湘一个人享有署名权,一个人又独享稿酬。后来听说稿酬做为党费上交了,她上交是她个人的事,不能越俎代庖,我与林志义联名给广州军区政治部反映了我们的意见。1983年2月,由广州军区政治部决定,分给马忆湘稿费50%,我和林志义各分稿费的25%。这种切西瓜式的分配,尽管不那么合理,我们还是表示接受。但是,既然执笔者享有稿酬权,自然应该享有署名权。以长篇回忆录《我的一家》为例,“文革”前,这是一本很受读者欢迎的书,发行四百多万册,工人出版社出版,署名陶承著。“文革”以后,改为“陶承口述,何家栋、赵洁整理”。既然回忆录整理者都可以署名,作为长篇小说《朝阳花》,更应该署执笔者的名字了。对此,作为执笔者,出于对马忆湘这位老红军的尊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她写信,希望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妥善解决,但是此时的马忆湘已非长征中的马忆湘了,自视清高,拒绝回信,拒绝接见,在此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于1985年10月30日向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起诉。1985年12月6日法院立案受理。历时3年,此案无法开庭,原因是法院找马忆湘调查案件,马拒绝接见,连广州军区大院的门都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建议我们撤诉。我们理解法院的苦衷,同意撤诉。中院于1989年3月10日裁定准予撤诉。当时我正在长沙修改长篇小说《太行儿女》,我不理解的是,之后,马忆湘在1989年这一多事之秋究竟嗅到了什么气味,或者说, 她为反扑巳创造好了什么条件,居然反诉我们侵犯了她的名誉权。法院于是决定撤消原裁定,继续审理此案。由于马忆湘是老红军,他的丈夫晏福生中将又曾任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委常委,后升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自然位高权重,关系甚多.很有可能往湖南有关方面打了招呼,由此一来, 这场版权官司未曾开庭审理则输赢已定。笔者乃一介书生,不知其中厉害,以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和人证物证,稳操胜券,结果却让现实开了一个大玩笑,同时,也开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大玩笑。
1989年12月26日,备受人们关注的《朝阳花》版权案在湖南省怀化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原告之一的林志义(广州军区歌舞团副政委)遭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不能前来参加庭审,甚至还写信给法院,申明自愿退出。
版权案审理的头一天(即1989年12月25日)晚上,马忆湘带领一班人马来到怀化,入住怀化军分区招待所,怀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