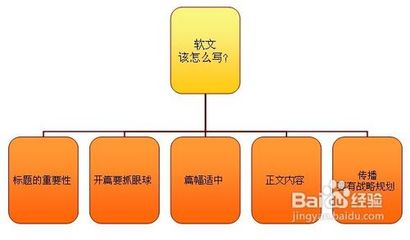“礼失求诸野”该求何处?
文/王王
博文悉知张石山、鲁顺民合著《礼失求诸野》一书,并连阅了作家尧阳发在《山西经济日报》的刊文《回望乡土致敬未来——读<礼失求诸野>》和陈树义的博文《鲁顺民难得清醒》,感思求理,切中倾吐之言,是以下笔如文:
查阅“礼失求诸野”出处,说是孔子之语,可《论语》中并无体现。明确之言在《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和汉代刘歆的《移太常博士》:“夫礼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犹愈於野乎!”才有体现。学术层面的探讨暂且规避,宁愿说这是一种方法,文学取材的方法、史料佐证的方法、学术论证的方法等。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抗战时期写的《浪口村随笔》一书,就是采用了“礼失求诸野”这一方法的典型之作。其作用就是在当文献记载不详、语句支离破碎难以论证时,且当下生活境遇中难以再现往昔古制中的风俗礼制,亦无实物可供考察下,可将视野转向民间,向一些老者智者、古法存礼去求知,诸如婚丧嫁娶、祭祀敬天、乡间礼约、旧俗习惯等形式去获取,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班固的“礼失而求诸野”之法。作家张石山、鲁顺民可谓是这一方法最直接的践行者和受益者。
作家尧阳说张石山先生属于山西省中部人,鲁顺民先生则是晋西北人,倘若二人能把对话范围扩大到晋南则是最好了。恰好,我在中原金三角地区运城,地地道道的晋南人,就姑且说一说这晋南农村中实际现存的“野”文化到底所剩几何!
我生在稷王山下一个8000人的大村,传统农业摒弃下,有螺钿工艺品制造、蜜枣厂、纸箱厂、 工程队等,经济活跃,对外联系频繁。周遭村落虽无这么多产业,但情况也基本如此。诸如尧阳讲的,没有墨汁香味机器制作的对联、越来越简化的传统礼仪等,都在由社会的流向引导着,紧密围绕着衣食住行的层次进行着。破败不堪的庙宇无人问津,一栋栋小洋楼却随处可见。以前无论老者或是少者,都会虔诚地来到庙宇里焚香烧纸、磕头作揖,现今却是灰尘满布、蛛网覆盖;儿时春节闹故事纯粹在延续着古文古艺,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节日情节。现在闹故事则只奔着敛财的目的,没有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更别谈文艺的创新;往昔节日里,互相恭贺祝福,串门走亲戚是人们情感交流的最好方式。而现今传统佳节里却只顾消遣,比如打麻将就已成为农村里最广泛盛行的娱乐方式和交流渠道,精神性的文化交往已经消失殆尽;东西文化的冲突而摒弃自己的文化,只信奉耶稣教理而不跪天拜地,信耶稣的农村人现在成本倍成倍的增加,其现状真是想象不到。所以,真实的“礼失求诸野”到底该求向何处?我想,只能是在学术高度、个体层面上求取了!学术层面上,到残存的文献资料里去找寻与梳理;个体层面上,也只得靠个别的文化老者和智者去一点点地口述,于他们断续的记忆里去想象那传统社会里让人回味的文化礼节。所以,要想在民间田野中向大众文化攫取活的源泉,真的很难,也不现实。

诚如陈树义在《鲁顺民难得清醒》博文里说讲:鲁顺民的清醒是在接受了所谓的“现代文明教化”后的皈依的清醒,而张石山的清醒是一种缺乏克制的清醒,有时甚至是一种炫耀般的清醒。假若再明晰一点,我以为张石山先生是在深厚的文化积淀里去寻求的一种文化返归的意识,他的文化思想高度和返归境界是深思熟虑、有意雕琢的,目的明确,在于传承中予以保护;而鲁顺民的求“野”认知是自然生发的,他是在传统文化的荒原里,以虔诚的心态与敬畏的心理去一点点地徒步前行。“礼失求诸野”,毫不讳言要尽快,在文化礼节消失之前把它们记载下来,浓缩于薄薄的书籍当中,是有益的,于后人也是欣慰的。
毕竟,“礼失求诸野”这项文化工作是个体性的,回归家乡,在故土的亲吻中感受到的只是一种田园式的惬意,想要触及到文化的层面,在表象的交往视野里很难寻觅。因为,文化正在消退,时代变迁,需要张石山、鲁顺民这样的文化学者去担当这一角色,在还算“野”文化的乡村里去晦涩地挖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