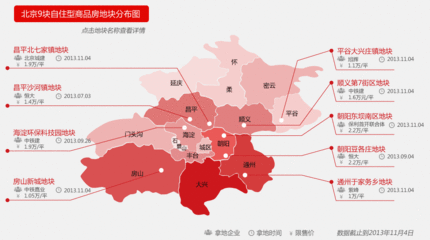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有过一个极富盛名的组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红色血液绝对“纯正”,曾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并一度深刻影响着革命的走势。那么,究竟是哪些人构成“二十八个半”的俱乐部呢?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原产地无疑不在山沟,甚至不在中国,而远在苏联。作为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1925年秋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所招学生既有来自国民党阵营的,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于右任之女于秀芝等,还有共产党的青年菁英。因此,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时风云际会,成了为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骨干的大熔炉。“四·一二”事件后,该校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但师生仍习惯于沿用中山大学的前称。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便起始于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当时的中山大学支部局竭力攻击、诋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等人。而在“十天大会”上,有一批学生赞成支部局的意见,另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所以充当了半个。
据亲历者刘英回忆:“激烈的争论在这次会上总爆发了……会场上很混乱,赞同时鼓掌、欢呼,反对时起哄,因为两派观点尖锐对立,所以鼓掌、欢呼的声浪和嘘声、起哄声常常混成一片。激烈的时候甚至挥舞拳头,相互威胁。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教学计划的问题、大革命失败的是非问题、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问题。”相对数以百计的参会学生,“二十八个半”原本是少数,但因为有校领导的支持,而且请来大学所在地的苏共区委书记压阵,最终还是居了上风。
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不限于参会举手的几个人。因为该俱乐部的头号人物王明,同年3月已回国。可见,“二十八个半”好比商标,虽在“十天大会”上注册,具体人员却包括了一部分缺席者。这一说法现今已得到普遍认同,可到底由谁组成“二十八个半”,仍然有形形色色的版本,竟涉及五十多人。当然,最无可争议的有“一个半”:“一个”是灵魂人物王明,“半个”是尾巴角色徐以新。
凡略知党史的人,对王明都不陌生。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从苏联回国的第一站,是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但才隔了一年多时间,即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一步跨入中央政治局,继而成为政治局常委,取得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权力。虽然明显欠缺资历,王明却自以为是,又绝对好斗。他最早批瞿秋白,后来批李立三,后来又批毛泽东,那副派头是十足的老子天下第一。
1931年上半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形势极为险恶。同年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这一安全地带,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开始遥控国内的临时中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也许是他此生最辉煌的时刻,王明被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中共不能正确实行政策上的转变,于是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所以,王明是深受信任的“钦差大臣”,来延安之初,对毛泽东的党内领袖地位带来很大冲击。好在那时的中共已不是幼年期,王明不管从哪一方面都难以同毛泽东相提并论。共产国际经过权衡,终究认清了这一点。季米特诺夫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而一旦失去了莫斯科的偏袒,王明就毫无分量,只配在一边满地找牙了。
相比王明,作为“半个”的徐以新名气要小得多。徐以新是浙江衢州人,1928年初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由于才十七八岁,政治姿态比较模糊。从苏联回国后,他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秘书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以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1952年随周恩来访问苏联,参加了同斯大林的多次会谈。在历任驻阿尔巴尼亚、挪威、叙利亚大使后,徐以新履职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因“半个”身份饱受折磨,直至1978年恢复党籍,随后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等职。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成员,虽众说纷纭,但根据多种资料分析,还是有一个相对更被认同的名单: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陈昌浩、何克全(凯丰)、夏曦、盛忠亮、沈泽民、孟庆树、张琴秋、何子述、杨尚昆、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孟超;加上王明、徐以新,构成了“全家福”。
在上述人当中,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等属于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杨尚昆、李竹声等属于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还有一些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来到中山大学的。其中女性四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沈泽民和张琴秋较早结为夫妻;孟庆树是王明追求的对象,回国不久两人即成伉俪;陈昌浩与杜作祥也组成了家庭。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自封的招牌,还是被动的嘲讽呢?作为亲历者的吴玉章曾对“十天大会”作了记述,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作为其中一员的袁孟超回忆道:“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对该称谓所产生的时间,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讲得更明确:“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集团’的说法,也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1929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清党时捏造出来的。”这表明,即使那些自视纯而又纯的布尔什维克,也不大喜欢“二十八个半”的封号。
“二十八个半”的人生轨迹迥异。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都曾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层,夏曦、何子述、陈原道等英勇就义成了烈士,盛忠亮、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李元杰等则投敌变节,还有一些人脱党了,其他追随革命的同志也各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大浪淘沙,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显露出了不同的品质。
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峥嵘岁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曾有红得发紫的黄金年代。就理论武装而言,他们中的不少人能大段背诵经典著作,所以极有资本搞教条主义,其思维模式、行事风格也为共产国际所信赖;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却被视作满脑子“狭隘的经验论”,“事务主义非常浓厚”,有“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那时的王明同志无疑是正确、英明的化身,“二十八个半”是根红苗正的精英群体。可到了“文革”时期,用康生的话说:“‘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对照一下名单,我们知道其中是有好人的,康生反而算不上一个好人。这不禁使人想起1931年10月,王明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指责“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可见,只要换一种立场、视角和尺度,连毛泽东同时都成了不会搞阶级分析、不会做群众工作,而王明这么一号人物则被打上了“高屋建瓴”的标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