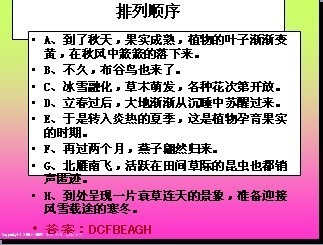悠悠千古月款款赤子情
——读贾平凹的《月迹》
悠悠千古明月,曾牵动过无数文人墨客的种种情思,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名篇佳作。人们吟咏边关冷月,卢沟晓月,床头明月,“杨柳岸晓风残月”;人们写月形月影,“缺月挂疏桐”,“飞镜又重磨”;写月色月波,“滟滟随波千万里”,“梨花院落溶溶月”……“月诗月文”浩如烟海,各出机杼。以至于令后人望月而兴叹,不敢随便吟咏摹写这涵蕴无穷的月。然而贾平凹却敢凑这个热闹,于“月山月海”的诗文路上另辟蹊径——写月迹。写得虚虚实实,掩掩映映,写得那样娇美灵动,写出了只属于他而又能引起人们情绪共振的那神奇美妙的月迹。
写月迹并不稀奇,苏轼早就写过“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写得幽幽静静,缠缠绵绵。而像贾平凹这样写得如此别致的却不多见。其奥秘何在?
从描摹手段来看:一是拟虚为实,巧妙地设置参照物,将无形无态的月迹写得可触可感。作者巧妙地用竹帘,葡萄叶,小酒杯,小河水,小孩子的眼睛,清清晰晰地写出月亮轻盈的踪迹——她“款款地,悄没声儿地溜进来”,“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的圆便满盈了”。后来又在葡萄叶丛上发现了她,还装在了酒杯里,落在了小河里……如轻盈飘逸的少女,又像是淘气调皮的小男孩,可触可摸,有情有意,是那样令人惊喜,那样富有情趣。虽是镜中月,杯中月,水中月,却是全无虚无空幻之感。
二是虚实转换,虚实一体。当听说月宫中有桂树时,倏忽间觉着“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而且似乎“就在身后袅袅”,仿佛又“到了头发梢儿上”,甚至还“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我们已在了月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作者巧妙地将视觉形象变成了嗅觉、触觉意象,遥不可及的月形月影变成了可闻可触的近旁存在。而同时又因为月宫、桂树、嫦娥、玉兔等虚拟物象的掺和,又使得真真切切的月变得虚幻而又奇妙了。这种境界,不是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中的你我他;也不是苏轼“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虚空超越。而是月我同一,天人融合,虚实一体而又忘我忘神的境界。令人分不清是人在月中,还是月落人间。这样写,突破了写月形月色,月影月波的窠臼,从“感觉”这个角度着笔,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意境。也改变了读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客观对象的传统审美方式,而是通过这样的情景设置,让读者走进这美妙的月色之中,和作者一起追寻这月的踪迹,同作者一同天真地、全身心地去感受,去体验,从而获得一种美的愉悦。
三是虚实相生,一箭双雕。作者将嫦娥比三妹,或者说是将三妺比嫦娥,让三妺也拥有月亮,并为这种拥有而自豪。将凡俗与神幻融为一体,交织于“漂亮”这个立意上,使空灵的月亮美得实在,美得真切了,也便现实的人儿美得神妙,美得飘逸了。
古往今来,大凡写月者,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抒覊旅怀乡之情;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写睹月思人之意;或“春去秋来不相待,水中月色长不改”,感叹人生的短促,时光的流逝……而在本文中,全然没有这许多的沉重复杂的情和意。有的只是一种轻轻松松的童心与童趣,以及只有这种童心才拥有的纯真与美好。整个构思都是从孩子的灵心慧眼去发现月迹,感受月迹的角度,以孩童盼月,寻月,问月和关于月的联想、想象为线索来建构文本的。在跌落反转的过程展示中,写出孩子的一种真切的心理历程。
作者先从平静处起笔,很快推进到情绪高扬处——中秋节的夜晚,早早--地就坐在院子里盼月亮。月亮进来了,特别惊喜,“都屏气不敢出,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会一口气吹跑了呢。”从痴情的期待,到专注的神态,凸现出孩子们沉浸于美妙的月色之中的那种纯真与童趣。然后适时地来了个跌落反转——当那月迹悄悄离开那镜子,“亏了,缺了”,末了“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也留下了“一个失望”。作者将一种心理情绪交织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用景物的渐变过程来写孩子们的心理感受过程。可以想象,伴随着穿衣镜上的月迹的出现,从一道白光——半圆——满盈,再到亏了——缺了——全没了,这样一个月迹移动的过程,孩子们也经历了一个由期待——惊喜——惬意——满意,到紧张——遗憾——失望的心理历程。而这种心理过程则完全是因为痴情与专注,一旦发现这悄没声儿的月迹移到了葡萄叶丛上时,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惊喜。作者就是通过多次运用这样的跌落反转,递相翻进,将孩子们的情绪推向高潮,从而写出孩童对月、对美的渴望与追求。
伴随看孩子们追月寻月的天真稚嫩的足迹,读者和孩子们一同发现了那娇美的月亮在水中,在空中,在眼里,在心里。“玉玉的”,“满满的圆”。她属于院落、竹帘,属于桂树、葡萄叶丛,属于小河、沙滩,属于三妺,也属于所有的孩子。她无处不在,只要你愿意,你就会拥有。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温柔与安宁的美!无处不有的恬适与雅静的美!谁不想追求这种美的圆满?谁不想拥有这种美的纯净?作者的用意恐怕也就在这里。真是入于孩童而又出于孩童了。(华文写作在线http://www.hwxz.com/hwxz/index.aspx)
浅析贾平凹散文集《月迹》
李晖旭
禅学不仅是一门高深的佛学,更由于后世诸多文人骚客,古圣先贤的参禅悟道而发展为一种人生的哲学。禅门以不着语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即心即佛,一切现成。禅宗对中国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在当代散文家中,没有谁的散文会像贾平凹散文那般浓重地浸染着道禅味了。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使贾平凹的散文清丽脱俗,秀美难言,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灵异的奇光。读他的散文,与其说是艺术欣赏,不如说是在书卷中作美的参禅,你获得的十二分快感,三分是艺术品味,七分是人生顿悟,还有两分是嗒然失身的灵的徜徉。这种浓浓的道禅意识,不仅表面在贾平凹的文艺观上,更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
《月迹》收入了贾平凹早期的34篇散文。其意韵之深远,恰似“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令人“欲辨已忘言”。这主要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尤其得益于他对禅意的妙悟。贾平凹是深受禅宗影响的当代作家。他曾在传统文化中寻根,并在禅道文化中寻找自己的体悟。他说:“对于佛道,看的东西不多,看了也不全懂,但学会了‘悟’,他们的一些玄理常常为我所悟,悟得与人家原义相差甚远,但我却满足了,反正只是悟出了对我有用的东西,便不管它原本是什么。” 他追求乡村的静美,并以“静虚”作为自己审美内蕴的核心,这一点恰与禅宗的“亲自然,远尘世”之风相契合,使他能深悟禅意之精蕴,同时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幽柔纤巧的审美风格。
《月迹》收入的是作者1980年前后的作品。此时,作者在经历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单纯入世”阶段后,由于读的书多了,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驳杂,逐渐地了解了生活的某些阴暗面,“发现了民性的愚昧麻木,世态的反复多变,人情的冷暖无常等等,以前对人生的光洁单纯的眼光,适足以加剧他此时的悲观、失望,甚至使他涌动着浩茫的痛苦”。“在这种痛苦惶惑的时刻,古代失意文人才子那种厌弃世俗,投向大自然去寻找美和心境和谐的共同举措,通过古代诗文向他呈现了巨大的诱惑力。”由于对庄子、陶潜、苏轼的喜欢,这些作家的追求自然,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庄禅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所不同的是贾平凹将他们出世的消极,妙悟为入世的超然达观。通过妙悟,他认为“人应该超脱、达观,应当站在宇宙中俯瞰时空,对世界、人生、历史作冷静的观照,而不应加入其中,汲汲于得失,与世风时观相俯仰。”所谓超脱、达观,“并不是彻头彻尾的遗世独立”,而是对生活的加倍热爱,一种更深沉的执著。因而,在《月迹》中,作者虽然有时也表现出抑郁忧伤,但旋即能解,旋即能悟,从主体上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热爱和追求,而这些又都被溶化并沉积在《月迹》所展示的空灵静寂的禅宗式的意境中,这种意境首先表现在作者给我们营构的一些禅意充盈的意象营中。
一
月是其中主要的意象,散文集《月迹》中直接以月为题的散文就有《月迹》、《月鉴》、《对月》,而另有《静虚村记》中的“月下树影”,《夜籁》中“显得很小的月亮”,《空谷箫人》中的溶溶的月,《夜在云观台》中的新月等等,作者给我们勾画了一群月的意象。
佛教中常以月来喻世界与本性清净,是心“无念”的具体体现。贾平凹以月来构筑他的空灵静谧的意境,来表现他对“静虚”的审美追求。在他的笔下,总是月下的空明,是“花开月下,竹临清风,水绕窗外,没有一点儿俗韵”的空灵之境。有真实的“水中月”之境:“月亮又上来了,月在水里,看得见那黑脊梁的在星群中间游行。”也有似真非真的水月之境:“果然,石崖走过,看见前面一色白茫,上接月空,漠漠不见源头,下注深谷,蒙蒙亦不辨终底。月下看不见那水气的五光十色……满世界只有一个乳白色的谜!”④还有直接取自禅宗的月境,比如《月迹》中的一段:“我们看着那杯酒,果真里边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捧着,一动不动的,手刚一动,它便酥酥地颤,使人可怜儿的样子。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噢,月亮竟是这么多:只要你愿意,它就有哩。”“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我们再看《住持禅宗语录•圆瑛江法》之云:“一月在天,影合众水,月无临水之心,水无现月之意,感应道交,法尔如是。试问此月,是一是多?为同为异?若言是一,千江有水千江月;若言是多,千江月只一月摄。若言为同,则天涯相隔;若言为异,则一相圆明。”又有:“人人自心月,无古亦无今,灵光常无味,体性本晶莹。辉映天地,迥脱根尘,不离当处,岂假外寻。”贾平凹正是妙悟了此中禅意,并将他的参悟,通过形象的描绘,传达给读者。这种参悟,少了禅的神秘,少了玄奥,在对月的追寻中,展示了“千江有水千江月”的空明,“人人自心月”的禅理。
我国古代文人也多喜欢写月。李白的诗文中,月的形象明丽、亲切,情意深长。有美丽得令李白欲挂于东溪松的月:“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有秋天明丽清冷的峨眉山月:“峨眉山月半轮秋”;有给诗人美好的回忆的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有可寄愁心的解意的明月:“我寄愁心与明月”;还有一往情深的山月:“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而王维的笔下,月的形象皆明净清冷。“草白霭繁霜,木衰澄清月”,这月是发着清辉的清冷的月;“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月是空静的月;而《白石滩》中的月如浣洗的轻纱,有些虚无缥渺。
贾平凹笔下的月则是淡淡的:“月亮已经淡淡地上来,那竹在淡淡地融,山在淡淡地融,我也在月和竹的银里、绿里淡淡地融了……”这样的月是可以融入一切的。而静虚村中的月下之景更是一种自然的、质朴的虚静之境:“看着村人忘归,我一时忘乎所以,月下树影,盘腿而坐,取清茶淡酒,饮而醉之。一醉半天不醒,村人已沉醉入梦,风止月暝,露星闲闲,一片蛐蛐鸣叫。我称我们村为静虚村。”而《夜在云观台》中的月更有一种脱俗的禅味:“我独坐在禅房里品茶。新月初上,院里的竹影投射在窗纸上,斑斑驳驳,一时错乱,但竿的扶疏,叶的迷离,有深,有浅,有明,有暗,逼真一幅天然竹图。我推开窗便见窗外青竹将月摇得破碎,隔竹远远看见那潭渊,一片空明。心中就有几分庆幸,觉得这山水不负盛名,活该这里没有人家,才是这般花开月下,竹临清风,水绕窗外,没有一点俗韵了。”在禅房里赏月,品茶,观竹,使我们想起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那份宁静,那份超然。
贾平凹吸取了李白的达观,王维的超然。李白的月达观,而贾平凹于在达观中更多了一种虚静和进取。王维是用晶莹明净的月亮来喻自性清净,一尘不染的,但他的月多了一层出世的清冷。贾平凹的月是他主体精神的象征,是他追求、探索的美学象征:“月亮是亲爱的,月亮有时也是不可摸透的;使我为渴望着探索到它的秘密而被折磨着,悲哀着。”
贾平凹的月与李白、王维的月之所以有这种不同,是由于他们的时代和思想境界不同。李白、王维是封建士大夫文人,他们不满现实却又无法改变现实、超越现实,在矛盾的痛苦中或无可奈何地漂泊,流连山水,或厌弃世俗,离群索居,隐匿山林。他们追求的是“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追求心境的平和虚静。贾平凹作为一位当代作家,进取的时代决定了他必然会追求不息。在“复杂处世”中虽也偶有抑郁忧伤,但作者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发现美,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与他于禅道中所妙悟的“静虚”思想相结合,因而他的月是超然达观的“溶溶”的“静静”的月。
《月迹》中的意象还有水、清泉、小溪、飞鸟、白云等等,这些意象都具有象征意义,都能给人以神韵超然的感受。
水在佛教,尤其在禅宗被认为是清净无瑕,湛然恒静的最高境界。清冽的泉水,淙淙的清溪,是自性清净、任运自然的象征。《月迹》中多处讲到水、溪、山泉:《清涧的石板》中石缝里的水是清极亮极的;《溪》中的小溪是缓缓地悄悄地流淌着的;《紫阳城记》中的水亦禅意悠悠,深远而有韵致。
山,在贾平凹的作品中,也有一种超乎自身的象征意义。他曾说自己是山地之子,对山有着特殊的感情。《读山》,表现了他对山的内蕴的追求。山的神秘,山的莹透以及山的拙朴,都是作者对山的力量的一种解悟。最后作者说:“几次不知了这山中的石头是我呢,还是我就是山中的一块石头?”正是物我两忘,身世皆忘,超越了一切时空的禅意。

另外,作者还用飞鸟、白云等来表现自己对自然的向往:“漫天的鸟在如撕碎纸片的自由,一朵淡淡的云飘在山尖上空了,数它安祥。”白云、飞鸟在佛禅中是无所挂碍的禅悟象征。贾平凹正是用这些意象,构成了自己的空灵静谧的意境。
二
意境,是中国美学的特定范畴。王国维创“境界说”,谓“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中国的各种艺术无不联系着这一审美范畴。禅境所追求的是空寂闲静、一尘不染的境界。《月迹》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静寂空灵。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习应品》中有一段:“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空法,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世界既无生灭和垢净增减的变化,也无过去、现在、未来,整个世界一片空静。佛禅从心性观念出发,否认客观世界,也否认物质运动。他们认为世界是静止不动的,人们感到动,是因为心动。《坛经》中有则著名的公案——关于风吹幡动之议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只要能凝然守心,不执著于外境,就能达到成佛的最高境界。
我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孜孜追求着这种心的绝对的静。王维即是典型,他的名诗“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即表达这种绝对的内心寂静。苏轼有云:“欲令诗语妙,无如空且静,静能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贾平凹于《月迹》中所要传达的,亦为一种静虚的静境。
贾平凹的这种静境,“不是表现主体对客体的矛盾、冲突、征服,激发起奋发的豪情和斗争动荡的愉快,而是表现实践和实现统一引起的一种闲适、平静、超然、愉悦的感情。”贾平凹执著地追求这种静境,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静虚村”,并在作品中一再表现。在《静虚村记》的开头,他写道:“如今找热闹的地方容易,寻清净的地方难,尤其在大城市附近,就更其为难了。”在城市,他感到扭曲、压抑,感到有一种不能舒展的苦闷。只有回返乡村,他才能感到境与人和,人与境谐,适心宜性。
《月迹》中,作者写了许多村庄、村巷,无一不是静静的。静虚村中的村民,“厚诚”得几乎近于“傻昧”,生命形态呈现出一种原生的质朴。再看渭北瓷城陈炉吧,作者远远看到“青烟就端端地冒出来,而且有了鸡啼。这便是一个村了;屋舍看不见,人家都住在塄下”,这不禁令我们想起“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那种闲静来。还有《白夜》中的村子:“静悄悄的,没有一点人影,也没有一只狗咬。从巷道里过去,雪落得很深,一脚踩下去,没了小腿,却没有一点声息。走进一家,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直走近门口,门被雪封了半边,只看见那黑色的门环,一动未动,像画上的一般。”这样的一个村庄,被雪封住了也不知道,人们正在甜睡中,一切都正处于安谧的原初状态。
在作者的笔下,还有幽静的空谷,静谧得雄壮伟大的池塘,伟大静默的山,还有小小的文静的文竹,静若处子的兰,他们共同构成了贾平凹的静境。
贾平凹笔下的动境,“也不是表现主体和客体激烈冲突,抗争,唤起的不是斗争的激情,而是主客观世界谐调的愉悦,闲静,所以本质上也是静的”。即使是热闹的街市,在他笔下,也少喧嚣,烦扰。且看《延安街市》:“最红火的是那些卖菜者……买卖起来,价钱是不必多议。称都翘得高高的,末了再添上一点,要么三个辣子,要么两根青葱,临走,不是买者感激,偏是卖主道声‘谢谢’”。“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全没有。这里的人与人之间是那样和谐,一对老亲家,在街市上相遇了,便寻着块空地,投机地谈起儿女的亲事。拴在堤栏杆上的毛驴,便偷空在地上打滚儿,叫了一声,整个街市差不多就麻酥酥地颤了。”真是“境与人和,人与境谐”呀。虽曰闹市,却仿似“静虚村”,仿似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仙境。
禅被彻底理解时,就得到心的绝对的平和。人人从事其正当的生活。无论是静虚村中的村民,还是渭北瓷城陈炉的人们,或者是《白夜》村巷里的人家,他们都是那样平和而悠然地生活着,“接人待客,吃饭总要吃得剩下,喝酒总要喝得昏醉,才觉得惬意。衣着朴素,都是农民打扮,眉眼却极清楚”。他们在自己平凡的位置安居乐业,没有喧嚣,没有世故,没有庸俗,有的只是一种自然的质朴,一种心地无杂的清朗。他们身居苦境而不知其苦。静虚村的人们乐于他们的土院,《陈炉》中的人们,“吃饭极少吃菜,一顿饭,两个馒头,一碟辣子也便算了;洗脸水总是刚刚盖住盘底,依墙靠着,一家人老的洗了少的洗,脸洗湿了,水也便完了。”《夜籁》中的老汉喝着又苦又涩的汁汤,却哈哈大笑着说:“土命人也不像你说的可怜,苦是苦,苦中仍有甜呢。”这样一种身居苦境而不知其苦,能够于苦中见甜的达观超然的胸襟,正是作者于禅中妙悟到的,是作者审美内蕴的核心——禅宗的“静”、“虚”。禅宗要求人们从变幻的外界去认识动中所藏的静的本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说:“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不离动。”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贾平凹深谙此中真义,他常用动来表现极静。在幽谷中响起箫声,使幽谷更幽更静。在《夜游龙潭记》中写万籁俱寂:“桨起舟动,奇无声响,一时万籁俱寂,月在水中走呢。”再用满湖的啸嚣来衬托:“听满湖啸嚣,如千军万马厮杀战场,我身骨儿都吓得软了。”写出了静得可怕的绝对的静。
另外,作者既酿造出月下的空灵,也有迷迷蒙蒙的如水中月镜中花式的空灵。在雨中:“石板路是潮潮的了,落叶浮不起来,一时深、浅、明、暗,层次分明,远峰愈高愈淡,末了,融化入天之云雾。”是一种如飘渺虚幻的云雾似的空灵。在月下渡口:“夜里,船到山湾间,月显得很小,两岸黝黝的山影憧憧沉在水里,使人觉得山在水上有顶,水下有根,但河面却铺了银,平静静的似乎不流……”这是一种“水中月”式的空灵。云雾漫山时:“滚着滚着,满世界都白茫茫一片了。偶尔就露在山顶,树木蒙蒙地细腻了,温柔了,脉脉地有着情味。接着山根也出来了。但山腰,还是白的,白得空空的”。质言之,这些意境空灵而迷蒙,使景与意无隔,现实和幻象相融,使幽者更幽,静者更静,空者更空。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意无穷”。
贾平凹以他特有的气质、个性和感受力,妙悟了禅意,并在《月迹》中通过象征式的意象构筑了一种禅宗式的静寂空灵的意境,使他的作品读来意蕴深远,韵味深长。毫无疑问,这种审美取向,将给当前的散文创作提供一种别开生面的创作启示。
(摘自《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