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港顺访谈周全胜
周:你这里弄得挺好的,有人收拾和没人收拾就是不一样。你这是画的什么?好像是美国的总统办公室?
刘:对。
周:谁画过以前?
刘:利希腾斯坦。我画了一个房间把它挂起来······
周:画面本身形成一个美术馆环境,模拟一个美术馆环境。
刘:对,模拟一个。
周:你算不算是观念艺术这个范畴?
刘:有这个成分。
周: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一根绳子穿过一吨书》这幅画?
刘:左边是比利时艺术家的一件作品,右边是我们1994年做的行为作品“一根绳子穿过一吨书”的局部。
周:这个比利时的画家对你影响大吗?
刘:有影响不是太大,他也是一个当代艺术家,这几年在全球成长挺快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个艺术家。
周:那很年轻啊。他画的东西都是这类画?
刘:他画的东西特平淡,都是一些很司空见惯的东西,有点像莫兰迪画静物。
周:但是我感觉他画场景,画照片。
刘:他画场景,画照片,但他的处理手法有点莫兰迪的那种感觉。就是特淡化那个情节,淡化一些东西。
周:好像把油画处理成水彩之类的。
刘:他是画的油画,但是整个画面都是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的。
周:那你自己真的趣味在哪?为什么当时你灵机一动就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了?其实我理解你的东西,我觉得它应该最少是两个层面,就是你自己本身是激发你的趣味,每个人做东西都是有他的始发点,完成之后,你再解释,或者是观众的误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感兴趣的是你的始发点怎么就把它们突然放在一起去了,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不至于影响咱们回头去解读它,做另外的解释,但是······当时你们做这个“一根绳子穿过一吨书”的行为,我猜测,这些书肯定都给你们破坏了。
刘:对。
周:因为这个行为,那我猜应该是发生在书店,就是你自己的······
刘:不是我的书店,是我的一个朋友的书店,1994年我还没有开书店,我是1995年做的书店。
周:那他这些书是好书,还是不要的书?
刘:有用的和没用的书都有,1994年黄专邀请我们去广州做第二届双年展,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方案,实际上是一个装置,就是把“中国美术史”台湾出版的三万多块钱一套(那个时候挺贵的)60多本这么厚,用电钻和挺粗的麻绳把它整个穿掉,然后在展厅的中间做一个金字塔形状的陈列装置。那个展览的主题是“文化理想主义”我们做得有点反讽,带有一种解构性质。由于东辉公司当时说要投一笔钱给那个展览,后来可能资金没到位,那个展览就流产了。流产了之后,这个作品我们还想做,但是你不在一个场,不在一个环境去做,可能意义就不大了,我跟我们本地一个小书店老板的关系挺好,我就说在你书店环境里面去做这样一件作品,他答应了,然后我们就收了一汽车的书,他也提供了一些书,请了几个人帮忙,做了一天,那个电钻就不断的在穿,在那个小书店环境里,让它膨胀膨胀······实际上我们穿的不止一顿书,绝对不止一吨书。虽然没有膨胀出去,最后也形成了一个螺旋形的书山。
周:我对这个领域几乎完全无知,那它的趣味在哪里?你刚才说中国美术史,我是看到它的意味在那,那现在你做这个?
刘:通过我前面说的那个方案,和我们后来做的那个东西,它又发生了变化,就是场也变了,然后你选择的是同一种材料,但是它的意义也变了,选择一套“中国美术史”在展览那个环境里给它穿掉,它的文化针对性可能强一点,因为它是“文化理想主义”的主题,后来我们感觉你做一个东西,又没有把它做出来,然后老想做,你没做又过不去······
周:那还是觉得浓度不够。
刘;有点变了。
周:我觉得你一直对书店有个情结,包括你后来自己开书店,又倒闭,现在又继续画自己的书店以及别人书店的照片,甚 至包括新小说家,后来你画的这些作品又一部份是在梳理艺术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一根绳在穿过这个世界艺术史。
刘:对,它有一个线性关系,对我个人来说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
周:然后这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你又把它跟一个比利时的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你是感觉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联系还是怎么样?
刘:应该是没有联系。
周:你是怎么理解他这幅画?
刘:这个画不能说,不是不是,就是有时候可能两个东西并置在一起,对我来说传达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有意味的形式你很难说,它的神秘,或者它所传达出的其它东西。
周:我发现你的特点是这样的,你不是很清晰的,或者你的神秘本身就是你的一种趣味,你经常就是欲言又止的。
刘:对。
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还是你确实是在一种说不清的,一说就不对的,这样一种状态里。
刘:我比较喜欢莫名其妙或者说不清楚的这种关系。
周:我来跟你谈之前,是考虑过你的情况,因为你送我一本《这三天》然后还有网上你写的文章,比较诗意,然后比较荒谬,语无伦次,我看完之后,确实很难找到那根线索,虽然你写了三天,不像《尤利西斯》不到一天写了两大本,但是那种表达状态都是类似的。当然乔伊斯的作品,我还是看到一些故事,但是你的东西我确实没有看明白。
刘:你说得很多,顾左右而言他,是经常的。
周:你觉得是你本身长期以来故意培养的状态,还是仅仅是艺术家的一种姿态,或者作为一种策略出现的。
刘:那个时候不谈策略,不像现在,因为它是90、91年。
周:画这张画是什么时候?
刘:2007年。
周:这么跳跃性,这么神秘,甚至是这么不定向的一个东西,它的趣味到底在哪里?
刘:这个就很难说。
周:那你的本意是怎么去接近这件事情呢?你的作品有那么几件,我觉得几乎是最难解的。《两只蜡烛》比较清晰,有点那个比喻关系,两个人、两只蜡烛······
刘:有一种暗喻。
周:或者那个《呐喊》也是,我很重视趣味,因为我对观念确实是陌生的。
刘:实际上趣味也包含着观念,就是观念的门槛并不高,你所理解的趣味,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你不要把观念这两个字,单独提出来······
周:观念是趣味的一部份,或者你这么来说?
刘:趣味是观念的一部份,可能对,这样也不准确,就是谁也不能代替谁,但是它就是有一种关系,你刚才谈到趣味的时候,我觉得趣味也是观念的一种。
周:当时到底是怎样的?就是因为你喜欢他的画?比如说像莫兰迪,那你为什么不在旁边画莫兰迪。
刘:不是这种关系,我是刚才为了把它说得让你好懂一点,因为我说莫兰迪你可能知道,我说另外一个人,你也许不知道,我说他是比利时的一个艺术家叫卢卡·托马斯,那你肯定不知道。
周:托马斯的重要贡献在哪?
刘:他用的手法挺传统,但他做的东西也有一点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他老是指东打西,他也不是就事论事的那种类型。
周:就是说,他也带有很强烈的观念性,而这一点你跟他在精神层面有点相似?
刘:可能是这样,有时候艺术家是反对阐释的。
周:现在我隐约的感到你们精神上的共同性,还是没有看出你把它放在一起的真正始发点在哪里?
刘:这个就不要去纠缠,你纠缠的过程中对读这个作品就有障碍了,我可能相信这两个东西并置的时候,他有一种潜意识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能说清楚吗?你不能说清楚的东西,你就要保持沉默。
周:接着带来你的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跟你的作品对话,必须要有很丰富的艺术史知识,可能一般的观众面对你的画,那是彻底要一略而过的,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不是这么个概念?
刘:也许。
周:我昨天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你做的那件椅子的作品。在观念艺术史上似乎也有某一位艺术家做过椅子的作品,他好像把三个椅子并置了,你知道我说什么?
刘:我做那件作品没有考虑到(科苏思),因为他那个作品是《一把和三把椅子》,一个是文字解释的椅子,另一个是椅子的照片,然后是椅子的实物。博伊于斯1963年也做过《油脂椅》,中国85思潮时期黄永砅也做过“纸浆椅”。但是每个人的想法和做法都不一样。所要言说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用那个作品题目的时候,没有直接指涉这是椅子,而是用了一个日期来命名《星期二》。
周:你一开始我记得你们做了一个艺术小组,SHS,什么意思?
刘:80年代纽约苏荷区是前卫艺术的根据地,简称SH,黄石,我们老家是HS,中间共有一个H,所以我们就是SHS,那个时候是1992年。
周:92年这么早就做这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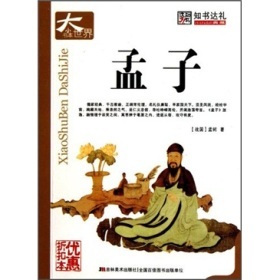
刘:92年3月份。
周:你是后来到宋庄才做绘画的?
刘:也不是,80年代中末期的时候,做一些抽象表现。类似于波洛克,阿尔芒,那种典型的美国风格,然后又有点德国新表现,巴塞利茨,基弗之类。
周:可能是比较自我的那种。
刘:比较自我的,挺情绪化的。
周:后来就开始做绘画了,那我在揣测它的原因是不是经济。
刘:肯定算,这个说白了肯定算。
周:我觉得在你绘画里面有两个情结跟你过去的经历联系很密切的,一个是做书店的那个情结,第二个,你似乎不再做行为了,但是做行为背后的那种思想模式或者说重视观念,这种东西在你的艺术里面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刘:很重要,而且我跟你说我真的得益于那些东西,而不是我这几年在绘画上的造化,我做作品来自于更多的不是绘画本身,而是来自于其他的一些东西。
周:我会画,但是我不太会画。我能不能这么说,我不觉得你的绘画里技术成分很多。我能不能这么说。
刘:这个很准确,因为我不是一个会绘画的人。
周:不是靠炫技的人?
刘:也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人,从大处着眼,我重视我要做的那个事情本身,技术可能在我个人身上永远是第二位的。
周:某种意义上来说观念先行以后就完成了吗?但是现在你依然要用画面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在这个反复咀嚼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新的东西。
刘:新的东西能不能发现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你在这个时候要去完善一个东西很重要。那个时候我不太强调完善,可能四十岁以后我们的责任感加强了。
周:我觉得我挺正面的理解,不光考虑销售问题,我挺认同你的,拍着脑袋一个想法出现很好,和最后实现它,和进入博物馆或者流通领域,这是两件事情,我对你这个表述确实是很正面的来接受的,也确实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可以理解的。一个创意和最后在适当的场合把它完成这是两件事情。
这么说你的作品我的理解又深了一层,在你的作品里,依然有两股很重要的思想在影响你,一个是来自于博伊于斯,第二就是来自于波普。我不知道我概括对不对?
刘:基本上是这样,80年代中末期以后,博伊于斯,杜尚,克莱因,约翰·凯奇,这几个人当时对我影响很大。
周:这里我打断一下,博伊于斯讲社会雕塑之类的,算观念艺术吗?
刘:他的涵盖都包括了。
周:像博伊于斯有很强的参政意识,但是你现在在做这些作品,似乎仅仅是停留在学术层面,不是去干预社会,而是书斋的,象牙塔里面的这样一个东西,它的意义性何在?
刘:60年代它的社会情况不太一样,激浪派的来源就是达达,是破坏而不是建构,最早的激浪派运动60年代初期在德国,早期博伊于斯的一些东西也还是很顽皮,很闹剧,很不强调意义的。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因为德国二战之后一直挺自卑,包括美国垮掉的一代,法国的五月风暴,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内心澎湃的一面。70年代激浪派的很多艺术家都在回归,我指的回归是有的去写作了,有的去养小孩了,有的可能就回老家了。当然激浪派最杰出的艺术家是:马修纳斯,白南准,大野洋子······
周:虽然是闹剧,但更纯艺术。
刘:1965年博伊于斯开始做“西伯利亚交响曲”激浪派就把他开除了,激浪派没有这一章(指对社会和政治的参与),但博伊于斯的野心更大,他是想扩大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那种观念,把整个欧洲作为共同体,来激活每个人的创造力。
周:就像一个在野的政治家。
刘:对,你不管是一个清洁工或者是一个经理,或者是一个什么人,你都可以在你的岗位上提供创造力。
周:沃霍尔说每个人可以成名15分钟。
刘:沃霍尔说的是典型的美国消费文化。
周:我们回到刚才,你现在有什么价值呢?
刘:从内心来说,我更愿意像现在这样回归,我现在做的有些工作,有点贝克特,或者乔伊斯的那种感觉。
周:我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你的位置不应该在宋庄,而应该在美院,或者是大学,为什么?你不但对观念性这些东西是了解的,而且你对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史是非常清晰的,你还用你的方式在重新解释,我觉得以你的姿态,做一个这方面的学者教授,会比一般不整天泡在里面的人,优势大很多。现在竞争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花样百出的环境下,我觉得你的那种刺激性,就不如别人强。你的作品似乎不那么表面,不是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你是一个新东西,你是怎么考虑的?你不觉得你不合时宜吗?
刘:不合时宜是偶尔有的感觉,但是我一直跟朋友说,我来宋庄是看中了北京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做作品跟他们强调的宋庄感没有关系,宋庄的环境比较安静,因为我当时开完书店来北京的时候,有一种归隐山林的感觉,这个环境适合我,它的生活费用也低,所以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我92年就下海了。到2002年整整十年,不管是做书店,还是做其它的营生,都是一种经营,实际上,我这个人挺不喜欢竞争的,在我没开书店之前,我都没有竞争的意识,就是开了书店也是一个学术书店,一个自视清高的反商业的商业。所以当时在地方也是相当出力不讨好。
周:你觉得今天是不是继续这样呢?
刘:十几年下来,我已经适应了竞争,但是现在在宋庄我还没有竞争的意识。
周:你做的东西,我想放在国际的大背景里,我不能判断它有多么的独特性,但是起码在中国这个环境里,你做得还是很罕见,你发现其他人做过类似的东西吗?
刘:每个人做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周:有跟你比较类似的吗?
刘:有的人隐隐约约,很偶然的转到这个地方来,很快又不见了。
周:你的东西还是蛮特别的。那么波普在你的艺术里面是怎么影响你的?
刘:波普90年代中期对我就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凸显,我是来宋庄以后发现了波普,又重新认识了一些艺术家,约翰斯我是比较喜欢的,包括波普的几个很重要的艺术家,沃霍尔,利希腾斯坦······里希特,我不是热起来才去认同他的,波尔克,也是一个挺棒的艺术家,所以来宋庄以后,我又重新发现了绘画,而且发现了绘画这一块的魅力,所以这个时候再重新梳理,那时候,我有一些朋友打电话,问你现在在干吗?在画画,他们感觉很奇怪,他们感觉绘画的观念是很落伍的,我们那个时候也说过绘画的死亡,对架上的东西毫无兴趣,所以我刚来宋庄的时候,跟朋友说:我可能来宋庄就是晒晒太阳,看几张DVD,或者看几本书,可能把画笔捡起来,太难了,太难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硬着头皮去做。然后看一些书,慢慢的往这方面靠,看80年代那口气还在不在。因为毕竟扔了十几年,对这一块没有兴趣了。
周:其实在宋庄,波普或类似波普的东西,是挺泛滥的,或者说这种东西商业上也因为它走得好,有一个互动关系。所以最后搞成这么一个局面。或者说它已经对你而言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是你把它拿来是你熟悉的一个元素。
刘:因为我做东西经常是交叉的,就是我做这样一些东西,你感觉有波普痕迹的时候,其实我又在交叉其他的一些东西。其他的一些元素。
周:你这件作品完成了吗?
刘:没有,可能还要一个多星期。
周:我其实坐在这,老看老看感觉挺好的。
刘:我的作品需要凝视。
周:你的那件《俄罗斯!》作品。用了极少主义的方法,黑白对比,而且用黑色的。
刘:不是,是生褐色。
周:第一印象很强烈,《俄罗斯!》挺意味深长的。
刘:有个上了年纪的朋友,在这件作品上获得了很大的共鸣,他就感觉俄罗斯的那个苦涩,那个国家的概念都含在里面,他读出了比我意义大得多的东西,包括它的感叹号。
周:你没有把俄罗斯的镰刀,锤子画上去,俄罗斯对老一辈中国人而言是红色的镰刀和锤子。
刘:我用的颜色是很中性的,又含有一种苦涩,它不是纯黑,纯黑的概念性太强,所以它是一种中性的东西。
周:也就是说当一个概念很清晰的时候而你心里是想把它稍微模糊化。
刘:我在用颜色的时候有考虑。
周:我发现你对国家概念很重视,无意中发现的,你看这三四件作品,都跟国家概念有关,这是因为来自于波普的传统,还是来自于博伊于斯,或者是什么复杂的,你想去进入那么一个高层对话的意愿。
刘:这样说有点虚伪了,实际上没有着意这样去做,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周:我猜测,在宋庄有一些类似的艺术家,跟我说,为什么这样,其实是潜在的目标市场,反过来影响了我们。
刘:这个可能在形式上有考虑,在市场上真的没有考虑。
周:对,起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刘:至少这样一件作品或者下面那样的作品,它们呈现出的东西,可能是独特的,我不能说是原创的,我用的基本上是既定的形式,不论是现实主义或者是波普,或者是观念,或者是什么东西,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个都成工具了,就看你怎么用,怎么升华它的小小新颖。这就是所谓的转换。
周:这些就是你的趣味所在,我今天来之前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你的趣味到底在哪里?你用转换这个词给概括出来了。
刘:所以现在很多人再提原创,是毫无意义的,都进入21世纪,早就进入后现代了。
周:我一直有个困惑,有一种艺术家是完全自我的,现在似乎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不再这样了,一般是青春期的,或者是后青春期的比较自我,到后面的就是超越自我,就是更大的,关注一些无我的客观的东西。然后你刚才讲的后现代转换,好像又超越了那样一个年龄段。
刘: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了乔伊斯所比喻的人生的三个阶段,年青的时候,是抒情的,中年的时候是叙事的,到了晚年60岁以后,他就升华了,就是一种大我,一种超越自我的戏剧性阶段,这是人生的三种境界。你刚才说的很准确,我年轻的时候靠激情,但是这种类型我不能保证能走多远,感觉特费劲,特累,就像过性生活,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保持在高潮,80年代你冲到一个山顶,老有一种很虚空的感觉,就是把自己抽空了。现在做艺术,我感觉心态平和了,它是一辈子的事,而且你要做得好,你真的要靠很多时间,包括你的生命,你的寿命,去完善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就长智慧了,我就开始升华一种东西了,我就在推进当代艺术的参数了。
周:其实你的作品类似于哲学的一个空空的概念,因为某种程度上还是挺抽象的,在你做作品的时候,总是把自己那根绳子抽掉,然后让大家猜谜语。
刘:你刚才说的那个抽象我爱听,它真正不是画面意义上的所谓抽象,而是给观众一种精神的抽象。这个很重要,我没有给一个具体的答案,就是所谓很现实的情境给别人。
周:你其实还是挺理性的。
刘:不能说理性。
周:很玄学的这么一个人。
刘:但不是故弄玄虚,对我来说是挺自然的。
周:你考虑过自己的定位吗?你对杜尚的人生经历怎么看?我觉得你的作品有很多杜尚的那种意味,在猜谜语,不把事说透。
刘:杜尚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挺大,包括生活方式,对欲望的奢求,为人处世。人要这样操守一辈子那也太难了,真的挺难的。
周:杜尚是超现实主义还是达达?
刘:他都不太介入,你说他是达达,他也不承认;你说它是超现实,他说跟他们都是朋友,仅此而已。包括他参加超现实的一些展览,总是布完展览就走人,他也从来不参加开幕式。
周:他好像和毕卡比亚是搭档。
刘:毕卡比亚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介入达达和超现实之间的一个人。
周:我挺喜欢毕卡比亚的,很多人不喜欢她。觉得他不严肃。我喜欢他的跳跃性。他每一个阶段都跟另一个阶段差异挺大,然后他做的东西挺轻盈,也就是他的不严肃性,他不把一个事弄得很严重,而且又在玩商品和艺术之间的游戏。
刘:前几年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亲爱的画家”向毕卡比亚致敬的展览。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萨利,施纳贝尔,波尔克,克莱门特公开承认毕卡比亚曾经对他们的影响。
周:现在看来后现代艺术它的起点好像是达达,是这样吗?
刘:后现代艺术,可能在西方从时间的概念来划分,现代艺术之父是塞尚,后现代艺术是杜尚,60年代始。
周:我跟朋友聊天,他把杜尚和博伊于斯联系起来,你是怎么看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刘:博伊于斯说:杜尚的沉默被估计过高了。(他不喜欢那种对社会,对政治的不参与)杜尚没有承认过他受东方影响。他的气质和他的生活方式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感觉他更像东方的高僧大德。
周:杜尚只是拿来实物,博伊于斯把它放大到社会,或者指定很多实物为艺术品。跟杜尚有关系吗?
刘: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有间接的关系,杜尚的现成品1914年就完成了,所以说杜尚间接的影响肯定是让后来人走的更自由,更宽广。
周:杜尚的生存方式,他在美国一直有赞助人在养他,让他闲职。
刘:实际上比想象的要惨得多。你看杜尚访谈录里就说:我不结婚成家,我不要房子,不要车子,我的生活要求很低,吃碗面条,喝点红葡萄酒,生活很简单,所以我很好打发自己。不要让自己这么累,不要有包袱,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自己也强调,我喜欢呼吸甚于喜欢工作,赞助人给他的钱很有限,他早期也卖一些作品,很便宜的价格。没钱用的时候也变卖一些其它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的市场跟现在不是一回事。
周:你能不能展望一下你未来艺术发展的一些想法?
刘:这个很难确定。我经常有时候这样想,但又很快的把这种念头打消掉。
周:明年一整年的创作构思有了吗?
刘:有时候涌现几件作品,我可能两三个月集中按部就班,也许这件做完后,还不知道下一件做什么,这种状况也挺多。它老形成一种交织,不像有的人做了一个符号,就这样复制,或者仅仅变换一个动作,一个什么东西。但这一点比较清晰,就是不出太大的左右,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我这个人的作品。所以现在他们也逐步的感觉,你现在有一点自己的面貌了。
周:你对未来的物质期待好像也没有那么一个明确的想法。
刘: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不是你去求的,物质上你不要去设定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可能比你想象的好,这一点是肯定的。
周:你现在怎么估计你的市场状态,是有画廊感兴趣,还是策展人,批评家以学术的角度开始帮助你?
刘:这几年开始,有这种迹象,包括画廊,或者是策展人,批评家,和一些藏家,开始在观察,也在买一些东西,但有的还在继续观察,跟你一样。
周:没有实力,又挑剔的人。
刘:他们有实力,但他们工作做得挺细。他们也是大的藏家,很谨慎,不是钱的问题。
周:中国的传统思想,像禅宗,道,对你有影响吗?
刘:我看这方面的书不是太多,我的根里面肯定有这种东西。因为我是阴历观世音菩萨生日的那一天生的,所以庙里面的师傅说我有慧根,但是我接触佛,道,禅的东西不是太多。看过一点,我喜欢净空法师说的,佛教就是智慧的教育。我感觉这一点挺好。
周:你知道李叔同也是美术教育家,他后来出家了。
刘:有些人还真说我有点像弘一。
周:今天收获很大,其实打算跟你聊一聊,聊之前我是很迷惑的,甚至有一点点畏惧,不知道跟你聊什么,不知道可能我们两个谈出点什么东西来······
刘:这个畏惧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有。因为我不知道你会带来什么问题,我又怎么回答你。
博伊于斯的帽子147.5x198cm2007布面丙烯.
工作间Ⅰ127X190.5cm2004布面油画.
我很抱歉147.5x198cm 2006 布面油画
镜子147.5cmx198cm 2005布面丙烯.
午夜出版社135x196cm 2004 布面油画
个性与他性120x150cm 2008 布面油画
博尔赫斯书店120x150cm 2008 布面油画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