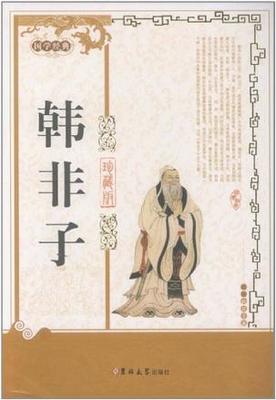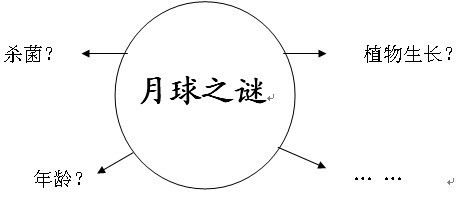这几日,由于学诗经的缘故,我又关心起了哈辉。
哈辉是陕西汉中人,中国青年歌唱家,唱了很多的古典音乐。中国国学推广大使,研创了所谓的“新雅乐”。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曾经先后赴美国、英国、土耳其、以色列、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南非、赞比亚、安哥拉以及中国的澳门、香港地区进行该方面的巡回演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代表作是《关雎》和《相和歌·子衿》。
对于像哈辉这样的人,我一向是十分敬重的,因为她正在把古典的东西与现在的精神元素相结合,做一件利于民众灵魂建设的大事,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勇敢者。在中国,在音乐文艺方面,这样的勇敢者,在我看来一共只有两位。于台湾,其白先勇;在大陆,唯有哈辉。然而,由于我一贯的意思,不因对一个人充满敬意而失去了对她的批判。今日便是。而且批判的对象正是哈辉女士的代表作——《相和歌·子衿》。

也许在大多数的人们听来,《相和歌·子衿》可能是哈辉所有作品中,最清雅,最悠扬的一首,然而《诗经》既然是国粹,是一种中华文化精神的象征,这也就使我们不能完全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这首歌曲,而更应该从学术的角度来勘探它的漏洞。
比如说它的题目在《诗经》的原题前面加了三个字“相和歌”。什么是“相和歌”呢?“相和歌”之名,最早来源于《晋书》:“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也就是说相和歌应该是滥觞于汉代的一种歌曲,“相和”二字取“丝竹相和”之意。根据现代的研究,相和歌在秦代或者更早就有所出现,但时间大约在战国时期,绝不会更早,达到春秋。而且就我们知道的来看,孔子之前,《诗三百》就已经成为了定篇——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所以《诗经》的出现至少不晚于春秋。绝对不至于到战国,甚至秦汉。这是哈辉《相和歌·子衿》中的第一个错误,时代的舛误。
第二个错误,在于她未能完全把握《诗经》本身的意旨,这一点从哈辉在两个字的发音就可以看出来——“挑达”。哈辉把这两个字唱成了“tiǎodá”,其实这两个字正音应该是“tiǎo tá”。挑达,亦作“挑闼”或“挑挞”。毛传上云:“挑达,往来相见貌。”朱熹《集传》上解释:“挑,轻儇跳跃之貌。达,放恣也。”而且《太平御览》卷四八九在引用的时候,就写作“挑兮挞兮”。这是字音的问题。更致命的地方在于,在哈辉女士的MV中,演唱的地点竟然是北京的辟雍。辟雍是什么地方呢?简单点说就是清代的国子监。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说,如果真是在清代,在国子监去演奏这样一首朱熹所谓的“淫奔之诗”肯定是不合适的。何况《诗经·大雅·灵台》上有言:“于论鼓钟,于乐辟雍”,就是说在辟雍之地应该演奏是钟鼓之乐,亦即雅乐,演奏国风是不合适的。何况又是郑风!
所以也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哈辉所谓的“新雅乐”。其实就她演唱的几首来说,我倒是觉得与其叫作“新雅乐”,不如叫做“新风乐”,或者“新国风”或者是更为合适的。所谓风者,就是 牲畜之间的雌雄引诱,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就是这个道理。再引申一点说,可以理解成广义的爱情。但是后来,风字慢慢有了另外一种含义,就是一种风气,一种风尚。所以,“国风”可以理解成各地的民歌,也可以理解成各个诸侯国的爱情诗。但不管是那种理解,这个风字是通俗的意思,有别于雅致和高雅。所以宋朝人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见《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可见,风者,俗也。说道这里我就想到,中国人有两个词语很有意思,一个是风雅,一个是风俗。风雅相异,风俗相同,但不管俗雅,它们都能够共同依存,共同构建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所以我也希望,如果哈辉女士经常演唱国风的话,那么也不妨把新雅乐就改作新国风,也是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在。
其实早在哈辉之前,已经有人这样做过了,这个人就是王洛宾。王洛宾先生的《康定情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阿拉木汗》、《亚克西》、《达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唱遍大江南北。而今,昔人已矣,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时代,能产生更多的王洛宾这样的人物。况且,受众批判的本身也正在于希望的价值。我们希望于哈辉,希望于民歌,希望于伟大的中华文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