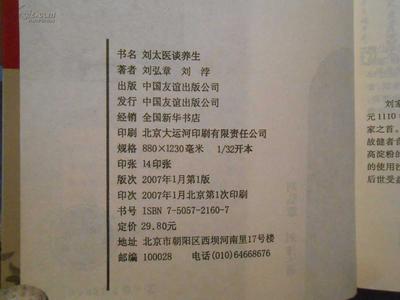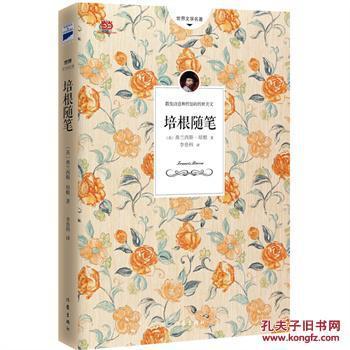承蒙鸿明兄关照,叫我写点东西,还特地寄来几张样报。我近来愁于文思枯涩,看到其中有篇谈到“文章”,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另外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正好前些时写过一篇关于约翰·玛西《文学的故事》中译本的小文,在一份报纸上登出来后,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这本书就其总体而言仍然能够逾越上述障碍,让我们体会到它的精彩缤纷,如同在林间感受日影斑驳。”不免有些纳罕,这好像不是我的文章。找出原稿,写的是:“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好处仍然能够逾越上述障碍,让我们体会到。而这‘一部分’已经不少了。”再看题目,原来是“精彩的‘个人之见’”,现在改作“林间有日影斑驳”。题目也是文章,也不是我的了。我说这些并无更正之意,区区一篇小文章,改动与否,均无价值之可言;只是要谈文章,这倒可以做个例子。也不是说我的文章就有多好,别人改动不得;我是觉得文章这件事情很不容易把握,敢情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譬如这里,大约是认为我写的乏味才给添上点儿“味儿”的,但是说实话我写文章,极力避免的恰恰就是这种“味儿”,一向担心的只是避免不了。然而别人想要这么写法,我想可能也有其道理罢。我们其实说不出什么是文章,什么不是;文章并无一定之规,除了错字病句,人家怎么写都可以;只是自己不是怎么写都可以。所以不能拿这个话题来限定别人,只能限定自己。我知道想写的是什么;退一步讲,知道不想写的是什么。大概文章之道,也就在这里了。
关于文章,我阅读多年,略有心得;后来学习写作,也不无想法。可都是只供自己使用的,与他人无关;我想写的文章,爱读的文章,大致不出乎这个路数。从前总结为四句话,即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这涉及到对以往散文史的看法,也关乎对一种风格的追求。近来我又觉得可以一概归结于作者的态度。有个意思,其实老老实实写在纸上就行了;如果能够达到清楚明白,何必非要形容一番。我们平常说话,有谁动不动就满口形容词、比喻句或者排比句呢,人家听着该有多么别扭。我觉得这是诗与散文的一点区别,诗不能如话,而散文可以如话。诗应该虚一点儿,散文却不妨坐实。从前我是写过诗的,虽然出息不大,形容几句总还是会的;现在写散文,我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对于不形容,可以不喜欢,但是用不着不放心。这里恐怕还涉及“美”的问题。其实美不止一种,而对于散文来说,形容未必是美。至少不形容也可以是美的,不过更难罢了。因为质朴简单,不是一味减少,是少而多,通过限制表现以实现最充分的表现。可派用场的字句少了,也就更要用的精心。文章不仅仅是指字面;所要表现的意思,作为表现手段的字面,以及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并叫作文章。当然如果有谁只喜欢看字面,那该说没有缘分,只好悉听尊便了。
从另一方面讲,形容也有高下之分。美不仅仅是漂亮,而漂亮应该是真漂亮。方才说不形容更难,其实形容也未必容易。通常所谓“滥调”,都是针对形容而言,不形容至少可以藏拙。难得有点新鲜感受,把这感受用自己的话说出来更见功夫。中国白话文章,做到今天差不多也是烂熟了,简直一下笔就落了俗套。而一落俗套,一成滥调,也就谈不上什么文章。我喜欢的两位散文家,周作人与废名,写文章都很少形容,其实他们对此并不加以排斥。比如《论语小记》中这一节: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不晓得为什么缘故,我在小时候读《论语》读到这一章,很感到一种悲凉之气,仿佛是大观园末期,贾母死后,一班女人都风流云散了的样子。”
这里有形容,有比喻,但是至少在我看来,要算很好的文章。感受是真切的,表现是自然的,一切都恰到好处。如果能够形容到这个份儿上,我又何尝不想一试,现在是没有这个本事。《诗》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不妨望文生义地把这里两个“止”字看作有所不为:不能形容就不形容,总比滥形容好一点儿罢。
(旧作,收《沽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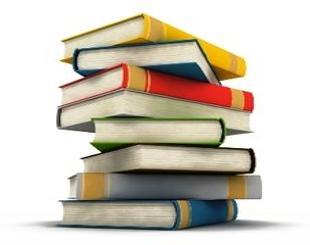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